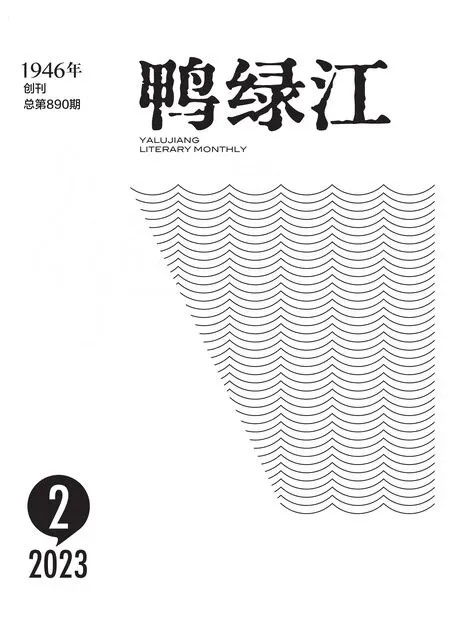驱鼠师(短篇)
2023-04-15于德北
于德北
在天幕的尽头,他看见灰色云层的四周被镶上了金边,尽管应该听到骇人的声响,但事实上,他处身之所死寂无比。如果不是他固执而空虚地要求自己保留一点颜色,那么,所谓的“天幕的尽头”也是不存在的。像一部浩大的五幕二十一场古典喜剧即将结束,更像一场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三十分钟现代独幕悲剧的开端,他演完了,或许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演完。一切必将变得无关紧要。到了此时此刻,他一生所历在别人的眼睛里,都只是绽放过魅力和欢愉的真实的幻影而已。
一个夜间遗尿症患者。
一个脑炎幸存者。
离开松城几十年之后,驱鼠师唐力兵终于明白了,无论你顺遂还是不幸,只要你遭遇孤独,它必将追随你一生。
事情还得从他十二岁生日那天说起。
不可否认,所有的命运都存在于微光之中。
十二岁那年秋天,只能独自奔跑的松城少年唐力兵跌进了一口菜窖,菜窖刚刚挖成,顶盖尚未完全铺好,泥土的芬芳使他有了瞬间地清醒,正是这瞬间的清醒让他有了呼喊的力量,他挺直脖子,睁大眼睛,冲着缝隙中的天空高喊了一声“妈”。这一声呼喊救了他的命,在附近挖地窖的另一个邻居找到了他,并快速地通知了他的父母,父亲的单位动用了唯一一辆卡车把他送去医院,经医生诊断,他得了一种在当时几乎为绝症的病——脑炎。
他连续三天高烧不退,最后是一位老中医哀悯她母亲的虔诚,送来一粒牛黄安宫丸,使他从九死一生的险境里化险为夷。老中医说,母亲跪在诊室门口不停地磕头,祈求上苍舍己身而续儿子唐力兵的命。医者父母心,世上的感念是彼此相通的。
唐力兵的病好了,并不代表幸福就此来临。
上文所讲“只能独自奔跑”,实属事出有因。
在得脑炎之前,唐力兵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到了十二岁还尿炕,这本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秘密,但是因为一次支农劳动,这个秘密被公开,只一夜之间,他获得了一个外号——尿炕精。太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孩子,到了少年时期居然还尿炕,这种异样的“画地图”的方式,同龄人难以接受,所以,唐力兵被自然而然地孤立起来。
常常遇到这样一种场景,一帮孩子突然从他身边闪开,又麻雀一样聚在一起,用充满无端敌意和嘲笑的童声高喊:“尿炕精,尿炕精。尿炕精,尿炕精。”
他们都说,他身上永远带着一股无可抵挡的臊气。
现在好了,尿炕精唐力兵的身上又多加了一个符号——大脑炎,他成了痴傻的代名词,就如同他独自奔跑的时候,那些孩子可以无比兴奋地指点说:“看吧,尿炕精的大脑炎又犯了。”
十二岁的唐力兵十分孤独。
但是,他尚没有能力完全地认知孤独。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在废公园奔跑的时候,有一只白地黄花的猫追随着他,他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他停下脚步,它也停下脚步。起初,唐力兵并未注意到猫的存在,等他跑累了,仰面平躺在荒草地上的时候,那只猫趴到了他的身边,“喵喵”地轻叫了两声。唐力兵侧过脸,险些吓了一跳,他从未见过这么丑的猫,臃肿的身体,杂乱的皮毛,最主要的是,它的一只眼睛是鼓出眼眶的,大如鸽子蛋,灰白灰白,外表如同蒙上了一层带细纹的乌玻璃。
唐力兵并不知道这是一只患了白内障的猫。
“你好。”唐力兵心生温暖。
“喵喵。”这是猫的回应。
“没有猫和你一起玩吧?”他问猫。
猫向他的身边靠了靠。
“我们做朋友吧。”
猫看着他。
唐力兵说:“也没有人和我玩。”
猫翻了一下身,抬起四只爪子,露出白白的肚皮。
就这样,少年唐力兵有了一个朋友,自从有了这个朋友之后,他变得从容又自信,他不再奔跑,或者说不再追逐和逃避,他一步一步地丈量着他所能应对和把控的时光,而那只患有白内障的猫,毫无疑问地在他的每一步丈量中加上了自己足以信赖的尺寸。
十三岁那年夏天,松城突降一场罕见的雷雨,水泼如注,接地连天,唐力兵惦念那只猫的安危,便撑起家中唯一的一把旧油伞,向废公园急速走去。他的怀里揣着早晨从自己嘴里省下的半个馒头,内心涌动着无可名状的悲切。他去了,他见了,那只猫蹲在一棵老榆树下,似乎正焦急地等待着他。少年唐力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走到猫的身边,把馒头放到一片牛蒡的叶子上,安静地看着猫慢慢地进食。雨太大了,风如此强烈,他只能蹲下身子,全心全意地遮蔽着猫,他不想让那半个馒头被雨水无情地浸泡成齑粉。
唐力兵是一个曾经给猫打过伞的少年。
最后的午餐过后,那只猫死了,它疾病缠身,或许也太老了,它留给唐力兵一份温馨的记忆,也不可争辩地把它的朋友重新归还给孤独。
是不是这样呢?
死去的大脑也是用来思考问题的吧?
谁又能知道新的欢乐不会在夜幕中孕育,并在旭日初升时来临。
唐力兵太思念那只猫了,有一天,他从老师的粉笔盒里偷出两支粉笔——一白一黄,在众目睽睽之下,抵达学校刚刚粉刷好的灰色院墙,他抬起手臂,笔走龙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一只患有白内障的大猫赫然出现在墙壁上,猫大如虎,其势生威,摇头摆尾,啸声震天。
然而,这些都是他虚幻的想象罢了。
在他的内心里,太希望自己可以复制那只猫栩栩如生的形象,可事实上,他失败了,他画的这只猫,除了眼睛外突,毛色黄白相间,其余的一切皆乏善可陈。那完全是一只四不像——耳朵像兔子,爪子像鸭蹼,体胖如猪,尾短似绵羊。唐力兵的怪异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目瞪口呆,继而哄堂大笑,最后愤怒之极。歪脖子的体育老师大步上前,伸出生满老茧的大手,在唐力兵的后脑勺重力一拍,一脚把他踢上了水泥砌成的领操台;麻脸校长把办公室的窗台捶得山响,一块玻璃经不起震动而出现了长长的裂纹;那个叫刘艳梅的大队长带头喊起了口号,在一片“打倒”声中,少年唐力兵惶恐地陷入了时间的黑洞,罪恶的渊薮虚席以待,苍茫的幻象如夜梦随行。
学校罚他清洗墙面,什么时候那个“怪兽”从众人眼前消失,什么时候他才可以重返课堂;当大脑炎发作状态下的唐力兵成为不折不扣的清洗工的时候,学校里至少有几百双眼睛在监督他,他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唐力兵刚刚已经清洗干净的墙面,转眼之间,消失的图景又焕然一新?那只猫的形象一寸寸长大,一片片更新——先是脑袋,之后是身子,接着是爪子,然后是尾巴。唐力兵无法让自己停止,他像一架古老座钟的钟摆,恪尽职守,昼夜嘀嗒,动作机械,不能自已。那只猫越来越逼真!一桶桶清水注入了它的血管,海绵和抹布的交替摩擦强健了它的骨骼和肌肉,患了白内障的眼睛隆起如珍珠,入夜变得莹绿,到了白天,就情不自禁地熠熠闪光。
终于有一天,那只猫拒绝消失了,它扭腰抬头,睚眦必报,裂目张须,魑魅魍魉,收腹提臀,杯弓蛇影,挥爪摆尾,风声鹤唳。歪脖子的体育老师汗毛倒竖,吼叫不止,下意识地摆出了短跑的姿势;麻脸校长推窗平望,慨叹连连,单指伸向半空,强直难收;还有那个叫刘艳梅的平日里最能挑唆男生鼓噪唐力兵的大队长,两条辫子都燃烧起来,她近乎绝望的尖叫掀开了学校走廊的地板,无意间为更为另类的死亡开辟了一条无障碍通道。
还有……
还有……
还有……
可是,这些又能说明或证明什么呢?一个令他们无法想象的事实出现了,原本隐藏在学校各个角落里的平日里让全校师生懊恼不已的老鼠全部出动了,大的,小的,黑的,灰的,黄的,褐的,一窝的,两窝的,同盟的,敌对的,三心二意的,不三不四的,皆执着地奔向有猫的那面墙,凭借着各自掌握的技能集体自杀了。看看这些老鼠临死之前的状态吧!它们蹑足噤声,低眉顺目,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誓言,没有遗嘱,死神的幕布一旦拉开,无声的挽歌摒弃了所有的半音和休止符。没有一只老鼠敢抬眼看猫,但它们都悉心感知着猫的存在,那只猫无视老鼠的魈魃魋蜮,有鬼无心,只用固有的巨大光明掩埋一切空洞无常的黑暗。
转瞬之间,唐力兵十三岁了!
十三岁,唐力兵应该上初中了,但他无能为力地退学了。他像一个自闭症患者,除了画猫,他不再与任何人交流。日夜厮磨,那只猫已经长在他的手上了,只要他想画,从头到尾,从尾到头,任意起笔,刷点即成。他和猫长相厮守,不再分离,自闭症患者唐力兵关闭了门窗,封锁了心路,曾经的羞辱培植了一种独特的优越感,话语的缺失成为他迷恋其中沉浸其中的生活常态。
那时还没有心理治疗师之类的行业,他的母亲除了独自流泪,找不到任何一家门庭再为唐力兵续命了。
“要去画猫了。”唐力兵在心里宣布。
“去哪里画呢?”另一个唐力兵问他。
“一切能画的地方。”
“对!一切能画的地方。”另一个唐力兵支持他。
一根白色的粉笔和一根黄色的粉笔成了唐力兵心里的拐杖,依靠这副拐杖,唐力兵离开了故乡松城。
在一个金色的黄昏,他行至一个农场,发现所有人都拿着镰刀站在地头发愁。这是为什么呢?地里的庄稼已经被老鼠提前收割完了,放眼望去,光秃秃的秸秆如同老鼠布下的寓言,应该由人类因辛勤劳作而获得的收成均被隐埋入地下,变成老鼠们过冬的烹享。于是,唐力兵拿出粉笔,在农场唯一的一块石头上画了那只猫。情形可想而知,正在地穴里窃笑的老鼠们纷纷出洞,被施了魔法一般,尽数死在巨石周围。与众不同的是,老鼠们不但自杀了,还自动交还了粮食,如此结局自然带给了农场人感激的泪水和此起彼伏的欢呼。
在一个银色的早晨,唐力兵来到一个木具工厂,他走到厂门口的时候,看到工人们聚集在厂区广场的花池边叹息: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批国外订单,却一夜之间被老鼠们重新“雕刻”了,那些图纸上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的花纹毁掉了这单生意,而这单命系全场职工的生意的失败,无疑会把木具工厂推进死亡的深渊。于是,唐力兵踢了一下脚底黄褐色的泥土,在木具厂最后的原木堆上画了一只猫。这一次,他把猫的侧脸画得特别大,那只灰白的白内障病眼睁得特别圆,那只眼睛里有炯炯精光,如同闪电,把木具厂里里外外都照得更加明亮。那正是晨曦微起的时刻,而这只猫眼像提前升起的太阳,掠过早晨,遮蔽正午,大地再无阴影,妖魔尽现本形。看吧,那些瑟瑟发抖的老鼠,前爪捧着自己的牙齿,先是恭恭敬敬地修补好被它们戏耍过的成器,之后,面含羞愧地咬舌自尽。
就这样,唐力兵成了一名驱鼠师。
就这样,尾随其后的官员、老板、明星、小丑、记者、艺术家,等等。不计其数。
多么奇怪的驱鼠师啊。
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话。
首先,是一位官员找到了他。该官员大腹便便,手足多肉,脸上戴着一副面具,笑容和蔼可亲。他以“加大城市卫生运动力度”为名,把唐力兵约到了自己的郊区别墅。这幢别墅高有四层,雕梁画栋,前有停车场,后有游泳池,占地六万平方米,与五A级国家森林公园隔河相望。官员找到唐力兵的时候,天色已晚,他在城乡接合部偏僻的荒野向唐力兵坦露心声。
“大师啊,我每天都过着谦虚又谨慎的生活,每当人们夸赞我的时候,我的内心……”他环顾左右,确信无人,“我的内心……”他的面具上渗出了汗水,“我的内心……我知道我的内心里藏着一个恶魔,可奇怪的是,我的恐惧战胜不了我对他的屈服和喜爱。他满足了我从未有过的欢喜感、满足感,那种心跳到几乎疯狂的感受,那种顺畅、温暖,那种沸腾,不能自拔,不想自拔,那种想哭的情愫……”
这是一位喜欢收藏的官员。
在他的游泳池下面,是一座宝藏,在这座宝藏里,所有的物体都是金子铸成的。墙壁、大门、虚拟的窗户,地板、摆放物品的架子、天棚,桌子、椅子、水杯,花盆、雕像、衣架,坐便、洗手盆、浴缸,刀、剪子、烟斗……目中所视,金光闪闪,无须灯火,昼夜通明。这里是官员的私人空间,他常在此独自休息,无论宦场沉浮、离合悲欢,无论人生抉择、精神扬抑,无论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只要人处密室,百无一忧。可是,这样的日子被一群老鼠给毁了。不知从哪日起,本地的老鼠发现了宝藏,它们由排气孔、排水孔溯源而上,倒行逆施,先是以金磨牙,满足好奇,后来发现金粉可做妆饰,雄鼠艳雌鼠面姣而涎,雌鼠惊雄鼠脸阔而喧,遂争相效仿,蔚然成风。老鼠有了进化,官员大受损失,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裂冠削履,剖肝沥胆,对外不能倾吐宣泄,对内暗气暗憋,惶惶难以主持会议,凄凄不思茶饭,寤寐不安,几成大病。
如是,才找到了唐力兵。
唐力兵站在官员的密室当中,犹如身处一片与世隔绝的沙漠,他透过面具看穿了官员那张满是锈蚀的脸,一股糜腐气息冲荡而来。他掏出粉笔,奔逃一般地画出了那只猫——眼所见,耳所听,鼻所嗅,口所吸,皆令人惊诧;之后,迅速离开此地。
唐力兵走了,官员并未因此获得解脱。唐力兵画的那只猫,源于金子的作用,身体呈黄色的部分不甚明显,甚至被金子取代,远瞧少毛,近观缺肉,白内障的那只眼睛如官员戴面罩一般戴上了“金眼罩”,目光被假象遮蔽,顿失威慑之力。老鼠们感知了猫的存在,无奈赴死,谁知赶来一看,不禁由惊转笑,继而大骂,上蹿下跳,疯狂报复。它们一夜之间破其门,毁其案,分割盗运,逃之夭夭。官员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痰迷气管,失心而疯,亲拟诉状,将唐力兵和老鼠一起告上法庭,其结果可想而知,官员锒铛入狱,自绝于拜金梦想。
不久,又有一个老板找到他。
这是一个在南方享有盛誉的纺织厂老板,他身上所具备的企业家气质和外形无人能比,他谈吐不凡,所有关于纺织的历史和技术他都了如指掌,尽可夸夸其谈。他有自己的工厂、研究机构、大学和国际合作伙伴,任何一种涉及纺织的买卖,只要挂上他的名字,无不决胜千里,业绩突出。他身高一米九〇,偏瘦,一身衣服料子均出自手下最得力的技工之手。据说这种料子冬暖夏凉,透气吸汗,不打褶,不起球,免洗免烫,轻松自在。他有一双如蚕美目,眼睫如丝,肤色若桑,汗毛似棉,走路无声,御风可行。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一生只吃素菜,设宴时多以桑叶为盘,柞叶为碟,满桌青绿,食者如沐春风。
老板找到唐力兵,一张凝固着微笑的脸现出一丝愁容。
他带着唐力兵来到他的私人博物馆。
这座恢宏巨大的宫殿,保存着他所有藏品,远至秦汉,近到明清,历朝历代出土的与纺织有关的文物应有尽有,各种棉、麻、丝、绸、缎、绢不计其数。他的博物馆不对外开放,所以,唐力兵是屈指可数的被邀嘉宾之一。
老板是多么谦卑。
他说:“这些东西将来是要捐出去的,毁了是多么可惜。”
唐力兵看到那些藏品上有许多老鼠噬咬过的破洞。
老板说:“我是多么怀疑它们是怎么进来的,它们是怎么打开的保险罩,任意妄为之后又安全撤离。”
唐力兵的视线被那些金丝银线晃得异常缭乱。
他突然出现一种眩晕感,复视带来的恶心从胃底向贲门翻涌。他的大脑被无形的气浪卷起,沿着不同的方向运动,形成大大小小数以亿计的旋涡。他尝试着闭上双眼,可是那些光斑像铆钉一样固定着他的眼皮,让他进退维谷,左右两难。
老板说:“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投入了那么多的金钱,召集了那么多的研究人员,我要找到最廉价的原材料,织出无可挑剔的产品。这浩瀚的纺织史啊,伟大的黄道婆们,上天仙女也不可能没有瑕疵。”
他的声音如同在祈求,他哭了,双膝跪在地上,向唐力兵展示他的悲伤。
他继续说:“那些研究员,研究员啊,多么大胆的假设,他们可以向这些藏品求证,小心地求证。如果把历朝历代优秀制品里的瑕疵找出来,再把它们连缀在一起,那得降低多少成本啊!成本的减少,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多。”
他说不下去了,伏地泣不成声。
唐力兵终于呕吐起来,在剧烈的抖动中,他口袋里的粉笔跌落在地,瞬间和呕吐物混合在一起。他的呕吐物里似乎带出了血丝,那血丝布满了猫的双眼,他且退且吐,直至把腹中之物全部吐空。
老板抬起头,解开自己的上衣,指着自己长满溃疮的结痂说:“他们已经在我身上开始了实验。你看,我身上的衣服就是用瑕疵一片一片织成,你们能看出问题吗?不能!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料子,穿在谁的身上都是那么合体。”
唐力兵布片一样向博物馆的大门退去。他的呕吐虽多,却不显污秽,清汤清水,米粒如珠。他整个人变成了一只画笔,踉踉跄跄,歪歪扭扭,那只巨大的生有白内障的猫,一点点呈现在宫殿的大理石地板上。那只猫浑身透湿,歪头卷尾,白内障的眼睛突兀如球,虽不协调,但红光四射。
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那么多老鼠,它们翻箱倒柜,破布裂绢,所有的制品都被它们扯成绳子,在一只黑色硕鼠的带领下,直奔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悬松挂桦,竖桩桩,直挺挺,纷纷上吊自杀。
猫头鹰的怪叫充斥寰宇,驱鼠师唐立兵的背影小了一圈。
啊!不久!永恒的不久!!
不久,又有一位女艺人急切地派人来拜会他,她让年轻的助理带去了谦卑的微笑和慷慨激昂的文字,并把她自己的写真照制成精美画册赠送给他。在女艺人写给唐力兵的信里,她诚挚地吐露了自己对他的仰慕之情,并言明她已说服她的制片人,把唐力兵的经历改编成电影,一定要请好莱坞的导演拍摄并全球发行。她主演那只猫,并强调,猫可以化身为唐力兵的情人。一个驱鼠师和一只猫的合作充满了寓意,这伟大的设想足以颠覆所有庸俗之辈的世界观,并为所谓的失衡之爱奉献由衷的赞美。她请求唐力兵为她画一只猫,也就是画另一个自己,她将像圣女贞德一样,为郎朗乾坤昭昭日月而战,驱尽世间所有的污秽和丑陋,为正义和善良树立不可取代的楷模。在信的结尾,她附录了她所设计的两段台词——一段是:“《驱赢师》,呃,怎么,这是一个象征的名字,戏中的故事影射着文艺界的一件谋杀案,导演是被害人,他们无需什么名字,杀他的人是他的妻子,您看下去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别人说?说什么?呃,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它不会对您——伟大的制片人跟我——这个灵魂清白的人有什么相干,让那有毛病的水军和段子手们惊逃退缩吧,我们的胸部都是好好的,好好的!包括其他部位!”还有一段:“(呼唤,转向响声)驱鼠师,这边儿来!(向着幕外)让我们去换好衣服,我不瞎!全是瞎扯,胡说八道!(快快活活笑)你哭做什么?可怜的尿炕精!大脑炎!你,到底怎么了?这不像话!好了,好了,这简直不像话!来,来,自闭症!别死瞪眼睛!什么让你这样瞪眼睛?好了,好了,(流着眼泪,拥抱驱鼠师)别哭了!有艺术跟天才的地方,就绝不会有什么孤独、寂寞这类事的……就是死本身也是一样,(哭)不,不,驱鼠师!现在我们全算完了!我算哪一类天才呀?我倒像一只挤干的柠檬,一只裂口的瓶子,你是这戏园子的老耗子……”
信里用了太多的惊叹号!
女艺人解释说:“以您伟大的鉴赏力,您一眼就应该看出,这些台词是从莎翁和契老夫子那里化来的,可是,这又有什么?艺术本身就是相通的,几百年几千年也不会变!”
唐力兵平静地坐在那里。
“您一定也可以驱赶梦里的老鼠吧?”女艺人问。
唐力兵无法回答她。
唐力兵在她写真集的扉页上画了那只猫,并请年轻的助理把所有的礼物带回去。助理虽然为难,但只能遵命。谁也不会料到,就在女艺人接到退回的相册并随手打开它时,在她并不漫长,甚至可以说十分短暂的艺术生涯里,许多曾和她合作过的制片人、导演、副导演等等——都选择自杀作为自己的人生归途!
……
驱鼠师唐力兵在又一个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来到了一座海滨城市,这个城市号称猫城,家家以养猫为傲,但是,在一个猫比人还多的城市,却无法阻止老鼠肆意破坏古老建筑。如果这些建筑消失了,这座城市也就失去了立足于地球的全部意义。唐力兵恰恰走到了这里,他希望可以遇见一只患有白内障的猫,他甚至遍访了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所宠物医院,但是,他所获回赠皆是失望。
他做出一个决定。
这一天深夜,喧闹的城市阒静无声,他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画着一条又粗又大的猫尾,然后向海边延展猫身,他且行且画,且画且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只猫身长二十七公里,高跨十六条大街,猫头设在闻名遐迩的望海礁上,而眼睛所视,正是常人根本无法看见的地平线那端的远方。这样的巨画是猫城人无法窥之全貌的,那些黄白的颜色被他们误认为是调皮的孩子的随意涂鸦。但是,晨起往海边晨练的人目睹了这世间奇景,难以计数的老鼠欢快地扶老携幼地向海边奔去,从望海礁的一侧葬身海底。
晨光照在海面上,海水出现道道粼波,陆地和海岸失去阻隔,远处港口的轮船上的海鸟也停止了寻觅。只有一群孩子还在奔跑、呼喊,他们无视脚下老鼠的存在,他们的笑声清脆,极大地震荡了空气。他们无视老鼠正驱赶着蟑螂和臭虫,而它们的头顶,苍蝇追咬着蚊子和瞎虻。这一道黑幕铺满了大地,虽有震荡却不带起一缕灰尘。望海礁的四周布满光点,刺穿着唐力兵心中永恒的漂泊,唐力兵的身影里没有杂质,他的目光对接着海天相连处灰蓝的云朵。这世间还有多少老鼠需要他驱赶?他的一生又何处才是终点?对他来说,他似乎永远也没有进入到某一领域的腹地,那些象征着航程的照明灯从来没有通电闪烁。他的头发白了,根根垂地;他的身体已经透明,无须精心遮蔽;他的骨头空了,正吹奏着古典风格的协奏曲;他的神经被注入了色彩,正应和着冉冉的朝霞向上喷薄。
“啊!啊!”唐力兵挣扎着发声。
有谁还会注意唐力兵?
他站在那里,恍然印证着一个事实,在他若干甲子的人生里,什么夜间遗尿症,什么脑炎,什么自闭症,这些都不是症结啊,真正的症结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属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