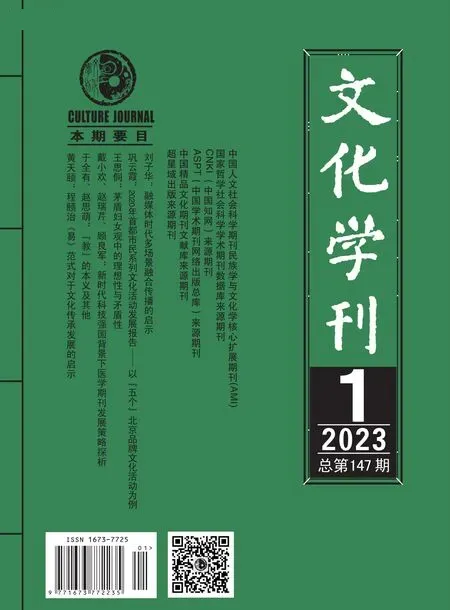新《著作权法》下广播组织权客体分析
2023-04-15武熙
武 熙
一、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历史沿革
随着三网一体化的发展,传递介质也由最初简单的纸质、胶片逐步发展到了电波,传递的声音形式也从原来静态的影像文字再到了今天富有动态的数字声音,并慢慢地融合到了今天优秀的音乐节目中,其传播方式也从最初单向、线性的文字传播逐步发展到了互动传播,而我们可以在自己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获得音乐,又能够在相应的网络平台上面共享视听内容,而传播主动权也开始由媒介传递至使用者的身上了。[1]《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是广播电视、广播电台最常见的传播对象,所以对于传播“作品”而作出贡献的主体也是《著作权法》提供的司法保障的重要内涵,而因为法律保护这种主体也就形成了邻接权。
《保护表演者、录制者及广播组织罗马公约》1961年签订于罗马,简称《罗马公约》,其是邻接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在该《条约》中所规定的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为“节目”,但是单个广播节目(例如某一电视剧等)又同时可能成为著作权的客体,其规则是具有一定的漏洞的,但是协定从理论和制度上依然都给我们的立法带来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在1992年以前中国并没有加入《罗马公约》,但是我国在1990年,借鉴公约将广播组织权独立于著作权保护的相关规定,也参照《罗马公约》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定义为了“节目”的说法。[2]而在2001年的修订中,是以《TRIPS协定》为蓝本,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表述为“播放的广播、有线电视”。这样的改变,将原来的“节目”说法改变为“播放节目”。但不久之后,在2002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依然是“电台、频道对其放送的广播、电视剧”。在2010年《著作权法》的修改中,也没有对广播组织权进行修改,还是使用了“广播、电视”的说法。
在2014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送审稿中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在41条中定义为“节目”,但是在第42条又将其定义为“信号”,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在2020年,我国《著作权法》又迎来了一次大的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第一次送审稿中,广播组织权客体被定义为 “其包含的节目信号”,同时还增加了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然而,在《著作权法》第二次审议稿和最终修订稿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被改为 “其播出的广播或电视”。之后有关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法规也几经调整,还是将其改到“节目”的说法上,但是关于此问题的争议,还远未结束,依旧是大家如火如荼争议的焦点。
二、广播组织权客体争议
(一)“节目说”
关于“节目说”,主要是指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认定为节目。[3]“节目说”的观点起源于英国,大部分支持“节目说”观点的学者都有受到英美法系对广播组织保护的影响,该观点主张授予广播组织著作权保护,更有利于其发展。支持“节目说”观点的原因主要有:首先,直接采用著作权保护的模式保护广播组织,有利于节省立法资源,另外相较于“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节目”更利于理解和被大众所接受;其次,节目说的学者认为“信号”只是传播广播节目的一种传播载体,而对于通过信号传播的内容的编排,加工等等,才是广播组织对其的真正的贡献;最后,“节目说”的支持者认为“信号说”弱化了广播组织对于节目的投资及利益,与广播组织的实际需求不一,会助长他人对信号所载内容的擅自利用的行为。“节目说”把节目视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对于这些广播组织而言拥有了更为普遍的权力,例如《著作权法》为广播组织新增加的信息网络转播权,以及一些专有权利、复制权等。
(二)“信号说”
关于“信号说”,主要是指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为信号。“信号说”最开始由美国的学者提出,是为了应对“信号盗播”的情形,随后由印度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支持“信号说”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广播组织权作为一种邻接权进行保护,广播组织所产生的需要被保护的新的劳动,是广播组织在传播广播作品时产生的信号,所以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对象应当是信号;其次,因为广播组织传播作品时产生了相应的信号,那么当信号被盗窃时,广播组织所投放的信息内容受众对象就会被分散,那其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就收不到回报,利益受损,所以信号才是广播组织权维护的对象;再次,在SCCR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时,“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就是大家认同的。只是在后来进行广播组织权的构建时,才产生了分歧;最后,在以前狭义的“信号说”中信号是不可固定的,广播组织能控制的只有载有节目的信号,只能控制对应的转播行为;后来又有学者在“信号说”的基础上延伸出“修正的信号说”。在“修正的信号说”中认为信号是可以被固定的,可以“被固定为录制物上的数字文件”,所以,广播组织权除了可以控制对信号的即时利用,也可以控制后续使用。
三、广播组织权客体分析
(一)“节目说”存在的弊端
首先,广播组织之所以能受邻接权的保护,是其在传播过程中增加的新元素而受到邻接权的保护。[4]广播组织制作节目主要有两种:一种属于创作作品,比如拍摄电影的方式拍摄电视剧等,这类创作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另外的一种是录音录像,例如制成录音带等,然后供给电台频道播放,从而获得保护。[5]从此可以看出广播组织获得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肯定不能是“节目”本身,其受保护的原因,应当是“播放”节目时技术上产生的新元素,这才是其受到邻接权保护的原因。“节目说”强调节目作为这个新元素,但是节目并不会因为转播而增添新内容。所以,广播组织也是如此,并不会因为其播放了节目,就产生新的元素,也不会仅仅根据其播放的行为就赋予了广播组织权。“节目说”的观点混淆了著作权与广播组织权的界限,权利归属和授权机制错位,造成法律逻辑的混乱。
其次,以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以“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导致大家错误地认为这是公认的选择。但英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着其特殊的渊源。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存在邻接权,所以为了保护广播组织,其只能对这种具有非物质性特征的节目进行保护。在《英国版权法》中所规定的作品种类,大致包括:文学、剧本、歌曲等作品,录音、影视和广播艺术的作品、以及出版物的版式设计。在这里只有“文字、剧本、歌曲和作品”要求的有原创性和得到版权保护,而对于广播也不能要求原创性,而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必须要具有独创性才能获得著作权保护,所以我国和英国之间的法律体系相差很大,根本无法以此来论证“节目说”的观点。在英国对于录音录像制作和电影也有一定的具体规定,也无法将广播组织纳入其中,只得单列为一种作品。同时,因为英国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英国版权法中的一些理念、概念、处理方式等都和反垄断法相似,所以在实践中,英国版权法也会产生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因此,我国并不能参考英国的立法,其与我国的立法方式差异较大,在此的可参考性很低。
最后,我国《著作权法》一直采取的是高独创性标准,沿袭着德国等大陆法系的传统。就目前我国存在着邻接权和著作权的二分体系,如果节目是由广播组织自行制作的,那么广播组织也就能够成为作者,从而得到了版权保障,再退一步讲,至少也能够得到声音录像制作者的保障;不过,广播机构如果播出的是别人的节目,那么,节目的内容中没有广播组织所做出的新贡献。另外,我国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当面对实践中的特殊情形,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而不需像英国一样运用广播组织权进行保护。
(二)“信号说”采用的合理缘由
首先,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电视等等,从技术上来讲,都是经由音响和显示屏将接收到的声音信号或者光信号,用专业设备把光信号或者声音信息再转换为电信号的步骤。而倘若以此主张广播信息可以以数字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则是不恰当地把信息和节目,把法学上的定义和技术意义上的定义混淆。[6]另外,若根据此理论的逻辑加以推导,则录音成品制作者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也就是把光信息和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讯号的整个过程,经过许可再次进行录制,还是将该信息换了一种方式保存下来。广播组织者在广播节目时,除了负责交换信息外,还包括编排节目的次序,并选定或合并新节目等。而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广播组织进行编排转化之后将作品的内容传播出去,这时承载作品产生的信号才是广播组织在其中所贡献的新内容。广播信号才可以代表广播组织在传递广播作品过程中的劳动,而“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则构成了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并给予了广播组织相应的转播权,是对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的保障。
其次,“信号说”也比较契合广播组织权设立的最初立意。就主张对录音产品和广播电台进行保护的国家而言,提出主张的大多是相关企业,这意味着对作者的保护除了财产权利之外还包含着文化利益不同,对机构、录音产品企业的保护大多是依靠其为生产广播电台或录制产品而作出的利益投入。所以,广播组织权立法的本意正是希望保证广播电台机构为获得和播出节目而花费的资金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其所有的资金投入目的并非创作出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传播特定的节目,而无论该节目是否为其所制作。[7]广播组织是对电视节目内容进行选择、播放和承担相应监测工作的主体,因此,一旦其播出了触犯有关法律法规的节目内容,就必须视为播出者以企业的身份接受有关的法律惩罚,而不是视为传播违法内容的原创作者直接接受惩罚。从这种角度上分析,对广播组织权贡献最大和负有责任的方面,也就主要在于广播活动而不在于节目内容本身。当然,广播组织对其所自行制造或表演、汇编的节目,自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版权。
最后,对于广播组织权作为邻接权,有观点指出,邻接权利客体必须具备“非物质性”,“信号”作为一个有实体的物质不可成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而对于邻接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却没有相关的论据支持。邻接权利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出于保障有关主体对创作传播等所做出的贡献,或者保护某些同样具备相当高智力创作水准而还未能达到作品原创性标准的权利客体。现存没有一个学说对邻接权利的客体应当具有无形性作过全面论述。[8]中国的知识产权和邻接权的保护起步较晚,我国的《著作权法》颁布后,一些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为了提升法制化程度等,国家在立法开始时就已对广播组织赋予了邻接权利。追踪对广播的有关权利的保护历程,不难看出广播组织权的形成也有其特点,广播组织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著作权。同样的,对客体“信号说”的理论,当然也无法消融知识产权的理论根基,导致邻接权制度的混乱。[9]
四、结语
广播组织权与客体问题仍争论不休。“节目说”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作品创作与广播之间的界限。广播组织客体“信号说”更符合中国邻接权及广播组织权的立法初衷,也可以使广播电台组织者的作用与播音、电视中含有的歌曲艺术家的功劳相区别。广播组织是一个独特的知识产权,“信号说”的理论并不会撼动邻接权制度的完整体系。“信号说”更具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