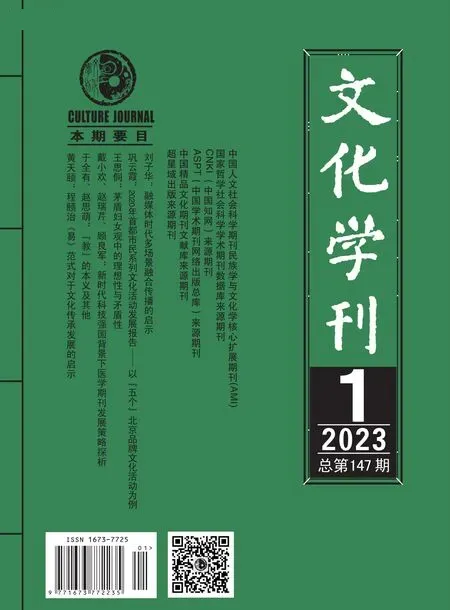被“击中”的普希金
——《诗人之死》后普希金形象的多重解读
2023-04-15李梦婷
李梦婷
一、引言
《诗人之死》(1)1837年1月27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决斗中遭杀害,莱蒙托夫在痛惜和激愤中写下《诗人之死》以作哀悼。本文引文采用顾蕴璞译文。是莱蒙托夫为普希金逝世而作的一首绝世名诗,在表达对诗人离世而惋惜及悲愤的同时,猛烈抨击了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沙皇专制制度。在莱蒙托夫等人看来,普希金之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沙皇政权的圈套,但也同时昭示着击败专制制度的曙光。普希金去世后,沙皇政府曾极力控制社会舆论,试图掩盖诗人逝世的真相,然而由诗人之死激起的强烈愤慨情绪使民众加大了对沙皇政府的抗争力度。沙皇政府迫于压力应允为普希金修建纪念碑,却迟迟未能提供资金款项和修建方案。沙皇政府前后反复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了不同立场的民众对普希金的纷纭意见。因此,在普希金逝世之后,关于诗人名誉和地位的争论几乎持续数十年不休不止。而如同莱蒙托夫在诗中预言的一样,后世“严厉的裁判者”以绝对的威严一反沙皇政府的论调,将普希金奉为革命的先驱、自由的歌者,将诗人的地位推往超越文学之上的高峰。
二、“荣誉的俘虏”
伟大诗人普希金死于1837年与法国保皇党徒丹特士的一场决斗之中,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将俄罗斯文学史的发展轴线划上一道不容忽视的刻度,同时也将俄国沙皇政府推向杀人凶手的嫌疑漩涡中央。莱蒙托夫在诗中直斥沙皇政府为策划这场决斗、将诗人逼入圈套的幕后黑手,也由此遭受了囚禁与流放。总体而言,普希金之死由多重因素导致,低级的职位与巨额的贷款、社会舆论压力、政治理想受阻等困难都是引发悲剧的诱因,而其中堪为致命一击的导火索则是以沙皇政府为首的上流社会对诗人的诽谤与侮辱。
事实上,沙皇政府早在诗人生前就开始对其进行各类隐性施压。普希金在沙皇政府下的低级职位与自己的才能并不匹配,而尼古拉一世贷款给普希金的4.5万卢布虽名义上用作于支持诗人的文学创作,表面上彰显了普希金与沙皇政府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却增加了政府对普希金的束缚力度。同时,丹特士对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的追求无疑传递了上流社会对普希金的挑衅,尼古拉一世又曾公开对娜塔丽娅献殷勤,种种迹象皆表明诗人的尊严已受到极大威胁。诗人和沙皇的关系最终被一封匿名信彻底破坏,蜕化成不可挽救的冲突。而在沙皇政府看来,普希金的影响力过于强大且有愈加不可控的势头。诗人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皆发表过大胆言论,并收获了一众虔诚的追随者,已经严重影响了沙皇政府的威信力,甚至极有可能威胁政府的统治地位。因此,普希金之死对于沙皇政府而言是潜在威胁的消失,也带来了修改舆论秩序的契机。沙皇政府曾在官方舆论中极力掩盖诗人逝世的真相,试图为直接凶手丹特士开脱,而为诗人发声、解密诗人之死的莱蒙托夫也因抨击专制统治遭遇流放。在1837年1月27日至29日艰难度过之后,普希金之死被作为公共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讨论,无外乎形成两种论调:一个美丽的宫廷贵妇的丈夫被一个名声可疑的外国人杀死,或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已经落山”,诗人的伟大道路被自己打断了。诗人的死亡被引作谈资,在社会舆论中遭到了流言蜚语的攻击,而死亡的真相仿佛并不是值得关心的事。此为普希金因“荣誉”而遭受的第一重痛苦。
此外,关于普希金本人的争议也随着诗人逝世愈演愈烈。1855年,尼古拉一世去世后,一些外交部官员就曾提议为诗人修建一座纪念碑以作怀缅,且在“五年之后,包括普希金同班同学在内的皇村学校几届毕业生再提此议。”[1]然而沙皇政府似乎有意忽视普希金逝世的影响力,避免助长社会民众对诗人高调的崇拜之情,对修建纪念碑一事仅勉强同意,并未做出任何实际性贡献。沙皇政府的模糊态度使“纪念普希金”一事未能及时得到官方定调。因此,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之时,来自各方各派的声音各不相同,各有论证。即便两个同样出于欣赏普希金而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对普希金的看法也会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更何况此时对诗人的负面评价依旧层出不穷。屠格涅夫在典礼上发表演说,大力歌颂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杰出贡献,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更无保留地将其奉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他强调,“确实,在欧洲文学中出现过无数艺术天才——莎士比亚们、塞万提斯们、席勒们。但是你能从这些伟大的天才中指出哪怕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那样具有全世界性的共鸣能力的作家来吗?”[2]两人对普希金的歌颂遭到了反对者的攻击,攻击的目标也不仅局限于两人的思想倾向,更明显集中于普希金本人的身上。诗人在其逝世的第一个大规模纪念活动中始终未能得到官方正名,却遭到了来自各种派别的锋利审视,此为普希金因“荣誉”而遭受的第二重痛苦。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后代几次周年纪念活动相比,此次纪念活动中在众人视角里所展现的普希金形象是最为全面的。在将对诗人的崇拜之情彻底格式化、制度化之前,各派人士对诗人的多元评价使诗人形象相对更为丰满,使普希金更贴近普通人民而非完美理想人格化身的“神话”,也使诗人为之献出生命的“荣誉”更为合理。
总体而言,从普希金逝世到1880年纪念碑落成之间,对普希金的争议伴随着众人不同的思想立场不断涌现。普希金的地位尚未得到官方认同,“普希金究竟代表了什么”则成为能够引起文学界、政治界甚至整个社会争论的话题。而各类论调并不影响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巨匠这一事实。1880年的庆典活动成功地将普希金的知名度大幅提升,使其在众说纷纭的背景下在俄罗斯境内得到“知名诗人”身份的广泛认可。
三、“恭维的合唱”
莱蒙托夫在诗中写道:“而今谁要这嚎哭、这空洞无用的恭维的合唱、这嘟嘟囔囔的无力的剖白!”在他看来,沙皇的阴谋已经造成了诗人逝世这一不可挽回的损失,来自宫中的任何“嚎哭”都是惺惺作态的虚伪表象。作为被普希金思想深度影响的后代诗人,莱蒙托夫反对的是整个沙皇统治的格局。因此,即便普希金本人曾歌颂如彼得一世般开明君主的政治面貌,沙皇政府也曾在普希金死后为其支付欠款,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普希金与沙皇政府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但从本质上来看,以独断专制为目的的沙皇统治与向往公正法制的“普希金一派”势必要站在对立面。
然而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是,1899年普希金百年诞辰之际,沙皇政府竟亲自出面,将“纪念普希金”彻底归纳成官方活动。这一转变并非仅代表历任沙皇对诗人的个人认可度不同,还从官方语境下将普希金重新定义,将其彻底收纳为“沙皇政府的朋友”。1899年的纪念活动里,每一位发言人都要“按照官方的规定,把普希金说成是沙皇专制制度忠实的捍卫者和尼古拉一世的忠臣”[1],一旦论及普希金的革命倾向,就会受到严厉惩罚。雅库什金只因谈论到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的联系就被当场驱逐。文学界极力反对政府将普希金形象片面化、简单化的说辞,大多数著名作家都拒绝出席1899年的纪念活动,以示自己对此次活动的批判态度。但沙皇政府仍借由纪念活动将普希金形象和普希金崇拜模式皆进行了官方规定,尽管未能收获各流派的普遍认同,却也因官方威信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附庸。
政府对普希金形象的重塑从根本上源于规范民族意识的需求。与1880年相比,普希金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已有显著提升,“普希金与沙皇政府的微妙关系”则如同埋藏在民间的定时炸弹,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基于普希金已经离世的事实,关于其曾发表过的言论和观点尚有重新解读的余地。对于沙皇政府而言,相比于彻底抹杀诗人存在的痕迹,借由诗人的影响力反将诗人塑造成政府一方的盟友显然更具效益。通过官方力量修改集体记忆,既能实现政府与反对意见共存的目标,同时又得以借机彰显政府的历史正确性,维护政府的统治地位。沙皇政府的挽救措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在1880年的纪念活动前,还有来自各方各派的声音讨论诗人到底能否代表俄罗斯的民间文学、是否仅仅以创作抒情诗来博取名声、是否背离了社会真理等,而在1899年间,大部分议论都围绕着“普希金究竟有没有支持沙皇”的中心问题。而实际上,普希金的确曾赞扬彼得一世的开明,钦佩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但其“尊皇思想”仅存在于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前提之下,并非盲目支持沙皇制度本身。
对诗人立场的解读激化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20世纪初期,普希金的地位问题引起极大的质疑,众人对普希金的评价天差地别。索尔仁尼琴讽刺道,“干巴巴的纯理性主义者和初出茅庐的虚无主义者要找个人来‘开刀’——那当然是从普希金开始。想要给市井写点庸俗的笑话——不写普希金又写谁呢?”[3]激化的社会矛盾使得普希金崇拜体系还未正式确立就遭到冲击。如果说19世纪对普希金的复杂评价还未动摇人们心中诗人的高尚地位,那么20世纪初期在社会斗争的背景下,就连普希金的文学地位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布尔柳克等作家甚至曾直言要将普希金“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去”[4]。因此,自从沙皇政府以官方话语权将普希金定义为沙皇一派后,“普希金究竟是革命的支持者还是叛徒”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反而使关于诗人地位的争论演变得更加激烈。
四、“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直至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之时,诗人与沙皇的矛盾和诗人逝世的真相才再度被搬到台前。苏联政府调动所有媒体、科研单位、学校等团体为普希金举行纪念活动,弘扬诗人深刻的人民性,侧面揭示了普希金与沙皇专制相反的政治观念。莱蒙托夫在《诗人之死》中愤慨预言,“还有一个神的法庭!有一位严峻的法官”会对杀人者进行审判,揭露沙皇政府的阴谋且归还诗人清白。从这一方面来看,苏联政府彻底推翻“普希金屈服于沙皇权力”的论点,的确如莱蒙托夫所愿澄清了诗人是政治斗争牺牲者的事实,也将诗人的崇高地位重新确立并巩固。但整体而言,苏联政府对普希金形象的宣扬同样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具有刻意为之的片面性。
1937年纪念期间,苏联政府调动各方力量,在科研单位、大中小学、部队、工厂、农庄等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研讨会,并“组织普希金作品的阅读晚会、讲座和关于他作品的报告、音乐会,仅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博物馆保护区便举行了五千次集会”。在莫斯科批准设立地方委员会后,又有百余个普希金地方委员会在国外设立,推动由苏联政府塑造的普希金形象的广泛传播。在这场狂欢式的盛大活动及其漫长余韵里,没有人记得普希金本属于“剥削的”贵族阶级,全国各地的集会都默认将普希金视为“我们的一切”。在这一将普希金思想与全民族自我意识相关联的苏联时期,普希金甚至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无神论者,其宗教信仰问题也被刻意模糊,以此来规范民族意识的组成成分。这一阶段的报道中用于描述普希金的词汇几乎全是积极正面的,对于普希金的一系列荒诞行径和陋习恶习却只字不提。此时的普希金形象是苏联时期共产主义文化事业中理想人格的化身,对诗人的评价统统带上了“天才”“先驱”的字眼。关于诗人的言论需围绕诗人的崇高一面而展开,任何不符合当局定调的发言都会遭到镇压,严重者甚至要被驱逐出境。对比而言,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还曾有人质疑或批评普希金在文学界的成就,但1937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之间,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官方极力维护。人们忽视了普希金早期浪漫主义诗歌中对拜伦的模仿成分,公认其为俄罗斯文学史上伟大的革新者和领路人,讨论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之类话题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普希金已然成为俄罗斯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中伟大、先进的开创者。至此,普希金的崇高地位正式确立,普希金同时成为苏维埃时期的标准化人物形象。
一个大国应有自己的史诗般的、世界级的超级诗人,苏联政府同样需要这样的诗人来建立文学资本,弘扬民族精神,进而获得超级大国的地位。1937年的纪念活动中,苏联政府号召全民参与纪念活动基于社会团结观念,符合苏联当时的文化政策。“营造一个社会大团结、民族大团结的环境,需要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形象,普希金成为了最受青睐的人选。”[5]而在全面的普希金崇拜情绪中,人们关注的仍是普希金作为诗人的伟大功绩、作为民族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作为十二月党人之友的先进思想,对于普希金的个人问题避而不谈。文学偶像需要具有神性的传奇色彩,在长期的文学创作历史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审视的目光,而普希金的形象在苏联政府的塑造之下,已经远远超脱了文学偶像的范围,甚至获得了消费偶像和精神领袖的意义。普希金在官方语境下成为当之无愧的爱国者、革命者,拥有对俄罗斯人民的无限关怀,怀有基于国际主义的普世性思想。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与生活传统下,民众在公认思想体系中建立起对普希金的共同认知,以群众而非个人的理解力对普希金进行解读。群体的结论由个人的结论中和产生,政府以强大的向心力使社会舆论逐渐汇聚在圆心处,得到“普希金是民族偶像”的共识结果。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宣传,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普希金的崇拜也已发展到近乎狂热的地步。曾在19世纪被广为议论的“伟大诗人竟因情敌挑衅而死”的庸俗调笑消失不见。在1937年被点燃的崇拜热情甚至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尽管有短暂的停滞,但新时代中的俄罗斯人仍坚持选择以普希金为打开世界文学的契口,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光辉地位。至今,绝大部分俄罗斯人仍认可普希金的神圣地位,认为他足以成为俄罗斯的象征。
苏联政府以普希金为规范标准和代表符号,以文学为渠道进行整体价值观的宣扬,通过渗透式的思想灌输,用来唤醒民众对祖国的激情,形成极大范围的道德认同。尽管其中仍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质疑或反对的声音,但从普希金身上发掘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国上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文化教育界人士尤其从中受到团结与鼓舞,从而为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凝聚起力量。普希金的作品在政府的大肆宣传中得到普及,普希金的知名度也在俄罗斯境内外获得显著提升。诗人的“正义”一面在苏联时期得到广泛宣扬和认可,但也仅有“正义”一面被挖掘。从沙俄时期将普希金视为宫廷的支持者,到苏联时期将普希金奉为主张改革的先锋人物,各个时期的不同解读代表了不同政府的立场,直接影响则是将普希金的形象裁剪得愈加片面。
五、结语
莱蒙托夫为普希金而作的悼亡诗在本质上出于对诗人逝世的惋惜,以及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他在诗中不断为诗人的声誉正名,称其天才的一生被黑暗的阴谋终止。《诗人之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普希金的正面形象。然而在复杂的社会舆论下,一方面,对普希金的抨击和批评不休地折损着诗人的名声,另一方面,对普希金的信奉和追捧逐渐演变得自相矛盾。尽管在普希金百年诞辰之时,沙皇政府亲自将普希金的形象重新定义,为他冠上官方认可的大师之名,但对普希金进行片面解读的行为全然不符合莱蒙托夫等人所期盼的景象。直至苏联政府将普希金与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彻底为诗人赋予了全民性的神圣意义,对普希金的崇拜之情自此演变成真正的崇拜体系。这一几乎覆盖了全国范围的崇拜热情与《诗人之死》中传递的狂热情绪十分吻合。普希金崇拜体系在苏联解体后曾一度失去官方地位,但俄国政府仍将普希金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以重振俄国文化,并为其思想赋予新的爱国主义阐释。在普希金逝世之后,对普希金形象的解释权全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普希金的精神思想、文化观念和政治立场被不同政权反复讨论,在不同时期得出互相抵牾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明了诗人已成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意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