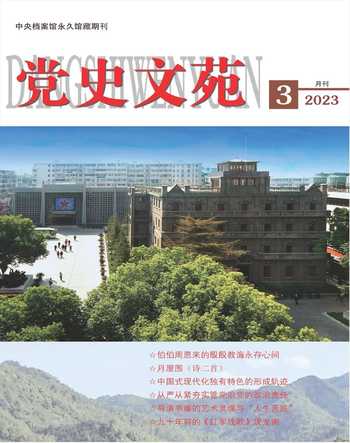中央苏区红军文艺组织流变考
2023-04-14廖美琳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队伍承担着武装斗争和宣传动员的双重使命,所谓“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手榴弹”。红军对宣传动员群众和武装斗争进行有效融合统一的探索,在中央苏区红军文艺组织的生成和流变中得到清晰的呈现。井冈山时期创建的士兵委员会娱乐科,成了红军文艺组织的雏形;古田会议后的俱乐部和列宁室,使部队文艺发展走向组织化;苏维埃时期的八一剧团和工农剧社,确立了部队文艺组织的体制化和专业化;苏区后期的“火线剧社”,则是整体战争思维实践的重要尝试。
一、士兵委员会的娱乐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部队忙于打仗,反击国民党一次次“围剿”,开辟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还未列入这支初创军队的议事日程,也没有专门机构,更没有连队俱乐部、剧团之类的组织。但追溯来看,红军文艺的初步萌芽还是始于井冈山时期。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队伍在“三湾改编”时建立了一个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机构——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源自苏俄红军部队。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为使旧军队转向革命阵营,苏俄红军创建了士兵委员会。1927年9月15日,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沃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认为,南昌起义军“可以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井冈山时期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建了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与红军宣传队一样,同属于政治部领导。宣传队负责对外的群众运动,士兵委员会则担任对内的军事政治训练。它的核心任务是一方面参与军队纪律和经济管理,一方面开展士兵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军团营连均设委员会,在连营团各级委员会中还设立了宣传委员、娱乐委员或宣传科、娱乐科。
据当时主要负责士兵委员会工作的陈毅介绍,士兵委员会的娱乐科活动主要是“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剧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红军中的游艺晚会非常频繁,每打一次胜仗就要举行一次晚会,唱歌、演戏,成为红军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之一。仅1928年间,士兵委员会举办的游艺晚会即达十余次之多。每天的“三操两讲”前后,娱乐科也召集士兵“经常进行唱歌活动”,还把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编成“红军纪律歌”来唱。红军初上井冈山时,由于当地许多群众不了解红军,甚至把红军当作土匪打,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士兵委员会实行了“宣传兵制度”,每个机关由“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此5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向群众宣传;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墙壁上统统写满红军标语,‘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因此,士兵委员会在“筹备各种文娱活动,引起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受”的同时,也以“工农革命的事实和豪绅阶级的罪恶编成戏曲歌谣来表演,使群众对革命以响应而有兴趣去求得认识”。
当然,从井冈山军队文艺的总体历史面貌来看,这一时期的军队文艺宣传并未深入展开,士委会更侧重军队政治中的民主意识塑造,而娱乐科的文艺宣传则相对还处于初步实践时期,无论从文艺组织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稍显粗糙单薄些。地方上的山歌“只有少数本地的战士唱”“歌咏在那时还不盛行”。但安源时期广受欢迎的化妆宣传,因其“介于口头宣传与演戏间的比较简单活泼的宣传形式”,成了井冈山宣传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打土豪》《活捉肖家璧》《大放马》《空山计》等,是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也为赣南苏区时期工农剧社的戏剧运动发展打下了基础。
1929年,井冈山军队南移后,由于“民主理想和军事命令”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中共遂将士兵委员会职能逐步弱化,直至取消。1930年,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结论强调:“士兵委员会,在原则上是要逐渐地取消它,但不是命令式地取消。”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苏区工作计划规定:“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到消灭。”大约在十一月份,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士兵委员会的内容取消,而代之以俱乐部、列宁室等苏联红军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
二、俱乐部与列宁室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在红军部队中建立“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
古田会议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会议专门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提出来讨论,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批评“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认为对红军宣传员的“‘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号,应该从此取消掉”,要发展“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提出“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建设俱乐部”。与此同时,共青团闽西特委与湘鄂赣大阳区宣传工作会议先后作出决议,要求“每一个组织一个俱乐部,每一个区组织一个大规模的俱乐部,每个县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俱乐部”,而且将其归于“文化建设”之中,称其为“提高和涵养群众的革命情绪和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力量”。
1931年开始,各地苏维埃政府把俱乐部的招牌纷纷挂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工农红军学校建立,校政治部专门成立了红军俱乐部。红军俱乐部是加强红军文化教育的基地,是“政治教育的补充,是发扬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必要工作”。因此,组织军内俱乐部,便是有计划的切实地向红军战士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一句话,就是“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红军学校因学员文化水平低,教学方法除正式军事政治课程外,特别注重各项文化娱乐的课外活动,以这种活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形象教育方式来辅导学员。1933年,中央教育部在总结各地俱乐部的经验时,对俱乐部内部机构的设置,作了統一与规范,在其制定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中,列出了六种委员会:运动委员会、游艺委员会、训练委员会、集会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展览委员会。俱乐部保留了20年代初安源工人运动时期创建的游艺股,还组建了山歌队、音乐队、双簧化妆表演队等。每到周六,俱乐部有军民联欢演出,“有唱苏联歌曲的,有唱我们自己编写的歌曲,有唱民歌的,有跳舞、双簧、清唱京剧等”。
在俱乐部组织之下,还有一个列宁室。1928年在井冈山建立的“军人活动室”,是列宁室的前身。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俱乐部是各小单位的文化、娱乐、教育的领导机构,列宁室则是每个单位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教育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这一时期,俱乐部和列宁室“在红军中成为教育群众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在《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中,明确指出设置俱乐部和列宁室的目的:“为要培养红色战斗员活泼的生活兴趣……所以要组织俱乐部、列宁室去有计划的切实的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发扬红色战士们生活求进步的精神,以适应创造铁的红军,争取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
红军中的列宁室设有干事会,“干事会由军人大会选举并决定一人为主任,在连政治指导员、师俱乐部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列宁室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娱乐体育教育,借用娱乐的方式深入政治教育。红军各部设讲演组、游艺组、体育组、识字组、墙委会、青年组。讲演组必须“经常按期进行讲演会、讨论会”,并“敦请革命领袖讲演革命的理论及革命历史和故事”;游艺组“帮助组织各种纪念节晚会或运动、游艺事宜”;体育组经常开展“打拳、劈刀、刺枪、乒乓球、篮球及跳高、跳远等活动”;识字组“经常计划识字课的进行,举行成绩考查、揭示或比赛”;墙报组“定期出版本伙食单位的墙报”,并“组织读报和指导读报员的工作”,还应“搜集士兵日常生活情形在墙报上发表,并向上级机关的报纸写通讯”;青年组“经常计划和吸收广大青年红色战士积极参加青年各种特别的游艺和运动,帮助和参加各种青年晚会的工作,搜集本单位的青年生活情形及有关青年问题的材料,充实墙报‘青年栏’的中心问题”。
由于红军的各级指挥员都很重视列宁室的工作,认为“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是政治工作的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发扬和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工作”,因而红军中的列宁室,成了每个连队“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教育等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地方上各基层单位的列宁室对群众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工农剧社
随着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胡底、沙可夫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中央苏区,苏区军队文艺组织逐渐走向专业化和制度化。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为了庆祝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盛大典礼,筹备委员会抽调了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李伯钊和中央保卫局胡底、钱壮飞等人负责筹办大会的文艺活动。1931年12月,宁都二十六路起义军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驻扎在瑞金九堡,中央苏区派出一支宣傳队前往慰问演出。为期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广受起义官兵的欢迎,尤其是《为谁牺牲》的戏剧,成了官兵们最喜爱的节目之一。这次演出后,红军学校政治部意识到戏剧的鼓动性在宣传工作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于是创建了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性剧团——八一剧团。八一剧团的诞生,标志着中央苏区部队文艺活动转入有领导的、专业的、有组织的创作和表演的新时期。
1932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对八一剧团进行改组,更名为“工农剧社总社”。成立之初,“由于少数人发起组织,未受任何革命团体所领导”;8月,正式确定其隶属于中央教育部;同年9月,因剧社大多数社员在红军学校工作,为方便工作,遵照教育部的指示,并征得红军学校政治部的同意,在第三次社员大会上,决定划归红军学校政治部领导。为了全面加强剧社工作,健全职能机构,剧社设立编审委员会及导演部、舞台部、音乐部、跳舞部、出版部等。
总社下附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蓝衫团”。与前期俱乐部相似,工农剧社也以“两条腿走路”,既走军队路线,又走群众路线。据李伯钊回忆,瞿秋白为此提出了具体构想:“第一、学校附设剧团,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动士气,进行作战鼓动。平时按期到集市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第二、他主张学校除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地方班在“扩红”运动中经常“到各乡各村红军家属家里,挨门挨户地去慰问和宣传他们,利用唱歌呀,说故事呀,谈家中事呀,作我们宣传的法门”。红军班则主要到部队火线演出,也由此派生出后期的火线剧社。
四、火线剧社
赣南苏区后期,随着国民党的围剿进攻日益猛烈,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工农剧社前往火线进行鼓动宣传的文艺演出愈加频繁。此时红军中的工农剧社分社正式更名为火线剧社。火线剧社随同作战部队行军,在火线上搭宣传鼓动棚,为鼓舞红军士气和瓦解白军而演出。中央苏区多家报刊还曾大力报道火线社的演出活动,比如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1933年6月14日)刊登《火线上的快乐晚会》、团机关报《青年实话》(1934年6月25日)刊登《火线上与白军士兵的联欢》、军报《红星报》(1934年8月15日)刊登《火线社在连队的活动》和《火线上进行瓦解白军工作的模范例子》等。除此之外,“火线剧社还组织战争动员的晚会”,常“和红军家属开一个联欢大会,大大感动红军家属”,“营造‘不回家’的空气”以稳定军心。
1934年秋,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火线剧社’分成三个剧团,即‘火星剧团’‘红旗剧团’和‘战号剧团’,在各自负责的战区中从事戏剧活动。团员们随身带着梭镖大刀和手榴弹,以便在遇上敌人时参加战斗。”
从中央苏区红军文艺组织形态的流变可以发现,红军部队逐渐跳出“纯粹战争”思维,将文艺宣传动员纳入到“总体战争”思维中。文艺活动的组织化、专业化、体制化,为中共军队总体战争文化塑造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日)秋吉久纪夫编:《江西苏区文学运动资料集》,汲古书院,1979年。
【基金项目】抚州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央苏区军队歌谣研究”(编号22SK10)
【作者简介】廖美琳,女,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黄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