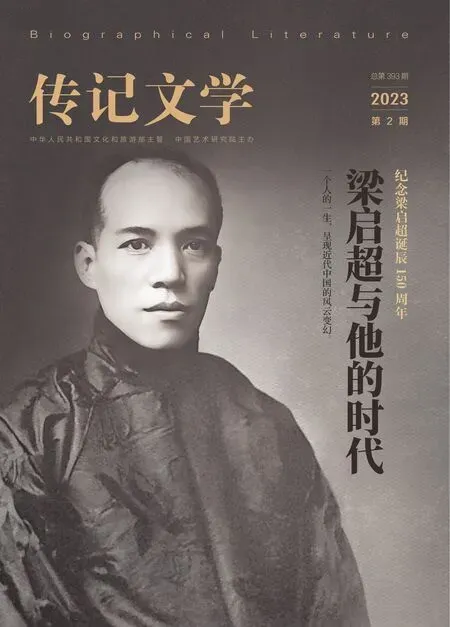天姥山中的文学记“缘”
2023-04-13缓之
缓 之
浙东石城有一座山,相传登山者听到天姥(母)的歌谣,这可能是“天姥山”得名的由来吧。让天姥山名扬天下的,是李白的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专家说,那首诗作于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李白离开东鲁,准备南下吴、越。他对现实社会深感厌倦,遂产生了云游神仙世界的幻想。他首先想到了天姥山:“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天姥山固然很高,总不能与五岳相比,而在诗人的笔下,却“势拔五岳掩赤城”,就连相传有四万八千丈的天台山也都要拜倒在天姥山脚下。读过这首诗的人,无不萌生一种登临仙境的向往。
2019年秋冬时节,我和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新昌县科协的俞良相约朝拜天姥山。我们从新昌出发,开车到天姥山大约一小时的路程,沿途并无高山,却风景无限。用画圣顾恺之的话说,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山川之美,有若画境;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惊叹此地为“天地神明之境”,“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东晋高僧支遁杖锡山间,读书、品茗、作诗、谈论,无不精湛。
我们的第一站是新昌境内的大佛寺。传实方丈热情地接待我们,一番寒暄、一杯清茶之后,他引导我们拜谒了昙光尊者舍利塔、放生池以及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纪念塔。新昌大佛寺开凿于东晋永和元年(345),石像就建造在球状凝灰岩上。《高僧传·梁剡石城山释僧护》中记载了修建这尊佛像的经过。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还留下一篇《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我当年读《文心雕龙》,始知有这通著名的碑刻,它是吸引我来到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齐永明四年(486),僧护发愿凿十丈石佛,经僧护、僧俶、僧祐三代高僧三十年的努力,于梁天监十六年(517)完成弥勒佛造像,通高16 米,仅头像就高达5 米,耳长近3 米。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诗中说:
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余照发光辉。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年(730)冬天,叙写作者礼拜之后,尘机濯尽,感到一身轻松的喜悦。在濯缨堂前,有一株相传是朱熹种植的梅树,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朱梅。据说朱熹注《四书》即在此地。“四书五经”的说法由此传开。其实不仅是朱熹,隋唐以来,王羲之七世孙智永、颜真卿、李阳冰等大书法家,李白、杜甫、王维、贺知章、李邕、皎然、白居易、刘禹锡、李绅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驻足、修炼、读书、创作。当地人为了弘扬唐诗精神,开发了“浙东唐诗之路”。我们的午饭,就是唐诗之路宴,每一道菜名都取自唐诗,是诗意盎然的精神大餐。
这里还有一座千佛禅院,为古元化寺,相传是由东晋高僧于法兰、于法开创建,南齐永明年间始凿二窟,造佛龛,共有一千多座佛龛、佛像。沃洲山上的真君殿也很有名,是为了纪念抗金英雄宗泽而建。进山之前,还要拜谒三白堂。晋代白道猷开山,唐代白寂然建寺,白寂然的从叔白居易应侄子之请,撰写了《沃洲山禅院记》,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沃洲山出来,天姥山就在眼前了。

左图:佛字前与俞良合影

右图:沃洲山与俞志慧合影
走进天姥山,首先要经过迎仙桥、丁公桥和司马悔桥。相传唐代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隐居天台桐柏山,无心仕宦。唐玄宗数诏其出山,至此而悔,故称司马悔桥。桥边有司马悔庙,庙门有一副对联:“太白梦游曾钟此,子微仙踪留今兹。”到此,武官下马,文官下轿,以示敬仰,故称落马桥。
走过古桥,就来到了古香古色的班竹古村。明代的徐霞客、王思任、清代的袁枚,现代的郁达夫等都曾在班竹驻足,“班竹铺”由此扬名。从班竹铺往前走,来到天姥古道前,迎面竖立一块长方石碑,上面有任继愈先生题写的“天姥山”三个大字。俞良介绍说,这是唐代诗人、僧侣前往天台山的主要线路之一。这条小路,是刘宋时期的大诗人谢灵运开辟出来的。《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刘宋元嘉六年(429),谢灵运伐木开径,直至临海,史称“谢公道”。为纪念这段经历,谢灵运还撰写了一部《游名山志》,详述天姥山的风光。他在《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诗中写道:“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这首长诗,作为中国最早的山水诗,被收录到现存最古老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影响深远。
从谢灵运的诗文中可以看出,这条山路极为险峻,而今已被拓宽。站在盘山路上,我们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艰辛。过了会墅岭,就是横板桥。这里是行人休憩的驿站,也曾热闹一时。清代著名文学家方苞到此,感叹天姥山的险路不过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名气呢?这是一种设问。他当然知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在这里留下千古佳句,想不出名,都不可能。
谢灵运当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在横板桥乡村记忆馆,还可以看到清人使用过的谢公屐实物。当年,谢灵运登山临水,常有“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的惋叹,300年后,他竟成为了李白梦中的异代知己。也是这样一个清秋时节,我们也仿佛穿上了谢灵运的木屐,登上了诗人走过的“青云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俯仰之间,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这让我们忘却了时间,忘却了疲倦。此刻,山中已有寒意,我们依然兴致盎然,一路攀爬,以至大汗淋漓。在距离山顶的最后200米,俞志慧索性脱去上衣,捡起树枝当拐杖,快速登顶。树缝中,听到志慧召唤:

任继愈先生题写的“天姥山”石碑
“快来啊,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钻出丛林,跑上山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眼前的景色让我们惊呆了:对面的天台山脉,被五彩缤纷的云雾所缭绕,层峦叠嶂;天台山脉主峰依稀可见,而群峰已被淹没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站在天姥山之巅,反而有一种“对此欲倒东南倾”的感觉,是我们在朝拜天台山。看来,李白的想象和我们看到的真实画面,迥然有别。《大明一统志》说:“天姥峰,在台州天台县西北,与天台相对。其峰孤峭,下临嵊县,仰望如在天表。”这段描述,更符合实际。不过,我们还是宁愿沉浸在诗人的想象中,静静地注视着远方,在落日的余晖中沉默良久。此情此景,任何语言表达,都是那样苍白无力,只能用心灵去感应。松涛阵阵,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悠远韵律,而归鸟喳喳,点缀着无边的空寂……
这时,志慧的电话响了,打断了我们悠远的思绪。

左图:天姥峰

右图:迎仙桥
电话是他的学生打来的。四小时前,在迎仙桥有一段巧遇,与这个学生有关。
相传刘晨、阮肇进山采药,走过这座桥,遇上两位仙女。他们一起上山,过了几天神仙日子。等再回到村里,发现人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这个传说,赋予这座古桥极为神秘的色彩。恰好那天,我们远远看到,在拱桥中央也有三位妇女坐在那里,正悠闲地织毛衣、闲聊天。我对二俞说:
“迎仙桥真有仙气,你们看,真有仙女在呢。”
这当然是玩笑,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志慧继续介绍着这座古桥的传说。我们的注意力也全集中在这座拱桥上,看起来很有年代感,青砖残破,苔痕斑驳。桥面的石板路,坑坑洼洼,留下古老岁月的痕迹。我们的聊天好像惊动了那三位妇女,她们的目光一下子都转向我们。其中一位目光停在志慧身上,站起来问:
“您是不是姓俞?”在得到确切答复后,那位妇女兴奋地说:
“您是俞志慧老师吧?我是您的学生啊!”
随即,他们用当地话开心地聊了起来。我一点都听不懂,就退到后面,远远地打量着他们。三位农村妇女,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左右。和俞老师聊天的那位妇女,面色红润,身材微胖,留着常见的齐耳短发。这时,志慧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他教过的学生,也姓俞,叫俞英,当年才16 岁,而今也快50 岁了。志慧回忆说,1986年到1988年,他曾在长诏中学任教。时隔三十多年,他没有想到会在天姥山的迎仙桥上遇见自己昔日的学生。
俞英同学很热情,邀请我们下午到她家喝茶。当时,我们心在天姥山,还要赶路,没有久留,就匆匆离开了。刚才,正是俞英来电话,邀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她家就在盘山公路旁边,一座二楼建筑。她丈夫在附近一家纺织机械配件厂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吃饭。得知我们要来,特意准备了晚饭,回来陪我们喝酒。蓦然间,我想起了孟浩然的诗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种淳朴的情感,让我们心头热乎乎的,眼眶有些湿润。主人很热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乡村野味。我们确实又累又饿,吃得格外开心。在群山深处,酒酣耳热之际,我们彼此说着热切的话,都是满满的祝福。那一时刻,作为老师的幸福感油然而起。人生际遇实在神奇,因缘巧合,有若前定。我相信缘分。我的微信个性签名,核心就是一个“缘”字:人缘狗缘今世缘,凡事皆缘;天边地边白云边,尽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