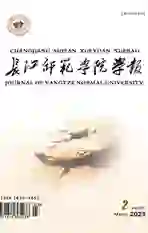《哥达纲领批判》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2023-04-12侯茂林
摘要:《哥达纲领批判》是一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蕴藏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经典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在对拉萨尔抽象的“公平共享”进行批判的逻辑起点上,建构性地展现了未来社会共享发展的美好图景,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论证了共同富裕实现的渐进性、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对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初步性、原则性构想。这一思想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对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新时代共同富裕;生产资料公有制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652(2023)02-008-09
DOI:10.19933/j.cnki.ISSN1674-3652.2023.02.0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视域下城乡空间融合创新机制研究”(22YJC71007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零工类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优化研究”(22BKS149)。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亿万民众的殷切期待,是党矢志不渝的使命追求。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起点上,将共同富裕置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两步走”的重要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1 ]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3 ]党的二十大立足于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再次强调要“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4 ]。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实践。我国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和推进必然离不开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指引,而这一思想蕴藏在《哥达纲领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一代表性著作中。
虽然“共同富裕”这一表述并未直接出现在《批判》中,但马克思在文中对拉萨尔错误分配思想的严厉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分配共享的理想追求,所指向的都是共同富裕状态。1875年,迫于形势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行合并,共同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以《哥达纲领》为新的党纲。然而,新纲领却充斥着拉萨尔错误的观点和策略。为此,马克思写了《批判》一文,对拉萨尔抽象空洞的公平共享观进行了严厉批判,并从唯物史观出发构想未来社会发展图景,不仅论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还阐明了共同富裕循序渐进的实现过程,从而科学论述了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和实现路径。因此,《批判》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深入挖掘它的共同富裕的精神宝矿,对准确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深入有序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科学批判: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哥达纲领》中,拉萨尔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公平共享,幻想通过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和依托“国家帮助”改变工人贫困的境遇,进而实现“分配正义”。这一纲领内容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有着原则上的分歧,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清算。在阐明拉萨尔错误的理论基础、抽象的分配正义以及虚幻的路径勾勒的基础上,马克思进入到对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平等问题的思考,萌发出共同富裕的思想火花。
(一)“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掩盖两极分化内在根源
“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是拉萨尔公平共享观的重要理论支撑。拉萨尔在各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脱离生产条件和生产实际片面夸大“劳动”“分配”的决定性作用,实则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维护,是对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经济根源的掩盖。
《哥达纲领》开篇写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5 ] 428,鲜明地表述了“劳动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这一立说具备极强的迷惑性,看似是褒扬劳动的话语,实则赋予劳动一种荒诞的“超自然创造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5 ] 428事实上,劳动与劳动对象(如矿藏、森林、棉花)、劳动资料(如生产工具、土地、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拉萨尔忽视劳动的自然制约性,单一地将劳动与财富相挂钩,在理论上预设了社会财富分配由劳动质量高低决定的错误观念,即资产阶级普遍富裕在于其劳动产出率高、产量巨大,而无产阶级普遍贫穷在于他们劳动产出率低、产量甚微。实际上,在私有制社会里,由于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资本家与工人在占有劳动以外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从而导致了财富分配上的差异。因此,拉萨尔的这一观点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问题,掩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剥削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
拉萨尔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状和弊端,并将问题的解决简单诉诸分配领域,片面地认为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是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进而主张变革分配制度,将社会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陷入了“分配决定论”的主观唯心史观。在这里,拉萨尔抛开现存社会的生产前提,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企图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变更分配关系,实现平等分配。这无疑是一种“乌托邦”设想。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拉萨尔割裂了生产与分配的内在联系,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 5 ] 436,不过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5 ] 436。实则,“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5 ] 436。这里的生产条件是指资本和劳动力,意味着分配是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并作出贡献而得到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资本居于主导地位,不断支配和控制着劳动,意味着资本家和工人按照资本和劳动参与生产的生产方式只能产生剥削与被剥削的分配形式,只能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分配结果。因此,要改变两极分化,变革分配方式,只能先消灭私有制,变更生产方式。可见,拉萨尔错把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以为分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忽视了分配背后的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从而掩盖了导致贫富分化的真正根源。
(二)“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力”是空泛抽象的分配正义
拉萨尔在“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的理论基础上,披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的“不正义”现象,即工人付出巨大劳动却取得微薄收入,资本家不劳动却占有大量财富,进而主张劳动产品应归劳动者所有,要实现“公平的分配”,获得“平等的权力”。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从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出发谈论分配的“公平”“平等”,实质是一种抽象空洞的分配正义。
《哥达纲领》认为,解决现实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5 ] 431。“公平分配”是诱人的论调,正顺应了众多挣扎在贫困线上工人的期待。对此,马克思指出,“公平”是由经济关系发展而来的,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法权概念,而“分配”作为一种经济关系,隶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拉萨尔将这些法权概念规定于特定经济关系之上,将“公平”当作调节经济关系的永恒原则,以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评判分配,本质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颠倒,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再现。事实上,“公平”不是人类理性思维抽象出来的衡量一切事物的普适标准,它的内容和准则内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并由现实生产关系赋予和决定。进一步说,公平的标准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适应特定生产方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优势获取巨额财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出卖劳动换取仅维持生活的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分配,也是唯一“公平”的分配。拉萨尔没有意识到,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实际是生产方式的不公平。不动摇经济基础,不变革生产方式,诉诸简单的道德控诉,从理论层面建构出符合伦理规范的“公平分配”,无异于一张笼络人心的“空头支票”,是毫无意义的。
《哥达纲领》宣称:“劳动所得应当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5 ] 428这一论断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马克思指出,一些囿于体力和脑力上的缺陷而没有参与劳动的人,是否应该享有劳动所得?享有的话,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就是“不平等”,不享有的话,“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就是空话。这一华丽的口号只能是真空中的理论,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与考证。“平等的权利”的诉求,实际是以贵族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对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一切成员”并不都是劳动者,也就不存在共同劳动的虚假前提。再退一步讲,即使劳动者依据既定的权利分配劳动所得就实现平等了吗?马克思强调,这一平等的主张在人与人面前,确立了同一尺度——劳动,即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劳动者本身在自然禀赋和社会身份等方面存在差异,按平等的尺度去对待不平等的人,这种平等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这里,拉萨尔忽视阶级差别、个体差别,将社会成员定义为抽象的社会成员,把劳动者定义为抽象的劳动者,也就只能衍生出抽象的平等权利和抽象的分配正义。
(三)“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国家帮助”无法实现公平共享
《哥达纲领》中对实现分配正义,提供了“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和依靠“国家帮助”的实现路径。拉萨尔不仅抽象地谈论公平共享,他所设想的实现路径也充满了虚幻性。马克思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披露了这一路径对实现社会共享的先验性和空想性。
《哥达纲领》炮制了一条“铁的工资规律”,宣称这一规律造成了工人的贫困。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是指工人的平均工资通常徘徊在勉强满足工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上,如果工资高于平均额,工人生存状况改善,则人口激增,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降低;反之,则人口骤降,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提高。在这里,拉萨尔将劳动者商品化,利用商品供求规律分析工资的波动,将工人的贫困归结于人口的自然繁殖和绝对过剩。而废除这一规律似乎就消灭了贫困,实现了公正。这一论调完全暴露了拉萨尔在工资问题上的糊涂认识,直接导致了他对工人贫困根源的错误理解和贫困问题的虚幻解决。马克思指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 5 ] 441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然而工资并非工人所提供的劳动量的等价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是雇佣劳动者被剥削的部分。在这里,工资以一种资本家与工人买卖劳动力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资本家以少量货币获取多量劳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雇佣劳动才是症结所在,剥削才是贫困的根源,工资不过是雇佣劳动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掩盖物。而拉萨尔在工资上下功夫,围绕工资兜圈子,不过看到了一种外显出来的剥削形式并要求废除这种剥削形式而已。事实上,不改变雇佣劳动,不变更资本主义制度,工人的贫困境遇不会改变,劳动所得的共享和财富公平的分配也不会实现。
抛出“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之后,拉萨尔紧接着又提出“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 5 ] 442的“救世良方”。拉萨尔认为,工人要免受“工资规律”的摆布并收获自己劳动的全部收入,就要创造实现社会共享的生产条件,即建立工人合作社,自己做工厂的主人。但考虑工人力量弱小,合作社的建立需要通过争取普选权在议会中发声获取国家贷款帮助。马克思指出为变革社会生产条件而创建合作社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国家帮助”这一实现前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谓的“国家帮助”,不过是取消阶级斗争,否定暴力革命,主张依托反动政府帮助无产阶级建立“普鲁士社会主义”。这不是开辟了社会问题的解决道路,而是开辟了“机会主义”道路。很明显,这一论点是拉萨尔超阶级的国家观念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显现。他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属性,而认为国家是合乎道德、人性的伦理存在,是为了保障人类自由发展的高尚存在。马克思对此讽刺道:“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5 ] 442马克思始终坚定地认为,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改变现存剥削制度,才能变更社会生产秩序,构建共享发展的现实基础。很明显,拉萨尔宣扬的“国家帮助”,既无法变革工人的生产条件,也无法实现他所想象的公平分配。
二、勾勒未来: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整体建构
《批判》起于批判,但并不止于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建立新世界是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建构方式。在《批判》中,马克思在对拉萨尔抽象的“公平共享”批判的基础上,立足唯物史观,对未来社会展开了设想,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制度保障
马克思并非脱离社会经济生活抽象地谈公平共享,而是立足唯物史观,深入考察社会生产过程,剖析现实生产关系,探寻两极分化的内在根源,从而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
在《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5 ] 436这就是说,生产决定分配,共同富裕看似是分配问题,实际是决定分配方式的生产方式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地主控制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民和工人在生产中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这样的生产方式自然产生了利于有产者的分配结果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首要的是变革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生产资料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属性,而转变为一种公共产品,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和支配。这就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占有了平等的物质生产资料,消灭了因生产资料占有差别而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所有制基础,为社会以劳动为唯一标准分配消费资料提供了根本前提,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制度条件。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还进一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
在《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5 ] 434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是依据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全部劳动量分配生活资料。这种“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主导和控制生产,支配着生产成果分配,导致劳动者参与财富的创造却不能参与财富的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谁都无法提供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生产,由此决定了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财富,也共同分配财富。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保证社会成员以等量劳动换取等量生活资料,使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排除在分配标准之外,从而消除了产品分配中的剥削关系,是不存在任何剥削的分配方式。不可否认的是,鉴于人在自然禀赋、劳动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以劳动为唯一尺度分配生活资料还会造成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有所不同,但由于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凭借劳动换取报酬,就不会再出现人剥削人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这是一种不存在财富分配差异的分配方式,是真正意义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总之,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的方式共享发展成果,是马克思对实现共同富裕所作的制度设想,对共同富裕实现规律的深刻揭示。
(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共同富裕实现的物质前提
在《批判》中,马克思以生产力为尺度和依据对共同富裕实现前提进行分析,对共同富裕实现标准作出判定,从而揭示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
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全体社会成员分配的只能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结果,即作为“集体的劳动所得”[ 5 ] 432的社会总产品。为此,他对《哥达纲领》表现出来的“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 5 ] 436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将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规定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是总过程的起点,影响并决定生产运行体系中的分配、交换、消费环节。这就意味着生产是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分配不能脱离生产领域。只有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数量,可供分配的产品才会增多,社会财富才能充裕,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相反,如果只注重分配,忽视生产力发展,其结果也只能是普遍贫穷。因此,共同富裕看似是分配问题,但仅依靠分配并不能实现,还需要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总产品的高度供给为前提和基础。
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先变革生产关系,铲除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实基础,而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在《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 5 ] 430所谓“物质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历史祸害”则是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力并非致力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是已经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是使资本家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倍增的一种能力。因此,生产力越发展,社会财富就越集聚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两极分化就越严重,两大阶级的矛盾就越尖锐,直至引起一次又一次革命的爆发,最终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些结果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蕴含着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力量,将会为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建立提供条件。
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中,马克思也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这种生产力是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但仍然难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距离实现真正共同富裕的生产力还有一定的距离,因而这一阶段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实现的还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人们实行按需分配,达到分配结果上的事实平等,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总之,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为生产关系变革创造条件,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对拉萨尔公平共享思想进行批判并不意味他忽视分配正义、否定共同富裕。相反,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设想中,从更具体和更深入的层面思考共同富裕的演变进程和发展规律。在《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剖析这两个阶段不同的分配原则以及由此产生共同富裕的不同实现状况,揭示共同富裕实现的历史渐进性和衡量标准的阶段差异性,表明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财富分配权利相同,但实际占有不同的差别富裕。在马克思看来,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唯一可能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这也是与该阶段的经济结构最适应的分配方式。在这一阶段里,个体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5 ] 434,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劳动者分得的生活资料则以其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为依据,通过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可避免的是,劳动个体在初始禀赋和后天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劳动能力,形成了劳动者各自的“天然特权”,使劳动者以劳动为唯一尺度获取的生活资料还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再退一步讲,即使忽视个体劳动能力的差异,不同劳动者提供相同劳动且获取同等份额收益,但劳动者之间不同的家庭负担、生活环境仍然会造成生活资料占有事实上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还会不同,还存在着不平等。因为按劳分配的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5 ] 435。因此,第一阶段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是带有资本主义烙印的共同富裕,是不存在阶级差别,但存在个人特权的差别富裕。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些弊病的不可避免性,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5 ] 435。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真正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阶段。在《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构想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5 ] 435-436在高级阶段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社会总产品高度供给,充裕的物质资源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被动活动,而是自觉自主的能动状态,个体各尽所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并按照自身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从社会储蓄中获取生活资料,实行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这就超越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按劳分配”的形式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限,确立新的分配尺度和原则,抽离以往私人财富占有的所有意义,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已经实现的结果,转而变成一种手段,致力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更长远的目标。总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论述,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对我国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三、观照现实: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启示
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挖掘不是为了将其束之高阁、时时瞻仰,而是要观照现实,充分研究其中的当代价值,形成重要思想启示,促进我国共同富裕向前推进。
(一)牢固坚持公有制经济,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在《批判》中,马克思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根源上解蔽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秘密,指明了未来社会共同富裕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当代中国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分配制度,为共同富裕实现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社会财富由“私享”到“共享”,关键在于将生产资料由“私有”变为“共有”。这种“共有”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在我国具体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再被私人所占有,社会成员在生产中除了劳动不能再提供其他的东西,这不仅铲除了有产者凭借生产资料占有而对无产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土壤,还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财富提供了所有制基础。因此,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共同富裕实现奠定生产关系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局限于不适应现存生产力发展的单一所有制的发展模式,共同富裕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这就需要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在“增大蛋糕”中的关键作用,实现两者并存、相互作用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最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着力解决国有企业营运效率不高、机制运行不畅等突出问题,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充分凸显国有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和推进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构建和完善国有经济的社会共享机制,使全民共享国有经济发展红利,为共同富裕提供共享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促进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格局,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动能。同时,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监督,限制其中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有序发展,协同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各种非劳动要素不断发挥作用必然打破单一按劳分配的格局,形成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多元分配模式。在整体分配格局中,我国始终将按劳分配作为分配的基本形式,保证按劳分配居主体地位、占最大比重、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也加大对私营企业财富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力度,限制剥削现象的产生,为全民共享劳动成果提供现实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元分配格局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利益分配不公、公平和效率冲突及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平分配问题,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他鲜明地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2 ]。这就为现阶段促进分配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遵循。一方面,初次分配要倡导按劳分配原则,提高劳动参与分配的比重,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增强劳动人群的获得感与成就感,使按劳分配不仅成为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要遵循效率优先原则,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创造更多财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挡加速。另一方面,需注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在调节社会财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再分配领域,要建立健全以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为主要手段的收入调节机制,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也要通过各种慈善组织和社会活动,依靠道德力量和文化感召,使已分配到个人的社会财富再次进入配置流程,加快形成第三次分配格局,彰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正义,最大程度实现共同富裕。
(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产力提质增效,才能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能分配的只能是生产力的结果。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演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以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以满足共同富裕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2 ]。这就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思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第一,坚持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从发展逻辑来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摆脱资源驱动、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加快转换发展动能,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 6 ] 3在众多发展难题面前,创新具有决定性意义。依靠创新,可以重新整合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综合效能,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形成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要坚持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创新的驱动作用,为共同富裕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依据区域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建设,实现发展方式高质量转变;建构层次多元的科技人才模式,完善创新主导的人才评价体系,激发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为创新格局注入不竭动力;聚焦重点领域发力,加大创新力度,突破核心技术,切实发挥创新在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上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劲保障;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对创新发展的束缚,为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创新政策与多项市场政策有机融合,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能,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变革。
第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共同富裕奠定牢固发展基础。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内形势深刻变革,发展方式急需转变,经济结构亟待升级,迫切需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共同富裕实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而言,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打造全新产业增长引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同时,积极改造传统动能,推动新业态、新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深度融合,使传统优势产业持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结构性调整,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刺激产品消费需求,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进而推动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
(三)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特征,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在《批判》中,马克思并非孤立抽象地谈“公平共享”和“共同富裕”,而是立足唯物史观视野,从社会形态演进角度论述了共同富裕实现的阶段性、渐进性特征,在更具体的层面对共同富裕作出阐释与规定,使共同富裕超越了抽象的维度,被赋予现实性和实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脱贫攻坚、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7 ]。马克思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和探索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现阶段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的理解,深化对共同富裕实现规律的认识,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战略定力,不断推动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从实现标准来看,我国现阶段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有差别的。所谓差别富裕,是指承认财富占有存在差异并将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的相对富裕。这种差异表现为不是所有人的同步富裕,而是存在先富和后富在时间上的差异性;不是所有地区一起富裕,而是存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在一定标准上的差异性;不是所有人绝对的同等富裕,而是存在富裕程度上的高低差异。在马克思看来,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相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但远未达到实现绝对共同富裕的水平,且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社会条件等因素限制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采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必然带来先富后富的不同步富裕、多富少富的不同等富裕。但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只会陷入共同贫穷的泥潭。相反,差别富裕才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其所具有的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的优势,将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走不平衡发展道路的现实性,承认财富分配保持合理差距的必要性,并努力从不均衡的富裕逐步过渡到相对均衡的富裕,以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从实现过程来看,我国共同富裕是渐进的、分阶段的。在马克思看来,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性演变、分阶段实现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同富裕有着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人们为达到这一标准所计划的努力就成了阶段性目标。当原有的富裕标准被超越、阶段性目标达成时,转而又会出现更高水平的标准和目标,激励人们向前迈进。一个个阶段性目标相互承接、循序渐进,揭示了共同富裕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性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要立足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制订并追逐与现阶段相适应的目标,脚踏实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以来,党中央在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和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阶段性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共同富裕目标纳入“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共同富裕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不断深化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再次将共同富裕提上发展日程,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4 ]。这些都彰显了党对实现共同富裕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科学性认识,对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裕的规律性把握。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些前后相继的阶段性目标的推进和实现中,我国共同富裕也会不断实现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飞跃,从而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1).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1).
[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ritique of Gotha’s Program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HOU Mao-L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on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a classic work which elabo? rates Marx’s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is book, based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riticizing LaSalle’s abstract“fair sharing”, Marx constructively demonstrated the beautiful vision and prospect of the shared development of the future society; he emphasizes that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ly devel? oped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material premise for common prosperity; he also demonstrates the gradual and phased characteris? tic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forms the preliminary and principled conception of the future common prosperity soci? ety. This thought is rich in content and profound in meaning. Thick, with distinctive scientific and forward-looking, it has impor? 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t this stage.
Key words: 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me; Marx’s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责任编辑: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