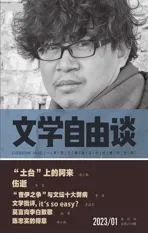文学批评,it's so easy?
2023-04-07李建军
□李建军
在有的人看来,文学批评者,小事一桩耳,it's so easy!譬若以手探汤,以舌尝羹,冰冷温热,醢咸醯酸,皆可瞬间感知,因而,评鉴文学作品,就是一件人人皆可为之的寻常事体。人们固然可以根据直接的感受,来简单地表达自己对一部作品的印象和评价,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可不是舌尖上的事情,而是心尖上的事情,是一种艰难而复杂的精神活动。面对一部作品或一个文学现象,只有经过深刻的解剖和分析,感性的印象才能升华为理性的认知,才能最终形成可靠的判断。
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说明,要想达到文学批评的“圆照”境界,就必须“务先博观”,因为,只有“操千曲”而后才能“晓声”,只有“观千剑”而后才能“识器”。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的专业难度和专业精神的问题。
从专业难度的角度看,文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要有敏锐的审美感受能力,甚至要有很高的文学天赋——有良好的语感和形式感,要有对调性和修辞等文学表现效果的精微的感受力;不仅如此,它还需要广泛的阅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因为,文学批评的深刻性和有效性,首先决定于批评家的知识视野和阅读经验。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要熟读世界上所有那些伟大的文学经典。正是这些经典培养了批评家雅正的文学趣味和鉴赏能力,培养了他对文学形式和意义世界的敏感和分析能力。文学批评意味着对照和比较。只有在比较性的认知框架里,我们才能看见一部作品的特点,才能发现它与其他作品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就此而言,没有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经验,就没有对照和比较,也就没有可靠的文学判断和文学评价。
要想将文学批评提高到很高的专业水平,批评家就必须培养自己心无旁骛的定力和专注力。阅读需要宁静的心态,批评需要沉静的心情。如果不能排除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专心致志的读者,也不可能成为具有专业素质的批评家。同时,为了保障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批评的自由,批评家还需要与被批评的作家保持必要的距离。然而,摆脱各种力量的牵惹,摆脱外在俗念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卓吾在《复焦弱侯》中说:“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两头照管。”所谓“两头照管”,就是想法太多,贪念太重,“既苦其外,又苦其内”:“官重于名,名重于学,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重于此者,必轻于彼;重于外者,必轻于内。试图“两头照管”的人,最终必然要牺牲一头,而且还是牺牲最不该牺牲的那一头,故而在面对严肃问题的时候,他便倾向于选择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面对“著名作家”的时候,他往往为了一时之惠利而奴事之——只要是有用的人,他都可以腆颜为之站台,急煎煎将一个平庸的作家吹捧为大师,硬生生将一部臭气熏天的垃圾作品,说得比金秋的桂花还芬芳,比天山的雪莲还纯洁。由于缺乏对事实的尊重和对原则的坚执,由于缺乏对文学的纯粹而认真的态度,这样的人也许会获得很大的利益,但是断不可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
文学批评的专业精神,还体现在批评家对批评本身的绝对忠诚。他应该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心,克制那种到处插一脚的冲动,尽量不在批评以外的其他文体的写作上,耗费自己有限的时间和宝贵的精力。他明白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也明白在文学世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属于两个绝然不同的创造模式:文学批评主要用理性的方式解析和阐释,文学创作主要用感性的方式描写和叙述;前者主要依赖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冷静的判断力,后者则主要依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活跃的想象力。因此,在文学批评的理性模式与文学创作的感性模式之间,横亘着一道高高的藩篱。有时候,作家可以翻过藩篱,闯入批评家的领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和阅读印象;但是,批评家要翻过藩篱,阑入作家的领地,凭着感性经验进行创作,却洵非易事。也就是说,作家无妨做一个“作家身份的批评家”,但是,批评家却很难做一个“批评家身份的作家”;小说家有可能成为不俗的批评家,但是,批评家却很难成为不俗的小说家;小说家可以“偏美”,也可以“兼善”,但是,批评家却只能“偏美”,而很难“兼善”。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作家身份的批评家,也很难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因为,他们拘于自己的趣味倾向和感性经验,在展开批评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排斥性和一定的主观性,就像雨果和司汤达在批评古典主义时所表现的那样,就像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时所表现的那样,就像纳博科夫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塞万提斯那样。
事实上,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那些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虽然也有过人的才华,甚至能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出丰富的诗性意味,比如刘勰和别林斯基简直就是批评家型的诗人,但是,他们终其一生,还是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文学批评事业。亚里斯多德、夏尔·圣勃夫、马修·阿诺德、徳米特里·米尔斯基、F.R.利维斯、乔治·卢卡契、莱昂内尔·特里林、哈罗德·布鲁姆、阿兰·布鲁姆都是用心极为专一的批评家,几乎没有在文学创作上浪费过自己的精力。别林斯基倒是雄心勃勃地写过小说,但写了半截,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擅此道,便又回到了本业,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文学批评家。
在批评家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家声名,也许最著,但受到的批评,也最尖锐。从艺术角度看,他的《怎么办?》实实在在是一部劣作。批评家拉津斯基批评它“没有一点才华的踪迹”;小说家列斯科夫说它在艺术上“完全不值一提,简直是可笑的”;高尔基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不是一个人,而是泥塑木雕”;诗人费特的批评,则更加尖锐——《怎么办?》“是一堆难解的、几乎令人不能忍受的东西”。在米尔斯基的权威的《俄国文学史》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享受过小说家应得的礼遇,只是在此书上卷第七章的“激进的首领们”一节里,被当作批评家来简单介绍,《怎么办?》则用介绍性的语言一笔带过,简直近乎忽略不计。事实上,对批评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对戴维·洛奇教授的小说,人们的评价也并不高。《1984》虽然像《怎么办?》一样广为人知,一样影响力巨大,但也同样并非艺术性完美的经典作品——思想上的深刻也难掩它概念化的痕迹,抵消不了因为趣味性和诗意性的匮乏而带来的沉闷。所以,那些理解文学真谛的批评家,知道自己的“立足境”在哪里,绝不三心二意,也决不让奢念的烈火,点燃自己的野心,试图征服一切文学领域。当然,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确系为不世出的无所不能的天才,那么,他大可随心所欲,无妨黎明写诗歌,上午写小说,傍晚写散文,深夜当批评家。对于这样的非凡人物,人世间的一切规则和纪律,自然统统都是多余而无效的。
与文学批评的专业精神一样重要的,是文学批评的思维质量问题,即文学批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质量决定着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也影响着批评家的批评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它要求批评家具备良好的感受能力,也要求他具备很强的思维能力。所谓思维能力,既是通过深入的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也是根据充分的事实和缜密的逻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批评性思维是一种高级的创造性的能力。它从不满足于停留在作品和现象的表层,仅仅对外在的信息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例如,对作品的情节和意象,进行低层次的复述和浅表化的评价;它的任务和目的,是根据广泛的阅读经验,在开阔的比较视野里,对作品的意义世界和形式特点,进行深刻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有清醒而成熟的怀疑能力,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严重问题。
这就意味着批评家必须提高自己的思维质量。他必须把事实感和真理性当作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为了尊重事实,为了获得接近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他就必须克制自己的主观冲动,必须克服思维上的懒惰习惯,学会以科学的精神和分析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把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当作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提高文学批评的思维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提高批评家的科学精神和批判能力。
然而,在当下的文学批评里,人们经常看到的,却是思维质量的低下和人格精神的庸俗。在他们的文字里,你看不到深刻的思想,看不到缜密的分析,甚至很难看到一句有价值的判断。他们的批评服从于一种外在的感性,即功利主义的感性——怎样说对我有利,我就怎样说;怎样写对我有利,我就怎样写。于是,利益决定了态度,屁股决定了脑袋。他们成了作家的庸俗意义上的朋友,成了像当下的黄桃罐头一样抢手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全都是肯定性的,准确地说,全都是颂谀型的。他们把低级的赞美当作高级的美德,他们把庸鄙的恭维当作高尚的慷慨。他们很少意识到,对文学批评来讲,思维上的懒惰和浅薄,态度上的卑下和庸陋,都是极其严重的病态和残缺。他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浅薄而庸俗的批评家,也许会获得很多的利益,也许会获得不菲的奖赏,但是,也注定难成大器。
当然,强调文学批评的思维能力,并不是将文学批评降低为按照形式逻辑展开的思维操练,或者降低为纯粹形式主义的批评实践,更不是试图排除价值判断,进而放弃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强调文学批评的思维质量,与强调批评家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并不矛盾。因为,理性思维与价值关怀并不矛盾。毋宁说,高级形态的批评思维必然会关注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那些伦理性和道德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无疑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纯粹性”,而忽略了它的复杂性。我们严重地忽略了伦理精神和道德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和真理:无论是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决定其境界和价值的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和诗人所表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也就是说,有伟大之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才有伟大的文学。
文学的等级,就是作品中人物的等级,或者,准确地说,就是人物所体现的“道德价值”的等级。所以,丹纳说:“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这个道德价值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倘使两部作品以同等的写作手腕介绍两种同样规模的自然力量,表现一个英雄的一部就比表现一个懦夫的一部价值更高。”丹纳将人物分为两个等级:一个是最低的等级,一个是最高的等级;前者一般是“狭窄,平凡,愚蠢,自私,懦弱,庸俗的人物”(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三联书店,2016年,第410页),而后者则是“完美的人物”和“真正的英雄”(同前,第413页)。比较起来,后一类人物的精神价值,无疑要更大一些。毕竟,人类的精神生活更需要那种真正伟大的价值。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思维质量的重要性,也要意识到,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是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和重要标准。司马光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事实上,如果不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那么,在文学评价上也会造成严重后果,人们就很难自信地说“又何失文之足患哉”。萨特的文学成就为什么不宜高估?他为什么不应该被称作伟大的作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就在于他的“德”与“才”之间是不平衡的。
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的“结束语”部分,尖锐地批评了萨特,认为这位存在主义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旺盛的创作力没有体现在一部卓越的著作中,而是断送在哲学与文学的混合体之中”;在政治上,萨特则“常常滥用错误的权力”。(《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杨祖功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40页)作为一个极端形态的利己主义者,他很精明地平衡着各种利益关系,很巧妙地周旋于东西方的对立阵营,很风光地出没于各种权力场域。木心属于为数不多的洞见萨特精神本质的人,所以,批评起他来,就表现出少见的尖锐和不屑:“他的刚愎自用,不可原谅。他是书斋里的政客。……他不是深奥,而是浅薄……也许,正因为萨特没有独创性,所以没有主见,没有一贯的思想。”(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0-911页)萨特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性格上的,也不是缺乏“一贯的思想”,而是缺乏爱的能力和健康的情感,是缺乏良好的正义感,是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他的作品里,有太多的黑暗,有太多的“恶心”,有太多的关于“地狱”的极端想象和冷漠描写。厌恶、蔑视和仇恨,是萨特面对人类和世界的基本态度。
从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感的角度看,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则是武断而错误的。这是一种破坏性质的虚无主义观念。罗洛·梅就质疑萨特的存在主义世界观,认为“萨特式的人会变成一种孤独的、单个的个体,他站在单独一个人反抗上帝和社会的基点之上。”(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萨特的文学创作所存在的问题无疑更加严重。他的写作态度是傲慢而自负的,也是极端而病态的。作为作家,他缺乏发现美和善的能力,缺乏感受爱和表现爱的能力。他只用怀疑和鄙夷的眼光观察人和生活,所以,也就只看得见人们内心的黑暗和龌龊。如果说,经历了战争和信仰崩塌的人们,已经备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和困扰,那么,萨特们的充满消极色彩的存在主义文学,他们的充满恶意和破坏冲动的极端主义写作,则使世界的精神气候更加恶劣,使人们内心所承受的折磨和痛苦更趋严重。
由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甚至助长了中国的“现代派”文学的极端主义倾向和虚无主义倾向,所以,我们更有必要把它当作严重的文化祸患和伦理灾难来反思,当作严重的价值问题和意义问题来反思。在当代的作家群里,萨特式的作家和批评家,岂少也哉!那种充满黑暗、极端病态、令人“恶心”的作品,岂少也哉!
总之,没有真正的专业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没有高水平的思维能力,我们就无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没有自觉的道德价值意识,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有可能失去重心和基础,文学批评就必然会准的无依,尺度混乱,不辨良莠,进而将低级的劣作奉为高级的经典,将三流的作家推为非凡的大师。
文学批评,it's not very easy——并不那么容易。
2022年11月28日,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