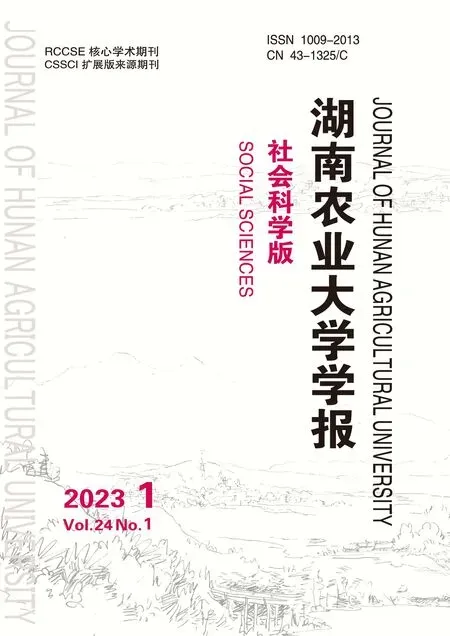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2023-04-07彭宇轩
彭宇轩
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及其完善路径
彭宇轩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专门教育制度替换了工读教育制度与收容教养制度,但专门教育制度仍延续了工读教育制度、收容教养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偏离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不当限制罪错未成年人人身自由、矫正效用不佳,及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应摒弃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防卫优先的管控立场,转而从监护人视角出发,遵循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兼顾社会防卫的基本立场;从封闭管控目的与期限着手,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积极运用社会场域开展社会化矫正活动,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专门教育制度;罪错未成年人;矫正模式;完善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伤人事件频发,社会对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正问题的关注度提升到了新高度。罪错未成年人,是指具有不利于自身健康成长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或违反刑法行为,不满十八周岁的人[1]①。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问题,我国法律规定了刑罚、治安管理处罚、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矫正措施,但上述措施仍难以满足部分情境下的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需求。具体而言,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以达到责任年龄为适用前提,对年龄较小的未成年人无法适用,并缺乏针对性。收容教养和工读教育②,针对的是因年龄较小不宜进行刑罚处罚、依据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原则不宜进行刑罚处罚,和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未成年人。但是,收容教养、工读教育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制度设定较为落后,且存在法律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实践中处于收缩适用范围或停用状态,已难以满足矫正需求。因此,对于因年龄较小或依据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原则不宜进行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或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未成年人,我国尚缺乏有效的教育矫正措施。
在此背景下,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厅字〔2019〕20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强专门教育制度建设的治理策略。为推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矫正制度体系完善在内的一系列涉未成年人政策构想的规范落地,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法》”),专门教育制度吸收替换工读教育制度和收容教养制度,成为承担罪错未成年人矫正职能的主要制度[2]。专门教育是一种专门性教育矫正活动,其针对的是实施了刑法禁止行为,但因年龄较小不宜进行刑罚处罚、依据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原则不宜进行刑罚处罚,和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未成年人。专门教育是在训导、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等矫正措施难以奏效,而刑罚又不宜启用时,阻止未成年人进一步滑向犯罪的矫正措施。依据《意见》《预防法》在适用对象、决定程序、执行主体、执行方式等方面规定的差异,可将专门教育分为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和特殊情形的专门矫治教育。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主要针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且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特殊情形的专门矫治教育,主要针对违反刑法规定,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
在《意见》《预防法》发布后,针对专门教育制度的研究也随之展开。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性、整体性问题,对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的研究缺乏深度、不够详尽。如在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的问题分析中,有研究指出封闭矫正模式过于严厉[3],但未能深入到长时间限制罪错未成年人自由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一核心问题。也有研究指出,封闭矫正模式存在交叉感染导致矫正成效不足的问题,但未关注到封闭矫正模式存在不符合个别化矫正需求和加深标签效应的问题。还有研究认为封闭矫正模式不利于罪错未成年人成长[4],但论述相对简略,未能阐明封闭矫正模式如何阻碍罪错未成年人的成长。在完善策略方面,有研究提出了应加强矫正内容的多元化[5],也有研究认为应加强社会化矫正并加入社会关系修复内容[6]。但相关研究对如何处理好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与社会安全保障,以及封闭管控和社会化矫正活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多有忽视,也未能系统论述如何加强矫正内容的多元化,以及如何开展社会化矫正。
为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本文拟于梳理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现状的基础上,从理念依据合理性、自由限制正当性、矫正效用性、罪错未成年人保护情况等角度分析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的缺陷,继而提出系统化的完善路径。
二、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现状
矫正模式,是指在矫正理论指引下构建的矫正活动基本构架和程序系统[7]。依据主要运转方式的差异,矫正模式可划分为封闭矫正模式、个案矫正模式、循证矫正模式等不同类型[8]。其中,将被矫正人长时间置于封闭场所,主要矫正活动皆于封闭场所中进行的矫正模式,可称为封闭矫正模式[9]。工读教育和收容教养制度采用的即是封闭矫正模式,但在具体模式内容上两者存在一定差异。在工读教育中,工读学校通常采取日常上课期间实行寄宿封闭管理,节假日可正常放假,对不稳定的学生进行假日调控的管理方式[10]。这种矫正模式,在日常封闭管理的同时,也留出了一定的外界接触空间,可称之为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收容教养则采用了全封闭矫正模式,罪错未成年人在整个矫正期限内皆不可离开教养机构。专门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封闭矫正模式。具体来说,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延续了工读教育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特殊情形的专门矫治教育延续了收容教养的全封闭矫正模式。
(一)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延续了工读教育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
通常,矫正方式与管理方式规定是判断矫正模式最直接的依据。但《预防法》《意见》并未对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矫正活动开展方式与管理方式进行明确规定。立法者对一般情形的矫正教育矫正模式的设想,需结合矫正模式发展的承继关系和《预防法》对专门教育制度的父母、监护人探望权规定进行判断。
从历史发展的承继关系分析,工读教育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对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制度具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工读教育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创办的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11],至2020年《预防法》修改前已运转60余年。在此过程中,工读教育制度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已具备了较强的制度惯性。立法者构建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时,需要面对如何处理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制度惯性冲击这一问题。具体处理方法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以法规范形式明确新的矫正模式或对封闭矫正模式进行调整;二是以规范形式明确对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的承继;三是以默示方式表达对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的接纳。《预防法》不明确规定矫正模式的立法策略,实质是以默示方式表达对留有余地的封闭矫正模式延续与接纳。
立法者对封闭矫正模式历史惯性冲击的放任与接纳态度,还可从《预防法》关于专门教育制度的父母、监护人探望权规定中寻得。《预防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专门学校应当与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强联系,定期向其反馈未成年人的矫正和教育情况,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亲属等看望未成年人提供便利”。现代社会强调对人身自由的尊重与保护,个体可以自由地交流与接触,无需其他主体提供便利条件。只有个体处在被拘留、服刑过程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时,其同外界的交流活动方需要拘留所、监狱提供探望便利条件[12]。探望权规定的出现,说明在一般情形的专门教育中,罪错未成年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其无法自由地同外界接触与联系,以至于父母、其他监护人、亲属也难以同其交流,获取其矫正和教育情况。
(二)特殊情形的专门矫治教育延续了收容教养的全封闭矫正模式
在2020年《刑法》《预防法》修订前,承担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矫正职能的是收容教养制度。在收容教养的实施细则《少年教养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不仅有“少年教养人员的亲属或其他监护人每半个月可以到少年教养管理所看望一次”的探望权规定,还有“少年教养人员直系亲属病危、死亡,凭有关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和当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家庭发生其他重大变故,凭原单位或街道(乡、镇)的证明材料和当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由其亲属或其他监护人接送,可以准假回家看望。准假时间不超过七天(不含路途)”的特殊情形请假规定。探望权规定和特殊情形请假规定,都是收容教养全封闭矫正模式的具体展现。专门矫治教育是专门教育中的特殊情形,也以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罪错未成年人为适用对象,其同收容教养具有直接承接关系。立法者在构建专门矫治教育矫正模式时,同样面临如何应对收容教养全封闭矫正模式惯性冲击的问题。不同于一般情形专门教育采用的默示承继,2020年修订的《预防法》明确规定专门矫治教育于专门场所或特定区域实行闭环管理,以明示方式表明了对全封闭矫正模式的延续。
三、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问题检视
专门教育制度采用封闭矫正模式,可避免罪错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罪错未成年人继续受不良环境影响加重恶习。但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仍存在偏离专门教育制度创设初衷、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不当限制、矫正效用不佳,以及无法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等问题。
(一)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的构建理念偏离制度创设初衷
制度初衷即制度创设的最初目的,决定了制度的整体走向。《意见》将专门教育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矫治体系重要步骤,提出“建立科学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矫治体系,努力培养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政策目标。可见,专门教育制度的创设初衷是为了更合理有效地矫正罪错未成年人,矫正在专门教育制度的各类目标中处于优先地位。由此,包括矫正模式在内的各项专门教育制度安排皆应围绕罪错未成年人矫正展开[13]。
从《预防法》对不同类型罪错未成年人规定的处遇措施来看,实施了不利于自身健康成长行为但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错未成年人,仅需接受训导、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参加特定的专题教育、参加校内服务、接受社会工作者或其他专业人员的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等不具有自由限制属性矫正措施。专门教育的封闭矫正,仅适用于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成为是否进行专门教育封闭矫正的决定性因素。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的决定性地位,体现了立法者在构建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时,以社会管理者自居,将社会安全保障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明显偏离了专门教育制度矫正优先的制度创设初衷。
(二)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的不当限制
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身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不法侵犯,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需由法律进行规定。法律通常仅可依据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限制人身自由,或出于约束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个体以维护社会安全的考虑限制人身自由。然而,在专门教育制度中采用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矫正模式,不仅不符合法律责任承担的前提要求,即便是考虑到罪错未成年人的再犯危险而限制其自由也存在自由限制过度的问题。
现代法律责任理论认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14],达到责任年龄具备对自身行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以及受刑能力,是对个体处以剥夺自由处罚的必要条件[15]。在法律责任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2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仅于特定情形方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人才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予行政处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予执行行政拘留决定。可见,我国法律认为未达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不具备接受剥夺自由处罚的能力。而未达责任年龄的罪错未成年人,是专门教育的主要适用对象。因此,法律责任不能成为专门教育制度封闭矫正模式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自由限制的法理依据。
既然法律责任无法为专门教育封闭矫正模式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限制提供法理支撑,那么仅可从社会安全保护的需要中寻取合理性依据。接受专门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通常都实施了违反《刑法》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对其进行管控。由此,为专门教育制度选取封闭矫正模式似乎成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但是,即使是出于社会安全保护的需要,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也存在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限制过度的问题。应当明确的是,出于社会安全保护的考虑进行的自由限制,本质是个体向社会进行的权益让步。同基于法律责任的处罚相比,基于权益让步产生的自由限制的可谴责性相对较低。因而,此种自由限制的严厉程度也不应过高,在保障社会基本安全利益的同时,应尽可能保留罪错未成年人的自由。依据《意见》的规定,专门教育的矫正期限为3个月至3年,罪错未成年人将受到3个月至3年的自由限制。3个月的最低期限,已远超治安管理拘留15天的自由剥夺期限。3年的最长期限,也已超过部分犯罪和部分刑罚措施的最高刑期。这显然不符合基于权益让步的自由限制所要求的低严厉性,是对罪错未成年人自由的过度限制。
(三)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的矫正效用不佳
在封闭矫正模式中,罪错未成年人通常被安排在班集体中进行管理,矫正活动也以班集体为单位开展。以集体为单位开展矫正活动,存在忽视个别化矫正需求和交叉感染问题。这将极大地影响矫正效用[16]。
一方面,封闭矫正模式以集体为单位开展矫正活动,难以适应罪错未成年人矫正的个别化需求。在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应寻找罪错行为生成机制与作用因素,并对生成原因进行针对性矫正。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成因,国内外研究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形成了遗传原因理论、精神障碍论、不同交往理论、紧张理论、标签理论等种类繁多的理论学说[17]。理论研究现普遍认为罪错行为是未成年人自身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多种组合方式,导致不同罪错行为的生成机制差异较大。不同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专门教育封闭矫正模式中,以集体为单位开展矫正活动,必然侧重于罪错未成年人共有的不良恶习,满足多数人的矫正需求。而作为单一个体的罪错未成年人独有的矫正需求,则多被忽视。这将使专门教育矫正仅停留于共性矫正阶段,难以彻底根除罪错未成年人的不良恶习,矫正效果无法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封闭矫正模式还存在加重不良恶习与加深罪错标签的风险。在封闭矫正模式下,罪错未成年人同外界的接触几乎中断,其他社会主体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了解局限于“罪错者”这一身份。同时,以集体为单位开展矫正活动,使不良恶习种类和程度各不相同的罪错未成年人集中在一起,罪错未成年人之间的不良恶习交叉感染将不可避免[18]。在交叉感染的影响下,接受专门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不仅自身不良恶习难以得到矫正,还可能沾染更多不良恶习。长此以往,社会将逐步把专门学校视为罪错行为与不良恶习加深场所,将经过专门教育矫正的罪错未成年人视为更具有危险性、难以纠正,甚至是无法挽救的人。此种牢固的罪错标签,将成为经过专门教育罪错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主要阻碍。
(四)专门教育的封闭矫正模式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
未成年人保护需求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脆弱性、易受侵害性以及成长性等特性[19],产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全过程的保护需求。其不仅包括侵害行为的拒止,还包含健康成长的保障与促进。然而,专门教育的封闭矫正模式并不能适应罪错未成年人的生长规律[20],难以满足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求。
首先,在基本健康需求层面,专门教育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对罪错未成年人看护力度不足与看护不周延的问题。其一,人身安全保护力度不足。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上报的中小学安全事故中,发生在学校的安全事故占到了总数的39%,而发生于家庭的安全事故仅占5%。学校安全事故频发的直接原因是学校看护力度不够。作为专门教育的执行机构的专门学校,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专门学校师资配比通常高于普通学校,但专门学校面对的是人身危险性与不良恶习程度显著高于普通学生的罪错未成年人,对其人身安全的看护难度相对较大。专门学校同样难以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严密看护。其二,心理健康观护的质量不佳。除了人身安全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观护同样重要。罪错未成年人中具有较为严重心理问题的整体比例较高,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所需要的心理观护要求也更高。在专门教育的封闭矫正模式下,外界专业力量难以长期介入,由专门学校工作人员开展的心理课程、定期心理测评和心理咨询等活动通常质量不高。并且,封闭矫正模式使得罪错未成年人和父母、其他近亲属的交流与接触受到较大限制,由此导致对罪错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的亲情陪护的缺失。
其次,在发展需求层面,封闭矫正模式阻隔了罪错未成年人同外界的交往与联系,阻碍了罪错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发展。社会生活作为个体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其直接影响个体人格发展与健全程度。而在封闭矫正模式下,罪错未成年人同社会的连接几乎被完全阻隔,罪错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发展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在个体成长与发展的高速阶段与关键时期,专门教育制度封闭矫正模式直接刨去罪错未成年人社会生活与交往的根基,实质是忽视了对罪错未成年人正常社会生活机会的保障。
四、专门教育制度的矫正模式完善路径
(一)确立监护人视角和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立场
社会管理者视角与社会安全保障优先立场,是专门教育制度延续具有显著缺陷的封闭矫正模式的根源。理念转换也就成为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首要步骤。面对罪错未成年人,我们不仅要关注罪错行为,还要把注意力放在未成年人上,关注未成年人的特性。
现代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多以国家亲权理论和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为理念基石[21]。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专门教育制度也不例外。国家亲权理论,要求国家作为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在父母等一般监护人不能良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国家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22]。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强调涉及未成年人核心利益,关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项制度安排,应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23]。立法者应在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构建中,贯彻国家亲权理论和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具体而言,立法者应从监护人视角出发,在利益衡量时,优先考虑罪错未成年人不良恶习矫正需求。在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理念下,专门教育制度矫正模式的完善,应从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融入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化矫正内容,完善罪错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
(二)调整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管控措施
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过度封闭管控。完善专门教育制度的封闭矫正模式也应对罪错未成年人封闭管控加以限制。此种限制具体可以从调整封闭管控的目的和管控强度两方面着手。
其一,调整封闭管控的目的。在封闭矫正模式中,封闭管控是贯穿了专门教育始终的必要措施。罪错未成年人接受专门教育,必然要受到全过程的封闭管控。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安全,是社会安全保护优先立场下的产物。在监护人视角和罪错未成年人矫正优先立场下,矫正需求优先于管控需求,应减少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封闭管控,尽可能给予其在社会场景中进行矫正的机会。但社会安全保护对罪错未成年人矫正的让步也存在限度,社会化矫正的开展应以不对个人生命健康、重大财产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安全产生威胁为前提。代表社会安全保护的封闭管控的目的,也应当进行调整。封闭管控的目的,不再是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安全,而是为保障个人和社会的重大利益安全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短期管控。在此过程中开展行为约束矫正,降低罪错未成年人对个人生命、健康安全、重大财产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危险性,为后续的社会化矫正打下基础。
其二,调整封闭管控的强度。高强度的封闭管控,是封闭矫正模式管控过度的主要体现。在封闭管控的目的,转为防止罪错未成年人对社会重大利益产生现实性威胁的背景下,封闭管控强度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一方面,在封闭管控期间,应放开对亲情陪护的限制,增加亲情陪护机会与时长。在单纯的会见方式之外增加共同进餐、共同观影等多样化的陪护方式,满足罪错未成年人成长的亲情陪护需求。另一方面,应对封闭管控时长进行限缩。封闭管控不应伴随专门教育的全过程,而应仅在矫正初期适用。在罪错未成年人对个人生命、健康安全、重大财产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已不具有现实威胁时,即可采取白天于专门学校进行矫正学习,晚上由具备管教能力的监护人接回的管理方式。白天矫正学习夜晚接回的管理方式,既可减少专门学校的看护压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课余时间不同罪错未成年人之间交叉感染的风险。
(三)提升矫正科学性与效用性
在经过封闭管控后,罪错未成年人对个人和社会的重大利益已不具有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即可在严密监管下将罪错未成年人置于社会之中开展矫正活动。在社会化矫正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场域贴近生活、资源充分的优势[24],将矫正活动与受损社会关系修复相结合[25],提升矫正活动的科学性与效用性,为罪错未成年人社会复归扫清障碍。
其一,运用社会场域,开展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的巩固与重塑活动。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是个体行为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罪错未成年人通常存在是非观念模糊,道德观念与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重塑是非观念、加强道德观念与法治观念是罪错未成年人矫正的必备内容。在观念巩固与重塑过程中,单一的课堂说教往往效果不佳。在社会化矫正中,应发挥社会场域贴近现实生活的优势,通过旁观治安管理处罚案件、旁听刑事诉讼案件和参观各类学习基地等多元活动,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接触、了解和接受正确的是非观念、道德观念与法治观念。
其二,在社会化矫正活动中融入社会关系修复内容。修复矫正,是以修复教育为主要方向,以受损社会关系修复为途径,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新获得社会接纳与认可[26],从而实现恶习矫正同社会回归良好融合的矫正方式。专门教育中的社会关系修复,可分为同被害人关系的修复和同社区关系的修复。同被害人关系的修复主要出现于伤害行为、侵财行为等有直接被害人的罪错行为的矫正中。同被害人关系的修复方式,不仅包括对直接损害的赔偿,还包括通过座谈会议增进罪错方与被害方的相互了解,解除相互间的偏见、误会。同社区关系的修复不仅适用于直接侵害社区利益的情形,在有直接被害人的罪错行为矫正中也需要修复罪错未成年人同社区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可通过社会服务活动对社区进行补偿。另一方面,社区圆桌会议也是修复罪错未成年人和社区关系的良好方式。通过社区圆桌会议,可增进社区主体对罪错行为发生前因后果和罪错未成年人自身情况的了解。通过社区圆桌会议,既可减少社区主体基于对事件起因经过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慌效应,也可通过罪错未成年人的悔过和致歉,化解社区主体对罪错未成年人的道德谴责,减轻罪错未成年人身上的“罪错者”标签,为其回归社会打下基础。
其三,集合社会资源,开展职业培训。通常来说,接受专门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多数都未能很好地适应普通教育,继续升学较为困难[27]。若无一技之长,罪错未成年人在结束专门教育后难以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极易在生存压力下再次实施罪错行为。职业培训可通过提升罪错未成年人的职业知识、技能和素养,减少其在回归社会后因生存压力再犯的可能性。从以往实践状况来看,封闭矫正模式中的职业培训效果不佳。多数矫正机构并非专业的职业培训主体,所具备的培养能力较弱。在社会化矫正中,可通过吸纳专业化和多元化的职业培训参与主体,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发挥社会性矫正场域同社会生活的高贴合度优势,将职业培训同社会职业活动相结合,促进所教授职业技术知识向职业岗位技能的转化。另一方面,应充分吸收不同职业领域的培训机构参与罪错未成年人矫正活动中的职业培训,提升职业培训的多样性与前沿性。
(四)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其一,完善封闭管控中的罪错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在监护人视角下,封闭管控的强度虽被进一步限缩,但如何保障罪错未成年人权益的问题仍然存在。对此可从加强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两方面着手。
于内部管理方面,应制定契合罪错未成年人保护需要的专门教育封闭管控标准。具体来说,专门教育封闭管控的标准应包含以下内容:1)结合可调动的力量和罪错未成年人看护需要,明确科学的师资、安保和心理辅导专业人员配比,保证在专门教育封闭管控中有充足的看护与心理疏导力量,降低罪错未成年人安全事故和心理问题的发生概率;2)明确封闭管控的硬件设施标准,保证封闭管控的硬件设施,满足罪错未成年人良好生活的需要。于外部监管方面,应进一步完善《预防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监督制度。具体而言,可依据封闭管控规模的大小和监督需要,分别采用定期进校巡查与派出长期驻扎检察官监督两种方式。对于封闭管控规模较小的,可由检察机关定期派出人员巡查,接收罪错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意见。对于封闭管控规模较大的,可在条件允许时派出长期驻扎检察官,监督封闭管控活动。
其二,完善社会化矫正中的罪错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机制。首先,应强化社会化矫正中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监管与看护。在社会化矫正活动中,应为罪错未成年人配备专门的看护人员。看护人员的职责是避免罪错未成年人在社会化矫正中同不良环境接触,并避免罪错未成年人受到被害人的报复。其次,应加强罪错未成年人特别隐私权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特别隐私权,是将罪错未成年人的罪错事实、个人信息以及其所接受的处置情况,作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秘密[28]。特别隐私权,对罪错未成年人摆脱罪错标签,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9]。虽然《预防法》规定应对接受专门教育罪错未成年人的档案信息进行封存,但在案件旁观和旁听活动、社区圆桌会议、职业技能培训等社会化矫正活动中,各参与主体都有可能知晓罪错事实和罪错未成年人个人情况等信息。仅通过档案信息的封存,已难以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特别隐私权的保护。因此,应于《预防法》中明确规定,任何参与矫正活动的人,都负有对罪错行为事实、罪错未成年人有关的信息的保密义务,并规定违反保密义务的法律责任。
其三,加强亲职教育,提升监护人监护能力。亲职教育,又称父母教育,是针对父母的教育活动,旨在提升家长监护能力、培养合格称职的好家长[30]。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产生同监护不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31],多数不良恶习都是趁监护空隙侵染未成年人。经过专门教育的罪错未成年人若再次处于监护不当境地中,极易再次沾染不良恶习,继续实施罪错行为。在矫正后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护,是避免矫正后罪错未成年人再犯的关键。对此,在专门教育过程中,也应加强对父母和其他监护人进行监护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升监护人的监护能力,为罪错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监护条件。
注释:
① “罪错未成年人”最初为理论概念,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18—2022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所采用,并逐步为其他政策文件接纳,成为理论研究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共同认可的概念表述。
② 收容教养,是将实施了刑法禁止行为且情节严重,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罚处罚的罪错未成年人,置于少年教养所进行管教的矫正措施。工读教育,是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违反刑法但情节较轻的罪错未成年人,置于工读学校进行半工半读的矫正措施。通常来说,收容教养针对的罪错未成年人危险性较大,管控措施也更为严厉;工读教育针对的罪错未成年人危险性较小,管控相对宽松。
[1] 肖姗姗.“罪错未成年人”概念选择与适用的理性证成[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4):60-71.
[2] 周颖.专门教育定义的思考——以中美比较为视角[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3):126-136.
[3] 刘双阳.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触法未成年人处遇机制的检视与形塑[J].云南社会科学,2021(1):92-99.
[4] 吴立志,樊晓萱.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3):1-7.
[5] 周颖.回应型立法理念下专门教育立法的走向——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为视角[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3):11-19.
[6] 李川.从教养式矫治到修复式教育:未成年人矫治教育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31-139.
[7] 王敏.矫正基本原理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129.
[8] 周勇.罪犯教育矫正模式的创新与发展[J].中国司法,2013(3):55-59.
[9] 张建伟.监禁权专属原则与劳动教养的制度困境[J].法学研究,2008(3):159-160.
[10] 刘燕.从工读学校教育历史发展探究其时代价值[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8(3):4-15.
[11] 石军.中国工读教育史60年:回顾与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17(4):116-121.
[12] 安文霞.中国罪犯家庭支持系统面临的问题与完善建议[J].中国监狱学刊,2021,36(4):5-14.
[13] 王传敏,李子熙.我国专门教育制度的由来及未来制度建构[J].中国司法,2020(9):105-111.
[14] 屈奇.从自由刑到社会化行刑过渡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17(3):246-253.
[15] 姜敏.联合国成员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40(2):89-100.
[16] 顾泠涓.专门矫治教育的权利保障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展开[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1(3):67-78.
[17] 吴宗宪.西方少年犯罪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1:535-539.
[18] 许晓娟,张京文.论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中被忽略的问题[J].法学杂志,2013,34(9):110-116.
[19] 梅文娟.少年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54.
[20] 沈颖尹.关于《刑法》第十七条的审思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J].北方法学,2021,15(3):151-160.
[21] 赵若辉,姚学宁.完善我国内地非亲权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之探究——以澳门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为镜鉴[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3):132-140.
[22] 姚建龙.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J].法学杂志,2008(3):92-95.
[23] 肖姗姗.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兼论对我国少年法的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9(9):70-80.
[24] 俞国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模式的建构——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2(04):77-83,157-158.
[25] 白星星,袁林.未成年人行为矫治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构建[J].北京社会科学,2022(2):74-85.
[26] 刘双阳.从教育矫正到损害修复:社区矫正教育矫治模式的重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0(2):44-51.
[27] 贾洛川.中国未成年违法犯罪人员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28.
[28] 高维俭,杨新慧.论少年特别隐私权——一项源于刑事法领域的拓展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24-137.
[29] 黄明儒,张继.涉罪未成年人救赎之路探究——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为切入点[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3):41-55.
[30] 吴宗宪,张雍锭.未成年缓刑犯社区矫正中强制亲职教育的制度构建[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8):185-195.
[31] 鞠青.中国工读教育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3.
A study on the rectification mode of special education system
PENG Yuxua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Therevised in 2020 replaced the work study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reception education system with a special education system, but the special education system still continues the closed correction model of the work study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reception education system. The closed correction model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system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deviating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ystem of priority of correction, improperly limiting the personal freedom of the delinquent juveniles, poor correction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 to meet the protection needs of the delinquent juveniles. To improve the correction mod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system, we should abando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osition of the social administrator's perspective and the priority of social defense, and instead follow the basic position of giving priority to social defense in the correction of delinquent juveni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rdians; Adjust the intensity of closed control from the purpose and duration of closed control; Actively use the social field to carry out social correction activities,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ness of correction activitie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linquent juveniles.
specialized education system; delinquent juveniles; correctional model; improvement path
D926.8
A
1009–2013(2023)01–0086–08
10.13331/j.cnki.jhau(ss).2023.01.010
2022-08-17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C0831800);司法部一般课题(21SFB2013);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科研创新课题(FXY2022017)
彭宇轩(1994—),男,湖南株洲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