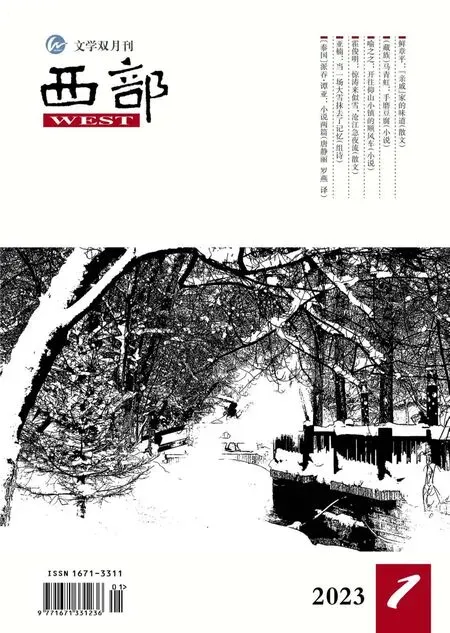再次相遇
2023-04-07维吾尔族安沙尔丁沙地尔丁
(维吾尔族)安沙尔丁·沙地尔丁
在七十七岁生日后的第二个月里,我正在整理门前的小花园,花香四溢,芬芳馥郁。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蝴蝶呼扇着翅膀,落在玫瑰花上。阳光灿烂,我拄着拐杖,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一只蓝色的蝴蝶落在我肩上,过了许久才飞走。胸口一阵刺痛,我捂着胸口瘫倒在地上。家人发现后,将我送进了医院。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我已经没有恐惧,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敬畏人生如戏,敬畏生命如梦。脑海中回想起那段对白,我问她很远是多远,她说远到回不来,也不会再见面。我痛苦地呻吟着,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抽泣声。
人生的每一幕如同电影画面,不断在我脑海里划过。第一次接吻,第一次离家出走,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有孩子。我努力地回想她的容颜,她的面孔却如此模糊。我慢慢地闭上双眼,恍惚听见她在呼唤我的名字。
一束阳光斜洒进来,我缓缓睁开眼睛。周围的一切那么熟悉,我恍然大悟,这不是我童年时期的房间吗?屋外的鸟叫声越来越清晰,鱼缸中的小鱼也慢慢摆动着尾鳍。微风吹过,桌上的本子被风吹开,“德恩”两个字清晰地写在首页。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一个小男孩径直走到桌前坐下。自来卷的头发、麦色的皮肤,蓝白条纹衬衫搭配卡其色的短裤,黑色的皮鞋。这不是我吗?原来这是我脑海中的回忆,可就像是在现实中。“德恩!德恩!”楼下孩童的呼唤声转移了我的思绪,我将头伸出窗外,在一群小孩中一眼就认出了她——穿着碎花短裙的小女孩,莱拉。
那年我们七岁,青梅竹马。我父亲和她父亲曾在同一家工厂工作,我们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家也住在同一条街道上。母亲乐意我和她一起玩耍,奶奶还经常念叨:“他俩真是天生一对啊。”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形影不离。她很漂亮,像天使下凡。她的眼睛像一汪清泉,我似乎可以看见她眼神中溢出的爱意。她短而蓬松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暖棕色,白皙的皮肤像是窗纸吹弹可破。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感觉。偌大的公园里,除了她,其他都模糊不清。她穿着鲜红色的裙子,风儿轻抚着她的脸庞,路边的野花为她绽放,掠过天空的鸟儿也为她歌唱。我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心脏咚咚地跳动着,可能是在为她打节拍。我多么希望时间能静止,让这一刻变成永恒。我们在夕阳下奔跑追逐,累了就躺在草坪上仰望天空。秋风吹起树叶和枯萎的花瓣,在空中飞舞。我们静静地望向天空,似乎天空才是我们的归宿。
转眼我们来到十七岁。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因为她是学校里的大红人,自卑的我不敢向前迈出一步。也许青春就是如此,情绪忽上忽下,漂浮不定。我很爱她,可我们没能在一起,虽然不舍,但毫无办法。直至今天我都在思考那个决定是否正确。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跟她相约在公园散步。夜空繁星点点,夜莺在树丛中鸣叫,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回应夜空中的星星。我看着她那深邃的眼眸,大脑中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将自己的爱意说出口。过了很久,她看我没有说话,就向前走去。我错失了这个机会,也错失了我的整个人生。后来,我尝试着找过她,可她一直躲着我。后来看到她和她的男友,我才明白,暗恋是属于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是她来时在路边随手摘下的野花,片刻后枯萎了就被撇到一边。我是飞机舷窗外努力追赶她的极乐鸟,直到毙命的前一秒都没能看到她的容颜。我是浩瀚星河里与她相隔几光年也要燃烧生命的末日行星,想用微弱的光芒得到她瞬间的关注。我是夜空中一闪而过的烟花,尽情地展示自己只为看见她淡淡的微笑。我是操场旁永远不会倒下的白杨树,静静地看着她不求珍惜。我是宿舍楼旁断了根胡须的狸花猫,拼命地撒娇为博得她的同情。我是前些日子义无反顾从万米高空冲向她的雨滴,轻轻地落在她的肩头,向她诉说着我的爱意。可她看不见我。
几个月后一个晚秋的早上,天气很冷,天空雾蒙蒙的。街上行人很少。我穿着缝线开裂的羊绒夹克,戴着那顶老款的贝壳帽,踩着新买的牛津鞋,裹着厚厚的条纹围巾,路过街角的面包店。扑鼻的香味让我久久驻足,翻了翻外套的口袋,又翻了翻裤子的后口袋,仅翻出几枚硬币,犹豫再三,还是买了一块全麦面包。结完账转过身去,我看到了她的身影,可我不敢认,我怕我会控制不住地扑向她。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去找她。刚转过街角,就看到不远处她和一个棕色头发、脸有雀斑的男生卿卿我我、搂搂抱抱。我迅速躲在墙后不敢出声,直到他们走远。我移步至无人的街巷深处,默默抽泣。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闭上眼睛就是她看向我时的模样。老天爷啊,这就是你所说的爱情吗?
那年我们二十七岁。因为祖国的召唤,我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头发修剪得干净利落,我穿着军装,脚上是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父亲抚着我的肩,仿佛看着年轻的自己。临别之际,我捧着一束玫瑰和她相约在初见时的公园。她依然那么美丽。那天我们不那么尴尬。她让我照顾好自己,我红着眼哽咽着说出了再见,并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
隔天我上了部队的汽车,前往了新兵连。过了许久,我们在一片戈壁滩上下了车。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些许兴奋和紧张,死气沉沉的戈壁滩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正调侃着这里的环境,突然有个磁性的声音打破了压抑的氛围。“开心点,小伙子们,这里至少没有该死的蚊子。”我们齐刷刷地回头望去,只见一人带着副官向我们走来。看到他的军衔,我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指导员。他个子不高,满脸胡茬,古铜色的皮肤,左脸上有一条四五厘米长的伤疤,笑起来满脸褶皱。当然,他很少笑。新兵训练就此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战术安排和体能训练让我们倍感煎熬,战友们都想去前线杀敌,没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三个月后,我们被分派到各个连队,我和几位新兵战友被分到了A 军某合成旅第一突击团三营机动二连。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连长竟是新兵连时的指导员,这让我们倍感亲切。听老兵说他曾三次负伤,荣获“勇敢骑士”勋章。老兵的话,让他在我们心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某天早晨,连队紧急集合,准备悄无声息地穿越战线潜伏到敌人后方。连长让我带领小分队从代号为“黑色肿瘤”的森林穿过,阴森的森林里传出几声鹿鸣,我们俯身隐蔽屏住呼吸,握着枪的手在不停地出汗。我打开父亲送的怀表,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表盖内侧被我嵌上了她的照片。过了很久我们才起身前行。就当我们以为是虚惊一场时,突遇伏击,炮弹像雨滴般落下。身后是她,是家人,更是祖国,这三句话瞬间占领了我的意识顶峰。我红着眼冲向了敌人的阵地,手指不断地扣动着扳机。突然眼前一黑,耳边战友喊出一声“卧倒”。我努力地想睁开眼睛继续冲锋,可怎么也没有办法睁开眼。
一片黑暗之中,突然有一道光落下,照在一朵沾着血渍的玫瑰花上。我拾起玫瑰花,抬头的瞬间似乎看到了她的身影,本想奔向前去,可剧烈的疼痛使我回到了现实——睁开眼睛,只见白色的天花板,吊瓶中的不明液体正在滴入血管。我口鼻中插着供氧的橡胶管,头昏脑胀。我想起身观察,却似乎有点不对劲,我的右臂很痛,像是被什么撕裂般又带一点灼烧的感觉。这时看见母亲和父亲走到我身边,母亲泣不成声地将头埋入父亲的怀里。我努力发出声音想问些什么,可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看着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我那条疼痛难忍的胳膊,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失去了一条胳膊。就这样我们又一次错过了相遇。
那年我们三十七岁。我在这个城市的一角拥有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我被分配到邮局,有了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薪水不多,但足够我一个人开销。我终于有勇气迈出下一步了。
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射在枫木地板上,房间格外温暖明亮。微风吹拂着奶白色的窗帘,屋外的桂花树沙沙作响,香气四溢。蓝色的西装整齐地摆放在床边,白色镶金边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写请柬时用过的钢笔,笔尖的墨水似乎还没来得及干透。旁边就是订婚用的戒指,戒指内侧刻着我和未婚妻的名字。时钟在摇摆,时针停在了上午十一点零七分。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安逸的时刻,我缓步走到电话前,犹豫片刻之后拿起了电话,问道:“喂,哪位?”对面传来一声叹息后,缓缓发声:“德恩,我是马修。我已经把请柬送过去了。”原来是马修,他是我多年的好友,也将是我婚礼的伴郎。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什么事情都一起经历过。童年时和他一起捅马蜂窝,被蜇得满身是包。少年时一同被老师赶出教室,在城里逛了一天,害得父母跟着所有的老师一起满大街找我们。在战场上就是因为他舍命相救,我才捡回了一条命。“嗯,我知道了。你送去时她没说什么吧?”我不安地问,心里却想要一个顺心的答案。“没说什么,我找到她时她正埋头工作呢,就说了句谢谢。”我心中的遗憾又多了一点。“哦,那就好,没说什么就好。”我口是心非地回答,随后就挂了电话,转过身坐在了床头。看着床头柜上的布偶,我不由回想起她的模样。她是什么模样来着?是短发还是长发?是高还是矮?啧,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算了,不想了,也不敢再想了。
我尝试过忘了她,可无论怎么做,她始终都浮浮沉沉地在我的脑海里。月圆时分,耳边偶尔会传来曾经的誓言。后来,我发现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安排,就真的不会再见了。我曾经以为我们会是地久天长的那一对,可不曾发现人心的善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好奇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从来没有想过以后会发生的一切。大概人和人还是最初相识的时候最好。我们会各自完成学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努力打拼,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屋,步入婚姻殿堂,养一只猫咪,生一个宝宝,在夕阳下相拥一生。可我们失散在这错位的时空中。或许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错与对,只不过是相遇的时间不同罢了。我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错误的身份,相识在这个错误的时代。
我和马修赶往婚礼举办地。马修边开车边递给我一支烟,吐槽道:“怎么现在一个婚礼都有彩排?真是的!”我笑了笑,没有吱声,看了看他满是胡茬的脸,他的黑框眼镜,他那泛着油光的额头和杂乱的头发。看着他这般模样,我就知道他昨天晚上干什么了。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哎呀,酒是个好东西呀!能让人忘却一切。”他通过后视镜瞟了我一眼,我转过头去看着窗外掠过的高楼大厦。电台里正放着皇后乐队的单曲,车窗外的喇叭声似乎也融进了音乐里。我闭着眼倚靠在座位上,回想曾经发生的一切。
我要结婚了,新娘不是她。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命运。咎由自取也罢,生不逢时也罢,结局就是这样了。如果当时再温柔一点,再心软一点,再多在乎她一点,那么整理嫁衣、梳妆打扮的就是她。可惜当时不懂事,做事不计后果,年轻气盛嘛。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和她再次相遇的那场生日聚会,马修也在场。也许她不记得我这个童年玩伴和懵懂年少时的追求者了,可我永远都记得她,记得她的所有。
马修凑到我耳边说:“还想再次错过吗?你就不想试试?四年前你没勇气,这次的机会可得好好把握。”我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角,在朋友的怂恿下,我鼓起勇气准备邀请她跳舞。我忐忑地走了过去,支支吾吾地说出了请求:“你好,那个……能不能和你,呃……跳个舞?”她转过头笑着看了看我,又转过头看了看身旁的朋友,最后还是站起来了。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进了舞池。我搂着她的腰,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跳起交谊舞。舞池里摇曳的灯球抖落光辉,她月牙状的眼睛死死勾住了我的魂。音乐似乎越飘越远,我仿佛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音乐停了,我们站在原地,似乎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我凑到她耳旁轻轻地说了句“谢谢”,她微笑回应。回到座位上,马修打趣我说:“看看啊!是谁来了?是我们最美的情郎!”众人哄笑,可我的脑子里还想着她,想着她的笑容,她是那般完美。在马修和她朋友的撮合下,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了与她的故事……
“到了,快醒醒!上帝啊,明天你就要结婚了,还睡得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的婚礼呢。你再不起来我就把你的义肢锁到后备厢里!”马修埋怨着,拍打着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看到一排排气球和装饰用的丝巾挂在大门口,打开车门走了下去。“布置得不错嘛,还得是马修你找的人。”我摘下墨镜,走到场地门口。“那当然,不看看是谁安排的!”马修得意地说道。大厅里桌椅摆放整齐,舞台旁放着我和未婚妻的巨幅画像。我双手抱胸站在会场中央,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本来是喜事,我怎么会开心不起来呢?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吧。
晚上,我打开台灯,拉开抽屉,拿起那封为了挽留她写下的最后的情书:
亲爱的,原谅我当时的天真烂漫,认为我们会有很美好的结局。可惜的是,我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却没有收获爱情的运气。那些回忆像破损的放映带,断断续续,朦朦胧胧。我们一起许过的愿,一起看过的电影,一起游过的风景,在我的脑海中像走马灯。
最近我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感性一点,做出不同的选择,多看看你的优点,结局是否会有所改变。可我知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我羡慕雨可以抚摸你的肌肤,我羡慕风可以为你整理衣边。眼角的泪珠闪烁,犹如夜空中的繁星。欢乐似乎与我无关,孤独也没有和我阐明身份。我走在洒满月光的路上,似乎尘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眷恋。我常常抱怨生活的不公,人生的跌宕。黄粱一梦也好,为情所困也罢,就这样了。可是手上的指南针永远指向一个方向。顺着那个方向走去,我看到的依然是你的身影。有人说我错过了落日余晖,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我默默向上苍祈祷,祈祷你不会因为与我的分离而误入歧途,不会变成别人口中的坏孩子。愿你在我不在的寒风中裹紧外套,在我不在的夜路上注意安全。希望你的下一个爱人能无私奉献,也希望你可以永远忘了我。
新婚当天来了很多亲朋好友,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也来到了现场。年轻的俊男靓女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孩子们在欢乐地追逐打闹。随着婚礼进行到高潮,我单膝跪地深情地望着我的未婚妻,将婚戒缓缓戴在她的无名指上。面前的新娘,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没她好看,但也不差。我牵着新娘的手,郑重地念着誓词。余光看到站在远处的她红了眼眶。犹豫片刻后,我大声说出了“我愿意”。
前来贺喜的有同事,有挚友,也有我们连队仅剩的那七个战友。母亲的眼里泪水在打转,父亲正接受着来客的祝贺。我穿着黑色西服,内搭白色衬衫,将头发梳成三七分。夕阳照在我身上,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我。马修凑过来小声问我有没有什么遗憾。我笑了笑,说道:“有什么好遗憾的啊,爱过了就不遗憾。”转过头,却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背影。
我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她的到来让我在这个世界有了新的念想。我们给女儿取名莱拉。是啊,对她的遗憾和愧疚随着相同的名字,转移到了女儿身上。我带着女儿走在游乐园的路上,就像当年牵着她的手走在游乐场里。那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卖气球,我选中了一只蓝色的气球,也许是童心未泯吧。我给女儿也买了一只蓝色气球,就像当年买给她一样。看着在旋转木马上玩耍的女儿,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和她一起玩耍的日子。我放飞了这只蓝色气球,可能是由于没有抓紧,也可能是为了让她看见。我看着渐行渐远的气球与天空融为一体,仿佛看见了她的身影。
那年我们四十七岁。我失业了。妻子扯着嗓门抱怨着:“就只剩下三块面包了,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当初怎么没想到会有这般窘境?”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的。儿子走过来说道:“爸爸,我们真的没有钱了吗?”我吻了吻儿子的额头,之后拿着那件灰色的大衣出了家门。
大街两旁有很多等待招工的人,工头一般只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我尝试着去找份像样的工作,却无济于事。谁会录用一个即将踏入知天命之年的小老头呢?何况我还是个只有三个肢体的怪物。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想起了她最喜欢花。靠着仅存的一点积蓄,我在古城的广场边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我干不了什么体力活,但插花技术还是不错的。无事时坐在店口的摇椅上,阳光照着我黝黑而满是伤疤的脸庞,我看着过往的人群,感叹着时间的无情。突然想写点什么,于是我拿出了她当年送给我的记事本。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秋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她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每天在人来人往的古城中,看着一朵朵盛开的玫瑰,就会想起她。我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但那些玫瑰都化成了她。
那年我们五十七岁。
花店经营得很好,但各种疾病接踵而至。一个初冬的雨天,雨下得很大。路面的积水映射出城市的碎片,恍惚间不知天上飘下的是雨还是雪。妻子走到我身边说:“早点关门吧,今天大雨,不会有客人来了。”她低下头叹了口气,转身将“正在营业”的牌子拿下来。雨还在下,呼出的气变成了雾。妻子和女儿走在前面,我独自跟在后面。到家后,我坐在老旧的沙发上,不停地咳嗽,似乎要把肺咳出来。儿子走到我旁边,握着我的手说:“爸爸,您就别硬撑着了,去医院看看吧,别为花店而毁了身体。”儿子的眼神像是责备,也像是关心。我搪塞着答应下来。
隔天,我独自一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来到了医院。我不喜欢医院,更不喜欢医院里发生的故事。我坐在走廊尽头,消毒水的味道让我感到不适。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孤零零的我。我始终惦记着花店里的玫瑰,害怕它们没人照顾。等了很久,护士才叫到我的名字。我拿着检查结果报告单,蹒跚着走入诊室。医生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皱着眉头,嘱咐我不要操心,最好不要在这把年纪还过度劳累。
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将花店关了。
那年我们六十七岁。
我带着孙子去了一趟老战友马修的家,他家在离县城五十公里的乡下。我牵着孙子的手上了汽车,坐在了有条条裂纹的仿真皮座椅上。汽车不一会儿就开出了城。城外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麦田,青色的麦浪如诗如画,孙子好奇地看着路边的一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提示我们终于到了,马修已在路边等候多时。我激动地和马修握手拥抱,热泪盈眶。一阵寒暄后,我们一起走到了他家的院子。
院子很干净,我们坐在一起享用着饭前点心。他突然皱着眉头提到我们曾经的连长:“他上个月已经去世了。”我心里一阵悲凉,感慨着生命的脆弱和时间的飞逝,内心深处恐惧着死亡。马修从怀里掏出的信件,打破了我的沉思:“这是关于莱拉的信,是连长妻子给我的。”我疑惑地问道:“莱拉?莱拉的信为什么在连长那里?”马修微微摇摇头说:“命运啊,命运,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老连长竟然是莱拉的亲哥哥。在莱拉很小的时候,他就去当兵了。”我迅速从他手中拿过信件。
莱拉写给哥哥的信里记录着那年所发生的一切,飘在心头的那片乌云也慢慢散开,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哥哥:
他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我知道已无法挽回,但还是止不住地难过,我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
结婚请柬就放在桌子上。床上是一堆沾有泪水的纸巾,电话铃声一直在响,几个空酒瓶放在地上,我双眼含泪蜷缩着坐在墙角,不敢去面对当时那个错误的选择带来的沉痛后果。时钟滴答,时针停在了午夜十一点零七分。
“砰砰砰……”一阵强有力的拍门声响起。“莱拉!你开门啊!你别吓我!快开门!”大声喊话的人,是黛西。她是我最要好的闺蜜,我们平时形影不离。她肯定是知道了请柬的事,怕我一时想不开,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黛西一进来就埋怨我:“你怎么搞的?大不了去闹婚啊!别哭哭啼啼的!给我振作起来,没他你活不了是吧?”我沉默不语,心中的愧疚感让我无法作答。我不停地抽泣,眼泪止不住地流。黛西抱着我,安慰着我说:“都会过去的……”
上午我在工作,同事走过来说有人找我。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马修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什么。我走过去打了声招呼,他留下请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他为什么是这种态度。我站在原地,深呼了一口气,打开了请柬。封面上写着他和他未婚妻的名字,中间还画了一颗爱心。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这一切。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却眼泪横流。
“他很爱我,我知道。”
“那你怎么还……”
“我当时以为他只是想玩玩。”
多年的内疚始于那段对话,我本来不打算告诉妈妈那件事的。阴差阳错之下,我还是给妈妈讲述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经历。妈妈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我回到卧室看着时钟一点点转动,开始回想着我和他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最后一张合照、最后一封来信。巨大的愧疚感突如其来将我淹没。
还记得最后一次跟他约会,是在一个咖啡店里。他很高,也很帅。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当天发生的一切。我知道那天发生的所有,知道我们坐在咖啡店的哪个位置,知道我们点了什么咖啡,就是不知道他当时在说什么。我本来很喜欢他,也不知道是上天的考验,还是命运的安排,在和他交往的时候,和朋友走在街上,总会有男生来问我要联系方式,会有朋友要给我介绍帅哥。可能当时还小,我们之间又太熟悉了,我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和陌生的人。我随便找了个理由,稀里糊涂地和他提出了分手。我起身离开时,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双眼无神地看着我,很严肃地说了一声“再见”。
后来不知道是好奇还是内疚,我会偷偷去他工作的地方看他,会向朋友打听他的状况。可能是自欺欺人的表现吧。我尝试着去和别的男孩相处,甚至于置身酒精的海洋。明明是我提出的分手,明明是我希望离开,明明是我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到头来却忘不了他。我开始害怕,害怕他的出现,害怕关于他的一切。当朋友放他曾经放过的歌时,我会起身离开。当听到关于他的话题时,我会避之不谈。甚至闻到和他衬衫上相似的肥皂味,我都会像被巨石压住一般无法呼吸。
我想过道歉,一想到自己曾经给过他的伤害,就害怕自己会被他像我对待他那样伤害。我后悔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受到报应。渐渐地,我不敢睡觉,怕他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将我撕碎。我向黛西诉说,想尽力将恐惧消除,可黛西的一番话再次让我沉入谷底:“他好像有新欢了,是那个追了他三年的女孩子。”我不想打扰他现在的生活,只能将无法囚禁的愧疚和遗憾写在字里行间,把他藏在一张张信纸里。直到他结婚的那一天,信件都没能送到他手里。
那天晚上,我抱着酒瓶,含着眼泪,打开了一封写给他的信:
“每个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失去一些东西,等到发觉时,它早已不在身旁,只留下一段段回忆。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虽然我没能珍惜。我还记得那个新年夜,在缤纷的烟火下看着你的侧脸。此刻,我只能点燃仅剩的几根蜡烛,我们的爱就像这蜡烛一般燃烧殆尽。每当我只身一人时,我都会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做?每当我路过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咖啡馆,我都会进去坐一会儿,期望着在这里能制造偶遇。坐在窗边,刚刚还阳光明媚的天空,现在已乌云密布。天空中的片片乌云就像是我心中的阴影,赶不走扫不尽。背包上的布偶就像你我的爱情,早已褪色,可我还是会把它挂在背包上。对你的想念,总会变成呆滞的目光。时间一久,就会变成苦涩的泪水。倘若哪一天我们在时间的拐角相见,只想和你说一声:谢谢。”
哥哥,现在想起他,回忆起和他的点点滴滴。发现他是真的爱我,想和我有个未来。可惜当时太小,只想着挥霍青春,他的真心我没能珍惜。在黛西的劝说下,我放下所有回忆,准备穿上最美的礼服,画上最精致的妆容,带着最真诚的祝福,在他婚礼当天勇敢赴宴。婚礼那天,看着精心布置的婚礼现场,我百感交集,这是属于新娘的风景,而我只是个嘉宾。西装革履的他依旧帅气,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美丽动人。我站在人群之后,看着他和新娘不由得红了眼眶。等待片刻后,我悄悄地说了一声“我愿意”。
莱拉
饭后我们出门散步,走过一段田间小路,到达有名的蓝色海岸。我抱着小孙子坐在海边的摇椅上,分享着一块面包。摇椅吱吱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微风拂面,我呆呆地坐着冥想着一生的所有选择,也在思考着那封信的内容,目光所到之处皆是她的影子。孙子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全麦面包,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夕阳西下,海水波光粼粼,彩霞满天,海鸥鸣叫着飞向远方。我思索了一辈子的选择,不知是否正确。
很多年之后,我们的尸骨会化为尘土,共同滋养着大地上的鲜花和树木,一起经历四季的轮回。我们会再次相遇。
现在,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