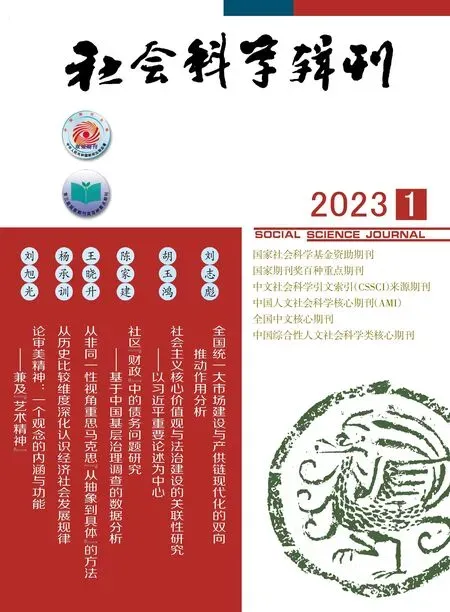元宇宙空间的虚实匹配及其社会性延展
2023-04-06时立荣
时立荣
随着虚拟现实、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元宇宙逐渐从科幻小说中的词语转变为影响现实世界人们交往沟通方式的客观存在。虽然元宇宙概念刚出现时颇具争议①尽管国内外元宇宙发展势头迅猛,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元宇宙是概念炒作〔1〕、新式乌托邦〔2〕,或者它只是一个由控制我们生活并将我们推向“消费黑洞”的力量创造的幻想世界〔3〕。,但技术突破、资本追捧和政策驱动②资本市场表现方面如元宇宙第一股Roblox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Facebook宣布更名为Meta,英伟达(NVIDIA)的“实时仿真与协作平台”(Omniverse)正式上线以及百度发布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希壤”。政策的推动肯定了元宇宙的“合法性”: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列为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之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目前已有22个省市在“十四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元宇宙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中提及元宇宙,或出台了元宇宙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其中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于2022年8月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数字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让人们逐渐看到构建虚拟数字世界的可能性。元宇宙正在成为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虚拟空间之间关系、个人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未来数字图景。
一、元宇宙空间的二重性
元宇宙空间的二重性是指元宇宙具有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映射的性质。元宇宙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独立空间,没有现实空间就没有元宇宙空间。因此,元宇宙的二重性是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去中心化交往关系和社会垂直分层体系之间所做的现实回应。
(一)对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致性认识
关于元宇宙的概念与应用场景,业界与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均认同元宇宙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存在融合、互补和互动关系。苹果CEO库克认为,元宇宙是由增强现实技术所构建的虚拟世界。〔4〕风险投资家马修·鲍尔将元宇宙定义为一个由实时渲染的三维虚拟世界组成的大规模、可互操作的网络,可由有效的、无限数量的用户同步和持续地体验,具有个人存在感,并具有数据连续性,如身份、历史、权利、物品、通信和支付。〔5〕扎克伯格将其描述为一个由无数相互关联的虚拟社区组成的世界“虚拟环境”,用户使用虚拟现实眼镜,通过应用程序沉浸其中,满足人们“见面”、工作和娱乐的需求。〔6〕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提出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社会、经济、文化、社交、身份等生态上密切融合,并允许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环境编辑。〔7〕
可见,从技术层面讲,元宇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映射现实世界的数字虚拟世界,它是由虚拟现实、语音交互、脑机接口等多种技术集成所呈现的虚拟空间体,人们可以以现实身份和数字身份进入其中进行社交、娱乐、科学实验等。元宇宙的本质是一个延伸现实世界的人造在线数字空间〔8〕,也是一种对数字媒介发展终极形态〔9〕的构想,兼具虚实相融、时空再构〔10〕、去中心化〔11〕等特征,整合并构造了包括政治、经济、信息、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上的多重虚拟环境。〔12〕因此,元宇宙也可以被视为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建构。
(二)元宇宙空间存在三种虚实匹配关系
元宇宙是万物互联、人机互动、高度沉浸的虚实混融的交往世界,无论元宇宙空间与真实世界中的人是否一一对应,在这一空间中都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13〕。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元宇宙视为连接虚实世界的桥梁和媒介,也可视为虚拟社会得以存在的载体。元宇宙空间正在从单一的技术和功能模块向具有完整世界观的虚拟社会空间发展。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技术条件下,元宇宙空间与现实世界存在三种可能的匹配关系,即数字孪生关系、虚构关系和虚实共生关系。
数字孪生(Digital Twin,DT)是一种实现物理系统向信息空间数字化模型映射的关键技术〔14〕,可以对拟研究对象进行仿真,并将仿真结果反馈给物理对象,从而帮助物理对象进行优化和决策。〔15〕其技术基础可追溯至美国密歇根大学Grieves教授2005年提出的“镜像空间模型”〔16〕和中国科学院王飞跃研究员2005年提出的“平行系统”〔17〕。数字孪生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检验和实验的场所,在虚拟场景中进行虚拟仿真应用,实现“虚实融合,以虚控实”〔18〕。例如,数字孪生城市可以感知城市的水文气象、机场车流等;数字孪生地球可以预测全球气候变化,助力环境治理;数字孪生工厂则可以在元宇宙中对产品进行设计、测试,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在数字孪生关系中,虚拟空间是实体空间数字化模型的映射,它以虚拟仿真为实体空间提供优化和决策方案。因此,它的虚拟体验价值并不脱离现实物理对象,又具有超越现实空间的预测性,这也正是数字孪生的意义,其最终目的是给现实世界的改造提供参考和依据。
虚构关系分为完全虚构和并非完全虚构两个部分的关系。所谓完全虚构部分指的是场景和人物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并不存在,但这些场景具有一套独立的世界观,人们可以进去体验,如游戏、旅行、接受教育甚至工作,也需要重新建立社交关系。并非完全虚构是指人们创造的这个场景背后所依赖的依然是现实世界中学到的技能、知识,比如游戏中的世界或者科幻电影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不存在,但作者在创作游戏或者电影时还是有现实世界的影子,尽管角色外形怪异,但都有五官、身体等,设计思维也仍然遵循现实世界的基本逻辑。离开现实世界基本逻辑的完全虚构、架空历史的世界被认为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玩物丧志”〔19〕。因为看似平行的时空消耗的是人们现实中的时间,挤压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并且在体验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后,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所谓的完全虚拟空间背后实质上体现着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意志和构想,是人们意识世界的表象化。因此,与现实世界呈现虚拟关系的元宇宙空间形态看似不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表面上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较弱,但其与现实世界具有内在的隐性关联性。
虚实共生关系是元宇宙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关系的终极形态。未来虚拟世界最终趋向于把现实世界容纳于元宇宙世界〔20〕,虚实共生的元宇宙不仅对物理世界进行复制,同时还将呈现的是超脱现实生活更多层次的数字空间,能够呈现真实世界无法企及的超现实、想象性的虚拟场景。用户的主体性得以增强,数字价值得以更好地发挥,进而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中的生活与交往,与人类的发展实现协同进化。人类自我认知的深化、创造性的发挥,也将使元宇宙空间更快进入自组织境界,在不断地动态演化中实现与现实社会的互构。这种形态的元宇宙空间不仅面向现在(映射当下的人类社会)和未来(大数据技术的预测功能),同时也面向过去,即对人类历史和文物的构建,在数字化时空和场景中构建现实社会与数字社会、历史社会与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元宇宙社会主体的虚实关系
在元宇宙空间形成的虚实共生的“新型人类社会”〔21〕必然具有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连接,演化出新的数字交往文明景象。这也意味着现实社会的主体——“人”——的身份在虚拟空间中将面临解构与重构。那么,元宇宙文明的主体是否与真实世界的人一一对应?元宇宙空间中的虚拟人是否就是真实世界中真实人的化身呢?有研究者将元宇宙中的数字人分为产生虚拟数据身份的虚拟假人、意识上传的真人以及由程序设计而成的AI数字人。〔22〕简单来讲,就是数字化的真实人和虚拟的数字人两类。
数字化的真实人包括真实人的真实人格和真实人的虚拟人格。真实人格在元宇宙社会中代替真实人完成日常生活和交往,他们是以人的意识为主体的“意识上传的真人”〔23〕,通过可穿戴设备或脑机接口,实现虚实主体的互联和切换。他们与真人是数字孪生关系,可帮助真实人实现虚拟场景中的“在场”体验、与现实世界无缝衔接的社会交往,弥补了网络社会“缺场”〔24〕交往的遗憾。当然,用户还可以在多个虚拟空间拥有不同的虚拟人格,他们是用户的化身。但无论是数字孪生人,还是虚拟人格人,他们均是真实的用户对自身身份建构的反应,是他们在虚拟空间的自我形塑,背后隐含着他们对于现实和虚拟社会的认知与期待。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发展和进化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和形成了元宇宙的文明基础。需要警惕的是,主体身份的不断切换和交替有可能导致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以及自我价值认同的危机,还有可能加深人们对真实自我的焦虑和质疑,甚至不愿再回归现实。
而虚拟的数字人则不仅包括真人生理的数字模拟、虚拟新闻主播、聊天机器人、为已故者复现所创造的数字人〔25〕等,还包括AI数字人。虚拟的数字人是为元宇宙空间专门创造的建设者,有虚拟教师、虚拟工程师、虚拟建筑师等,他们摆脱了物理身体的束缚,以数学为边界,只受数学规律的限制〔26〕,属于元宇宙的“人工数智体”。在这种设定下,元宇宙社会的主体实现了从实在个体(真人)向非实在个体(非真人)的转变。这种多重的个体自我与多元化的社会主体构成了多层次、多种可能的元宇宙社会形态,也将会创造多元化的元宇宙文明。
二、元宇宙空间虚实关系的价值取向
元宇宙按照虚拟沉浸体验的程度可划分为无沉浸期、初级沉浸期、部分沉浸期。有研究预测,到2026年元宇宙将进入完全沉浸期,其特点是网联云控和有机融合〔27〕,这时元宇宙成为人类进行全面数字化迁移的生产、生活、生存的载体,也成为具有超越性力量的新型媒介。那么,元宇宙空间中的社会交往有可能追求的是虚拟端的体验感,也可能追求的是虚拟社会作用于现实端的意义感。在元宇宙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应该走向虚拟的乌托邦,还是走向虚实结合所构建的现实意义,即坚持怎样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虚实结合的现实观
有研究将元宇宙的特征归纳为身临其境、无缝映射、永远在线、无限边界、数字分身、社交计算、文化多样性、无障碍访问、无摩擦、互用性、虚拟经济化。〔28〕也有元宇宙五大特征之说,即社交性、没有硬件限制、用户生成内容、生存与呼吸、连接世界。〔29〕从特征可以窥见元宇宙的成熟形态。由数字代码构建的元宇宙空间,犹如钱学森所意指的“灵境”,去实体化和非物质化的数字信息仿真景观愈加凸显人的心境和心灵世界〔30〕,也引发学界对于“脱实向虚”的隐忧。在技术的加持下,如果人们习惯了通过界面语言去感知世界,以脑机接口代替大脑想象力,以计算机语言代替社会文化语言,便会渐渐模糊自身与虚拟空间中的数字孪生人之间的区别,高度沉浸感的空间让用户迷失在数字假象和虚假身份构建的“立时快感”中,进而引发数字世界的“纳西索斯反应”,难以完成虚实之间的切换。
从本质上看,元宇宙空间作为一种新的虚拟生活场域,既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精神的诉求,更是一种文化想象的产物。因此,元宇宙的时空结构虽然相对独立,但运转模式仍未脱离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31〕元宇宙空间的一切都作用于神经元,而真实世界则作用于人的物理身体,元宇宙空间形态必将成为虚拟空间和真实世界相结合的存在。〔32〕从社会视角看,元宇宙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数字化呈现,其运行可以为人类现实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和启迪。虽然人们在元宇宙中的虚拟交互对象可能是真人的数字映射,也有可能是单纯的AI数字人,但是人们在元宇宙社会中劳动、消费以及进行虚拟文化体验,均是为了获得现实端的体验主体(真实的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物质和金钱的回报。因此,虚实结合的现实观追求的是以虚拟的身份在虚拟空间反映现实生活世界。
从元宇宙空间中主体的身体化建构上也可见一斑。为了获得“在场”感的具身性体验,元宇宙进行了“以身体为中心的空间建构”〔33〕。元宇宙空间与现实世界类似,有展览馆、会议室、公园等设置,尽管虚拟数字人不会疲倦,也不需要休息,但对元宇宙的大众期待依然并非一种“去身体化的数字存在”〔34〕,而极力将元宇宙空间构建成一种类似现实世界的存在,追求一种虚实结合的“社会临场感”①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由心理学者Short、Williams和Christie提出,用以研究不同媒介的沟通效果对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Biocca、Harms和Burgoon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临场感包括虚拟共在感、心理卷入和行为参与三方面的内容。〔35〕。社会临场感包括虚拟共在感、心理卷入和行为参与三方面的内容〔36〕,元宇宙空间中的社会临场感通过具身化的在场体验使人们产生身体和心理双重临场的感知,实现与他人在元宇宙空间的“虚拟共在”。网络社会中,赛博空间是不能被直接感受到的缺场空间。〔37〕这种以网络媒体为中介的智能交流通过语言文字的信息流动进行,缺乏真实个体的姿势、着装等非语言特征的交流,也缺少物理空间的环境背景。而元宇宙社会则通过对这种“社会临场感”的打造,弥补网络空间缺场交往的割裂感,重塑了交往中的个体对他人及环境的感受力。这种临场感和感受力的增强无疑也是为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的沉浸式体验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将虚拟空间中的体验反作用于真实人的意识活动、感知和记忆。
(二)虚实互构的共生性
元宇宙中的虚实空间交往关系一致性的形成就在于其“共生性”。一致性空间交往关系依赖于共生性互动而不是冲突,共生是虚拟与现实一致性的理念、价值。共生的生长立足于现实,昔日重来和跨越未来都以现实为参照点构建元宇宙空间,所以现实是元宇宙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们现在不仅有生物人、社会人,元宇宙数字媒体技术也会创造出数字人,即人类本体的数字化,导致人类本体与数字分身在“身份、社交、生活、娱乐”的多维度融合现象,导致虚实结合的“身份共生、场景共生、内容共生、社交共生、文化共生”〔38〕。因此,元宇宙空间是一种沉浸式、立体化、可感知且与主体融为一体的具身性空间〔39〕,是具备现实映射性的数字空间,它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虚实相融、相生、共生,与现实世界具有高度耦合性。“虚拟数字对象与现实物理对象会彼此介入各自所处的环境,彼此之间也会发生各种因果相互作用或因果相互影响”〔40〕,存在紧密的“因果依赖关系”,并可以进行动态化地相互构建,促进彼此的社会进化。
具体而言,数字人作为元宇宙的主体,通过主观能动性可在元宇宙中积累大量的人文性成果,发展出相对独立于现实的虚拟文明,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人文社会系统”〔41〕。在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中,基于上传了真人意识的数字人的身份,其所处的场景、生产的内容、所依赖的社交和文化体验不断进化,并得以保存、记录,在元宇宙空间获得永存。这些更新和进化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系,因为数字人在元宇宙空间中的经历也是与其相对应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经历。真人与数字人对这段记忆具有共享性,或者说二者的表象身份虽然不同,但本质上是一个主体。虚拟经历对主体的影响反映在现实世界中,则必然会影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认知、观念及交往方式,进而影响现实世界的发展。而现实社会的发展作为环境因素又会对真人产生影响,使得主体进入元宇宙空间后,以被影响后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作用于元宇宙社会的进化。于是,元宇宙的身份共生导致了社会场景、内容、社交和文化的共生,虚实空间以用户为媒介实现共生和互构,实现首尾相接、交叠共进的持续发展。因此,要建立以实为本、虚实共生的元宇宙价值观,就要以动态演化的理念来理解、建构和发展元宇宙世界。〔42〕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元宇宙社会的未来必然会与网络社会一样,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的发展协同进化。
三、元宇宙空间的社会性延展
在元宇宙空间中,人们的构想空间可以直接被形象化,形成再现的空间。这种将空间实践过程压缩的特性使得抽象的概念和思想形象化,不但强化着人们的表象思维,同时也影响着元宇宙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属性。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元宇宙空间形成的是网络社会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态,是一种新的社会场域。互联网创造了一种信息流动的缺场空间,而万物互联、高度沉浸的元宇宙创造的是一种虚实混融的伪在场空间。具身强调身体是直觉与环境互动的中介,实在具身是指人客观存在的物质身体,而虚拟具身则是指人体验到的身体。〔43〕人们在元宇宙空间中通过去中介化的虚拟具身体验构建新的更类似于真实世界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这种社会关系和情感连接的根源在于现实社会,而又超脱于现实世界而存在,是现实社会的延展。
(一)虚实结合的社会结构关系
如上所述,元宇宙所构建的虚拟景观涵盖了人类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虚实结合所形成的元宇宙社会的结构关系也必将是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现实获得与理想追求的结合体。
第一,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互映。智能技术与数字技术体系正在重构当今世界的结构,拓宽世界的外延,实现现实社会、网络社会(基于互联网技术创造的虚拟社会)、元宇宙社会(基于虚拟现实和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社会)的发展进阶。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呈现出看似独立又万物互联的关系。一方面,虚拟社会的超越离不开现实中的人已经形成的社会结构关系;另一方面,虚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习惯也影响其现实中的自我理解与认知,改变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认同。这种相互影响体现了元宇宙社会多重现实的交互性与反身性,呈现出人类本体与数字分身在身份、社交、生活、娱乐等方面的多维度融合现象,以及虚拟空间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实体深度融合的社会结构特征。因此,元宇宙社会虽然看似是虚拟社会,但其社会交往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其对现实社会也具有深度的参与性和极强的影响性,是虚实结合的社会空间。
第二,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贯通。人们在元宇宙空间与网络空间中的交往类似,都是体现集体表象特征的交往形式。集体表象是“通过形象意识活动形成的可以记忆、传递和传承的集体共识”〔44〕。集体表象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原则使元宇宙社会具有了类似于传统社会的家庭、宗教、社群等。因此,元宇宙空间的社会交往体现着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共同信念和群体崇拜等精神层次的集体共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元宇宙空间毕竟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边界,具有突破传统现实社会的空间无限性和广泛性,也呈现出“数字表象”的特征——尽管人的身体具有地方性和排他的感知性,但是数字表象的无限扩展性将呈现出社会主体更加丰富和无限可能的精神世界。在数字化、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技术的支持下,元宇宙空间将会呈现出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的表象世界。人们通过对自身经验的提取,对文学、艺术、建筑等思想性创造进行形象化表达和表象性呈现,实现对新世界秩序的共创共建共享,而在传统社会中这些仅存在于个人的脑海想象和语言表述中。这种精神层次的形象化展现不仅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物质水平达到一定条件时人们对精神追求的真实感、沉浸感以及感官刺激强度的自然要求。
第三,现实获得与理想追求的场景构建。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互构共生的新空间,由于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构建的,因此自然而然带有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和愿景。“元宇宙就是人类一贯的、从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神奇的想象和美好的愿望,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技术支撑下的一种实现形式。”〔45〕它在出现之初就被赋予了构建一种理想化社会场景的使命,其“自治的生态系统被认为是孕育民主属性的摇篮”〔46〕,人类期望可以在元宇宙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中自由表达、相互交流,世界运营的政策和规定也可以通过自治组织“DAO”①DAO是英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首字母缩写,是基于区块链核心思想理念衍生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它将组织的管理和运营规则以智能合约的形式编码在区块链上,因而是在没有集中控制或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运行的组织形式。进行。因此,人们对元宇宙空间的理想不仅仅包含着对空间运行方式和虚拟社会交往方式的想象,还包括了人们对自身身份、个人定位的追求。例如,前述真实人的虚拟人格背后隐含的就是人们对自己身份和个性的期待,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可以在元宇宙空间中得到完成。而人们的理想追求是现实社会的理想化映射,也会在人们进入元宇宙空间之后,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因此,元宇宙社会的构成包含着人们的理想追求、价值诉求和未来观,通过虚拟的场景建构,在理想与现实获得之间穿梭往来。
(二)感性映射下的社会联结方式
与互联网的发展类似,在元宇宙建设初期,感性建构占据了主要位置。比如,通过游戏式的沉浸体验和交互方式实现感性映射,利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丰富生动的形象化活动形式以及感性化的表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引发涂尔干所说的“集体兴奋”〔47〕,人们在元宇宙空间中的群体特性、集体记忆、价值认同不断形成,逐渐显露出集体表象。而数字表象则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述元宇宙空间超越真实空间的凝聚力和想象力,展现出社会主体因其感性化、表象化而呈现出的更加多元化的社会联结形式。元宇宙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精神社会”〔48〕。元宇宙社会看似指代线上虚拟交往,却包含着真实的社会交往关系,并据此拓展了新的精神空间。可以说,元宇宙实现了人类感官在虚拟仿真平台上的场景化延伸,也是人类自身叙事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实现了数字空间的社会性延展,因此也被称为“虚拟社会化”〔4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时空看似无限,行动看似自由,其中的体验对个人来讲却是割裂的和碎片化的。缺乏中心的生命历程极有可能加速个体更深层次的异化,人们的体验被割裂成数不清的碎片飘浮在元宇宙空间。因此,如何在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数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融合中探寻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将是社会学未来亟须探讨的问题。
(三)数字人、数字空间和数字社会中的多层次社会关系
作为元宇宙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媒介,“人”成为虚实共生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现实世界中的人将规则、法律、宗教、文化等精神性的内容引入元宇宙空间,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也影响着元宇宙的社会结构。不过数字技术的赋权导致元宇宙空间的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等级结构,也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元宇宙空间中所有数据的生产、占有和使用,以及数字资源的分配将形成新的数字权力,也会反作用于现实空间。
个体由现实进入元宇宙空间,从现实空间的历史和社会中暂时脱离,去往另一个空间以其数字身份进行社会交往,个人在元宇宙空间的活动创造的是元宇宙的历史和社会。但元宇宙社会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扎根于现实世界,与现实社会具有相互映射的关系。元宇宙因其数字属性实现了多重想象空间的形象化和仿真化。这种承载人们理想追求的空间脱胎于现实,实现了数字超现实。因此,现实空间与元宇宙空间的动态过程呈现了从相互结合形成的嵌入关系,到延伸形成的映射关系,最后实现想象空间再造的超越现实关系。
在此我们可以援引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思想,空间产生于劳动和劳动分工,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品,元宇宙空间的形成也是元宇宙社会发展的结果。〔50〕元宇宙空间与社会空间一样,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社会主体在元宇宙空间中,首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场所搭建等具体化的生产,这被称为数字空间实践。在元宇宙空间中,人们的构想空间可以直接被形象化,形成再现的空间,不但强化着人们的表象思维,同时也影响着元宇宙空间的社会关系,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属性。
总之,由于元宇宙空间以现实世界为根据,并作用于现实世界,由此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虚实互构的共生性,但它仍以现实世界的意义追求为主,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去改变现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在把元宇宙作为媒介、平台或者另一个虚拟空间时,会不会发生“脱实向虚”的趋向,即盲目地追求虚拟世界的意义建构。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元宇宙空间中具身化体验及其形成的感性表象所引发的全民狂欢和技术崇拜,对个人和社会的异化现象。应当清楚,在元宇宙空间及其形成的整个数字社会系统背后的主体依然是真实的、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