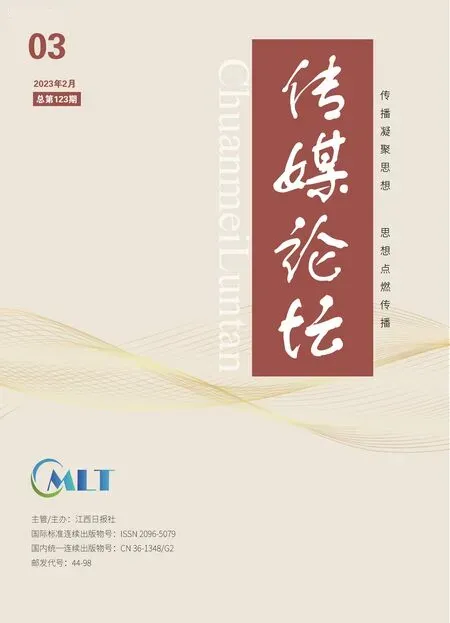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看中央苏区的妇女动员工作(1931—1934)
2023-04-06林舒倩
林舒倩 谢 菲
《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充分发挥了舆论宣传主阵地的作用,唤起苏区人民积极参与共建苏维埃政权的热情。《红色中华》中有大量的文字对苏区的妇女群体进行描写、刻画和宣传,投射了苏区妇女热烈投身革命建设各项工作的鲜活形象,彰显中央苏区妇女动员工作的蓬勃有力。本文以1931—1934年间《红色中华》关于妇女的相关报道为中心,剖析中央苏区的妇女动员工作,并思考其对于当今妇女工作的重要启示。
一、中央苏区妇女动员工作的重要意义
1931—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工作,迫切需要动员苏区群众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之中。苏区妇女积极拥护、充分信任、坚定服从于党和政府,是党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苏区妇女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解放运动,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旧思想束缚的体现。所以,通过《红色中华》做好中央苏区妇女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对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对党的事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妇女动员工作的实践内容
(一)社会经济层面:广泛动员妇女参与苏区经济建设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央苏区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工农业一度遭到极大的破坏,田地荒芜、工商业凋敝、金融混乱。为了打破这一被动局面,苏区政府大力动员苏区妇女参与根据地经济建设。
1.动员妇女学习耕种,参与发展农业生产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苏区妇女艰苦努力,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学习耕种,广泛参与农业生产,以实际行动扩大苏区农业生产,保障军用民需,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保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引领苏区妇女学习耕种,《红色中华》发表《“三八”妇女节的国际意义》一文,号召全体苏区妇女“加入革命的生产战线,努力学习耙田犁田,参加每乡每区的春耕计划的决定和执行”。[1]而苏区妇女也以冲锋陷阵的精神,去完成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紧急任务。《红色中华》记载了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妇女春耕的热烈场景,“在上杭才溪区的春耕运动中,有十分之八的女英雄参与犁田耙田,在今年的夏耕秋耕中,估计可以使妇女同志百分之百参加”。[2]为使妇女能熟练掌握劳动技术,苏区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的带领下,设立教育生产委员会,积极推进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据《红色中华》报道,“苏区政府以乡为单位,组织教育生产委员会,并组织了十三个学习生产组,组织劳动妇女学习生产”。[3]此外,为了免去苏区妇女担心投入生产而疏于照顾子女的忧虑,苏区政府还组织建设托儿所,择优选择看护人。[4]设立托儿所这一措施对于改善苏区劳动妇女、儿童生活,以及对于革命胜利都有极大意义。
2.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工作,筹措革命经费
国民党在军事“围剿”过程中,对苏区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手段。在持续斗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中央苏区补给受限的情况下,苏区政府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引导。一是开展粮食突击运动。1933—1934年,党中央两次号召群众借谷给红军,妇女节衣缩食,纷纷响应。跟随党中央的号召,1933年,兴国永丰区长岗乡妇女刘金秀将其丈夫送去参军之后,在秋收时又主动拿出一担半谷子给红军。[5]二是动员购买公债。1932年6月至1933年7月之间,苏区政府曾三次发行公债,以充实军费和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苏区妇女拿自己的银器换了毛洋,从而购买经济建设公债票。[6]
(二)政治建设层面:广泛动员妇女参与苏区政治生活
中央苏区政治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动员和组织广大苏区妇女参加苏维埃革命和政权建设,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参政的热潮。
1.保障妇女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毛泽东在《红色中华》撰文指出:“苏维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7]由此强调保障苏区妇女的政治权利,党亦重视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苏区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8]其后在1933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个训令(22号训令)中更进一步对妇女代表比例做出份额规定,写明“除了选举法规定的工农成分代表比例之外,劳动妇女的成分应占25%”。[9]由此,法律上对妇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规定不断细化、明晰,妇女也在实践中广泛参与政治生活。1933年,在上杭县才溪区的选举运动中,“妇女代表会开会热烈讨论本身对选举运动的实际工作,在各乡村做了挨家挨户的宣传”,[10]在最后的选举大会上,“妇女各乡都占30%以上”。[11]同年,在江西省瑞金县武阳区武阳乡的选举大会中,“妇女代表占了13人,这是给二次全苏准备委员会关于吸收百分之三十妇女参加代表的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12]此时妇女参与选举的人数比例都已超过此前规定的25%。1934年初新组成的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有些地方如上杭县的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妇女代表分别占54.6%和64.8%。[13]妇女对政治愈来愈抱有高度的热情,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
2.号召妇女加入党、团组织
苏区妇女群体的入党、入团,是体现妇女政治意识、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为了尽快壮大党的队伍,1933年4月17日,中央苏区在《红色中华》发布《为五一节征收党员运动告苏区民众书》,发出了“不让一个先进觉悟的工人、雇农、苦力、红军战士,站在共产党的外面”的号召,[14]特别要求劳动妇女党员人数应增加一倍半以上。为此,苏区党委号召每个党员要发展一名党员:“每个支部至少要吸收一个女同志”,“不要让一个积极进步的劳动妇女留到党外”。[15]在苏区政府的引领下,苏区妇女提升参政意识,登上政治舞台,向世人展现了一股历久弥新的巾帼力量。
(三)军事斗争层面:广泛动员妇女支援革命斗争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斗争的主要内容,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妇女也是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支撑。
1.动员妇女发动亲属参军
在苏区战争期间,苏区政府广泛发起扩红运动,妇女是扩红运动的突出贡献者。在党和苏区政府的历次扩红动员中,她们纷纷发动身边亲属参军,为红军源源不断地汇入补充力量。苏区政府主要通过建立组织、妇女干部宣传动员等形式掀起妇女的扩红积极性,如“永丰女工部在扩大红军工人师的动员中,发动妇女宣传自己的丈夫、叔、伯弟兄到红军工人师去”。[16]在苏区政府的大力宣传及苏区妇女自觉燃起的爱国爱党之火蔓延下,苏区涌现出了诸多妇女扩红模范。《红色中华》有许多版面报道了妇女扩红模范,如“汀东长宁区彭坊乡的江银子、万太上茅区大庄乡的李五妹鼓动丈夫参加红军。宁化禾口区陈埠岗乡的进才女、木香女,则不仅鼓动自己丈夫去当红军,还鼓动兄弟去参军”。[17]此外,苏区政府还通过召集妇女代表会议,进行各地扩红竞赛动员工作,各地妇女对亲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动员。[18]
2.动员妇女做好革命后勤
妇女在红军后勤保障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妇女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发展妇女的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如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来领导和组织她们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19]对此,在中央号召之下,苏区妇女组织了各种战时服务队,为不断扩大的红军革命队伍提供物质支撑和精神保障。她们常常慰劳红军,为红军战士编织草鞋、缝补衣物等等,战时服务队的妇女同志还经常上门动员家庭妇女、女青年。向她们解说革命的严峻形势以及帮助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使得苏区妇女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不仅如此,苏区还通过各县乡组织扩大与慰劳红军的竞赛,有计划地做慰劳红军的工作,动员妇女们“草鞋要做得好,做得长大,并在草鞋绣上各县各名”。[20]妇女对红军的慰劳与奉献,使红军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获得了有力支撑,助力红军在前线奋勇拼杀。
(四)权利保障层面:广泛动员妇女追求平等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妇女的翻身解放,切实维护和实现苏区广大妇女的权益,使妇女能在婚姻、经济上得到彻底解放,提高和改善妇女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1.保障妇女婚姻自主,促进婚姻公平
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人强迫和包办当事人的婚姻。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21]苏区各乡各县政府保障妇女权利,坚决执行婚姻法,对违法者大力惩处。《红色中华》中提到:“福上乡李兴才的女儿,年方十九,凭媒与赤竹乡谢芳忠之子结婚,表面上是新社会的自由结婚,但实际上仍是封建制度买卖婚姻的办法。这一事实被乡负责人察觉,遂将李兴才谢芳忠二人拘捕。”[22]苏区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保障,打破了数千年以来约束女性的封建锁链。冲破封建礼教而收获新生的妇女们,把精力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为革命作出贡献。
2.保障妇女独立经济权,促进经济公平
苏区妇女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为了在经济上保障妇女的权利,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劳动法》除规定男女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之外,其中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应对妇女的产假、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对于《劳动法》的执行,苏维埃政府设立女工部、女工代表会,要求“实行劳动法,发动女工经济斗争,订立集体劳动合同,增加工资,女工与男工一律平等,改善女工生活”,[23]苏区政府在土地分配上也保障了妇女的权利。《红色中华》中《劳动妇女们!武装起来拥护苏维埃!》一文提及:“分田的时候,女子和男子是完全平等的。假如女子出嫁时,她有自由处置分得的田地的权利。”[24]可见苏维埃政府对妇女的经济权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予以保障。
三、中央苏区妇女动员工作的当代价值
(一)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女问题上的运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妇女运动政策、指导方针,为当时各地妇女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宏观指导,使得妇女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条件下的妇女工作实践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群众动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的妇女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科学理论的指导往往具有领航作用,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一条基本准线,始终坚持、毫不动摇。新时代背景下,全党全国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将其作为领导妇女运动的“定盘星”,坚持党对妇女工作的正确领导,总结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开展妇女工作的经验,从中国妇女群体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当前妇女工作,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不断增强妇女群体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二)关注女性权益,建立平等两性关系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保障苏区女性的经济、政治、婚姻等权利,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男女性别平等、权利平等,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现实难题。如有苏区政府单位成为妇女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壁垒,对妇女工作较为懈怠,又如法规上对妇女权利规定不够明晰,造成一定的纠纷等等。
当下我国的妇女工作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家暴、性侵、离婚等事件中对于女性的权益保护问题引起争议,存在妇女工作还不完善的情况,良性平等的两性关系实际还未完全建立。如在职场中,女性较易遭受歧视。又如在许多家庭中,仍有重男轻女现象。因此,在往后的妇女工作中,应重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要加紧完善针对妇女权益保护的法规政策;另一方面要运用媒体发声,传达关于男女平等理念的声音,在全社会营造男女平等的氛围,推动党中央对于妇女工作的持续开展。
四、结语
1931—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各项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妇女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通过国家权力干预使苏区妇女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一时期广大妇女在参加经济建设、投身革命、支援前线、扩红动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释放出蓬勃的活力与创造力,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一篇绚丽华章,也为新时期的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