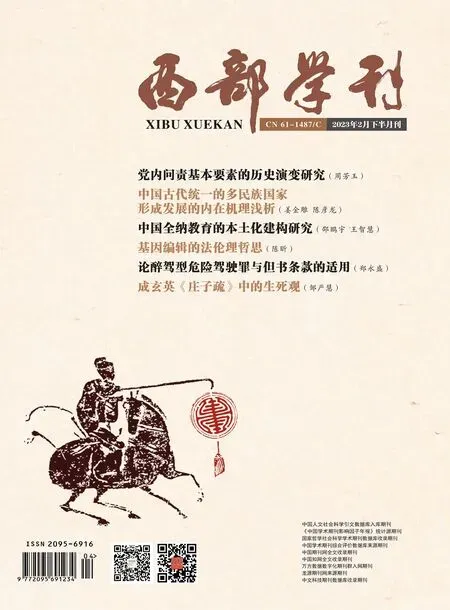《黄色墙纸》中“暗恐”的修辞叙事解读
2023-04-06张馨艺
张馨艺
《黄色墙纸》是美国女性主义小说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其是以作者个人经历为蓝本进行了艺术化加工创作的。女主人公产后被诊断患有焦虑症,听从医生丈夫的意见采用“休息疗法”,租住在乡间一栋老旧别墅里。在三个月的休养期中,主人公被禁止进行一切写作工作,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顶楼一间墙体铺有黄色墙纸,窗上加有栅栏的育儿室内。随着时间推移,黄色墙纸的形象在主人公想象中愈发生动也愈发恐怖,最终使得她走向疯狂,像婴儿一样在密闭空间不停爬动。
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使读者不得不采用叙述者的视角直面恐惧,探究其恐惧根源。由“暗恐”理论切入,思考女主人公压抑的恐惧与其最后的疯狂间是否存在联系。女主人公的视角下墙纸图案莫名其妙发生了生动的异变,使阅读者产生诡异之感;结局女主的疯狂在其第一人称叙述下逻辑严谨呈现出合理性,却更使读者震惊困惑。作者吉尔曼这样进行情节设计,是希望读者如何理解这些恐怖元素?通过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对女主叙事话语的暗恐性进行分析,以探讨作者如何利用叙事中的“暗恐”影响读者的判断。
一、女主人公“暗恐”的心理溯源
暗恐,又称非家幻觉、恐惑(the uncanny/unheimlich),弗洛伊德认为,个体过去遇到过的事物,因压抑而进入潜意识,故个体对那些不再现身于意识中的事物之熟悉度降低,当这些事物(以其他面目)再次出现,个体对该事物便产生似曾相识的恐惑感[1]。所以“暗恐”是把人带回到很久以前熟悉和熟知的事情中的惊恐感觉,是一种压抑的复现[2]133。被持续压抑的元素不能进入意识,只能存在于无意识中。但在特定条件下对这些元素的恐惧记忆还是会被唤醒,在个体的无意识中进行再创造后,以个体不知觉的方式以不同的样态一次又一次地复现[3],这些样态被称作“复影”(the double)。
女主居住的育儿室是诱发其暗恐的媒介,是沟通女主“回忆”与“现实”的桥梁。童年独自一人呆在房间的生活情景与成人产子后搬进育儿室休养,“孩子”这一主题使两种经历产生了关联。弗洛伊德在《论暗恐》中分析,暗恐不是复现压抑的全部,而是再现被压抑的某些痕迹[3]。“独居育儿室”这一情景的再现兼具“熟悉”与“陌生”两种形式,在其无意识的再创造下,童年回忆中面对空白墙壁发挥的想象力借房间的黄色墙纸形成了实在且压抑的具象。似曾相识之感导致女主产生暗恐,使其将无意识中最深的恐惧投射到了墙纸上,而这一恐惧与“眼睛”有关。在迈向最后的疯狂之前,女主认定图案上有众多女人的眼睛——
没人能从那图案里爬出来——它堵死了通道;我想那就是为什么图案上有那么多头颅的原因了。
她们想强行通过,然而图案紧紧扼住她们,把她们倒转过来,这样使得她们的眼珠都泛白了[4]!
弗洛伊德研究发现,失去眼睛具有阉割的象征意义。其起源来自俄狄浦斯为赎弑父娶母之罪自瞎双目代替自我阉割。身体器官如眼睛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男性阳具的丧失,因此对失明的恐惧几近于对阉割的恐惧。而女性在从母亲子宫中产出的时候就以“阉割后”的形态存在。在《黄色墙纸》中,育儿室提供了“产出”的象征意涵,从墙纸中脱逃因此带有了生产的意味。面对儿子居住在外,母亲强制疗养于育儿室的局面时,精神不稳定的女主人公在无意识中发现,身为阉割完成体的女性本应没有眼睛,但实际上竟然依旧存在眼睛。而存在眼睛的女性(象征未被阉割),被捏断脖颈窒息翻白眼,无法顺利分娩降生于世,一如她目前的境遇。“被阉割的恐惧”变为“对被再次阉割的恐惧”。而这一自己的眼睛竟从自己的复影——墙纸中脱逃不得的濒死女子身上回视自己,继而暗恐之感加剧。拉康在《论焦虑》中提出,当“复影”于主体我之外独立存在并自行行动时,主体我的主体性就被严重质疑和异化[2]133。在暗恐的影响下,女主对自己身为女人的主体性产生了质疑。“被阉割的恐惧”使得女主对自己是否已被阉割——已经降生于世产生疑惑,因此陷入疯狂后,拒绝离开育儿室,拒绝再次出生——被阉割。
《黄色墙纸》的外部环境也形成了一个大的子宫意象。弗洛伊德称,房间、带围墙的花园、围栏等作为女性意象,可以成为母亲“子宫”的替身[5]。《黄色墙纸》中的独栋别墅,“篱笆隔墙上锁的围墙门”,“花园棚架神秘浓荫如盖”,形成了具有保护、遮蔽和限制作用的外部子宫。花园中的幽深小径和私人码头相当于产道,有与外界相连通之意。女主想象投射出,逃出墙纸在窗外爬行的女人依旧困在大子宫内并未出生;女主休养所居的“育儿室”,自带子宫的哺育意涵,四面的窗户上订满了栅栏,将其困于子宫。墙纸上的图案在女主的暗恐下形同围栏,女主自我的投射——墙纸里爬动的女影,和被扼断头颅的女性被困其中。
女主在暗恐的影响下,用绳子——象征着“和子宫相连”的“脐带”,阻断自我的出生意图。“用那条藏匿的很好的绳子把自己安全地捆紧——你休想把我拖出去,拽到那条路上去!”[4]女主被暗恐攫住,丧失了主体性,失去了在房间之外的现实世界里生活的能力。
二、不可靠叙述的“暗恐”效果
《黄色墙纸》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手法写成,身为人物的女主也是小说的叙述者,这缩短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读者只能从女主的视角阐释判断,因此也清晰地感知到了她的暗恐。而随着女主的精神状态愈发不稳,读者逐渐意识到她叙述的不可靠性,开始对其讲述的事实产生怀疑和疏离,继而对她叙述的全部内容重新审视判断,或越过其讲述组建新的故事,或补足其叙述不足的部分[6]。因此读者也会超越叙述者的视角,体会作者吉尔曼创作的人物不可靠叙述的“暗恐”效果。
首先,女主对常用之物的“陌生化”叙述使读者产生暗恐之感。神经敏感的叙述者对黄色墙纸的观察和评价呈现陌生化的特征。寻常生活中不会引起注意的墙纸粘贴的方式与墙纸在墙面上呈现出的图案重复规律在女主的陌生化叙述下“像患了震颤性谵妄症般趔趔趄趄地在队列里来回走动,这队列既孤零零又昏庸不堪……散乱的线条像斜向飘逸的波纹,形成恐怖的光影,就像无数涌动着的海草在全力追赶着什么”[4]、“墙纸外面的图案是富丽堂皇的阿拉伯风格,这种图案令人想起了伞菌……一种带节的伞菌科菌,一长串的伞菌含苞待放、发芽抽蕊,延绵不断地盘绕着”[4]“伞菌不断吐出新芽,而且不断冒出来的黄色阴影始终笼罩着它”[4]。小说背景所在的时期,中产阶级家庭中广泛使用壁纸。当时人们常用的墙纸类型之一就是东方风格的阿拉伯式藤曼花纹。黄色也是这一时期常用的室内装饰色,流行使用黄色颜料带有毒性但因颜色鲜丽,价格低廉,常被用于墙纸制作。这种黄色墙纸在潮湿环境中会发出特殊气味[7]。平常环境与无生命的壁纸呈现出惊悚的动态效果,既让读者对生活中习以为常而不再仔细观察的墙纸铺设产生了全新感受,也使读者对女主被迫居住的环境产生似熟非熟的“暗恐之感”,更加强了女主这一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在对叙述者被强制关在一个房间的压抑感受的共情之余,推动了读者对挑拨叙述者“暗恐”神经的原因进行探寻。
其次,女主的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造成其不可靠叙述的暗恐性增强。随着叙述者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其叙述中对丈夫和小姑的防备心理越来越重。
在约翰不知道我在看着他的时候,我曾经注意观察过他,我以最单纯的借口突然闯进房间,有好几次我撞见他正紧紧盯着墙纸看!我有次撞见詹妮把手放在墙纸上。
她不知道我在房间里当我用一种平静,十分平静的声调和克制得不能再克制的态度问她,她正对着墙纸干什么时,她慌乱地转过身来,质问我为什么如此吓唬她。[4]
由于暗恐,女主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敌意,在孤立无援下加强了与读者的对话,提供了读者专享的信息,既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心理距离,也使读者感受到其叙述话语的暗恐效果。丈夫和小姑的日常活动在逐渐神经质的女主叙述下变得诡异,别有所图。当读者超越叙述者的视角,试图还原事件原貌时发现,实际上惊悚恐怖的是女主的言行。悄无声息站在小姑背后突然发声,假装愉快欺骗两人,实际另有密谋,且动机疯狂。在女主叙述话语的稳定性、和谐性下,读者感知到其中的压抑、焦虑与暗恐。女主与丈夫、小姑之间言语的和谐中暗含着的暗恐叙述是女主无法宣发的心理困境,而意识到这一点的读者将重新审视家庭关系带给女性的心理压力。
最后,作者吉尔曼利用女主的不可靠叙述的暗恐性追问其解除暗恐的现实可能性。黄色墙纸的图案以“非家”的形式再现了女主无意识中压抑的女性阉割恐惧,在传统社会,女人社会认知下被视作心理没有成熟的婴儿,丈夫不尊重妻子则作为成人的理性与才能,作为成年女性的新的生命体验被添入再创造的素材,在其心里投射出兼具“幼童”特征与“女性”特征的“爬行的女影”。女主对女影行为变化的叙述呈现出暗恐性,而作者吉尔曼通过女主的暗恐性叙述指出了女主不自由状态的根源。弗洛伊德认为,消除暗恐的方法是将压抑的欲望带入意识,通过意识消除抗拒,达到精神的整合[3]。陷入疯狂后的女主从“墙内的不停爬动的女影”的观察者叙述者转变为以“墙内爬动的女人”自居进行自述。“从图案后面走出来到这间宽敞的房间里,我愿意爬到哪就到哪,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4]这一转变在女主自己的叙述中是走向了可喜的自由。而在作者的表达下,读者不得不思考,女主最终以墙中女子自居自述,是预示着女主压抑的欲望通过不断帮助女影冲出墙纸的尝试逐渐释放,还是与她想象中在墙纸里爬动的女影达成了完全的认同,丧失了自我,迷失在了暗恐之中。而无论如何,女主在拘束的现实环境中无处容身,只有步入疯狂成为逃出墙纸的影子才能使自己摆脱暗恐的努力生效,社会文明的禁令与自我的冲突造成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恐惧最终造成疯狂,这一结果使读者生出暗恐之感。
总之,女主的第一人称叙述使读者深刻感受其暗恐心态,但女主的不可靠叙述凸显了女主对事物认知判断的错误,既是她“暗恐”心理的结果,也是造成她心理压抑无法宣泄恐惧只能走向疯狂的原因。读者对其心理变化进行了解与共情亦造成暗恐之惑。
三、“暗恐”叙事的读者判断
在育儿室这一封闭空间中,黄色墙纸图案作为唯一可进行阐释的意义载体,刺激叙述者发挥想象力,召唤女主对其进行意义阐释、伦理和审美判断。女主对黄色墙纸的阐释与她的心理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叙事进程中的全局不稳定性。由于女主叙述的重心放在墙纸的解读上,读者对叙述者的暗恐性阐释和心理异化的判断进程构建了叙事进程的全局紧张因素。
女主身为作家的感知力、想象力与语言表达能力使其对墙纸的叙述生动形象,对图案的解读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似有现实基础的叙述使读者试图找寻文本证据对女主的叙述做出解释。读者或可做出如下阐释判断,叙述者将视觉上的感知和自己的思维性理解相互结合,对墙纸的图案颜色形状、在不同光影下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判断。育儿室位于顶楼四面有窗、采光充足。白天的时候,阳光从四面八方朗照。劣质墙纸褪色状态不同,呈现为不同的样态,在女主的情绪作用下演化为各种恶心的图像——滋长的伞菌、被勒断的头颅和泛白的眼睛;夜晚月光幽暗,窗上栅栏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形成黑色条状阴影,在女主的丰沛想象和心理投射下形成监狱围栏的效果。光线沿各个窗户移动,投射在墙上使墙纸上图案产生波动的视觉效果。而有关“女影在墙纸下爬动、摇动栅栏想要逃出、女人白天沿着每扇窗子爬行”的疯狂想象是否是在客观实在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加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分析判断。
由于在女主对墙纸的审美判断中,图案本质上是混乱无序的,在试图给墙纸图案建立秩序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因此,读者在解读其对墙纸的阐释时,无法厘清叙述中真实与虚幻,遭遇与女主相仿的暗恐困境。在解读中遭遇层层迷雾,无法对女主的解读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使得读者对女主无力解读墙纸图案产生的暗恐情绪产生审美上的共情,最后做出有利于作者的叙事判断:女主结局的疯狂使她心理上获得平静和自由。
作品的结尾满足了读者阅读的期待。当读者发现女主撕毁全部的墙纸,并执意让丈夫自己找出钥匙进入不再有墙纸的房间时,读者对她的意图做出判断:向压抑她的势力表示反抗。在前文女主的叙述话语中,读者看到叙述者对丈夫的诊断和决定深信不疑,十分顺从。然而,静养疗法使女主的精神状态越发恶化。这一事实使读者发现了叙述者这一错误报道背后有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分歧。当读者发现女主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苛待,并以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冲破了压制在她身上的束缚,对施压者进行了反抗时,读者对女主的终获自由形成审美上的愉悦。
作者有意通过故事的结尾,借女主的反叛行为,净化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暗恐情绪。一直稳定自信控制女主,影响女主身心状态的丈夫不堪眼前的冲击精神崩溃,而女主坚定地一次又一次爬过昏倒丈夫的身体,这一情景具有反讽意味。读者在叙事进程中对叙述者的共情,逐渐产生期望她释放压力,获得心理自由。阅读者的这一愿望在反讽中得到满足,叙事上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放,继而对叙事文本产生正面的审美判断。
结语
“暗恐”性叙事将压抑在无意识的焦虑与欲望引入叙事话语之中。对女主的心理溯源后发现,女主“暗恐”心理的源头是社会对女性毫无道理的规约,其本质与“黄色墙纸”的图案一样缺乏秩序,毫无审美,对女性心理造成压抑。当读者感受到了她具有强烈的达成目标的意志,产生女性反抗压迫、追求自身解放的胜利感。但细思之下,虽被女主叙述通顺的逻辑和强大的行动意志遮掩,结尾依旧给人一种很强的暗恐感。叙述者真的摆脱自己的暗恐了吗?或者说作者吉尔曼将人物的结局设计为“只有疯狂才能将压抑的恐惧释放”是否真的是值得读者庆祝的胜利?造成她暗恐心理的社会规则依旧存在,限制了她以正常人在社会存在生活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吉尔曼留下的问题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