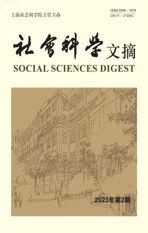谈谈解释鸿沟
2023-04-06陈嘉映
文/陈嘉映
所谓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指的是物理—生理性状似乎很难或不可能解释我们的体验。查尔默斯认为,“即使我们成功解释了一个意识系统的物理运作和计算运作,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系统拥有意识经验”。神经活动与思想感情活动之间,似乎最多只能建立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据此,解释鸿沟有时也被说成是“相关性和因果性之间的鸿沟”。解释鸿沟是针对物理主义提出来的——有些鹰派物理主义者主张一切物事最终都可以由物理物事加以解释,但感觉、体验等似乎对此提出挑战:从生理学上也许可以说疼痛就是C纤维放电,但这无助于我们理解疼痛感受起来是啥样子。查尔默斯所谓意识问题中的难题,指的大致就是这条也许无法跨越的鸿沟。
鸿沟的两岸都是什么?那一岸,有原子、分子、神经系统等,它们固然都是“客观可观察的”物事,然而,神经系统和导电系统的工作方式很不一样。神经这种“物质”,更接近近代早期所称的“会思维的物质”,查看大脑神经的活动并不能简单比喻为参观莱布尼兹磨坊的内部。这一岸同样繁杂:意识、感受、体验、感受质、个人经验等,它们显然不是同样的东西。这些东西被刻画为个人的、主观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等,当然,个人的不等于主观的,主观的不等于不可言说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不一定是神秘的;把个人的、主观的、神秘的等这些意义不同的概念塞进同一个箩筐,个中缘故就值得琢磨。
在实际论及解释鸿沟的时候,相关论者通常不去辨析这些概念,而是笼统地讨论物理物事能否解释心理物事,或客体物事能否解释主体物事。就此而言,解释鸿沟虽然是在当代知识背景和问题意识的脉络中提出并讨论的,它的核心困惑仍然是主客观问题、身心问题、物质/精神这些古老的问题。有些论者认为科学永远无法从客观物事一岸摆渡到主观物事一岸,包括脑科学在内的生理学永远无法解释感受等“主观现象”。但是,科学曾克服了那么多初看起来的“不可能”,另一些论者由此受到鼓舞,相信科学能够找到一条从客观通向主观的道路,一旦建起跨越鸿沟的桥梁,生理学将涌入主观世界的各个角落,巨细无遗地解释主观世界。在原则上,生理学家若掌握了屈原创作《九歌》时的全部脑神经活动,他就能够解释屈原在这个过程中都在想些什么?
客观物事与主观物事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生活里,似乎并没有一道鸿沟横亘在客观和主观之间。鹅毛搔后脖颈解释了痒痒,砖头砸到男孩解释了他感到疼痛,长途跋涉解释了疲劳感,丧子解释了悲痛感觉,屈原壮志难伸解释了他为什么深感抑郁。挨砖、丧子之类都是客观物事,这些物事可以愉快地解释主观感受。
日常经验解释并不面临主客观之间的鸿沟,科学呢?生理学家不做哲学的时候,似乎也不感到有什么鸿沟,他们颇为自由地用高血压解释晕眩,用C纤维放电解释疼痛,用血清素水平变化解释抑郁,用神经网络的剧烈活动来解释感受强度。然而,当科学家面对因果概念的时候,他们变得谨慎起来。科赫在谈到人工诱导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会触发相关的知觉印象时说,神经活动变化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止于相关关系,但“作为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们更谨慎地采用了意识的‘相关物’这一概念,而没有更明确地使用‘原因’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还不曾掌握确切的因果机制。
这里涉及的不只是解释问题。果真客观物事与意识感受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么,一开始意识是怎么从物理—生理物事中产生出来的呢?我们的宏观世界图景大致是,有感觉的生物从没有感觉的物体生成,拥有意识的生物从不拥有意识的生成。弄清楚一环又一环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当然不容易,但要弄清楚的不是纯粹客观的物事怎么“转变为”纯粹主观的物事,而是有些物事怎么会产生“主观的东西”。砖头砸到孩子他感到疼痛,这里并没有出现客观物事“转变为”主观物事这样的事情,而是石头作用于一个拥有“主观感知”的东西。用砖头砸到脑壳来解释男孩的疼痛,并不是用客观物事解释主观物事,若这里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东西,需要解释的是:孩子是怎样拥有感觉的。
“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这些用语显然不应该让我们误以为物理物事和生物物事并不存在于同一个世界里。这类用语标识的是我们看待、理解、解释物事的特定角度或特定层级。我们多少能够听懂“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类话,但不会求之过深,把自己误导到准笛卡尔的二元世界,仿佛精神和物质是两类实体,可以相互作用,甚至“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不幸的是,这还真是不少论者预设的本体论。大脑科学家埃克尔斯说: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脑与心,或“世界Ⅰ和世界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既定事实”。于是老问题来了:这两个世界若不是完全隔离的,它们是怎样互相作用的呢?埃克尔斯提出“新量子物理学的假说”即“微位假说”来回答这个问题。“微位假说”的核心在于设想“意向或有计划的思考所涉及的精神集中可能以一种类似于量子力学概率场的过程来引发神经事件”。
不过,这里似乎有一个明显的老问题:量子力学概率场属于世界Ⅰ还是属于世界Ⅱ?按常情想,它该属于世界Ⅰ,果若如此,精神就无须等到概率场过程引发神经事件才开始影响物质,有计划的思考之类的精神活动产生概率场的那一刻,精神已经在影响物质了。另一个问题是:埃克尔斯主张“世界Ⅱ具有完完全全的自主性”,以此来抵制还原论。我也反对还原论,但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完完全全的自主性”这么强的主张;其实,既然埃克尔斯认可世界Ⅱ承受世界Ⅰ的作用,它就不是“完完全全自主的”。
点线模式vs经验网络
依照流行的因果理论,原因中包含着某种力——因致力,是这种力把结果产生出来。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依笛卡尔,因和果之间传递的、转移的归根到底是动量。因果关系被分解成原因—因致力—结果,不妨称之为因果关系的点线模式。
原因事体被分离为一个事体加上该事体所包含的因致力,类似于区分实体和属性。一方面,因致力是真正产生结果的东西,原因事体本身对于结果事体无关紧要,这类似于去除所有属性,实体只剩下一个空壳。另一方面,这种被单独分离出来的因致力变得难以索解,成为一种神秘的力。休谟所理解的同时也是质疑的,正是这种因果观念。
休谟质疑的影响深远,罗素干脆申称,因果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遗迹”。不过,因果观念不仅在日常经验层面上重要,科学也并不满足于相关性,而是努力达至因果解释——否则科学家也不会为解释鸿沟苦恼。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抛弃因果观念,但我们不能自限于从点线模式来理解因果关系,尤其需要看到,点线模式中的原因并不提供通常意义上的解释。
原因和解释是紧密交织的概念,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找到原因就提供了解释。原因的一个含义是责任人。在很多侦探小说里,聪明的侦探构想出合乎情理的案情发展,以此确定谁是作案人。但是,确定了作案人不一定等于案情大白,作案的动机、作案的前因后果仍可能隐没不彰。概括说来,确定责任人意义上的原因不等同于提供解释。
那么,为什么丧子对悲痛有解释力呢?这并非一个单个事实对另一个单个事实有解释力,解释力来自这两个事实坐落在其中的广泛经验。悲痛与丧子不是两个孤立的点,它们埋在立体的、多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丧子这件事跟丧女、丧父、丧母、丧失朋友是同一类事情,丧失朋友跟走失宠物、丢失珍贵的纪念物也颇为相似。另一方面,悲痛跟悲伤、痛苦、悲哀、难过、伤心、沮丧、绝望纠缠在一起。丧子导致悲痛、丧父导致悲痛、挚友绝交导致痛苦、宠物走失导致心疼、珍贵的纪念物丢失导致沮丧、故国沦陷导致悲愤,这些不是一个又一个互相独立的因果关系,而是埋在千丝万缕联系中的一条一条线索。因果关系不是两个孤立的点之间的联系,而是在一个网络中才成立的联系,是整个经验网络把因和果稳定联系起来。拥有解释力的不是原因事体中包含的神秘的因致力,而是因果事体坐落于其中的整个网络。
我们用丧子解释悲痛,并非这一解释才建立起丧子和悲痛之间的联系,这两者的联系原本就在我们的经验网络之中。同样,同胞遭受苦难也联系于悲痛,亡国也联系于悲痛,丧子解释所做的是在诸种可能的原因中确定一种。我们用闻道来解释颜回的快乐也是这样——快乐有种种可能的原因。与其说闻道解释才建立闻道与快乐的联系,不如说这一解释是在种种可能原因之中确定一种。
用闻道来解释颜回的快乐,远不止于确立因和果两点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闻道与快乐的联系是现成的一般联系,并不是有待解释的东西。这样一种一般联系所起的是中介作用;解释借由某一已知的一般联系形成对个殊物事的综观。一个人饮水饭疏食居陋巷怎么还会快乐,原是我们的困惑之点,而对颜回的生活和性情形成适当的综观将消除这一困惑。方便起见,我把这样的因果解释称作叙事因果解释。
机制解释vs叙事解释
解释鸿沟所表达的核心困惑是,确定了C纤维放电是疼痛的原因,似乎并没有解释疼痛是怎么回事。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确定原因并不意味着事情得到了解释。丧子解释了悲痛,靠的不是这两项之间的点线联系,靠的是支持这一联系的经验网络。我们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经验网络来支持C纤维放电和疼痛之间的联系。不过,要解释C纤维放电和疼痛之间的联系,我们本来也不期待这样一个经验网络,如上引科赫的那段话所表明的,科学家之所以谨慎避免使用原因概念,是因为他们还能够为这一类联系提供因果机制。
显而易见,机制解释与叙事解释是两类解释。泛泛说来,叙事解释和机制解释都是因果解释。然而,在科学主义当道的今天,似乎只有机制解释才是“真正的”因果解释。如果我们对意识现象感到困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等待大脑科学来发现意识的神经工作机制。
为什么机制解释会被认定为“真正的”因果解释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叙事解释是在一个共享的经验网络里进行的。谁共享这个经验网络?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会有多多少少相异的经验网络。一个解释在这里行得通,在那里不一定行得通。叙事解释不具有唯一性,这一点在历史解释那里十分显眼。机制(机器、机械)则是这样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按照一套特有的固定的程序运行。机制一旦启动,它将以固定的程序运行,因此,确定的输入将获得确定的结果。与之相应,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机制解释。
机制的固定程序保障了机制因果的必然性。与之对照,叙事因果不具有必然性。丧子不一定导致悲痛——也许这对父子早已成仇,父亲完全不为儿子之死感到悲痛。
机制遵循一个必然程序运行,在机制解释那里,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与此对照,在叙事解释那里,有些事情有原因,有些事情无缘无故发生。我们问到一个朋友为什么陷入抑郁,问的是他是否遭受挫折一类,如果他婚姻美满、工作顺利,那他是“无缘无故”变得抑郁。叙事解释是综观性的,它要区分的是可综观的和不可综观的:可综观的是可解释的,不可综观的则是无缘无故地、“偶然地”发生的。然而,机制解释不留死角。那位性情开朗、顺风满帆的朋友忽然陷入抑郁,叙事解释无能为力,生理学仍能成功解释——医生查明,那位朋友生了脑瘤,导致脑神经活动出现紊乱,进一步导致血清素分泌过低。依照“凡事皆有原因”这一条“形而上学原理”,把具有普遍性的机制解释视作真正的因果解释似乎不无道理。
把机制解释视作真正的解释,还有一个实际的理由。对物事机制的系统理解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实际效用。发明抗抑郁药物是千千万万个实例中的一个。与之相比,叙事解释和叙事理解,例如历史学的工作,即使与实用有联系,其联系也相当迂回。一位顶尖精神药理学家说:“重点是,我们现在可以医疗抑郁,而哲学性地思考它从何而来,迄今没有丝毫的治疗效用。”
然而,在我看来,“机制解释才是真正的因果解释”这一主张完全站不住脚。叙事解释跟机制解释索求的是颇为不同的因果。这两类解释有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概念,遵循不同的逻辑。
一个机制只对特定物事或某一物事的特定方面做出反应。温度计对温度做出反应,不管那是水的温度还是铁的温度。杠杆只对力做出反应,不管这个力来自什么东西。引发机制做出反应的物事不是作为完整个体引发反应,是它的某种性状引发反应。叙事解释所解释的则是个殊物事。闻道所解释的是颜回的快乐,壮志难酬解释的是屈原的抑郁。叙事解释依托于个殊物事,并最终以理解个殊物事为归宿。
一个机制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这也是说:机制与机制互相独立。在叙事解释那里,原因和结果连成一个整体,生火、烧饭、吃饭,这是一个连续的叙事;然而,柴草燃烧的机制、生米煮成熟饭的机制、消化淀粉的机制,它们是些判然有别、不相连属的机制。
一个机制自成一体,隔断了此前的整体物事和它所产生的结果。不管什么林林总总使得屈原抑郁,最后这些林林总总都导致屈原的血清素水平下降,并因此导致抑郁。而在叙事解释那里,原因不能脱离它所依附的个体物事得到确定,也不由于它产生了结果而不再相干。
大脑科学不可能解释《九歌》的创作
科学家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已经大致掌握了燃烧的化学机制、促进植物生长的光合作用机制,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大脑神经的工作机制。缺少对相关机制的了解,仅仅确定C纤维放电是疼痛的原因,自然谈不上对疼痛做出了解释。
不过,所谓解释鸿沟,主要不在于机制研究尚有不足,而在于神经科学提供的只是一个特定方面的解释——意识的生理生成机制解释。“意识解释”是个笼统的提法,包括很多性质不同的问题: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是否所有感知都具有意识?意识有什么功能?何为自我意识?无论神经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掌握了意识活动的机制,大多数意识现象都仍然没有也不会因此得到解释。
关于这一点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不少论者认为,要么在生理学和思想感情活动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要么,一旦架起一道桥梁,生理学就能够解释全部意识活动,解释整个“主观世界”。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根据大脑电信号确定这位残疾人想让轮椅向左转,或者确定他正在努力尝试写出L这个字母,这似乎意味着,我们明天原则上就能够根据大脑电信号了解屈原的所有思想感情。我们一开始就提示,被笼统归到“主观世界”这一岸的东西是些颇不相类的东西。弄清楚脑中发生了什么,也许能知道一个人感到的是疼痛而不是痒痒,但这不能告诉我们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是怎么形成的,不能告诉我们屈原创作的《九歌》而不是《九辩》。
《九歌》的创作依赖于屈原的个人生活史,这一生活史又交织在楚国的险恶情势的大局之中,同时,《九歌》的创作离不开诗经,离不开楚国的语言文字、民间仪式与歌谣。所有这一切赋予《九歌》里那些诗句以意义——离开这些意义,当然无法解释屈原的思想感情。扫描图不仅无法为《九歌》及其创作提供因果解释,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相关关系。
解释《九歌》根本不是神经科学的用武之地——即使生理学家掌握了屈原创作《九歌》时的全部脑神经活动,读《九歌》碰到不解之处,我们还是会去请教文史学者而非生理学家。同样的道理,就系统理解意识现象而言,脑科学也帮不上很多忙。曾有论者抱怨,“当代‘生命科学’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们很少研究生命本身……而是将无限精力投入到对生命的载体的物理—化学研究和分析当中”,这话可用到当前的意识研究上。意识总是跟意义相连,即使我们掌握了大脑神经的工作机制,仍然远不是完备的“意识解释”。例如,要探究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显而易见是在寻求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解释。
关于局部的、简单的意识的产生机制的研究只是意识探究中的一个角落,无论在意识研究领域中大脑科学有多热闹,产生的成果有多少,在我看来,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心智哲学整体上与神经科学只有遥远而微弱的联系。如海尔(J.Heil)所言,心智哲学的问题“要么完全处在科学的视野之外,要么部分处在科学的视野之外”。
叙事解释总体上是在寻求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并没有直接提供什么效用。只有掌握了机制才可能控制自然。掌握了链式反应机制之后,人类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核电站。掌握了脑膜炎的病变机制,医生才能确定使用何种药物来治疗。医学界至今只了解抑郁症的部分发病机制,但由此找到的药物已经大大缓解了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不过,抑郁症不同于脑膜炎,生理因素恐怕只是它的一部分原因。“我们现在可以用药物医疗抑郁”言过其实。《正午之魔》的作者所罗门本人数度陷入重度抑郁,身为病人和作家,对抑郁症的方方面面做了大量研究和思考,依他看法,“抗抑郁药帮助自助之人”,“依照我的经验,除非我们(患者)一同努力,否则百忧解也是罔效”。
无论如何,依靠机制研究取得的成就不可让我们忘记,正是在这些巨大进步的同时,抑郁症正在变得更加广泛。曾长期担任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所长的因塞尔(T.Insel)坦承,“在让数千万精神疾病患者减少自杀、减少住院治疗和提高康复率上,我们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何况,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鸦片可在临床上用于止痛,也可以让一个民族变成病夫。百忧解减轻重度抑郁患者的痛苦,这是好事;但它能让百无聊赖的人士快乐起来,这是不是好事呢?倘若“快乐丸”成为我们如何自处于世界的通用方剂呢?所罗门说,他能想象一个“药理学乌托邦”,那里的人们生活得很轻松,也许太轻松了,“以致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药物也许能够消除痛苦,但人类所需要的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消除痛苦,因为“痛苦对人类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切不可以为,增加血清素分泌才是王道,有了百忧解,我们就不需要费心去在叙事层面上认识个人的生活世界——而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有可能让生活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