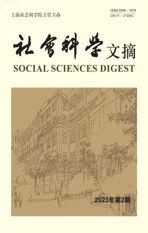人类学转向:新文科的跨学科引领
——以李泽厚、杨伯达、萧兵、王振复为例
2023-04-06叶舒宪
文/叶舒宪
新文科先驱:人类学转向
新文科建设近年来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自上而下之方针,相当于高等教育的文科改革的国家策略,其现实意义在于突破西学东渐以来所有的文科设置唯西学马首是瞻的全盘照搬局面。这一方面需要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隔阂,鼓励文理交叉和文科各学科间的交叉,以激励学术创新;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面向中国本土现实,更关注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更进一步发掘中国经验。
教育部2021年3月发布《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简称《指南》),写入这样的原则:探索推进跨专业、跨学科门类交叉融合的有效路径。《指南》针对现有的文史哲艺专业划分的改革方针,有如下表述:推进文史哲之间、文史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打破原有以固化学科专业培养人的“传统模式”。可见,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学、宗教学等各个学科本位式的模式,已成为旧文科束缚学术创新发展的现实瓶颈。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有曾经倡导过跨学科研究和无学科界限(non-discipline)的呼吁和努力,都属于自下而上的突破现有瓶颈的尝试。这方面虽然成绩斐然,但是毕竟都不足以撼动由教育制度本身所支持的分科教育的模式,也就无法让广大学子走出学科本位主义的瓶颈。唯其如此,才需要来一场自上而下的文科发展大变革。分久必合,这就是当下学术发展亟待突破的大方向。
这场文科学术的大突破,需要怎样的学术理念来引领?回顾20世纪以来的当代学术史,不难看出,实际上已经有某种学术理念在引领着各个原有学科思维的突围与创新,那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观念——“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提供给学者们走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本专业领地后,某种统领意义的整合性视角。本文用“人类学转向”或“文化转向”,来标志新时期以来我国新文科发展大趋势,四位人文学科不同专业的专家及其著作——李泽厚《说巫史传说》、杨伯达《巫玉之光》、萧兵《玄鸟之声:艺术发生学史论》和王振复《中国巫文化人类学》,即是“人类学转向”现象在文史哲艺和文博考古学科中的代表。
文化自觉与华夏文明根性探寻
巫史问题、巫玉问题和广义的巫文化问题,是新时期以来文科研究的新亮点。哲学学科的李泽厚、文物考古学科的杨伯达、中文学科的萧兵和王振复,在共同的问题意识驱动下,拓展各自的研究方向。他们的人类学转向路径可被概括为:李泽厚的“巫文化视角与中国思想史视角的融合”,杨伯达的“巫文化视角与中国特色的玉文化研究的融合”,萧兵的“巫文化视角与文艺起源研究的融合”,王振复的“巫文化视角与中国文化关联性的理论研究”。
(一)李泽厚:巫史
李泽厚早年研康德哲学,后成为当代影响力广泛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名家,晚年时关注点转移到康德最看不起的非理性的巫术方面。他希望通过对巫史传统的认识,找到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性所在,相继写出《说巫史传统》(1999)、《论语今读》(1998)和《由巫到礼释礼归仁》(2015)。他意识到,中国思想传统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人上帝的观念,也不存在类似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等。儒家的仁学,其侧重点在现世社会的人情。“情本体”本来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过多的玄秘。他关注作为原始宗教的巫术,如何先转化为周礼,随后又在礼崩乐坏语境中再度转化为儒学,希望借此梳理出儒学思想内蕴的宗教性品格。
《说巫史传统》指出,所有原始民族都以巫的宗教实践为特色,但对西方文明而言,其巫术后来明显分化升级,一方面变成科学,另一方面变成宗教。从希腊到近代,哲学思辨总是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由巫史传统催生出的中国思想,不同于西方纯粹的形而上思辨传统,而是信仰、情感和理性糅合在一起的华夏传统。
李泽厚的这些观点,比亦步亦趋跟随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而大讲中国古代思想如何实现“轴心突破”的余英时等高明。在挪用西方哲学理论模式方面,首先要清醒地洞察本土国情的实际。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混淆中西文明的不同语境。但是,因为缺乏一个本土神话学视角的语境化理解和诠释,华夏的信仰世界的存在,也就被“由巫到礼”的进化论理论模式,事先解构掉了。文学人类学派对此已经做出本土立场之质疑:若不能从每个文明特有的神话信仰观念入手,就无法有效理解该文明的核心观念,包括宇宙观、价值观和生命观。
神话观念决定论,指每一个文明的文化原编码始于其特有的神话信仰和观念。李泽厚在反驳中国古代思想“突破”或“超越”时,认为古代思想与原始部落思想一样,具有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特点,这样的判断在理论上能够说得通,但是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则很不利,似乎与认识中国文化根性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容易落入殖民时代以来某些西方人类学家(如《原始思维》的作者列维—布留尔)将中国传统等同于原始思维传统的做法。这方面的认识关键,不在于如何强调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在于像人类学家逐个解读部落社会那样,找出每一种文化自己特有的神话信仰和文化编码逻辑。
(二)杨伯达:巫玉
如果说李泽厚是从“道”的立场看待华夏巫史传统,那么杨伯达的《巫玉之光》则要将巫史这个文化寻根视角完全应用到对上古之“器”的研究。他提出,文物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器物挖掘、器物形制源流和玉石材质鉴别方面,需要引入人文关怀和信仰驱动的文化解释学研究视角。杨伯达和李泽厚一样,主要通过借鉴美国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的著作,开启自己的人类学转向之旅。
《巫玉之光》卷首的导言副标题是“以‘巫书’释巫玉”,所谓巫书是指《山海经》。他认为“玉神物也”这句话最重要,指出了玉的独特功能。他对玉神物这一要领作出三点解释:(1)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2)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杨伯达提出,华夏国家玉礼器的直接源头,就是史前宗教所崇拜的对象——玉神器。他认识到的玉文化另一个重要的宗教性内涵,便是“巫以玉事神”。李泽厚对巫史的关注焦点在于从巫到史的演进,以及巫术礼仪的理性化改造方面,而杨伯达则要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先于文明国家的史前时代。书中提出玉文化发展三段论,也是参照人类学的进化论模型而来,他命名为“巫玉—王玉—民玉”。而巫玉作为玉文化的开端阶段,其文化基因的意义非同一般。
杨伯达晚年有两部巨著问世,即《中国史前玉文化》和《中国史前玉器史》。这两部书都将研究的范围聚焦到“中国史前”,因为这正是充分体现玉文化发展三阶段中的初始阶段,即巫玉阶段。唯有在这个时期里,前文明国家的巫教社会特质,才表现得最为充分。
以河南灵宝西坡21世纪新发现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玄玉玉钺为标志,一个比夏王朝还要早一千多年的中原玉文化曙光期,从距今五千五百年一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这就是文学人类学团队完成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玉成中国”系列著作的第一部《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的成果。可以说,杨伯达先生开辟的史前中国玉文化史体系研究,不仅在文学人类学派这里得到继承和发扬,而且从巫玉理论再出发,更进一步提升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理论系统。
从一万年的超长时段看,中国统一的历程先后经历过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玉文化的统一,这也是玉石神话信仰及以玉祭神礼仪行为的文化认同过程,完成于距今四千年之际;第二阶段的统一是以甲骨文为首的汉字书写符号的统一,完成于距今三千年的商周时期;第三阶段的统一才是秦帝国的军事和行政版图的统一。由此可见,人类学转向带来的中国历史认识的大变革,既包含历史深度方面的变革,也包含百年中国考古的系列新成果。
源于李泽厚《美的历程》和《说巫史传统》的华夏文明传统大反思,到杨伯达《巫玉之光》和《中国史前玉器史》,再到文学人类学派的《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和《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这场学术的接力赛已经持续数十年,目前仍然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三)萧兵:巫傩
萧兵早期著作《楚辞与神话》(1987),就包括《巫咸为太阳神巫考》《黄帝为璜玉之神考》《西王母以猿猴为图腾考》等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明丛书”中,萧兵贡献了一部专研巫傩文化专著,题为《傩蜡之风》(1996)。90年代初,李泽厚先生大胆收录萧兵的著作《楚辞文化》,并纳入他主编的“美学丛书”。
2019年,萧兵推出煌煌三卷《玄鸟之声:艺术发生学史论》,是研究艺术起源的理论性著作,提出“艺术发生于学习及其成果的展演”命题,为已经众说纷纭的艺术起源大讨论,再添一种假说。人类学转向在他这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优势。他本人的学术兴趣不是在学院派的课程里培育出来的。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高校中,文史哲艺术专业内部一般不会有师资去开设文化人类学的课程或传授相关知识,而国学的文史研究传统自身中也并不包含巫文化的内容。若不是学者自发的持久努力,文学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等新兴交叉学科都不可能在旧有的学科格局中涌现出来。
(四)王振复:巫文化
与萧兵同属于中文专业的王振复,在2020年出版的《中国巫文化人类学》中,声称是“以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治学”。这一倾向开始于其早期著作《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他要从原始“信文化”入手展开,总括人类史前文化共性为“三维动态结构”说,即神话、图腾、巫术的三足鼎立格局,并以此作为宗教文化之母。从学术史视角看,王振复的“三维动态结构”说,可以视为本土学者对国际上人类学研究史与宗教史学方面已有的代表性观点的再整合。
在将此三维结构论框架运用到中国文化研究时,作者强调巫性,将其视为中国文化的原始人文根性作用所在。巫性的社会行为形态,表现为拜神与降神、媚神与渎神的背反与合一。他辨析中国文化的神的观念,认为其中蕴含着鬼与气的意识成分,因而与西方宗教的上帝观截然不同。他尚未涉及的,是从巫术信仰到拜物教信仰的本土宗教衍生与进阶过程。在此种学术空缺的意识作用下,笔者尝试撰写《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将一般化的巫文化理论与巫玉理论,提升到中国史前国教信仰的高度,从中梳理演进变化的脉络和规则。
王振复新著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是巫性文化与中国风水学说的内在关联研究。他认为中国巫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为类比思维。类比发生在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之间,自然而然会产生出神话的风水观。他还指出,风水文化作为中国巫文化,在人与环境之关系上是对于自然神灵与命理的一种迷信,但风水理论与实践中蕴含了一些朴素的生态环境意识。这也是具有当下意义的研究主题。
从比较文明史的对照看,所有的文明古国无一例外,都是在浓重的神灵信仰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催生出的。这就构成一般而言的文明共性:文明不是伴随理性和科学而来的,而是伴随信仰和神话而来的。不过,关键的难题在于,如何细致入微地区分不同文明的神话信仰之特点,尤其是确认和聚焦到唯独本土文明拥有而其他文明所无的文化特质方面。窃以为玉石神话信仰驱动的玉文化一万年持久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方面。而这也恰恰是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完全忽略的。
讨论与总结:新文科的创新引领
通过回顾四位本土人文学者的研究道路转型,可以表明新文科的先驱性探索和尝试,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界就已经存在,并且以某种不约而同的方式在文科各个专业领域中展开。正是人类学转向,给大家带来对学科本位视野的突破效应。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相比,在创新引领方面具有理所当然的优势,但是交叉学科的倡导者也自然面对比常规学科的学者们更大的学术阻力和现实困难。
20世纪后期以来,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诸如文学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还有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似乎人文社科中的所有学科都可以和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发生交叉,滋生出新学科。
唯有打破原有学科是不可侵犯的本位主义成见,创新引领的作用方可达到新文科实践者的自觉意识。自西学东渐以来,学科划分问题是最常体现西方观点的场合。本土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正在改变原有的学科设置,也促进着本土学人走出学科本位局限,与时俱进地补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如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理论等。文学人类学派希望将史前文化与华夏文明史传统对接成一个不间断的文化编码再编码整体,其溯源性的深度认识程度达到一万年的超长时段,这样能给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全程研究打开新思路。
过去五十年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经历文化人类学辐射性影响并完成学术范式转向的同时,文化人类学自身也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学术转型,即从早期进化论学派的效法自然科学模式,转到逐个地认识和解读特定文化的文化阐释学方向。更加具有改变三观作用的边缘学科效应,是来自体质人类学或称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从人类基因组的大数据方面重新看待人类文化和种族、族群分布源流的全新知识体,正在形成和完善之中。一个能够真正兑现文理交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新文科的早期先驱实践者们所集中关注的巫术或巫文化问题,也在方兴未艾的萨满文化研究大格局中获得知识更新与理论提升的契机。这将是文科学者接纳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以来的超长时段相关新知识,从而再造基于大历史、大传统观念的研究范式之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