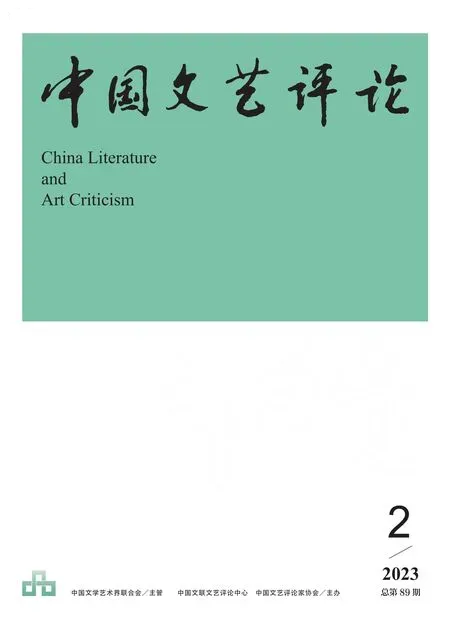2022民间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求
2023-04-06毛巧晖
■ 毛巧晖
2022年民间文学的研究依然是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文化主体、文本结构与形成、民间文学与社会记忆、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传播方式与传播语境,以及近年来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对外传播、民间文学的资源转化与当代价值等为主[1]本年度民间文学研究相关论著与文章非常多,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目力所及,著作近百部(以读秀学术搜索为主),文章有近3000篇(以中国知网检索为主,以“民间文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各个门类如故事学、神话学、史诗学、歌谣学等只是在论述中检索)。当然这并不是全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全部列出,只是在相关引用中列出注释或引文。另外,本文在相同话题的文献罗列中,以发表时间为序。,兼顾田野与文献、文本与语境,同时又推进了在媒介传播、文化符号及影像实践等领域的探索。从本年度研究成果来看,民间文学领域无论在学科建设、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实践研究层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一、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凸显
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一直有着文本与田野的分野。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人们曾专门讨论过文本与田野对于民间文学的不同意义,面对过度依赖田野调查、疏离文本的现象,也曾提出过“文本”转向或“告别田野”。2022年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结构、形成及民间文学独特的文本观进行了集中阐述,并在原有民间文学文本阐述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民间文学的“文本”与书面文学不同,它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文本搜集为第一步。从北京大学搜集歌谣开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一直是研究的重头戏。只是不同时期,搜集整理的发起者或群体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搜集工作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文学的研究。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意识到民间文学注重田野调查或搜集工作,并未推动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学术式微。面对此情形,部分学人呼吁“回到文本”。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到了2022年,民间文学文本从概念到理论都有了推进。
首先表现在民间文学不同文类的研究中,都有对文本的阐述与讨论,这为理论层面的总结提供了基础。故事学领域一直就较为注重文本的分析,既有历时分析,也有对共时(结构)的阐述;既有从文献中梳理文本的起源,也有在文献与口传文本的比照中梳理文本演化的进程;形态学、情节、类型、母题等理论运用及推进,不仅促动了故事学的发展,也对其他文类具有借鉴意义。本年度故事学领域文本研究值得提出的有对“文本”类型的拓展,如对视觉化故事文本《寻梦环游记》《玩具总动员》等进行故事编创法则、故事范型的分析与阐述。[1]参见施爱东:《〈寻梦环游记〉的角色配置与游戏规则》,《民族艺术》2022年第1期,第34-46页;朱家钰:《〈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的稳定性与变异性》,《民族艺术》2022年第1期,第47-55页。对故事的计量单位“核心序列”的阐述,指出它既是故事独立存在的根本,也是文本可持续发展的单位。[2]参见王尧:《论民间故事的计量单位——核心序列》,《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第140页。神话学领域在文献梳理、母题研究方面一直成果较为丰富,如王宪昭对神话母题的持续梳理与撰写[3]王宪昭近年来完成了一系列神话母题的梳理与撰写,成果较多,不再一一列举。;再就是近年来神话学注重“朝向当下”,除了关注传统神话文本外,在游戏、网文、有声读物、动漫等领域的拓展,极大拓宽了人们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知[4]参见谭佳、许雨婷:《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以综神话现象为例》,《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4-33页;周刘春:《神话叙事在影视动画中的当代重构》,《新美域》2022年第1期,第84-86页;杨利慧:《从“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到网络民族志——当代神话研究方法探索30年》,《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第5-13页;张多:《重估中国神话“零散”之问——从典籍到数字媒介的神话谱系化实践》,《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78-185页。;另外则是神话学领域对图像文本的关注,如对汉画像日月神话时间观的阐述[5]参见朱存明:《论汉画像“日月神话”图像的时间观》,《美术大观》2022年第4期,第96-102页。及利用南北朝皇族墓室壁画对“天命”和“不死”神话叙事体系的解释[1]参见王倩:《“天命”与“不死”:南北朝皇族神话叙事体系》,《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91-96页。。史诗学对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范式曾起到革命性意义,如口头程式理论等,本年度史诗文本研究集中于口头文学文本接受不同于书面文学的文本之“新生性和开放性特征”[2]参见朝戈金:《论口头文学的接受》,《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第5页。,及文本的经典化、文本与演述传统的互文和传承等问题[3]参见王艳:《格萨尔史诗的经典化建构刍议》,《文学遗产》2022年第2期,第22-33页;乌•纳钦:《〈格萨尔〉史诗新歌手及其文本的互文性》,《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7页;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悲剧的力量:〈玛纳斯〉史诗的传承动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03-110页;斯钦巴图:《论史诗的内部张力与〈江格尔〉类型群的形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1-117页。,尤其是对于石刻、壁画、雕塑、插图等史诗图像文本的跨文化流传应引起民间文学其他门类及文学领域的关注[4]参见陈明:《印度两大史诗的图像呈现与流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8页。。传说学近年来提出的仪式文本拓展了民间文学的文本样式,也进一步阐述了文学与信仰的关系。本年度传说学领域除了对传说圈、传说与历史(或社会记忆)、传说与地方性知识等研究外,仪式文本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对明清教派宝卷中仪式文艺叙事情节与功能导向的论述,彰显了仪式文艺情节与功能的独特性及考证《崔府君神异录》在崔府君信仰传播和传说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文本定型的关键作用。[5]参见程浩芯:《信仰传说的文本定型——〈崔府君神异录〉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64页。民间文学其他文类对于文本的研究也取得了推进。如以往的谚语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学或文化学领域,但本年度对社会类谚语中反义谚语的阐述拓展和丰富了谚语文本所呈现的社会观念的多样性。[6]参见安德明:《反义谚语:一个探究中国谚语的新视角》,《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第90页。
其次,除了各门类文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外,本年度从理论层面阐述与总结了民间文学的文本观。民间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从其兴起之时就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但大多论述以书面文学为标准或者以书面文学的标准建构民间文学文本。早在2013年已有学者提到建立民间文学文本学,希望能确定相对统一的标准将各类文本都纳入文本谱系,以发挥民间文学文本应有的美学功能。[7]参见陈泳超:《倡立民间文学的“文本学”》,《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115页。但是后续的研究中这一话题并未取得理论上的推进。本年度发表的《口头文学的文本观》[8]参见朝戈金:《口头诗学的文本观》,《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第21-34页。可以说是综合了劳里•航柯、弗里基于史诗的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分类基础上,在与书面文学的比较中提出口头文学文本的整序接受、书面记录文本所具有的口头和书面的双重特征,以及其彼此之间的言文互缘、文人创作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所具有的言文桥接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口头与书面文本联结、共性的阐述,不是在区别中理解口头文本的特性,而是在共性中实现口头文本的辨识度。这可以说是近年来口头文本观的一次总结与理论阐释,当然尚有继续阐发的空间,而对于言文互缘、言文桥接还有待进一步实现话语传递,也需要在不同文类研究中检验其效度。另外,文中还提到口头文本各文类以谱系共存于一个文化系统中,这与阿兰•邓迪斯在《亚文本、文本和语境》中提出的:只有结合亚文本、文本和语境三个层次的分析,才有可能实现对民俗文类的准确定义,进而定义民俗自身[1]参见[美]阿兰•邓迪斯:《亚文本、文本和语境》,谢亚文译,《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第25页。,有着理论连续性,同时在两者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文类划分都无法离开社会生活(或语境),也看到了我们对口头文本的阐述在中西理论衔接与转化中逐步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最后,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并未与实践割裂,而是注重在实践中阐发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民间文学现在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传承方式都有了极大变化,在大学生民间文学戏剧节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创意表演形式中,故事文本依然是核心,只是故事文本以“演述”的形式,而不是“阅读”的形式在接受者中传播,这有助于民间文学文本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演述与文化传统。[2]参见隋丽、沈莉:《民间文学日常生活审美化实践的路径探索——基于大学生群体的民间文学转化实验》,《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7页。这其实与上文所述口头文本是在演述中生成的理论相契合,同时也在当下民间文学传承实验中进行了一定的验证,当然后续如何目前尚无法确定,希望能有相关个案的长期追踪。
二、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进入21世纪,学科归属问题一直制约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在兴起之初,两者并未有学科割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学科体制建设,民间文学成了学科名称(当然其中亦有名称变化,如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文学等)。新时期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恢复,两者的研究群体主体是合一的,也就是常说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是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引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出现一定的区隔与差异。后来随着教育部学科调整,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归入社会学,而民间文学的研究群体大多在文学领域,这就造成了对民间文学学科归属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呈现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思考。
本年度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回顾中展开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者希冀从学术脉络的呈现中,整理出基本话语、基本问题的谱系,为当下学科问题的回应与反思提供借鉴。2022年学术史研究涉及对著名学者研究的学术回顾,如经过梳理胡适对康德、杜威自由和民主理念翻译接受过程对现代民间文学兴起的影响,以及对董作宾歌谣学研究、陈寅恪和钟敬文故事学研究、顾颉刚民俗学研究等的反思,探讨其与当下学术话语、学术问题对话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1]参见户晓辉:《发端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以胡适与康德、杜威的侨易关系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1期,第27-36页;施爱东:《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146-154页;漆凌云:《陈寅恪民间故事研究述评——兼论民间故事起源研究》,《民族艺术》2022年第5期,第42-52页;董晓萍:《民俗学中国化的一块基石——论钟敬文的故事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第50-67页;王杰文:《超越“文字中心主义”——重估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方法论》,《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第95-102页。本年度学术史回顾中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围绕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所展开的讨论。民间文学领域对《讲话》精神的回顾,既是梳理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延安传统,也是在学术脉络中总结民间文学文学性的时代话语。1942年,《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对文艺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民间文艺因为与民众的天然联系,成为联结文艺与民众、普及与提高的重要方式。文艺创作者积极加入民歌、民间故事等的采录,同时也借鉴与利用民歌、说书、秧歌、民间故事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进行创作。《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围绕张霖的著作《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展开研究,笔者与杨天舒、李超宇从通俗化实践、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民众中特殊群体“调皮鬼”和“正经人”的论述回顾了《讲话》对民间文艺、大众文化的重构与再造。这次笔谈中,参与人并未刻意划分民间文学、通俗文艺、作家文学,倒是重在三者弥合中探讨20世纪30至50年代所进行的通俗文艺改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潘鲁生《民间文艺发展的现代化创构之路——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理论与实践导向》强调了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文艺方针对于“民间”内涵的改写与重构的引领与指导,而“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理论和实践的自觉与指导意义上构建和深化了新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的‘民间’传统,指导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并不断实现民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发挥了定向纠偏、引导促进的重要作用”[2]潘鲁生:《民间文艺发展的现代化创构之路——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理论与实践导向》,《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第59、67页。。在对民间文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史回顾中,董均伦、周文、柯仲平等进入研究视野。《董均伦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研究》《周文的民间文艺思想研究》《理性与激情:论柯仲平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探索》梳理了董均伦、周文、柯仲平三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采录在承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拓展“文艺”的通俗化实践。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史上的典型个案,通过对他们研究历程的还原性历史分析,有助于推进对民间文学本土话语生成、嬗变的理解,也对延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纳入文学研究的脉络、机制有所了解,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间文学史上采风、搜集整理、田野作业话语的嬗变。[1]参见毛巧晖:《董均伦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第7-15页;杨培源:《周文的民间文艺思想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第16-23页;刘思诚:《理性与激情:论柯仲平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第24-33页。
其次,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本学科,而是在现当代文学、美术、舞蹈及当下兴起的群众文化等领域亦有提及。《作为方法的“集体创作”:从民间传说到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论述了左翼文学的写作传统、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政治要求以及自身的优越性等,共同促成了歌剧《白毛女》采用集体创作方式进行文本再生产。[2]参见贺滟波:《作为方法的“集体创作”:从民间传说到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东方论坛》2022年第3期,第147页。《走向革命的民间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红色故事对党的形象的塑造》主要讨论红色故事如何以“服务群众”和“为民而战”为切口构筑党的政治形象与军事形象。[3]参见潘振颖、江烜:《走向革命的民间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红色故事对党的形象的塑造》,《粤海风》2022年第5期,第62页。《民间元素与延安文艺大众化》从文艺导向、创作主体、大众化实践三个方面阐释延安文艺大众化中对民间元素的重视和吸收。[4]参见江守义:《民间元素与延安文艺大众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26页。《论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的本土经验》聚焦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运动,讨论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如何为中国新文学积累了宝贵的本土经验。[5]参见钟海波、李继凯:《论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的本土经验》,《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53页。此外,还有对“群众写作运动”[6]参见张慧瑜:《以写作为媒介:基层传播与群众写作运动——以晋冀鲁豫根据地李文波营长写作为例》,《新闻春秋》2022年第3期,第19-27页。“延安新秧歌剧创演”[7]参见周维东:《“运动”中的文艺法则——从延安时期“二流子改造”运动看新秧歌剧创演》,《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第100-112页;曾沁涵、曾荣:《“斗争秧歌”与延安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的生成》,《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6-24页。等话题的讨论。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的学术史梳理相较于“十七年”时期,难免带有一定的陌生感,但正是由于这种距离感的存在,无论是搜集整理、口述追忆还是考释研究,学者都能够从相对客观中立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与反思。
再次,民间文学文学性探讨的另一话题主要集中于故事诗学。2020年开始,刘守华提出了故事学的一个新方向——故事诗学,这一话题主要是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故事学方法开始走向多元化后,传统的文艺美学批评在故事学领域被悬置的思考。[8]参见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02-110页。故事诗学引起了故事研究者的关注,但是成果并不多,本年度主要有对兄弟纠葛故事和撵城隍故事的分析,重在对故事文本的精神品格和艺术化进行表达。[9]参见胥志强、张素素:《兄弟纠葛故事的诗学分析》,姜帅杰、晓苏:《神的脱冕与心灵的休憩——撵城隍故事的狂欢化诗学研究》,均发表于《歌海》2022年第1期。这一话题的集中讨论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学理论建设”研讨会上,刘守华对故事诗学的思考作了进一步强调与拓展,阐述了自己所提出的故事诗学的理论来源,即叶•莫•梅列金斯基及文艺学、美学的批评方法,希望能注重对故事选本的审美原则的探讨,也希望研究能回归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家园。孙正国强调了故事诗学对于故事研究回归文学的学科立场及希望能逐步建构故事诗学的理论体系。[1]参见荆楚网:《学者研讨新时代中国故事学理论建设》,2022年7月13日,http://cul.sohu.com/a/566854402_119861。
最后,本年度对民间文学文学性进行的讨论还集中于民间文学领域的诸多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学人就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检视及近年来的发展趋势都有涉及,如中国民俗学年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等设置了“神话纹理:神话叙事多样性的生成机制”“讲述的力量:民间故事研究与土地情怀”“八仙过海:古典民间叙事和古代民俗的流变层累”“图文互显:图像文献世界里的民俗”“口头诗学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研究”“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等专场。集中讨论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主办的“新时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会议围绕“民间文学的理念基石”“回归本体的民间文学学科范式检讨”“民间文学的学科路径与学术进路”等话题展开讨论,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民间文学概念与基本特征的当代适用性及基于文学性的学科建设、学科分类、学科路径选择等。[2]参见华东师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会议简讯 “新时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微信公众号“华东师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2022年12月14日。
三、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与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民间文学的记录在中国兴起得很早,但是现代民间文学的兴起则与西学引入直接相关。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从其兴起之时,其实就无法脱离中国学术的河床,同时学人在接受中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色。这些既是理解中国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文化根基,也是吸纳和转化西方话语和理论的基础。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中开始注重民间文学本土话语梳理,希冀能通过对本土话语的回顾呈现中西话语的对接与错位及其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在本年度的研究中主要有对“采风”“民俗志”“风俗”的讨论。
采风是中国传统的文学采录方式,“不是为了如其本然地记录、再现民间口头传统的声音模式和表演场域,而是为了把它们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记录、保存下来”[3]刘宗迪:《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58页。。在20世纪初期至80年代,资料的搜集采录方法似乎没有引起太多争论。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之后,采风被置于“科学的田野作业”的另一端。但长期以来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置,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2022年,关于“采风”“采录”“整理”等本土话语经历了从技术术语向文明生产模式的转变,虽然讨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但众多研究成果的出现足以引起对“采风”的重新思考。如《采风: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变》[1]参见祝鹏程:《采风:一种文明生成方式的古今流变》,《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第17-28页。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2]参见祝鹏程:《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第23-31页。认为采风承担起了将传统小社区中的“乡民文艺”转化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文艺”的使命,寄寓了新中国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产生全新的文艺生产主体的理想。当下学界对采风的部分批评有将其窄化之嫌,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历史语境中去,将采风视为一种主体生成方式和文化实践方式,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主要梳理了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认为只有回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3]参见毛巧晖:《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第5-16页。
“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在民间文学领域,民俗志的记录和书写方法一直处于重要位置,学人们早已有关注,本年度更多是围绕这一本土话语的研究与争论,为本土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路径。如《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提出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4]参见王霄冰、陈科锦:《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第94-107页。研究者主要围绕民俗志书写“标准”“主体”“视域”等问题展开论述,如《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通过对《浙江通志•民俗志》与《陕西省志•民俗志》的比较分析,指出民俗志的编写,最关键的是记录经验世界的鲜活民俗[5]参见张世民:《广域民俗志的学术评估和书写判断——以〈浙江通志•民俗志〉〈陕西省志•民俗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4期,第14-24页。;《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可能性及反思——以云南大理石龙村李绚金村民日志为例》提出地方精英日志书写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果能够较好地实现民俗主体参与并主导民俗志写作的需求,既回应了民俗学“朝向生活”的实践转向,又能在当下的“民俗乡建”中承载起传承村寨记忆、维系村寨传统的重要作用。[1]参见董秀团:《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可能性及反思——以云南大理石龙村李绚金村民日志为例》,《民俗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7-156页。
风俗是中国自古就有的语汇,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与生活特性的词语概括”[2]萧放:《“风俗”论考》,《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届网络学术会议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关于“风俗”与“民俗”的讨论自古就有。20世纪初,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民俗”地位上升,“风俗”地位衰落。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关于“风俗”与“民俗”的概念辨析,本年度日本学者岩本通弥的《“民俗”概念考》主要梳理了柳田国男在不同时期对“民俗学”这一名称的理解及日本“民俗学”的诞生。[3]参见[日]岩本通弥:《“民俗”概念考》,吴薇译,王晓葵校,《遗产》2022年第1期,第49-99页。《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梳理了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围绕“风俗”与“民俗”的交替、“史学根性、主体性及国家性”等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4]参见岳永逸:《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71-182页。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除了概念辨析与史学脉络梳理外,2022年对风俗的论述还将其置于中国古典知识系统,提出以风俗为遗产,将民俗学从具体经验研究拖入到超越性理念的范畴,并强调正视以“风俗为天下”的中国古典知识系统,对扩展民俗学的未来前景具有重要意义。[5]参见鞠熙:《天下与遗产:中国古代风俗学的两种面向》,《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8-115页。此外,围绕“风俗”的讨论还跳出了本学科范畴,逐渐与图像、节日、宴饮、医疗相联系。如《民国纸媒中的风俗画——〈北洋画报〉连载陈师曾〈北京风俗画〉册页的若干史料钩沉及分析》论证陈师曾在绘制《北京风俗画》时深受“到民间去”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以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平民化的风俗画题材回应了“眼光向下”的现代性命题[6]参见刘卓:《民国纸媒中的风俗画——〈北洋画报〉连载陈师曾〈北京风俗画〉册页的若干史料钩沉及分析》,《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第57-67页。;《中国古代风俗画的基本内涵——以农事风俗画为切入点》通过农事风俗画《豳风图》和《流民图》,阐释了风俗画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记录方式的社会价值及历史价值[7]参见施含牧:《中国古代风俗画的基本内涵——以农事风俗画为切入点》,《美术大观》2022年第4期,第18-33页。。在关于节日、宴饮风俗的讨论中,《敦煌节日风俗所见多民族文化交融》从晚唐五代出发,论述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在寒食节、二月八日、赛神、燃灯等节日风俗活动之中所形成的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民族和文化格局[8]参见魏迎春、朱国立:《敦煌节日风俗所见多民族文化交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25-34页。;《礼俗之间:宋代的宴请礼仪与风俗传统》聚焦宋代以宴请活动为中心而承载的社会礼俗,从宴请筹办、迎宾待客到席间秩序等方面展开研究[1]参见纪昌兰:《礼俗之间:宋代的宴请礼仪与风俗传统》,《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56-64页。。此外,还有《医疗、风俗与信仰:清代巫医的社会活动探究——以岭南为中心的考察》围绕清代岭南巫医对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参与,阐释其在地方医疗、风俗与信仰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参见刘梦雯:《医疗、风俗与信仰:清代巫医的社会活动探究——以岭南为中心的考察》,《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1期,第45-52页。
对民间文学本土语汇的梳理,近年来才引起更多学人的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有学者致力于对民俗学本土化的探索[3]参见秦文硕:《民俗、俗道与礼俗:许地山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礼俗转向”》,《民俗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6-135页。,只是之后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都更关注理论的“社会科学化”,并将其视为研究的“创新”[4]参见王铭铭:《新中国人类学的“林氏建议”》,《读书》2022年第5期,第11-12页。。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引入其他学科及国外的话语、理论等,出现了理论与民间文学基本问题的脱节、将民间文学作为材料注解其他学科和西方理论等现象。本土语汇的梳理对生发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的推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四、探求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
有关学科及其研究对象的价值研究不仅关乎学科存在的正当性,亦与学科危机密切相关,因为学科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源自从业人员基于特定问题意识对学科自身“存在价值”(正当性)的反思。[5]参见张多、祝鹏程、李向振、惠嘉、张青仁、梅东伟、孟令法:《回返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青年谈》,《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4期,第18-33页。民间文学接续学科发端的价值理想不仅有学科内在的必然性和它作为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也有基于时代的必要性。就此而言,接续“五四”传统为学科的正当性辩护,不仅是对蕴含“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与践行,也是推动民间文学参与国家的现代文化建构,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路径。民间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领域交叉,在遗产化语境中,民间文学的价值内涵被挖掘与凸显,同时民间文学也成为旅游或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活化或整合的重要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构建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之一。2022年度民间文学领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更加注重其形成的具体脉络。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一方面是从宏观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建构的阐述,如从“诗骚传统”与“史诗”的会通,论述了文学共同体观念构建和中华文学史话语体系的重构,同时强调这一话题也涉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现实意义[6]参见韩高年:《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第35页。;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视角审视不同民族戏剧的特点和内在联系,揭示在各民族共存共生背景下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1]参见黄永林、高艳芳:《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少数民族戏剧理论研究(1978—2000)》,《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页。;从多民族共享的生活内容与文化实践出发,阐释其对形塑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作用[2]参见王丹:《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48页。;等等。另一方面则是结合个案和具体实践所进行的论述,如通过对九隆神话流传和传播脉络的梳理,阐释其背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根谱,透视在“龙”叙事下的向心凝聚[3]参见刘波:《从九隆神话看藏羌彝走廊龙崇拜的迁播与民族文化的交流》,《民族学刊》2022年第2期,第118页。;对西南少数民族围绕诸葛亮传说及景观叙事所形成的递进式中华文化认同的阐述[4]参见熊威、刘文静:《西南少数民族诸葛亮传说及景观叙事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第127页。。无论是宏观理论层面还是个案实践,这方面研究可以说在本年度民间文学论著中所占比重并不少,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研究者关注多民族共享的民间叙事资源,大多也是在文化交流交融中阐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但是此类研究也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并未有太多理论上的提升。
2022年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文学的价值重塑也很受关注。如通过对历史故事与民众历史记忆、历史价值观关系的阐述,指出故事的社会价值及民众用自己特有的言说方式与思维逻辑所表达的对“善”的追寻。[5]参见张琼洁:《民间文学口述历史活动的言说机制与价值观念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2期,第59-69页;廖建媚、陈萍:《民间体育故事的记忆载体、社会价值与传承路径——以戚继光藤牌抗倭故事为例》,《体育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17-21页。本年度在这一话题的讨论中,还有通过对国外民间文学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的借鉴反观自身,即《泰国民间文学的当代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一文所提到的“泰国民间文学”,认为其传统性和现代性和谐相融的动力源于泰国民众对习俗文化的践行和学界的文化自觉行为,这可以为我国民间文学价值重构提供借鉴经验。[6]参见刀承华:《泰国民间文学的当代审美重塑与价值重构》,《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79页。
关于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的讨论还包括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如何挖掘民间文学的内涵,为乡村振兴提供内源性动力等议题。随着国家发出重建乡村生活的号召,对民俗、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引起了社会各层面的关注,但是对民间文学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本年度虽然有一些文章,但要真正找到适合的路径及重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实践与长期跟踪。[7]相关文章非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此外,讨论较多的是融媒体语境下民间文学资源的转化和发展。随着融媒体时代的来临,民间文学呈现出融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丰富样态,其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场域及审美表征均有所变化。[8]参见毛巧晖:《民间文艺如何在融媒体语境下自我重塑》,《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7期,第48页。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些新的方向与途径。如《民间文学影像化再演述的策略与价值》中谈到民间文学影像化再演述在创造性转化的策略上,呈现出人物的多元与嬗变、空间的现实与奇幻再造以及传统与当代意蕴重构的特征;在价值观念上,诸多改编自民间文学的影视作品则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本土与全球的桥梁。[1]参见陈金梅、梁家胜:《民间文学影像化再演述的策略与价值》,《文艺评论》2022年第2期,第122页。再如从白蛇传、志怪文学、敦煌壁画中的雷公击鼓图等,从图像史料学、新媒体文化研究等出发,在主流民间文学研究之外勾勒出更为丰富的理论版图,显示出一种学科交叉的生机与活力。[2]参见崔芃昊:《从“白蛇传”的重写现象考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1930—1949年)》,《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42-50页;陈旭光、刘之湄:《“白蛇传”系列电影: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想象力消费”》,《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5期,第78-87页;江秀廷:《巫鬼传统的叙事演进与文化心理嬗变——从六朝志怪文学到网络恐怖小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第148-158页;刘文荣:《文本、图像与音乐——敦煌莫高窟壁画雷公击鼓图的源流、表现与民间文化内蕴》,《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58-72页;等等。还有研究者立足于民间文学本体、使用不同方法分析情节、结构、叙事与价值旨趣,并引入“景观”“风景”等理论话语展开研究,如对当代实景演出如何利用“表演”和“景观”作为中介,将经典文学文本“跨媒介”地转化为综合性艺术形态并与地方文旅IP相互链接[3]参见王柯月:《当代实景演出中的文学资源及跨媒介转化》,《艺术评论》2022年第4期,第52页。;民间故事资源的跨媒介转化策略,推动民间故事从资源到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参见徐金龙:《跨媒介叙事:民间故事资源的转化策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08页。,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是新时代、新征程奋斗进取的全局性指导,是把握民间文艺发展方向与方法的重要指导。民间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须提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6]参见《中国民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艺术报》2022年11月9日,第1版。未来民间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推进与发展。
总之,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在延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年度特点。本文难以一一罗列所有有价值的成果,希望围绕本年度民间文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即文本研究、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讨论、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以及民间文学当代价值的探寻的阐述呈现本年度研究概貌及发展的新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