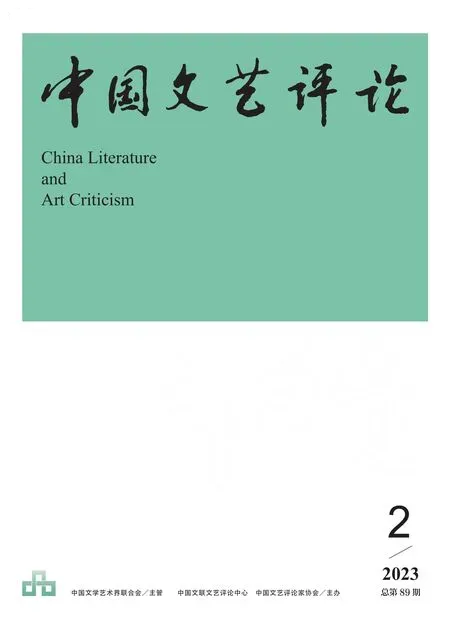论美学研究从“文艺美学”到“艺术美学”的发展之路
2023-04-06高建平
■ 高建平
最近一些年,艺术学空前繁荣,在由学科设置所造成的机制力量的推动下,研究者云集而来。一些原本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进入到艺术学研究中,出现了新一轮的走出美学的热潮,一些原本从事艺术史论研究的人聚集在艺术学研究的旗下,还出现了不少的文章,试图讲述这方面的道理。
然而,学术研究跟着既定的学科划分来作证明,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应该是学术决定学科,而不是学科决定学术。学科的发展,是为了繁荣和发展学术,而不是先确定学科,再为了说明和论证这个学科而发明学术上的道理,并根据当下的学科状况来剪裁过去的学术材料。学术研究应该面对问题本身,研究出成果来,从而有利于一个行政决定的形成;而不是在一个行政决定形成以后,论证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一、美学与艺术的关系
在对人文学科进行溯源时,我们会发现,一些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常常具有兼类的特点。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也是美学家、艺术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各门学科在写学科史时,都要追溯到这些人,从他们写起。中国也是这样。孔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艺术学家,从他一生的活动看,还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他作为万世师表,更是伟大的教育学家,其他如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都可溯源于他。同样的名号,也可放在孟、荀、老、庄等一些人的头上,这些人关于各门学科都有过著述,成为后来种种思想的源头。在那个被称为“轴心时代”的时期,许多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各方面全知全能。
此后,在欧洲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如此。中国的宋明理学家,也在各个学科史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各自出现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思想巨人,后来的众多学科在进行溯源时,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学科发展的线索。
古代思想家的全知全能特点,是由于当时的学科状况所决定的。许多后来出现的学科,在那时并没有建立起来。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不存在专门的美学、伦理学,更不存在艺术学,同样,也不存在专门的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如果说他们有哲学(Philosophy,来自希腊文的philosophia,由 philo- “爱”+ sophia “知识、智慧”构成)的话,那也是具有包罗万象的知识和学问的性质,与后来的哲学不同。那时的学问就像树干,后来的许多学科就像树枝,从这个树干上生长起来。我们撰写学科的历史,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那里溯源,就像树枝要溯源到树干以至树根一样。
但是,这种溯源也有局限性。在他们那里,学问和知识、思想和智慧是整体,而后来的人只是从中寻找某些表述,并在新的语境中进行解读而已。离开了这种原生的整体性,就常常会产生曲解。还是用树干和树枝来比喻,为树枝找源头,硬把树干切出一块说它属于某一个树枝,硬把某一个树枝与某一根树根相对应,显然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们在研究中,不知不觉地在做这种事。
除了这种古代整体性的情况外,现代人文学科的各部分之间,也具有兼类的特点。康德和黑格尔既是哲学家,又是伦理学家,还是重要的美学家,在许多艺术学的著作中,也经常提到他们。另外,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精神病医师,不仅发展出了心理学的理论,还可以在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理论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像索绪尔这样的语言学家,改变了20世纪哲学、美学和文艺评论的基本思路,形成了许多文学批评流派;更不用说,像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阿多诺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渗透到了各门人文学科之中。
关于人文学者兼类的情况,还由于这样一些特点:人文领域的一些学科,只是研究事物的某一种面向或呈现方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是在用不同的角度研究人,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本身,有着整体性,这就造成了研究者也需要通过兼类来提高研究水平。他们以为研究了人的不同面向,就接近人本身了。这种认定有道理,但在今天看来也有局限。
二、艺术是美学研究的核心
根据一般的理解,美学这门学科主要研究两个概念:美和艺术。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并列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一个变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说,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是18世纪在欧洲形成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艺术脱离了它原本与工艺的联系,获得了独立。这一追求,实际上是美学学科形成的根本动力。
美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形成,一般都从德国人鲍姆加登说起。鲍姆加登根据希腊词aisthetikos,即“感觉的”,组合成了 Aesthetica这个拉丁文词,取其感性学之意。鲍姆加登原本是在对诗的研究中来使用这个词的,他在《对诗的哲学沉思》(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de nounullis ad peoma pertinentibus,1735)一书中,以及此后的未完成的《美学》(Aesthetica,1750)一书中,试图“建立一门(主要与诗有关,但也可扩展到其他艺术之中)美学的理论”[1][美]门罗•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高建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257页。。在这本书中,他论述了美,认为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但是,他的目的还是讲述各门艺术。只是在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要从观念出发来对各门艺术进行研究,从而建立一种统一的美学。
鲍姆加登在世时,他的著作在学界认可度并不高。他在美学史上的地位,实际是后来被追认的。我们根据他对康德等人的影响,反向推导出他在美学史上的位置。Aesthetica这个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也是由于康德著作的英译,在19世纪初年被英语学界认可。
在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法国和英国在文化上有着更加重要的位置。法国美学家们没有像后来的德国人那样具有体系建构的雄心,而更加关注艺术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论题上,即艺术上的“古今之争”和各门类艺术间的关系之上。“古今之争”在法国反复出现,既体现在拉丁文与法语之争,也体现在艺术风格之争中。关于各门艺术关系的讨论,主要表现为杜博、巴托、狄德罗等一些人的论述。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诗、绘画和音乐这三个门类的艺术如何具有亲缘关系,能否构成组合。根据这个问题,形成一种对超越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一般”的思考,诗、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的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分。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学界逐渐形成共识,一种各门艺术之间既有共同的特性又有不同的特质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康德对“美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使之成为美学的核心内容。
美学以艺术为中心,在19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谢林和黑格尔是典型的代表。他们两个人都致力于艺术哲学的研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讲演录》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1][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20世纪中叶分析美学的兴起,对美学的定义变成了“元批评”,即艺术批评的批评,或者说,是对艺术批评所使用的术语的分析。这时,美学中的艺术中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18和19世纪,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在处理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艺术学研究无法避开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然美客观存在,美学研究必须面对,然而,这一时期美学的中心任务,却是区分“美的艺术”与“工艺”或“机械的艺术”,即当时的人们所说的艺术与自然。从本质上说,美学这个学科在18世纪就是为了区分“美的艺术”与“工艺”而形成的,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区分“艺术”与“自然”,从而为艺术的自律正名。
一些研究者认为,康德与黑格尔不同,康德重视自然,而黑格尔重视艺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从“美的分析”开始,这只是他的论述策略而已。他从最为抽象的“纯粹美”开始分析,接着加入了“依存美”,再分析理性与感性相互作用的“崇高”,最后还是要归结到“美的艺术”上来,分析“美的艺术”与天才和趣味判断的关系。对于康德来说,论述中的重心,最后还是要落在艺术之上。
罗纳德•赫普本(Ronald Hepburn)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当代自然环境美学兴起的重要依据。[2]参见Ronald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in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04, pp.43-62.这篇文章从欧洲美学史说起,认为美学史上长期存在着严重的重艺术而轻自然的倾向。确实,直到20世纪后期,像艾伦•卡尔松(Allan Carson)和阿诺德•贝林特(Arnold Berleant)这样一些学者,才像破冰者一样,将自然引入到美学研究中,使之成为美学的中心问题。
三、中国美学的特殊路径
美学这个学科,是1900年前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王国维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他,美学的概念以及一些欧洲重要的美学家的观点都传到了中国。
关于“美学”这个学科的译名,一般说来,是日本学者中江兆民在翻译法国美学家维隆(Eugène Véron)的书时,所作出的选择。此前有西周的《美妙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翻译。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不少的文章发表,但总体上并没有推翻由中江兆民翻译此学科名称使译名得到确立的结论。这一译名此后被日本文部省所颁布的学科目录所采用,后来东京大学设立了“美学研究室”,开始了在东亚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正如前面所说,鲍姆加登所确定的这一学科的名称,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感性学”,是在一本名为《对诗的哲学沉思》的著作中提出这个词的,后来黑格尔也说过,将这门学科称为Aesthetica并不恰当,应该称为“艺术哲学”;而既然这个学科名称已经流行,姑且就这么用而已。将之译为“美学”,只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对这个学科的理解而拟出的一个译名而已。当然,在当时日本学界选择这样的翻译,也有着自身的原因,包含了当时日本人对这个学科的理解。
中国学术界是根据日文汉字直接将这个学科名称引入的。最早引进这个词的人,不一定是王国维。关于此,有人做过一些考证。不过,在中文写作中谁最先抄录日文汉字中的这两个字,意义并不大。最早致力于在中国学界介绍美学知识,并进而运用这些知识研究美学的,则应该是王国维。王国维认真研读了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美学著作,并结合中国文艺进行研究,致力于实现中西对接,并对此后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很好的示范。他的美学研究主要还是以中国的古诗词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为中心。在当时以及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也就是说,他虽然引来了“美学”这个译名,但并没有对这门学科的名称望文生义,简单地将其理解成“研究美的学问”,而是在研究中坚持以艺术为中心。
此后,在中国推动美学学科发展的,是以艺术教育为中心的蔡元培的美育观和以“新民”为目的的梁启超的文艺观。此后的朱光潜,也是从诗歌开始他的文艺研究的。他自己强调,《诗论》是他当时最好的著作。他在那部影响最大的《文艺心理学》中,也是借助现代心理学理论对文艺进行论述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以文艺推动社会进步、救亡图存为目的,成为当时的美学最重要的特点。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美学这个学科引进中国之初,美学研究的专家们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关于“美”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探讨之上,而是在这个学科之下,研究文学艺术的问题。也正是由于此,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得到了兴盛发展。然而,这个译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不同的人对此产生不同的理解。在这个学科引入中国之初,就有着对“美”理解泛化的现象,扩展到对风景、城市、家居陈设之上,把这个学科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联结起来。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美学大讨论”。这一讨论原初的设计,是在“双百”方针之下,将美学作为进行“百家争鸣”的试验田,推动文艺思想的改造。也就是说,要通过美学的讨论,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艺术倾向问题。
这一讨论开始的标志,是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的发表。朱光潜的这份检讨所谈的是他自己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主要是指他在1949年以前,以“魏晋人”为人格理想,尊崇三本书,即《庄子》《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集》,赞美这些人的消极退隐的思想,并将之与西方美学中的“静观”“无功利”的思想结合。他认为这种思想在文艺上趋向于消极颓废,不适应20世纪50年代革命和建设的大形势,因而是“反动的”。
然而,“美学大讨论”后来并没有朝向这个方面发展,讨论的重点被转向了“美”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讨论之上,并将之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挂上钩。在当时,美学上被分为四大派,即认为“美”是主观的、客观的、主客观统一,以及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这四大派中,“主观派”从人对自然和艺术的感受出发,认为欣赏者主体在审美活动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主张后来被当作鼓吹主观唯心主义而被否定。主张“主客观统一”的朱光潜,寻找的理论根据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只强调客观因素,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美学要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主张“客观的”蔡仪,则强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认为审美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主张“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李泽厚,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美的客观性在于客观对象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于是,“美学大讨论”通过激烈的、哲学思辨式的争论,强化了美学这个学科对“美的本质”的关注,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这个学科的中心问题滑向了对“美”的探讨之上,也使这个学科名符其实地变成了“关于美的研究的学科”。
为了纠正这种美学上的高度哲学化,远离艺术的倾向,在当时,出现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形象思维”被认为是一种对艺术创作所使用的思维方式的研究。这种讨论,在一开始还有着政治正确性的因素,即在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大氛围下对俄国思想资源的接受。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再到50年代许多苏联美学家,都对“形象思维”作出过论述。这些都成为当时“美学大讨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也是对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对“美的本质”讨论的高度哲学化倾向的纠偏和补偿。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开始对“形象思维”进行质疑。人能否运用“形象”来“思维”,这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到了1966年,郑季翘的一篇反“形象思维”的论文发表,对“形象思维”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此,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消失了11年。
随着毛泽东同志1965年的一封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于1977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形象思维”讨论在随后的1978年复兴,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这对于美学重新关注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思维方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以及这个学科所固有的惯性,使得美学与文艺的关系仍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同时,在学科的归属中,美学被归入哲学之中,它的运行规律,就受着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既有思维方式和学科管理方式的制约。
四、“文艺美学”的提出及其意义
面对当时中国美学的状况,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胡经之提出了要建立“文艺美学”。胡经之原本就具有文学研究的背景,曾参加过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的写作。在1961年至1963年的那段时间里,他所参加的《文学概论》写作团队,与王朝闻主持的《美学概论》团队一道住在中央党校两年,期间有很多的交流。这些都成为他后来提出“文艺美学”的根源。
当然,提出“文艺美学”的主要机缘,还是来自当时美学界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美学热”,最初仍有着重提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一些观点,并进行整理和发展的特点。正像所有思想上的进步,在一开始往往呈现为从过去寻找资源一样,那一时期的“美学热”在学术观点上呈现出向50年代的讨论回归的特点。“美学热”从1978年重新掀起“形象思维”大讨论开始,迅速回到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上来。一些曾在五六十年代活跃的美学家们这时重新焕发了青春,整理他们此前发表的文章,编辑成书,并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发展和营构各自的理论体系。
原有的借助“形象思维”的研究而推动的关注艺术的思维规律,从而使讨论从抽象的哲学话题转向艺术本身讨论,在这一时期也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之上:第一,“形象思维”的讨论只在讨论艺术的思维规律,学术上的依据只是艺术感受加上俄国文艺家的一些论述而已,如何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这时遇到了瓶颈。第二,从当时流行的哲学模式来讲,思维被看成是一种理性活动,只有概念、判断、推理才能归于思维,因此,“形象”能否思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原先的“形象思维”说的拥护者李泽厚,在1980年就提出,“如果用一句醒目的话,可以这么说,‘形象思维并非思维’。这正如说‘机器人并非人’一样”。[1]李泽厚:《形象思维再续谈》,《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57-558页。这样一来,“形象思维”讨论原来设想让美学回归文艺,在文艺领域解放思想,却重新陷入到概念争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美学”的提出正合其时。用这样一个口号,绕开美学界所积累下来的种种概念之争,让美学回归文艺,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当时的一些重要的美学代表人物,例如朱光潜、王朝闻、蔡仪等人,与文艺原本就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正如前面所说,朱光潜原本就有对旧诗词的爱好,写过《诗论》,并自认为是他自己最好的书。王朝闻是一位雕塑家,有许多著名的雕塑作品。1961年中央教材工程请王朝闻来主编《美学概论》,虽有些出人意料,但也有在教材编写中避开派别之争的目的。他所主编的《美学概论》共分六章,第一章讲审美对象,第二章讲审美意识,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讲艺术家、艺术创作活动、艺术的欣赏和批评,可见其将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放在对艺术的论述上。这是对高度哲学化的“美学大讨论”的补充。蔡仪早年曾写作小说,对文学和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早年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研究过美术理论,后来才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其他一些重要美学家,如赵宋光研究音乐,洪毅然研究美术,刘纲纪研究书法,许多那个时代的重要美学家,都各有艺术的专长。正如朱光潜所说,“不学一艺莫谈艺”,他所指的,就是美学是“谈艺”的学问。
因此,文艺美学的提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个口号,以及相应的学科设想,在学科设置上也产生了重要的成果,许多在大学文学和艺术系科工作的人从事美学研究都具有了合法性。例如,蔡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蒋孔阳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胡经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周来祥在山东大学中文系,都分别带出了许多文艺美学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就形成美学研究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到了新世纪之初,就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主力。
新一代的研究者绘就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景观,他们进一步将文艺美学传播到全国许多其他高校之中。尽管“美的本质”的研究者还不断出现,也不断有人在这方面宣布形成新的流派,但避开概念之争,研究文学和艺术中所出现的具体美学问题,增加学科的广度和厚度,却是更多的人愿意付出艰辛的努力去从事的工作。
一些研究者发现,台湾地区也有人提出“文艺美学”,并写出文章讨论这个学科名称的原创问题。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语境中,即使是同样的词,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学者都提出这个词,也反映出汉语语境中对 “美学”这个学科的认识及其相应的学科建构上的特点,以及对这种学科建构情况纠正的需求。
当中国学者与西方美学对话之时,就会发现,这种从美学传播到中国之时就具有的误读,会进一步凸显出来。在欧洲,原本Aesthetics就是以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在中国创立一种“文艺美学”,将之翻译成“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s”,对于欧洲人来说,会感到奇怪而无必要。一种原本研究文学艺术的学科,在学科名称前面再加上文学与艺术,显得重复。然而,在中国,正如前面所说,由于翻译上的原因,以及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当时是及时的。正是 “文艺美学”学科的设立,促进了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繁荣。
毕竟,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在中国语境中说中文,却用欧洲的语言来思维,这本身就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事实永远比概念更重要,也正是从“美学热”开始,中国的美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也是与随着“文艺美学”的提出,许多从事文学艺术研究的人进入美学研究中具有合法性、美学研究对象范围被拓宽分不开的。
当前,中华美学学会有一千多名会员,这些会员中绝大多数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美学的名义,能聚集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在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做到。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从世界各国共来了三百多名美学家,然而在中国,有八百多名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这使国外学者大为震惊。他们很难想象,中国有着这么巨大的美学人口。中国固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也不能说,由于人口多,美学家就多。美学研究者并不是按人口比例产生出来的,而是相关研究发达的结果。这与文艺美学的倡导所带来的学科设置上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一个学科自有其内在的生态状况,形成内容的互补。当一部分人关注“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一个时期美学讨论的主流之时,就会有人看到其缺失的一面,产生补偿的要求。在此时,适时提出一个概念,就会形成一股力量的汇聚,促成学术生态平衡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美学史,就可以看出,中国美学走着自己的路。有些人延续过去的派别之争,并形成众多新的派别;有些人介绍研究国外的美学,引入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三大派别为主的西方现代美学,以及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文化研究和法国的社会学派为主的西方“左翼”美学;而以“文艺美学”为代表的众多关注文艺实际情况的美学流派在中国的兴起,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美学学科的思考和创造。
五、处在十字路口的“艺术学”与“美学”
过去的艺术学,在学科设置上并没有独立,附属在文学中的文艺学和哲学中的美学之下,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艺术理论不受重视,艺术只被看成是操作性的教学类别。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教育很容易形成重技术训练,轻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的局面。在文学研究中所常见的,并成为研究主体的史、论、评,即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三位一体的学科布局,在艺术研究中却得不到重视,有关艺术的史、论、评的格局很难形成,或发展不成熟。在艺术中,长期有着一种工匠式的从师学艺的传统,现代艺术类学院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对此进行纠偏,但这种工艺传统并不容易彻底根绝,会在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浮现出来。
18世纪至19世纪美学在欧洲的兴起,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推动艺术摆脱工匠式从师学艺的传统,促进艺术院校或大学中艺术系科的建立,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的形成。美学的这种对艺术学的推动作用,直到20世纪仍是如此。被认为是“一般艺术学”倡导者的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就是国际美学协会的创始人。他于1913年在柏林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美学大会,国际美学协会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算起的。有人认为,这位学者主张美学与一般艺术学分家,主张一种独立于美学的一般艺术学。这完全是对他的误读。有趣的是,马克斯•德索的这本现在被译为《美学与一般艺术学》(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Stuttgart: F.Knke, 1906)的著作,英文就直接翻译成《美学与艺术理论》(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Art, trans.Stephen A.Eme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在重视技术性的各门艺术之上,建立一种“一般艺术学”,是美学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有的追求。
最近十年,在中国艺术界出现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艺术学“升门”。这种学科制定方面的变化,对艺术研究的发展,当然是有益的。然而,在艺术学科中,艺术理论所要做的事,不是与美学划清界限,而是从两者间的历史联系开始,通过美学来推动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原本是为适应学术的需要而形成的。在学术与学科的关系上,过去都是学术决定学科。在建立三大体系的过程中,也是先建立学术体系,再建立学科体系,并进而建立话语体系。作为学术体系建立的标志,是成系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至于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是作为这个学科教学的完善的教材;而话语体系的建设则需要一些关键的概念和范畴。如此形成的三者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顺序关系。
这三者,尤其是前两者间的关系,常常会出现颠倒的现象。在历史上,原本总是学术决定学科。由于夏尔•巴托提出了“美的艺术”的组合,并论证它们如何归结为同一原理,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并以此与工艺区分开来。这种对组合的合理性的论证、对同一原理的论证,经过一段时期的讨论和论争,最终得以确立。它一方面在《百科全书》的辞条选择和归类上体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建立了一些研究和教学机构,从而使它在制度层面得到了肯定。这是从“学术”到“学科”发展的一个范例。类似的场景在其他方面也在上演。鲍姆加登提出了“美学”的概念以后,经过一些年的争论,在大学里就开始开设这样的课程了。甚至反对鲍姆加登体系的康德,在一开始也不得不以鲍姆加登的著作作为教材来讲授美学。在东方,中江兆民翻译了维隆的《美学》,从而选定了这两个汉字来为这个学科定名以后,才出现了日本文部省将之写入学科目录,并进而由东京大学开始成立“美学研究室”。这些都是学术决定学科的例证。
美学理论有一个特点,常常是由一些哲学家在晚年创立。康德出生于1724年,在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后,在1790年,即66岁时才出版了《判断力批判》。黑格尔没有能活到他的美学著作出版,幸运的是,他留下了一些关于美学的讲稿,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维特根斯坦没有能活到他的美学时期,除了一些谈话记录外,没有留下美学著作。然而在他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却在他提出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蔚为大观的分析美学学派。杜威也是在他75岁时,才出版了他的主要美学著作《艺术即经验》。可见,美学这个学科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哲学家们要在完成了自己的基本哲学体系的框架以后,才开始建设作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的美学理论。对于他们来说,美学是学术理论的产物,而决不是在既有的学科建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根据这个学科的需要而形成的理论。
当然,学科及其制度层面的设置,对于学术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肯定巴托和鲍姆加登的学术贡献,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提出的概念推动了学科制度的设立,并由此获得了学科发展的资源,例如,艺术学院的设立,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岗位的设立,相应的专业的形成。这本身对学术的发展,意义极其重大。然而,从其逻辑关系上来说,仍然是学术决定学科,而不是相反。如果相反了,就变成了位置决定道理。
位置决定道理,在有些情况下是通行的。例如,被委托担任案件某一方的辩护律师,所需要做的就是为委托人辩护。辩护律师必须站在自己的委托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想出辩护的道理。对于辩护律师来说,超越这一立场的发言是不正确的。谁是谁非、案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判决,由法庭决定,而不由辩护律师决定。所处的位置不同,说出的话就不同。其实,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层面都存在着。在不同的阵营、不同的党派、国与国的关系,都有这种情况,都会有人扮演代言人的角色。对于这些代言人来说,是立场决定原则,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然而,涉及到学术研究,情况则不同。学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必须超越个人和群体的立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不能位置决定道理,而应根据道理站队形成位置;不应该立场决定原则,而应该原则决定立场。正是由于学术的发展,才形成了学科,而学科的建立是为了学术的发展服务,如果顺序颠倒了,就会出问题。
结语:发展艺术美学
让我们再次回到艺术学的现实上来。正如前面所说,艺术学正处在十字路口。有人说,“艺术”很不幸,当年翻译这个学科的名称时用了“术”字,仿佛它只是一种“术”,其实,艺中有道。这说来很复杂,art一词原本也具有技巧和技术之意,只是后来的“美的艺术”的组合,推动现代美学的形成,使之脱“术”而讲“美”,从而小写字母开头的art变成了大写字母开头的Art。
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文艺美学”,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既促进了美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美学的推动,如前所述,改变了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聚焦,而关注文艺中的美学问题。对原来的文艺理论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原本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包含着各个方面的研究,既有文艺与政治关系研究,也有文艺与经济、社会、伦理等多方面的研究。在其中提出以“文艺美学”为核心,使文艺的审美特性得到回归,对于促进文艺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下,倡导“艺术美学”,使艺术研究除了关注技术之外还能聚焦艺术之美,与国外原本关注艺术的美学对接,挖掘发展传统思想中的美学因素,对发展艺术研究,使艺术进乎“术”而臻于“美”,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