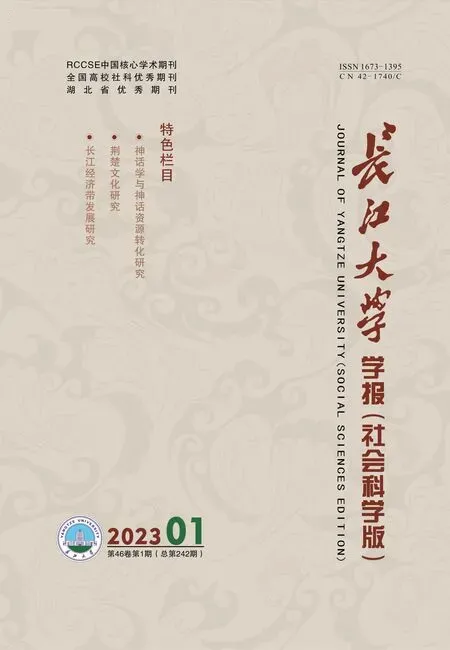楚都·楚城·楚墓
——安徽地区楚文化研究三题
2023-04-05蔡波涛
蔡波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61)
回顾中国考古学走过的百年历程,楚文化在考古发现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令人振奋。经过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我们已初步揭示出楚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拉开了中国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以1951年长沙地区楚墓的发掘[1]为起点,伴随着楚文化科学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楚文化考古研究在广度与深度层面不断拓展和提升。回顾近70年的楚文化考古历程,高崇文先生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的楚文化考古研究已进入全方位、多学科研究楚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新阶段。[2]
作为我国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地区楚文化研究在总体研究方向、研究目标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致的。但由于安徽地区自身较为特殊的地理区位,导致楚文化东渐进入安徽以后在遗址分布、遗存属性和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从地缘角度而言,安徽属于广义上楚“东国”[3]的一部分,所以安徽地区的楚文化考古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楚文化的东渐[4]、江淮地区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而展开的,而具体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楚国都城、楚国墓葬和楚文化遗物等内容。关于如何定位安徽楚文化以及如何开展安徽楚文化研究,陆勤毅[5]、杨立新[6]、张钟云[7]等先生均在不同时期就安徽楚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分析与探讨,并对之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笔者认为,安徽地区楚文化考古学研究应主要着眼于楚都、楚城和楚墓三个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安徽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均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本文试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角度,对这20年(即2001年至2021年)的工作进行梳理和小结,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计划和设想。
一、楚都
作为楚国晚期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城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8],通过借助遥感等手段对城垣范围、护城河、城内河网布局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推测和界定[9]。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01年,中断了近十年的寿春城考古工作才得以继续开展。截至2003年,针对寿春城第二阶段的考古工作得出了初步结论,基本否定了此前划定的面积约26.35平方公里的外郭城范围,并通过对蔡国“下蔡城”以及“州来城”的地望分析,推测州来、下蔡和楚都寿春城均位于今寿县城[10]。2004年之后,伴随着寿县新城区的建设,寿春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钻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2004~2016年,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有助于推进楚都寿春城研究与认识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明珠大道车马坑和定湖大道M6[11]的发掘,这两个考古新发现进一步揭示出西圈墓地可能为下蔡重要的墓葬区;二是2011年为配合寿县西门复建工程开展考古发掘的同时,对古城西城墙进行解剖性试掘,其所揭示的战国晚期遗存从侧面佐证了第二阶段的基本认识,即今寿县城很可能是楚都寿春城的宫城或内城。必须承认的是,西门南侧城墙剖面的试掘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现存寿县古城墙区域内可能为楚都寿春城之“宫城”等问题,但仍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寿春城城垣遗迹的核心问题。
为解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了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思路[12]。在这一工作思路的指引下,为继续探索寿春城遗址城垣、布局等相关问题,同时也为申报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提供学术支撑,自2017年起我们重新启动了对寿春城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工作[13]。根据州来城、下蔡城和寿春城的承继关系,我们考虑是否可以从探寻下蔡城的范围和城垣遗迹来反证寿春城的相关问题?根据城址和墓葬的分区关系,是否可以从墓地的发掘入手,通过墓地布局反向验证城址的方位?通过连续4年对西圈墓地的发掘,截至2020年,我们已经能够确认西圈墓地为下蔡城的重要墓地之一(1)蔡波涛、张义中:《“下蔡”探索的新进展——寿县西圈墓地2017-2020年度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21年9月3日,第8版。,结合蔡昭侯墓、蔡家岗赵家孤堆蔡墓及东津村蔡墓等分布情况,也更加支持下蔡地望“寿县说”,而非传统历史地理学认为的“凤台说”[14]。
除此以外,在配合寿县城南新区的发掘中,我们在八里遗址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15]。从该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晚期大型建筑基址,为研究和探讨寿春城遗址城内建筑布局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作为寿春城遗址范围内继柏家台[16]和邢家庄北01F1[17]之后的第三处大型建筑基址,从出土遗物的情况来看,其等级和属性与前两者存在较大差异。与夯土建筑基址匹配的重要设施有排水管道等,高等级遗物包括空心槽形砖、铺地砖和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等。与柏家台遗址明显不同的是,此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生活类实用陶器。与建筑基址相关的水井、陶缸和陶烟囱等遗存的发现也显示出其浓郁的生活气息[18]。1987年,考古队通过遥感解译发现,寿春城遗址南部有纵横交错的“水道”类遗迹,虽然其真实性在后来的工作中遭到了部分否定,但由于更为细化的验证工作迟迟未能全面展开,导致这一问题至今仍存在继续讨论和探索的空间。本次发掘揭示的南北向长度超过150米、宽度约5~8米的灰沟遗迹,为重新理解和审视“水道”类遗迹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作为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因受制于各种条件,寿县老城区内的考古工作一直未能开展。2019年,为配合寿县古城西南拐角塘的环境整治工程,我们在此进行了小规模考古发掘[18]。发掘区内的文化层堆积较厚且层次分明,时代跨度较大且延续性较强,依次是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西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两处夯土基址的发现,从层位关系来看,其被战国晚期遗迹所打破,叠压在战国早期的堆积单位之上,且夯土内的包含物时代均为战国早中期。经过对夯土的解剖可知,夯土层总厚度约0.9米,夯层及夯窝痕迹明显,每层夯土厚度较为均匀。夯土基址的南侧还发现有同时期的窑址区。这批战国早中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窑址是寿春城遗址范围内的首次发现,从遗存年代与历史记载对比角度来说,一方面为探索下蔡城提供了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也为探讨楚灭蔡以后对下蔡城的经略提供了新视角。
二、楚城
除了都城以外,楚国还有“别都”“地方城邑”等,为行文方便,我们统一将其称为“楚城”。在楚都丹阳地望的讨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19],湖北江陵的“纪郢”、河南淮阳的“陈郢”和安徽寿县的“寿郢”是比较明确的三个都城。楚之别都则主要包括鄂、鄢、鄀、陈、蔡、不羹、城阳、项城和钜阳等。有学者统计,春秋和战国时期,楚国的地方城邑分别有125座和151座之多。[20](P177~188)分布在安徽境内的楚城主要有钜阳、英、六、夷、焦、舒、桐、钟离、胡、慎和潜等。近年来,有关安徽地区楚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钜阳城的探索方面。
《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年)“徙于钜阳”。由于在同书《楚世家》《春申君列传》中均不见类似记载,所以关于楚国是否有迁都钜阳一事,学界有不同观点。陈伟认为“徙于钜阳”前未出现“王”字,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王亡走陈”和考烈王二十二年“王东徙寿春,命曰郢”等体例不同,且考烈王十年前后楚稍富强,而北方邻国亦未发生较大变故,所以楚都仍在陈城,没有迁都钜阳[21](P157~158)。徐少华也否定楚曾迁都钜阳,但认可钜阳为楚之陪都[22]。而以往学者多以《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凤阳府颍州“细阳城”条引的记载,认为“战国时,楚考烈王迁钜阳,此即钜阳城。后讹为细阳,汉置细阳县”,据此将钜阳作为楚由陈迁至寿春之间的都邑[23](P267)。《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的钜阳为楚都之三迁[24](P45~46),陈立柱也认为楚“徙于钜阳”有充分事实根据[25]。罗运环则认为钜阳城可能为当时的陪都,其目的是为避秦取陈城之意外或对外关系紧张,以防不测,并推测楚曾迁至钜阳不到两年,后又迁回陈城[26](P378)。
关于钜阳城的讨论,之所以存在争议和分歧,主要原因还是缺乏有力的物证支撑,也就是缺乏考古学层面对应的城址材料。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亳州—阜阳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太和县殿顶子遗址进行了局部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2)本次考古工作未公布正式的考古发掘简报,只在汪景辉先生的论文中有简要介绍。见汪景辉《楚都钜阳城试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首次从考古学角度探索钜阳城问题。根据发掘者相关论文中的介绍,殿顶古城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其文化层厚度约0.9~2.5米,遗迹以沟渠和水井居多,发掘区的遗存分上下两层,其中上层为唐宋时期,下层为战国时期,出土器形有平底罐、红陶盘、灰陶盆、灰陶豆等,综合文献材料分析后认为该遗址即为钜阳城。
关于钜阳城的地望,学界更是说法不一,有学者梳理大概有“阜阳说”“光山说”“六安说”“安徽太和说”等四种意见(3)熊贤品:《从近期考古发现看殿顶子遗址与楚都钜阳之关系》,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八辑),2020年。。目前来看,多数学者主张应在皖西北的阜阳、太和地区。如李天敏认为太和县原墙镇的“细阳城”就是钜阳城(4)李天敏:《钜阳考》,载《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二辑),1980年。,杨玉彬认为应在阜阳与太和交界处的腰庄古城一带[27]。随着近年来阜阳地区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我们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201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了一次颍河流域新石器至汉代遗存的考古调查工作,调查队在进入阜阳和太和县境内时,也对该区域内的相关遗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其中,颍泉区宁老庄镇的古城遗址由于面积较大,且地表采集有大量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和铺地砖、排水管等建筑残件,结合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以往出土有春秋时期墓葬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可能为春秋时期的“胡”国都城,也可能是钜阳城。如陈立柱认为钜阳城应在位于郢陈南下江淮的冲要地带,古城遗址位于颍河拐弯处的南岸,地理位置极佳[28]。2020年,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的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有西周至宋代的墓葬、车马坑、夯土基址、陶窑等遗迹,并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发掘者认为这些发现对于探讨该遗址与胡子国的联系以及钜阳城的地望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29]。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殿顶子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新进展。2017年,安徽省文物鉴定站等单位对以殿顶子遗址为核心的区域开展了一次专题调查与勘探工作。调查结果认为,根据初步划定的范围,殿顶子城址含城墙在内,南北长约3.8公里,东西宽约3.4公里,面积约12.92平方公里,如果加上护城河和城外建筑设施面积就更大,对遗址的定性是一座由楚人建造和开始使用并延用至两汉时期的特大型城址(5)方松高、黄飞、刘铭:《专家一步步揭开殿顶子遗址神秘面纱》,《颍州晚报》2017年9月21日,第A5版。。2019年至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殿顶子遗址持续开展了考古工作。据介绍,在殿顶子遗址马庄地点发掘出土有东周、秦汉、唐宋时期文化层,遗迹类型有窑、作坊、房址、墓葬、沟、祭祀遗迹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诚如有学者所言,就2019年以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有关殿顶子遗址是钜阳城的认识仍是一种“推论上的推论”。
除此之外,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有关钟离城、沈子国城及城父城的讨论也逐渐提上了日程。1980年,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件青铜鼓座,外围发现上下两圈铭文[30]。多数学者对上圈铭文的前段部分释读为“唯正月初吉庚午,余敖厥于之玄孙童鹿公鱼,择其吉金,玄鏐钝吕,自作凫鼓”[31]。若据此,则该器座与钟离国有较大联系。1991年,凤阳大东关村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器类包括编钟、鼎、锛和车马器等,而其中15件青铜编钟和一套编磬的出土昭示出该墓葬等级较高的特质,由于其距离钟离城遗址较近,且时代相当,学界推测应与钟离国有重要关联[32](P173~184)。2006年蚌埠双墩一号墓[ 33~35]和2007年凤阳卞庄一号墓[36]的发掘,是钟离国考古工作的新突破,对于研究钟离国君墓葬[37]、钟离国史及文化等问题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这两座国君级别的墓葬情况可以窥探其葬制葬俗和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也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钟离国的存在和具体地望。
沈子国城址,又称“沈丘古城”[38](P300~301),其地望在阜阳市临泉县城关镇古城社区。根据调查[39]得知,城墙堆积内含有战国时期陶片,且在城西有相应时期的墓地。城父古城,遗址位于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40](P126~127)。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田野考古资料,我们对于该城址的情况尚不清楚。
三、楚墓
对安徽地区楚墓的关注,除了李三孤堆楚王墓以外,杨立新[41]、宫希成[42]两位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分别对安徽境内楚墓的分期、分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观点基本反映了安徽楚墓其时发现的基本情况。目前安徽楚墓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以楚都寿春城为核心,其周围三个墓葬区的分布是比较明确的,即:淮南、长丰、杨公一带的高等贵族墓葬区;寿县西南双桥一带中等贵族墓葬区;寿县城北、八公山南麓沿线为小型墓葬分布区[43]。近年来,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三个墓葬区均有新发现。滁新高速和商合杭高铁均经过寿县八公山南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施工线路内清理了大量战国、两汉时期墓葬,但由于墓葬绝大多数被后期盗扰,墓葬均保存较差。2014年,为配合济祁高速寿县段建设,我们在双桥镇清理了一批小型楚墓[44]。从墓葬尺寸、随葬品及墓葬位于中型封土墓边缘的情况来看,这些小型墓葬应为战国晚期中等贵族楚墓的陪葬墓。而凤台段毛集镇史集村胡台孜楚墓[45]的发掘,则是首次在淮河以北地区发掘的较高等级的楚国贵族墓葬。该墓墓口边长为9~10米,形制规格属于中等贵族,葬制为一椁重棺,也属于中等规格,但墓椁长3.7米、宽2.4米的尺寸又属于中小规模。更有意思的是,其墓道两侧放置有对称排列的矛与盾牌,这一情况与长丰杨公发掘的中大型墓葬[46]葬制相同,这种类似于“卫队”或“依仗”的象征彰显出较强的军事感,可能与墓主生前身份为武将有关,而以胡台孜楚墓为代表将墓葬埋葬于淮河北岸地区的情况,应该与当时楚国王室忌惮北部边患威胁而加强防御力量有关。2020年1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淮南市博物馆发掘了淮南市汤家孤堆一、二号墓[47],两墓年代均为战国晚期,可能为夫妇异穴并葬墓。而两墓积炭和积蚌的特殊葬俗实乃该地区楚墓中首次发现,其具体文化内涵需要进一步探讨。
六安城区的基建考古项目长期开展,据统计,每年发掘墓葬的数量基本维持在400座左右。在持续性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除了数量庞大的汉墓[48,49]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楚墓发现[50]。这其中,六安白鹭洲M566[51]、M585[52]两座战国墓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两墓均未被盗,葬具及随葬品保存完好。这是一组夫妻合葬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偏早,墓主身份为下大夫,是楚国在东部地区的下级官吏及其配偶[53]。根据对M585男性墓的人骨检测与分析,发现其掌骨受伤,颈椎被砍断,从伤口断面微痕分析推测,应为兵器所致。从随葬品形制分析可知,这两座楚墓包含有中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因素和本地的群舒文化传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文化态势。
在江淮南部及沿江地区,楚墓的发现主要集中在枞阳、潜山、安庆及宣州[54]等地。进入新世纪以来,安庆王家山[55]、潜山彭岭[56]和公山岗[57]战国墓葬发掘资料的发表,以及枞阳旗山战国墓群的小湾[58]、沙河[59]、潜山林新[60]和安庆圣埠[61]等墓地的发掘,为进一步深化该地区楚墓的研究与认识提供了重要基础。从陶器形制与组合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其文化因素主体为楚文化,其次是中原文化,此外还有传统土著文化、越文化和秦文化,且楚文化的特征与湖北地区同时期风格更接近,这与寿县、淮南、六安一带的楚墓风格与豫南地区相近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可能与楚人东进江淮的路线不同有关。
近年来,皖北地区的楚墓也不断有新发现。2007年,在蚌埠双墩钟离君墓旁边发掘三号墓[62],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风格判定其为典型的战国晚期楚墓。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阜阳市文物管理局对阜阳储台墓地(6)刘建生:《安徽阜阳储台墓地发现战国墓葬》,《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9日,第8版。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以M1为代表的等级较高的战国中期楚墓的发现,在皖西北地区属首次发现,进一步拓展了楚文化在皖北地区的经略和发展等问题。2019年至2020年,在亳州市谯城区西菜园墓地也发掘了一批战国墓葬,从出土陶鼎、陶豆、陶壶等器物形制与组合以及“山”字镜的情况来看,是为典型楚墓无疑,而吴王夫差铭文残剑的发现则为吴、楚相争在皖北地区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线索。在皖北东部,主要在宿州、灵璧等地发现有少量零星楚墓,如宿州邱园[63]、灵璧孟山口[64]等,均为战国晚期小型平民墓葬,代表了楚文化晚期阶段对该地区的渗透和影响。
四、结语
通过以上简单梳理,笔者认为下一阶段安徽地区楚文化研究仍是以楚都、楚城、楚墓为重点。楚都方面,要在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课题引领下,继续深化寿春城的城垣遗迹和城内功能布局的探索,注重古今重叠型城址的考古资料积累和串联,建构都城演变的历时性发展序列和共时性发展格局。钜阳城的工作基础尚且薄弱,关于其是否为楚都,需要继续开展深入的考古工作才能逐步解决关键问题。楚城方面,需要开展专题性调查,对楚城的分布、城址规模、堆积结构、时代、属性等问题进行摸底式排查,除了对已知楚城的复查以外,还应注意出土典型器物(7)如蒙城小涧镇出土有一批重要青铜器,其中不乏典型的楚器。铜器出土地点附近有红城遗址,保留有较好的城垣遗迹,就应该成为重点核查对象。参见鹿俊倜《安徽蒙城出土春秋青铜器》,《考古》1995年第1期;蔡凌凯《蒙城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文物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指引下的城址核查。楚墓方面,首先是要抓紧已有田野发掘资料的整理、简报发表和报告出版,为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提供基础资料的支撑;其次是对楚墓中高等级墓葬尤其是楚王一级大型墓葬的研究,因一直受制于材料的不足而难以开展,由于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并没有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我们对其墓葬形制、结构等问题尚没有清晰的认知。可喜的是,伴随着淮南武王墩大墓的发掘,这方面的工作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安徽地区楚文化的研究需要有动态视野,楚文化东进江淮的历程就是安徽楚文化形成的过程。安徽地区楚文化研究也需要系统性考量,必须将楚都、楚城和楚墓三位一体进行整合,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以遗存为本位,方能揭示出安徽地区的“楚化”乃至“华夏化”的进程,充分认识中国文明的多元性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