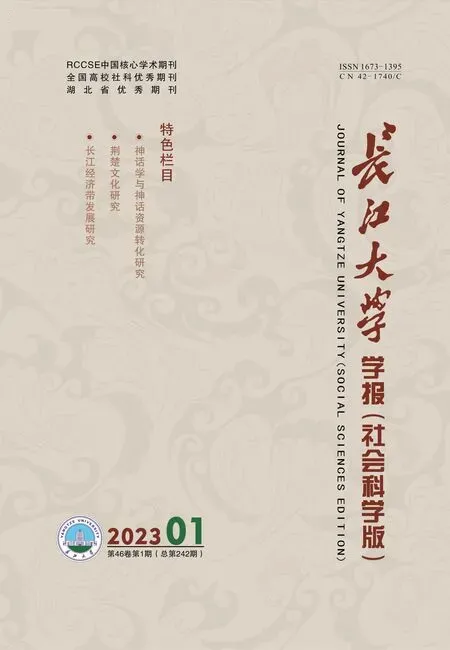危机禳解与象征意蕴:重阳节习俗过渡礼仪探微
2023-04-05俞玲
俞玲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江西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生院,江西 南昌 330022)
重阳节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深挖其文化内涵,弘扬中华优秀敬老孝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细细梳理纷繁复杂的习俗,可见其文化体系的杂糅交错,既有辟邪消灾之寓意,如祭祀大火星仪式,又有祈祝长寿之内涵,如祭祀老人星仪式。如何理解重阳节差异性较大的各种习俗,或者说,怎么厘清重阳节辟邪消灾、祈福长寿两大主题的内在关联性,并客观分析其习俗的仪式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一、重阳节研究文献回顾
重阳节,又名九月九、重九、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老人节等,与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并称,是我国七大传统节日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尽管国家对传统节日更加重视,但相对其他传统节日,重阳节的存在感并不高,学界对其关注比较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重阳节起源演变研究。重阳节起源,学界有多种声音,“先秦说”为主流。张君认为重阳节的前身是先秦的九月节庆。[1]袁学骏也认同这个观点,认为重阳节“起源于农业社会到来时的生产劳动程序和祭祀活动”[2](P116)。傅功振也认同重阳节滥觞于先秦。[3]郭佳认为重阳之名及“辟邪消灾”观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老祈寿”观更早,来源于先秦秋季的养老节与秋尝之祭。[4]黄涛也认同“辟邪说”,认为其形成年代为东汉时期。[5]陈艳认为重阳节起源有“先秦说”“西汉说”和“东汉说”三种说法,她支持“东汉说”。[6]余全有认为九月九日作为传统民间节日,定型在西汉初期以前,但重阳作为节日名称使用,则在东汉之后。[7]值得一提的是,杨琳未从时间维度探讨重阳节起源,而是针对关于重阳节起源的四种说法,即“祈寿说”“尝新说”“辟邪说”“大火星祭仪说”等进行了分析,她支持“辟邪说”,并进行了深入论证。[8](P23~31)
二是重阳节习俗内涵研究。登高是重阳节的一个重要习俗,学界探讨较多。刘伟生将上巳踏青和重阳登高并列,分析了其中蕴含的生命情绪。[9]刘爱萍也探讨了登高习俗,并深入思考了其宗教维度和义涵,她认为“‘登高’乃比喻,指生命的超越与升华。‘重阳登高’就是生命超越的圆满本体论事件,是本体论上的生命圆满超越”[10]。徐燕琳探讨了郑仙诞与重阳登高习俗的融合现状,认为民俗节日呈现出变与不变的特点,在现代社会获得了发展。[11]王小明以天津玉皇阁重阳节登高习俗为例,认为社会转型期传统节日空间遭受了重大冲击,基于此,她提出了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建议。[12]同样关注当下,黄意明、秦惠兰认为重阳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报本反始的敬老功能得以深化,而文人雅士构筑起的重阳诗性文化则是另一特点,因此,今天重阳文化的创新必须注重原有的历史资源。[13]萧放对重阳节习俗内蕴演变进行了梳理[14],黄岚对菊与茱萸文化的内涵予以挖掘[15]。重阳节习俗内容丰富,学者关注较多。有意思的是,同样探讨重阳习俗,李炳海分析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巳、重阳的习俗,认为这个时期因为民族融合,两个节日均融入了北方民族讲武习射习俗,推动了节日氛围的转变,重阳节也由抑郁色彩向欢快气氛转变。[16]重阳节习俗内涵研究中,不少学者关注其宗教色彩,如郭云涛[17]、黄俊[18](P48~49)、王永平[19]等。
三是重阳节现代发展研究。林继富强调应以重阳节核心传统为中心进行重阳节品牌建设,使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20]张勃、王改凌认为重阳节敬老孝亲文化诉求与20世纪80年代的再次改名相关,肯定其行为,认为它既是一种文化唤醒机制,也是一种文化转换机制,推动了其现代转换。[21]郑土有也认同这种现代转化,认为它既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容易被民众所接受。[22]
四是重阳节域外传播研究。重阳节域外传播,日本作为邻国,其影响最为明显。刘晓峰探讨了重阳节在日本的传播过程,认为它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先抑后扬的过程。[23]陈巍指出降至中唐,诗宴替代登高,成为重阳节活动中心,日本嵯峨天皇重阳诗宴很可能是以唐德宗为模范。[24]邱丽君也关注日本重阳节诗宴习俗,认为在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数位天皇努力下,重阳赋诗活动使其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贵族化走向庶民化,开辟了其文化延续的新途径。[25]王琛发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北斗九皇圣诞与重阳节重合,其大众礼斗拜祭抗清死难先辈的国殇活动,导致重阳氛围褪却。[26]
五是重阳节文学艺术研究。关于重阳节的诗词研究很多,这里仅简要提及。翁敏华以元杂剧《东篱赏菊》为例,认为其很好地塑造了陶渊明的形象,增强了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也有助于人们对陶渊明的纪念和崇祀。[27]叶洪珍认为菊花意象在明代重阳词中远多于茱萸意象,其原因在于菊花更具观赏性,更贴近生活,内涵也更为丰富。[28]《万水千山入韵来:古今重阳诗词选》[29]一书从不同时代、不同角度出发,选择了历代优秀重阳主题诗词。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对重阳节的起源、习俗、内涵等方面均有涉及,但就研究的广度、深度来说,还有待加强,既缺少鲜明区域性的深入案例分析及阐释,也缺少宏观层面对重阳节形成、习俗、宗教仪式及其象征寓意的深入探讨,缺少对重阳节习俗、仪式与人类生存发展关联性方面的研究。而且,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出入,如敬老孝亲的观念,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重构,历史并不长,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其起源于先秦秋季的养老节与秋尝之祭。因此,重阳节的研究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笔者拟借助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对重阳节习俗及其象征意蕴进行深入阐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解读重阳节的危机禳解,旨在为学界深入研究此问题抛砖引玉。
二、重阳节习俗的仪式性及象征意蕴
重阳节的起源,学界基本上认同“辟邪说”,笔者也比较赞同,客观来说,即便是“祈寿说”,也可以纳入“辟邪说”之中,因为辟邪消灾的主要目的也是避免接触邪恶或污秽,减少对个体健康的威胁,从而实现个体顺遂康健,延年益寿。“从源流关系上来看,求寿是从辟邪的动机中派生出来的,是辟邪的副产品。”[8](P31)也就是说,求寿或祈寿乃至祈愿在心理诉求上属于更高追求,但其动机仍是基于主体的身体康健,应该归属于辟邪消灾这个范畴。重阳节登高“辟邪说”传播最为广泛的说法,源自南朝梁吴均所著《续齐谐记》中的一个故事。“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30](P229)此故事的历史真实性,我们且不去讨论,作为一个传奇性的神话志怪故事,它能够广泛流传,表明其具有生活的真实性,故事的内核不是虚构或编撰的,它是“层累地”发展的,是民俗事象历史演变的结果。
为什么重阳节要辟邪或避祸?学者们对此有不少研究,有三个观点值得深思。张铭远认为包括重阳节在内的秋季节日蕴含死亡抗拒的节日主题,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上海重阳节吃糕与登高避灾之关联,表明平原居民无高可登,以“吃糕”代替“登高”。另一个是江西萍乡有重阳节登山携带柑果,将其抛至小儿身上的习俗。他认为小儿是祖灵的种子,死而又育,蕴含死而复生的形象。柑果与小儿相连,小儿成为多籽的种子的象征。[31](P103~128)张君也视重阳节为死亡节,认为古代还有一个与大火星“内火”现象相应的哀悼送终仪式。表层结构的辟邪方式如登高,为后来羼入的因子,可能与升天、成仙、远古逃避洪水的神话传说掺在一起,导致重阳节逃避死亡和升仙的深层结构为逃避死亡(洪水)所置换。整合后的哀悼、逃避因子,如登高、食蓬饵、饮菊花酒等,比庆丰年的祭祖酬神地位更重要,因此成为后世重阳节的主要内容。[1]郭佳认为重阳节的源头应为老人节和秋尝之祭,前者通过老人星祭祀仪式,祈求长寿,构成盛大的养老节,《史记·天官书》《史记·封禅书》有相关记载,后者通过秋尝仪式,在歌舞宴饮中向祖先祈寿、相互祝寿。[4]这些研究表明,九月九日(阳九之厄)作为死亡节,其禳解的方法就是辟邪消灾,后世辟邪方式如登高的羼入及儿童、妇女的象征意蕴,致使其习俗呈现更为复杂。可以说,登高、食蓬饵、佩茱萸、饮菊花酒、尝新、诗宴、祭祖乃至抛掷柑橘、散放牲畜等习俗,既是“祈寿说”的行为体现,也是“辟邪说”的内涵反映。对今天重阳节重构来说,它不仅为理解多元的习俗提供阐释框架,也为深挖文化内涵提供脉络线索,更为敬老孝亲文化诉求提供了直接注解。
重阳节习俗类型多样,其仪式性相对较弱,突出体现了辟邪消灾和祈福祝寿两大主题,从其行为方式及效果来看,重阳节习俗大致又可划分为三类。
一是规避类习俗。此类习俗包括登高、放纸鹞、佩茱萸、食蓬饵(重阳糕)及相关禁忌等。安徽《太平府志》载:“重阳日携酒登高,插茱萸,远望,以避邪秽。乡俗馈糍糕。芜邑乡村是日击鼓喧哗,以驱狸豕,谓之禳疫。”[32](P2)其击鼓喧哗的场景,类似于跳傩习俗,具有逐疫功能。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已经指明登高辟邪功能,而茱萸又被称为“辟邪翁”,寓消厄避灾之意,具有辟恶气、御初寒的功能。《太平御览》引《风土记》载:“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以此日茱萸气烈成熟,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33](P409)唐代郭元振《子夜四时歌·秋歌二首》也说:“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34](P579)这里不但提及茱萸囊,也暗示菊花酒功能类似。重阳节还有一些禁忌,亦可归入此类。明万历十五年《绍兴府志》引《嘉泰志》载:“(重阳)是日俗忌不相过,必有丧者乃往哭其灵几,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35](P820)山东滕县、枣庄等地有出嫁不到三年的闺女忌回娘家过节的习俗,民谚有“回娘家过重阳,死她婆婆娘”[36](P196)。
二是祭祀类习俗。此类习俗包括祭祀祖先、神灵及庙会等。《吕氏春秋》载:“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37](P153)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载:“‘重阳’……习礼之家,前后省墓,祭以时食。”[35](P886)福建莆田及山东长岛、文登一带,旧时重阳节家家也上坟扫墓,纪念先人。重阳也祭祀各种神灵,有些神灵甚至与平安健康没有关系,也在祭祀之列,这可能与辟邪消灾观念的泛化有关,以“我”为中心,祭祀各种有利于自身的神灵,也是广义的对个体生命有益的行为。山东泰安旧时有祭奠“眼光奶奶”的习俗,人们到眼光殿里祭拜,祈求“眼光奶奶”保佑全家人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36](P195)有意思的是,郓城民间认为重阳是财神生日,家家烙焦饼祭祀财神。邹平人则到范公祠祭祀范仲淹。[36](P196)福建莆田人认为九月初九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村的天后祖祠、宫庙等地祭祀,祈求平安顺利。
三是祈祝类习俗。此类习俗包括饮菊花酒、女儿归宁、抛掷柑橘及北方骑射习俗等。尽管从节日起源来说,求寿仪式可以纳入辟邪消灾范围,但从节俗分类来看,求寿行为可归属于祈祝类习俗,且在追求高度上,人类求寿的心理寄托、心理渴望远胜于辟邪的心理慰藉、心理解脱。《太平御览》卷三十二引《卢公范》云:“九月重阳日上五色糕、菊花枝、茱萸树,饮菊花酒,佩茱萸囊,令人长寿也。”[33](P411)菊花又被称为“延寿客”,是长寿的象征。《荆楚岁时记》杜公瞻注称;“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38](P65)“酒”与“久”谐音,饮酒本就寓有长寿之意,加上菊花的长寿寓意,群宴会上饮菊花酒就更有祈祷长寿的心理暗示。
重阳节也被称为女儿节,是女性节日之一。与前文在重阳节回娘家的禁忌相反,不少地区,如陕西、河北、天津等北方部分地区,都有出嫁的女儿在重阳节回娘家省亲的习俗,即女儿归宁。父母接女儿回娘家吃重阳糕,俗谚说:“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有的地方重阳糕又称为重阳花糕,面上塑两只羊形,取重阳之象,其寓意是“吉祥如意,百事皆高”。老北京也有这样的习俗,在重阳日,父母要备名酒、花糕、水果等,接女儿回家,并取片糕搭在女儿额头上,祝福其“百事俱高”。“重阳节妇女回娘家食糕,表面上的意义是团聚、热闹,其隐含的原始动机是向母系家族乞求生殖力量。”[39](P176)乞求生殖力量,前文提及的江西萍乡过去有抛掷柑果至小孩身上这种带有巫术性的仪式,将柑果多籽与小儿联系,亦有此象征意蕴。
三、危机禳解与重阳节习俗过渡礼仪模式分析
重阳节的仪式性活动比较复杂,其习俗的主题是辟邪消灾,如桓景登高避祸传说,并由此衍生出祭祀神灵、祈祝长寿等习俗。这些习俗具有一定的仪式性,通过仪式活动,实现危机禳解的目的。借用法国著名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模式和阈限理论,可将其研究对象从封闭的“半文明”社会扩展至当代社会,从而更好地阐释人类礼仪行为的心理、文化背景。“如何应用此模式来认识一些当今尚未从此视角分析过的礼仪实践,将成为重新认识哲乃普的过渡礼仪的重点。”[40]范热内普认为,“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唯一用来对此社会划分的分水岭便是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亦即世俗(le profane)与神圣(le sacré)”[41](P3)。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世俗世界与宗教世界或世俗与神圣的交融状态,也存在着巫术-宗教性(magico-religieuses)的组织基础。“宇宙本身受一种周期性控制,而这种周期性体现于人类生活。”[41](P4)岁时节令作为其探讨的一个门类,无疑也可以用过渡礼仪理论来阐释。
按照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理论,过渡礼仪模式包括分割礼仪、边缘礼仪与聚合礼仪,在这些礼仪之下可进一步细分,他强调过渡礼仪的动态性,关注仪式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阳节的辟邪消灾主题亦可纳入过渡礼仪。从宏观角度来看,出现灾厄,如瘟疫、火灾、九月内火等,可作为分割礼仪阶段,灾祸的出现使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进程被打乱,灾祸状态的生活区别于日常生活,并被日常生活所分割。重阳节的边缘礼仪实际上就是禳解方法或途径,其仪式包括祭祀大火星、老人星、妈祖、山神、灶神、财神及祖先等,还有登高、骑射、放纸鹞、佩茱萸、食蓬饵、赏菊、饮菊花酒等。当然,这些习俗或仪式非常复杂,“由于掺入了远古先民们逃避洪水的记忆,导致上古时的在九月哀悼火神死亡这一深层结构为逃避死亡(洪水)所置换”[1]。重阳节的聚合礼仪则是经过这一系列的边缘礼仪或禳解方法,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了慰藉、解脱,从而重新聚合进日常生活。
边缘礼仪是过渡礼仪的最重要内容,是世俗与神圣交融的状态,可以说是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角力、交流、对话乃至达成妥协的过程。“边缘礼仪是整个交流过程,即‘过渡礼仪’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40]
根据上文对重阳节习俗的分类,重阳节边缘礼仪,笔者亦可尝试将其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规避性边缘礼仪。人们通过登高,可以远离火灾,或者通过登高山、登高楼、登高塔等健身运动,在日常生活场所之外,在这种边缘性状态实现远离瘟疫、火灾等灾厄的目的。还可理解为在高山、高楼等高处接近天界,接近神灵,远离世俗,因而登高是规避日常,使主体可能升天、成仙的边缘性状态的一种媒介。“在先民看来,大山含泽布气,离天最近,是神灵的住所,苍天的意志是通过大山传导给人间的。”[42](P19)古人都有大山崇拜,故走进大山,登上高山之巅,可以进入神灵的世界,从而能够有机会获得神灵眷顾。而放纸鹞也是古代的一种巫术,将邪魅阴晦通过纸鹞放到天空中,从而保证人身健康。也就是说,选择一个场地,让自己处于边缘性状态,并通过一种巫术-宗教性手段,将不可控的超自然力量变得可控或可规避。佩茱萸、吃重阳糕等习俗或仪式也是一种巫术手段或心理暗示,通过佩戴茱萸、吃重阳糕,将自己置入一种边缘性状态,与日常生活状态隔离,可以规避灾祸,从而为聚合进日常生活做准备。
二是祭祀性边缘礼仪。人们祭祀大火星,既是为作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时间坐标的大火星隐去恐慌,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好心理准备。通过这种祭祀仪式,让自己进入边缘性状态,而祭祀仪式的完成,则意味着边缘礼仪的结束,人们将逐步聚合进日常生活。古人有仲秋养老习俗,人们祭祀老人星,也寓有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祈祷健康长寿之意。“因为古人将对长寿的祈愿寄托在这颗星辰之上,祭祀寿星(老人星)以祈求长寿。”[43](P67)祭祀的过程就是边缘性的过程,并伴随祭祀结束而逐步聚合进日常生活。人们祭祀祖先,除了秋报之意外,也有祈求祖先神护佑后代,让其渡过灾厄状态,并祈祷美满幸福之寓意。其他如祭祀山神、灶神、财神、妈祖、“眼光奶奶”等神灵及参加各种庙会活动,对主体而言,均为对当前非正常状态的一种禳解,也包含从边缘性状态向日常生活状态的演进过程。
三是祈祝性边缘礼仪。这种礼仪与祭祀性边缘礼仪有交叉重叠之处,即对未来和谐状态的一种祈祷祝愿,如祭祀老人星,除含有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外,在仪式上更多寓有祈祝的意味。饮菊花酒,通过关注养生、益寿延年的方式去规避灾祸,饮用过程就是边缘性过程或禳解过程,也伴随由边缘向日常过渡的过程。女儿归宁习俗,父母接女儿回娘家,给女儿额头贴片糕,或准备糕点食品,亦含有通过祈愿规避灾祸之意。至于其“向母系家族乞求生殖力量”的原始寓意,亦可理解为女儿归宁的过程也是一个边缘礼仪,处于夫家和娘家之间,其身份还在转变过程中,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通过贴片糕或吃糕点等行为,附加了母系家族的生殖力量,为更好地进入夫家,获得和睦温馨的家庭日常生活做准备。当然,登高习俗亦含有祈祝仪式,高山接近神灵,祈祝能够获得神灵的护佑,且高山之上,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有益于身体健康,自然有助于延年益寿。其他骑射、赏菊等活动亦可纳入祈祝类习俗,均有边缘性特点。
通过上述重阳节习俗仪式过程分析,可以发现,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重阳节纷繁复杂的习俗可以按照分割礼仪、边缘礼仪与聚合礼仪三个环节对其进行初步解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过渡礼仪模式进行一般性阐释。但重阳节作为一种本土的节俗文化,不能简单套用过渡礼仪理论,它的习俗体系比较复杂,不同于丧葬礼仪或婚礼,在时间维度上并没有紧凑的仪式进程,不遵循线性演进轨迹,或者说,其仪式之间比较杂糅,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虽然‘过渡礼仪’模式有很宽的应用范围,但基于不同文化内涵,对过渡礼仪中的进程和象征的分析,则不可一概而论。方法论也需针对不同文化做出调整。”[40]也就是说,对过渡礼仪不能简单套用,要针对不同文化进行相应调整。而且,随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对其理论反思也在不断进行,“在一个既有的整体主义范式和概念普遍遭到怀疑的时代,过渡礼仪模式也无法独善其身”[44]。
四、结语
重阳节是我国的重要传统节日,其名称记载最早出现在三国时代。曹丕《与钟繇九日送菊书》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45](P148)古人认为数字“九”为阳数,日月并阳,故名重阳。重阳节习俗体系纷繁复杂,有登高、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赏菊、饮宴、女儿归宁、祈寿及祭祀老人星、祭祀大火星、祭祀灶神、祭祖、习武骑射、放纸鹞等习俗,集中展现了辟邪消灾和祈福祝寿两大主题,从其行为方式及其效果来看,大致可以归为规避类习俗、祭祀类习俗和祈祝类习俗三大类。而后者则成为重阳节的重要内容,也是今天将其命名为老人节的重要依据。
如何深入分析三大类习俗的内在关联性,或者说,将关涉较少的两大主题统摄进重阳节文化系统,并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无疑是重阳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范热内普的过渡仪式模式,对重阳节纷繁复杂的习俗进行仪式过程分析,即探讨了其分割礼仪、边缘礼仪与聚合礼仪。这种分析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但基于重阳节较弱的习俗仪式性和非线性的仪式进程,且过渡礼仪模式适用性的局限,重阳节习俗仪式进程分析仍有不少缺陷,因此,过渡礼仪模式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也有其阈限,需要对其进行在地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