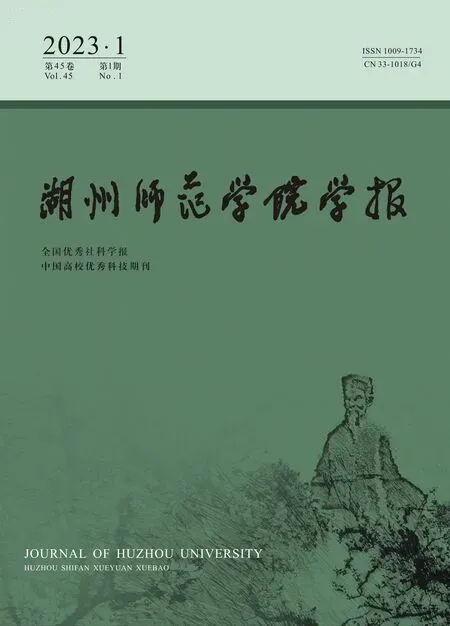“艺术是前世的回忆”*
——木心特殊艺术思维研究
2023-04-05杨大忠
杨大忠
(1.杭州师范大学 木心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1121;2.桐乡市高级中学,浙江 桐乡 314500)
要说木心是个“迷信”的人,恐怕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毕竟在他身上,博古通今、中西合璧的特征体现得极为明显,很难想象一个既接受中国古典教育又由衷接纳西方文明的学者身上会有浓烈的“迷信”色彩。这种“迷信”色彩既不同于西方各教的教义在信徒身上的体现,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鬼神的信仰,木心身上的“迷信”色彩最主要体现于对艺术家身份的认同与极高礼赞。仔细解析这些“迷信”色彩,也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木心的艺术思想。
一、木心“迷信”的原因
木心非常“迷信”,这一点他身边的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和他最亲近的陈丹青曾说:“他迷信,几次说及幼年的卜卦,说是算命先生嘱咐他母亲:‘孩子一定要离开血地!’‘血地’,旧说乃指出生之所。”[1]54木心17岁后就长期离开乌镇,半个多世纪才回来定居,不知其中有没有算命先生的论断之故。
木心思想的一大基点就是对过去民俗社会的深沉缅怀与追思,这应当是木心有着“迷信”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木心小时候生活的乌镇,位于传说中凤凰落宝之地——桐乡,凤栖梧桐的传说至今在桐乡仍旧家喻户晓。木心后来在美国给陈丹青等人授课的时候就说到过小时候凤凰现身桐乡的故事:“我外婆家开地毯厂,晒开来,有一天忽然飞来一只凤凰,周围都是鸟叫。学徒看见了,回来告诉老板,老板赶过去,什么也没有。”引用这个百鸟朝凤的传说,实际上反映出木心对艺术家的推崇:“你是艺术家,你就是人间的凤凰,一到哪里,人间的百鸟就会朝凤——你这凤凰在百鸟中是一声不响的。”[2]1074
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诞生于盘古开天辟地时期,乃飞禽之首,这在《西游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既然是传说中的神鸟,凤凰在现实中哪有现身的机会,但木心对凤凰却深信不疑。凤凰的故事诞生于民俗社会时期的乌镇,可见民俗社会在木心身上的烙印之深,他相信民俗社会里诞生的迷信之物,哪怕是荒诞的事物;木心将艺术家比作“人间的凤凰”,又可见木心对艺术是多么虔诚。
木心又非常相信算命与相术,认为这些都有着一定的合理依据:“巫术,是一种统计学,千百年来积累了无数统计例,算来往往神奇、准确。有什么生辰八字、什么面型五官,就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是‘然’。为什么会这样?谁决定这样?讲不出,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算命相术不是哲学。”[2]956“然”,就是结论正确;但“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无法找出原因。木心非常相信算命的结论:“我以前在台湾南部写生的时候,抬头看到天空一张笑脸正对着我。我算卦的时候,总是与我心里想的暗合,非常准。”[3]260不仅如此,算命有时还使木心在艺术方向上做出转变。木心不止一次说过算命对自己艺术方向的影响:
记得有次寄出稿件后,卜了一签——“小鸟欲高飞,虽飞亦不远,非关气力微,毛羽未丰满。”好厉害!上帝挖苦我,我不再写诗而专心画图了。……因为我年轻无知,才会真的写了一本“哈姆雷特泛论”。从此,就此,一篇篇写下去。某日独游灵隐寺,又拔了一签:“春花秋月自劳神,成得事来反误身,任凭豪夺与智取,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可不是挖苦而是警告了。[4]21-22
木心自视极高,始终将成为“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并且他也相信自己就是个天才艺术家,因为这是算命先生对他做出的剖断:“以前在西湖散步,一个看相的从后面叫:‘大艺术家,你好!’他说我有姜太公之相,是可以辅佐周文王的人。我当时想,我不喜欢做姜太公,所以没有搭理他。他其实是有学问的。我应该给他点钱,和他聊聊。他的专业知识还蛮扎实。”[3]266木心小说《寿衣》中算命瞎子给陈妈算命,结论与陈妈之前的遭遇完全相符,论断也符合陈妈后来的人生轨迹,这可谓木心相信算命的间接证据。
木心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民俗社会时期的乌镇生活,尤其是乌镇民间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文学回忆录》《海伯伯》《塔下读书处》《夏明珠》《寿衣》等等,都涉及乌镇的世俗风情,有很多篇幅写到了木心童年时期听到家里仆人们讲述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中难免有很多迷信情节,木心对此都深信不疑。如:军队出征前旗杆突然被风吹断,主出师不利[3]260-261;“有人打算与李世民争天下,先去见他。李世民衣着随便地走进来,那人一看,大惊,自动投降、缴械,承认他比自己高。这是古代小说里面的故事,但是有道理。”[3]266
不仅相信中国民间故事中的迷信情节,谙熟西方经典的木心也相信西方“耶稣降生马槽,三博士看到流星划向东方,于是赶去东方朝圣”的故事,原因就在于“三维的宇宙尚有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神秘的力量存在”,“科学家无非是把整个宇宙解释成物质世界”[3]261,而科学家的做法却是有缺陷的。
所以说,木心有着浓厚的“迷信”思想是童年时期乌镇民俗社会的影响,加上他独有的宇宙观所致。木心将“迷信”与艺术联系起来,认为艺术家是百鸟中的凤凰,相信自己是个天才艺术家。如此等等,都说明木心身上“迷信”与自信并存的特质。
二、“相从心生”
木心相信“相从心生”,即一个人的相貌体现出一个人的固有素养、身份与前景,尤其前景,更是可以从一个人的相貌上体现出来。前文所举对李世民帝王之相的认同以及西湖边看相的对木心艺术家身份的预测,都是木心深以为然的。
木心曾经向曹立伟说起过一件趣事:托尔斯泰、契诃夫和蒲宁三人一起喝咖啡,看到窗外某个行人,托翁提议每人描述一下。托翁先描述那人的性格,契诃夫谈那人的身世,轮到蒲宁,蒲宁望了那人一下,说,是个坏人!托翁听了一愣,立刻赞美。故事说到这里,木心说:“就那个评论而言,蒲宁最厉害,不说什么衣着啊,职业啊,特征啊,什么的,不说那些,直指灵魂。”对木心的评论,曹立伟不以为然,认为木心偏于以貌取人。木心听了,认真地说:“是的,但是呢,相从心生还是对的。”[5]181
这种“相从心生”,体现于木心对艺术家身份的认同上。木心认为,艺术家之“相”是很显然的,体现于艺术家的外貌与气质。如他对斯特林堡的评价:
斯特林堡是个精力充沛、性情乖僻的人。易卜生初见他的照片,说:这个人将来比我更伟大(现在看,我认为易卜生还是比斯特林堡更伟大。他凭照片能出此判断,已经伟大)。斯特林堡长相雄伟,像海盗王,人称“暴风雪之王”。[2]685
斯特林堡像“海盗王”似的雄伟长相,使易卜生认为他必将会成为超越自己的艺术家,木心虽然不完全认同易卜生的观点,但也不否认斯特林堡的伟大。再如卡夫卡:
卡夫卡的荣誉超过了他的实际成就。写甲壳虫和地洞中的鼹鼠,我原先就觉得不对。卡夫卡是有精神病患的。但是,卡夫卡,你去看他那张脸,多伟大啊。[3]260
卡夫卡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不得了。等到看见照片——这么苦命。从耳朵、眼睛,一直苦到嘴巴。这么苦命,和中国贾岛一样。[2]853
木心认为,卡夫卡面相“苦命”但又“伟大”,这与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大有关系:卡夫卡终身郁郁寡欢,老在疗养院过日子,又有严重的肺病,所以说此君“苦命”;卡夫卡老是喜欢“焚稿”,境界极高,临终嘱托好友布罗德烧毁他的全部作品,但最终被好友保留下来,这些作品成就了卡夫卡的“伟大”。从卡夫卡“苦命”且“伟大”的面相上,木心就认为卡夫卡是个天才的艺术家。
木心自视极高,且认为自己就是天才的艺术家,这也体现于他对自己的面相与著名艺术家面相的相似上:
法国诗人兰波、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面容很像,像极了。
兰波的相片摄于一八六九年。
马雅可夫斯基的相片摄于一九O九年。
智利诗人聂鲁达把这两张相片挂在一面墙上,酷肖的程度,认为有某种神秘天谕。
我认为:偶然,纯属巧合——偶然的巧合的以上的意义,绝不是聂鲁达能说得明的。
(聂鲁达果然说了,说了一大篇,果然越说越糊涂。因为聂鲁达的脸不像兰波,不像马雅可夫斯基)[6]102
木心不赞同聂鲁达对兰波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人面容极其相似的解释,认为两人相貌相似既有“偶然的巧合”,更有“偶然的巧合的以上的意义”。“偶然的巧合的以上的意义”是什么?木心认为聂鲁达无法解释,因为聂氏的相貌与兰波、马雅可夫斯基根本不像,倒是邱智敏先生看出了木心的心思:
“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木心先生的脸(尤其晚年),如兰波和马雅可夫斯基,有着“偶然的巧合的以上的意义”。这层意义非才识非想象力所能说明,而是艺术的天性——如木心的“心”,是草木之“芯”,柔弱无形却能破土而出,随性自在的生命精魂。[7]92
原来如此!因为木心认为自己的相貌与兰波和马雅可夫斯基非常相似,这体现出艺术家之间共有的“艺术的天性”,这才是“偶然的巧合的以上的意义”。此论切中肯綮!木心曾言:“听到聂鲁达说马雅可夫斯基和兰波很像,我心中狂喜。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狂喜。我写他,心中充满对他的爱。因为是爱,不能不说实话。”木心“狂喜”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兰波、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是艺术家中的三大美男子,自己与其中的两人长相酷似,岂不是说自己也是美男子一枚;另一方面,木心与兰波、马雅可夫斯基相貌酷肖,意在说明自己和他们一样,都有艺术家之“相”,自然也是真正的艺术家。这正是木心梦寐以求的愿望。
木心相信“相由心生”,信奉“以貌取人”,这一点也为朋友所熟知。木心交友谨慎,且十分挑剔,“进入他视野认可为朋友,首先他得认为其人品可靠,对己不会有什么伤害,同时确信‘相由心生’,认为人是可以貌相的。木心曾学过看相,因此也常以貌取人”[8]9。
木心对形象“恶俗”之人,往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排斥感。形象“恶俗”之人即便身处难中,也难以勾起木心的同情与怜悯,这一点木心没有隐晦:“我一向自私,而且讲究人的形象,形象恶俗的弱者,受苦者,便很难引起我原已不多的恻隐之心。我每每自责悭吝,不该以貌取人;但也常原谅自己,因为,凡是我认为恶俗的形象,往往已经是指着了此种人的本心了。”[9]61在木心看来,形象恶俗,往往就意味着人的“本心”也是恶俗的。
三、命运预兆、人与生灵的思想共通
木心不仅相信“相由心生”,而且相信人的命运是可以依据生活中的一些迹象进行显现与预测的;同时,自然界的生灵与人的思想情感也往往有着共通性,与人类同喜同悲,这在木心的散文《九月初九》中有深刻的说明:
中国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说过了再重复一遍也不致聒耳,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这个俄而形上俄而形下的谛旨,姑妄作一点即兴漫喻。譬如说树,砍伐者进来,它就害怕,天时佳美,它枝枝叶叶舒畅愉悦,气候突然反常,它会感冒,也许正在发烧,而且咳嗽……凡是称颂它的人用手抚摩枝干,它也微笑,它喜欢优雅的音乐,它所尤其敬爱的那个人殁了,它就枯槁折倒。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幸蹇,或盈或涸,或茂或凋,或憔悴绝食以殉。[9]10
木心曾说到过一件事:
在美国有一次和童明聊到晚上两点,忽然外面的鸟都叫起来了,一大群。他说不会是天亮了吧,我说,是它们感受到思想的光了。思想有光,人感受不到,鸟先感受到了。
我母亲死的那一年,她种的那株月季也凋殒了。[3]263
关于此事,陈丹青先生记载得非常详细:
木心,几次三番说起过一件事,带着自我的神话感,圆瞪双眼。他说,加州的童明那年专程来杰克逊高地采访他,谈到深宵,有一刻,当他刚刚说出自以为绝好的意思,登时,窗台外不停地有只夜鸟欢叫起来,叫到黎明。木心迷信——或者,这就是他所谓的诗意——我听出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被视为征兆的鸟叫,不是关于俗世的命运,而是,天界正在报告他的非凡。[1]112
在木心眼里,特定情境下的鸟儿欢鸣、月季枯萎,其实都是生灵因为感受到人的光辉或死亡的有灵性的反应。
月季枯萎,是因为主人死亡;那么,枯木逢春呢?木心说:
我欣赏另一种传说:《牡丹亭》试演时,当时有玉兰树久不开花,丝竹管弦起时,满树齐开花——这种传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2]413
类似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所以木心说“假的,也好”。但木心又真心希望这样的传说是确实存在的,因为《牡丹亭》描述的爱情实在过于唯美浪漫,唯有枯木逢春,才能间接显示出这个剧本的价值。所以木心又说“真的,也好”。
人的命运预兆,主要体现在人的脸上:“现在正巧是一个先知辈出也无济于事的时代,谈不完的卡夫卡,其实他是个‘预兆’,二十世纪的不祥之兆,他的作品、人、脸、眉目,都是‘预兆’。并没有‘卡夫卡’模式,萦心不去的是‘卡夫卡现象’。”[10]99前文已经说过,卡夫卡的脸,实在是苦透了,正因为“苦”得太深,就不仅是个人悲惨命运的预兆,而且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不祥之兆。木心一直认为二十世纪是令人厌恶的商品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是倒霉的事,他垂青的,是天才辈出的十八、十九世纪。所以,将生活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卡夫卡的过“苦”的脸作为令人生厌的二十世纪的象征与预兆,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接下来就是个人命运的预兆了。这体现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是手掌。木心言:“我看过林风眠先生的手掌,掌纹有断裂,人生会大起大落。”[3]266林风眠先生“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木心在《双重悲悼》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二是无意之笔,不祥之句。木心写道:“世上有几对伟大的朋友,歌德和席勒是模范,至死不渝。每年元旦,两人都要写信祝贺,1805年,歌德无意写上‘最后的一年’,惊觉不对,换了纸重写,又出现‘我们二人中,总有一个是最后之年’。”[2]482席勒终于是年死。
三是作品题目。德国诗人奥尔格·海姆(1887—1912),曾见人落在水里,跳下去救人,结果自己死了,年仅二十五岁。木心写道:“他生前出过一本诗集《永恒的一天》,这题目不祥。”[1]860
四是“被人挂在嘴上”。木心写道:“从前我和李梦熊谈卡夫卡,其实都没有读过他,都是骗骗自己。来美国后只听港台文人卡夫卡、卡夫卡,家里还挂着他的像——我心中觉得情况不妙。一个人被挂在嘴上,总是不妙。”[2]852
当然,一个人的命运预兆尤其艺术家身份的命运预兆,最主要还是体现于人的“面相”,这在木心的作品与言论中比比皆是。如木心评价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穷,但深知自己的才华,他是真的贵族,高额头,一副苦脸,像猫头鹰,深沉。”[2]708评价美国作家自然之子的梭罗(1817—1862),木心说:“看他的相,还是一个知识分子。”[2]716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尤其是真正的艺术家,他的面部特征还是有迹可循的,曾经学过算命的木心对此非常有心得。
四、“艺术是前世的回忆”
见到艺术家时的那种“心有灵犀”,就是木心所说的“艺术是前世的回忆”。木心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自己第一次见到艺术家的画像时的那种特殊的感受:
其一,关于叶慈,木心写道:
叶慈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一听名字,就神往,这种感觉我常有,许多人也有。这道理要深究下去,很有意思——人有前世的记忆(我最早看到的还是‘夏芝’的译名,已觉得很好了)。”[2]692-693)
其二,关于音乐家和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木心写道:
我小时候不看这类不许看的书(注:指“三言”“二拍”等话本以及明代拟话本《醉醒石》《石点头》《今古奇观》等),冷静明白:这不是文学。……到后来,听到勃拉姆斯、舒伯特、瓦格纳,看到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一见如故:这就是我所要的音乐、文学!这种本能的选择分辨,使我相信柏拉图的话:‘艺术是前世的回忆。’纪德也说得好:‘艺术是沉睡因素的唤醒。’再换句话‘艺术要从心中寻找。’你找不到,对不起,你的后天得下功夫——你前世不是艺术家,回忆不起来啊。”[2]439
其三,关于诺瓦利斯,木心曾在多种场合说到过初见诺瓦利斯时的那种特殊“因缘”:
(1)早年,偶见诺瓦利斯的画像,心中一闪:此卿颇有意趣。之后,我没有阅读诺瓦利斯作品的机会。近几年时常在别人的文章中邂逅诺瓦利斯的片言只语,果然可念可诵——诺瓦利斯的脸相,薄命、短寿,也难说是俊秀,不知怎的一见就明白有我说不出的某种因缘在。[11]10
(2)想起诺瓦利斯,十八世纪德国的Novalis,柔发稀疏,玻璃花如的面容,不满三十岁就离开尘世,初次见到他的画像,就觉得以后会想起他,那种引人怜惜的脆弱,是否锋锐的灵智必定要有如此头颤然欲碎的形相呢,他曾说:
“哲学原就是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科学,更是一种大乡愁的剧烈冲动。[11]94-95
(3)我少年时见他(注:诺瓦利斯)一张铜版肖像,眼神特殊,一直不忘——人是可以貌相的。从他身上说,以貌取人是行得通的。心有灵犀,一点是通的。有诗集《零片集》。他的句子,一读狂喜,通灵。[2]613
其四,关于博尔赫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著名作家。木心说:“1899年生——比我大二十八岁,应该称他文学前辈,感觉上他是我文学表哥——从小热爱文学,这非常对。说起来也怪,没有考虑的,就喜欢,谁也没有告诉你:你要去爱艺术。都是不假思索。仔细想想,这很怪。现在我想通了: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中国叫作“命有文昌”。命无文昌的人,出身书香之家,也等于文盲。”[2]1055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木心的想法: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前世就是艺术家,今生与艺术是有缘的,成为艺术家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命有文昌”。因此,无论对音乐还是文学,他都有一种天然、本能的悟性与赏鉴力,并且与之产生共鸣。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他才决定不辜负艺术对自己的眷顾,决定做一个“知易行难”的艺术家。
真正的艺术家在相貌上是独一无二的,非常有特色,并且往往非常俊美。这就是木心的想法。木心非常崇拜个性十足的拜伦:“司汤达在世上最崇拜拿破仑和拜伦。由此在意大利,一晚会据称有拜伦。司汤达大喜,去,原来座位就在拜伦旁边。远远看见拜伦入场,他已昏昏沉沉,根本无心听音乐。他说拜伦皮肤如大理石中点了灯。那晚,他说未听到音乐,但看到了音乐。”[2]515-516司汤达认为拜伦的肤色“如大理石中点了灯”,可谓极其俊美了,木心却认为司汤达的说明还不够深入:“拜伦本人的肤色就精妍得宛如云石中点了灯(我相信司汤达不致言过其实,恐怕还是言不能过实哩)。”[10]20木心甚至把拜伦的俊美与壮阔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1948年我乘海船经台湾海峡,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杆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
而我当时的行李中,就带着拜伦诗集。[2]515
木心称勃朗宁的诗“淡远简朴中见玄思”,勃氏是个“博大精深”的诗人,纪德称其为“四大智星”之一。“他像一座远远的山,不一定去爬,看到他在,我就很安心。他相貌极好。”勃朗宁的夫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嬛·勃朗宁,“是英国女诗人中最有成就的,相貌也极美”[2]527。再如木心认为乔治·吉辛“长得俊美,聪明”[2]544,托马斯·卡莱尔“是很有魅力的男人,长得雄伟,爱默生推崇备至,敬爱他”[2]552。“在世界诗人中,兰波、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三人,长得最漂亮。叶赛宁像天使,兰波无确切照片画像可参考,一张一个样。”[2]884“莱蒙托夫也死于决斗。他的大眼睛泪汪汪的,真是悲剧的眼睛,天才诗人的眼睛。”[2]638-639“卢梭长得很俊,这类人都长得蛮好看,这是他们的本钱。”[2]468
勃朗宁夫妇、吉辛、卡莱尔、兰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卢梭等人,要么相貌极美,要么威武雄壮,要么眼睛非凡,这与他们艺术家的身份是相匹配的。反之,有的艺术家,因为相貌不尽如人意,即使作品令人佩服,也不能深得木心的青睐。如木心评价萨特:“萨特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他演砸了。别的戏,他演得很成功。我生来讨厌戏子,看他照片,即觉得非我族类。”[2]924“我看到存在主义时想:存在主义行,萨特不行。他那张脸你看看。”[2]904“他(指萨特)长得难看,又崇拜‘文革’,我起初讨厌,后来看了作品,还是佩服他。”[2]889即便佩服,萨特也不能深得木心之心。
木心从不相信天才能够遗传。艺术家一旦去世,就带走了满腹才华,他们的后代不仅远远逊色于先辈,而且在相貌上也缺少了先辈的机灵与俊美。“莫扎特他们都是无后的,前几天报纸上报道莫扎特的第七代子孙,还有照片,喔呦,你看那些人的蠢像,愚钝麻木,和莫扎特有什么关系呀!天才都是吝啬的,不肯把才华给别人,不肯的!”[5]177“我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我讲俄国人,是讲普希金,不是讲他的第九世孙——一个大胖子,又胖又蠢。”[2]614在木心眼里,艺术家的才华与相貌是成正比的,艺术是非常吝啬的,不会随着艺术家的基因而传承下去。
木心信奉“以貌取人”,认为生命轨迹与人生发展在人的外貌特征与行事作风中有着一定的规律。他尤其崇尚艺术家之“相”,相信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有着让人称道的外形与肖像。同时,他依据自己初次见到艺术家画像产生的那种难以言表但确实存在的亲近感,果断认为自己“命有文昌”,是艺术家的再次转世。既然“艺术是前世的回忆”,自己就不能辜负艺术对自己的涵养,这恐怕也是木心这辈子献身艺术而从不后悔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