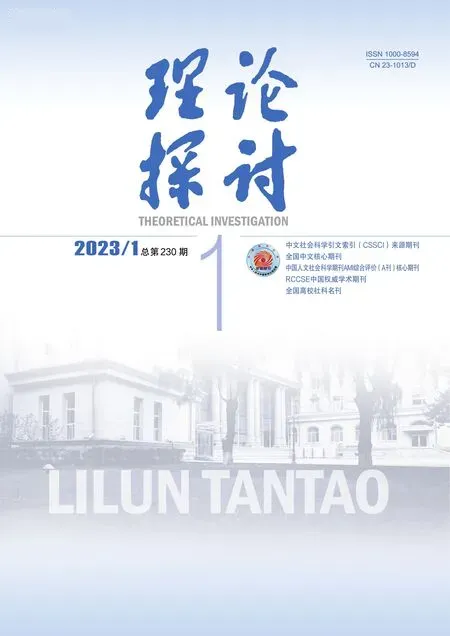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贡献及特征
2023-04-05柴文华王春辉
◎柴文华,王春辉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06
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部著作的贡献在哪里?特色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地位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
一、开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历史时间和代表人物书写;另一种是按照问题书写。
按照历史时间和代表人物书写是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史家所采用的范式,如谢无量、胡适、冯友兰、钟泰、范寿康、冯契、萧萐父等。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书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全书共分三编,每编又分上下两部分,分别是上古哲学史(古代及儒家、道墨诸家及秦代)、中古哲学史(两汉、魏晋六朝唐)、近世哲学史(宋元、明清)。其特色一是出版时间最早;二是具有了初步的现代哲学意识;三是初步运用了西方哲学的框架、概念梳理了中国哲学史;四是初步运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五是具有较为浓郁的经学味道。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人运用现代方法书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全书共分十二篇,在《导言》之后,分别写了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大学》和《中庸》、孟子)、荀子、古代哲学的终结。其特色一是采用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二是坚持老子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人;三是运用了逻辑证明的方法;四是高度重视墨家的科学和逻辑思想;五是非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是中国人运用现代方法书写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全书共分两篇,即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分十六章,分别涉及绪论、泛论子学时代、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孔子及儒家之初起、墨子及前期墨家、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学、战国时之“百家之学”、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墨经》及后期墨家、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韩非及其他法家、秦汉之际之儒家、《易传》及《淮南鸿烈》中之宇宙论、儒家之六艺论及儒家之独尊。经学时代也分十六章,分别涉及泛论经学时代、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古文经学与扬雄王充、南北朝之玄学(上)、南北朝之玄学(下)、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隋唐之佛学(上)、隋唐之佛学(下)、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及二程、朱子、陆象山王阳明及明代之心学、清代道学之继续、清代之今文经学。冯友兰自己说过,他的这本书有两点可以引以为豪:一是把先秦的辩者分为两派,即“合同异”和“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二是把二程的哲学思想区分开来,明道乃心学之先驱,伊川乃理学之先驱。冯友兰也谈到这部书的两个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然而,从今天的视域来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开创了成熟的、完整的以历史的自然秩序和代表人物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范式,而且运用了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勾勒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范围和框架,对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时期,还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与谢无量的历史阶段划分类似,分四编,即上古哲学史、中古哲学史、近古哲学史、近世哲学史。其特色是委婉拒绝“以西释中”,认为中西学术属于不同的系统,如果强行进行比较,很容易出现牵强附会的现象。因此主张采用史传的方式,一用旧文、一从常习。按照今天的说法,钟泰所选择的是“以中释中”的诠释框架。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分六编,即先秦时代的哲学(子学)、汉代的哲学(经学)、魏晋南北朝的哲学(玄学)、隋唐的哲学(佛学)、宋明的哲学(经学)、清代的哲学(经学)。该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以马释中”的先河,这也是这部著作的最突出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哲学史通史性的著作,如冯友兰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其特色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框架书写中国哲学史,不过有的侧重“对子结构”,有的侧重“螺旋结构”。诸上论著都是按照历史的自然秩序和典型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书写。
第二种就是按照问题书写。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哲学问题史》,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三大部分。宇宙论部分包括本根论、大化论;人生论部分包括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致知论部分包括知论、方法论。该书是第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中国哲学范畴史,开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书写范式,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也如张岱年自己所说的那样:“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1]17新中国成立以后葛荣晋的《中国哲学范畴通论》、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等都是对《中国哲学大纲》书写范式的继承和发展。
二、运用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
因为张岱年是用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哲学问题史的,这是典型的西方哲学框架。“20世纪10年代,随着哲学作为现代学术建制在中国登场……中国哲学史也摆脱了传统学术史的羁绊而独立成科,中国哲学史在那一时代就是用西方哲学范式剪裁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制作出来的新衣”[2],“以西释中”构成当时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主流方法,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术产物的重要标志,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得到了认肯。如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要想把中国哲学史编成系统,不可能依赖古人的东西,只能依赖西洋的哲学[3]。冯友兰也是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为框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张岱年自己也说过:“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1]17-18“中国哲学史要想进入‘现代知识’的范围,就不得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这种‘不得不然’就是指必然。胡适还对参照西方哲学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指出,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现代视域,让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传统思想资料里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充分肯定了西方哲学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价值”[2]。
可以说,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家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哲学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他们使‘潜在’的中国哲学浮出水面,并自立于学术之林。按照胡适的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条理,无头无绪,做中国哲学史的人的任务,就是在无条理中找出条理,在无头绪中找出头绪,从而制作出有历史有逻辑的中国哲学史,亦即就是把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与现代逻辑系统结合起来,从而以一种新的面目呈现于世。以西方哲学为框架建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功不可没。时至今日,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能说已经过时,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离开西方哲学还能谈哲学和中国哲学吗?不可能”[2]35-36。众所周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哲学都是在与西方哲学的结合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哲学的框架、方法、范畴等建构了现代中国哲学,如梁漱溟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借鉴、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逻辑方法的应用、金岳霖对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运用、贺麟对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汲取等。同样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西方哲学的语言、理念、框架成为重要的参照系统。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离开西方哲学,我们很难论说哲学和中国哲学。
三、用中国哲学史中的特有观念来表达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大纲》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古代哲学建构为一个由诸多问题组成的系统,这就使得表面上没有系统的中国哲学显示出一个宏大的系统,并分解为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哲学问题都是用中国哲学史中特有的观念来表达的,如“道论”“太极阴阳附五行说”“气论”“理气论”“大化论”“变易与常则”“反复”“两一”“始终”“有无”“坚白”“同异”“形神”“天人合一”“天人有分”“天人相胜”“性善”“性恶”“仁”“兼爱”“无为”“有为”“诚”“明心”“践形”“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志功”“名与辩”等,这与我们今天提倡“自己写”“写自己”的方法论转向是合拍的。
新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版了一批以教材为重点的中国哲学史通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齐勇先生主编的十卷本的《中国哲学通史》已经出版,可喜可贺。新世纪以来,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自己写”“写自己”。“自己写”就是试图摆脱格式化或教条化的偏向,按照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书写中国哲学史,即冯友兰所说的“海阔天空我自飞”[4],张立文所说的“自己讲自己的中国哲学”[5]《前言》2。“写自己”是凸显本土特色亦即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更加接近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讲述中国哲学的逻辑系统和概念范畴(名字)体系,以凸显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卓越爱智、独特品性、崇高道德、神妙神韵”[5]《前言》3。“‘自己写’‘写自己’,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再一次提出了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重要性,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通史书写的主流导向,这是对百年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反思后的一次方法论转向,体现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挺立,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树立了明确的航标”[2]35。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诠释框架虽然是西方的,但内容、概念、风格都是中国的,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
这里表面上似乎存在一种观点上的紧张,《中国哲学大纲》既采用了西方哲学的框架,又突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这里是否存在某种矛盾?很明显,提出这种问题的学者是基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不可通约的理念,是一种错误观点。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是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哲学,“类”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决定了通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又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这恰恰是一种“和而不同”之“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四、人生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
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大块,其中,“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中国哲学所特重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哲学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194。张岱年的这一说法并非夸大其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中国传统哲学的确是以人为核心的,从由人发散的多维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肉体与精神)来探讨人,提出了丰富的人性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思想和学说。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关注人,而是说中国传统哲学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和集中。中国传统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不与自然、神、科学相冲突的广泛的人文主义。张岱年举例说,先秦时期,孔、孟、荀等都不注重宇宙论的研究,主要讲的是人生论;宋代以后的思想家虽然有不少关于宇宙论的学说,但核心部分仍是人生论。张岱年是从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等方面来阐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生论的,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人性论和“天人合一”。
(一)人性论
人性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容非常丰富,“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1]194。张岱年认为,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历来讨论不休,出现了诸多不同类型的学说。
1.性善与性恶。孔子认为,人性是“相近”的,不能以善恶论人性。之后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但二者对性的理解是不同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性中所固有的,随时而发现,无待于学习,但孟子并不否认人具有与禽兽相同的自然欲望,他所说的性是在人禽之辨中凸显出来的人的特性,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就是仁义礼智“四端”,也可称为“理义”,而失去这些,就是“非人”了。张岱年总结说:“孟子所谓性善,并非谓人生来的本能都是善的,乃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要素即人之特性是善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之端,故人性是善。”[1]216荀子所说的“性”与孟子大不相同,是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这些“天之就”“不事而自然”“生之所以然者”,性中并无礼义,因此为恶。所有人皆如此,“尧舜与盗跖,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与性相对的是“伪”,即人为,性虽恶但可变,可“化性起伪”,“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仁义,仁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张岱年的解释是正确的,按照劳思光的说法,孟子的“性”是“Essence”,是德性自觉之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荀子的“性”是“Nature”,是自然之性,是人与动物所同有者。所以一个主性善,一个主性恶,但二者都是强调仁义礼智的重要,殊途而同归。概而言之,“孟子言性善,乃谓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无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虽然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并非完全相反”[1]220。
2.性无善恶与性超善恶。性无善无恶为告子所倡,“性无善无恶也”(《孟子·告子上》),所有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生之为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生来具有的食色即性。这与孟子所谓“性”大异其趣,所以被孟子作为批判对象。告子的“生之为性”与荀子的“天之就也”略近,但毕竟有异,荀子所谓的恶的内容如“好利”“疾恶”等非“天之就也”。王安石认为,情可善可恶,“性”无所谓善恶;苏轼认为,“性”不能有善恶,但善恶皆由“性”出等。性超善恶论为先秦道家所倡导,“道家不承认仁义是人性,亦不承认情欲是人性,而认为仁义情欲都是伤性的。道家所认为‘性’者,是自然的朴素的,乃所谓‘德’之显现。宇宙本根是道,人物所得于道以生者为德,既生而得之表见于形体者为性”[1]222,“道家所谓性,既非孟子所讲仁义之性,亦非荀子所讲情欲之性。其谓仁义非性,同于荀子;谓情欲非性,同于孟子……道家只教人顺性自然,无知无识的生活下去,这是与诸家都不同的”[1]224。胡宏认为,“性”与宇宙之本根同,善恶不足以言性,这是一种性超善恶论;王阳明以无善无恶便是至善,是超乎善恶之对待的善,亦是性超善恶论,等等。
3.性有善有恶与性三品。张岱年认为,性有善有恶说是一种调和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学说,分两种情况:“一谓性有善有恶,后来发展成性善恶混论;一谓有性善有性不善,后来发展成性三品论。”[1]228王充《论衡·本性》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认为性中兼含善恶,这是有善有恶说的源头。“讲性有善有恶较详审的,为汉代董仲舒,认为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不全是善,也有恶的要素”[1]228。董仲舒还由此提出了他著名的“性三品”说,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依次是纯善、有善有恶、纯恶。王充也认为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等。扬雄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韩愈认为,性分上、中、下,上为善,下为恶,中可导而上下,与董仲舒“性三品”说近似。张岱年指出,性有善有恶论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即所谓“性善情恶”说,以董仲舒、刘昼、李翱等为代表。这种学说实际上是变相的性有善有恶论,只不过是把性中之恶称作情而已。
4.性两元论与性一元论。性两元论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形态的人性论,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这种人性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宇宙论为基础而推演出人性论,或者说把人性论和宇宙论统一起来,具有较为浓郁的形上学味道。明确提出性两元论的是张载,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程颐认为,世界由理和气构成,人性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无不善的理性,相当于张载的“天地之性”;二是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理性是宇宙本根之理,“气质之性”则来源于气。朱熹是性两元论的集大成者。与程颐一样,朱熹认为,世界由理与气构成,而人也是“理与气合”而成,“天地之性”专指理言,无有不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结合,有善有恶。性一元论在明清时期较盛。这种学说发端于陆九渊,他虽然也分别性与气质,但认为心性不二,具有一元论的倾向。王阳明也主张心性不二,认为不必分性与气,四端都是气,气也是善的。刘宗周讲性气一元较为详备,其核心观点是认为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更直接地说,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其弟子黄宗羲也认为“性”只是气质之条理。颜元是彻底的性气一元论者,认为性气一体,离开气无所谓“性”。戴震是性一元论的大成者,认为人的血气心知就是性的实体,离开血气心知别无所谓“性”,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缜密的论述。
除了性两元论、一元论以外,张岱年还特别提到了王夫之的人性论,称其为“性日生论”,是人性论中别开生面的新学说。王夫之把气化日新的理论应用于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日新的,是不断生成的,生来具有的是“性”,后来养成的也是“性”,“性”不是固定的,常在创新之中。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广泛的人文主义,其中人性论学说十分丰富,张岱年对此进行了有统有分的细密梳理和分析,他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分成不同类型,如性善、性恶、性无善恶、性超善恶、性有善有恶、性三品、性两元论、性一元论、性日生论等,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的所有类型,有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不刊之论,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提供了重要参考。张岱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的解读基本是“述而不作”。在我们今天看来,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按照冯友兰的观点,是“正性”和“辅性”的统一,“正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如道德、理性、文化、符号、创造等,“辅性”即人与动物都具有的如饮食男女等的自然属性。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生物人类学的观点,自然属性本身也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构成人之为人的特性,如饮食男女,人的饮食男女绝不等同于动物的饮食男女,人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即追求美味等。因此,仅仅以善恶探讨人性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天人合一”
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特异”的学说,“是中国人生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1]195。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有两种意涵: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
“天人相通”说的是天的根本性德是内含于人心的,虽然有天道,有人道,但天道人道只是一道,二者“一以贯之”,“宇宙本根,乃人伦道德之根源;人伦道德,乃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1]202。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哲学不注重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区分,“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1]194。“人之心性与天相通”也是人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之一。这种学说发端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性”在于“心”,尽心则知性,“性”禀于“天”,知性则知天。当代大儒熊十力曾经说过,在“新唯识论”的视域里,“心”“性”“天”虽三名而实一体,都是“体”的别名,以其为身之主宰名曰“心”,以其为人之为人的依据名曰“性”,以其为宇宙的本质名曰“天”。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包含理性认知的认识论意义,但主要是伦理学的,肯定人的善性与天的本质是一致的,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张岱年指出,孟子提出的“天人相通”说得到了后儒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但由于理学和心学的差异,两派的“天人相通”说有同有异,“两说之根本不同,在所说心性之关系不同:一谓心中含性而非即性,一谓心即是性。但认为人含有宇宙之本根,天人相通不隔,则两家无异。两说都认为宇宙本根乃道德之最高准则;人之道德即是宇宙本根之发现……此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汉宋儒家哲学中之一个根本观念”[1]206。张岱年指出,清初王夫之论天人相通最为明晰,指出天人形质上虽有差异,但都“所继惟道”,这表明天人合一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
“天人相类”说是董仲舒的观点,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类似,集中体现在“人副天数”的学说中。“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人相类”说和“天人相通”说虽有较大差异,但也是“天人合一”说的一种类型,“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虽然董仲舒对之论述得很具体,但具有明显的牵强附会的色彩。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究天人之际”的“天人合一”说确如张岱年所说的是一个根本观点。“合一”并非简单相加,而是指内在关联。人们对“人”的理解差异不大,是指个体或群体或类的人,但由于对“天”的论说不同,至少出现了三类“天人合一”说:
第一,“天”指“神”“帝”,亦即最高的主宰者,可以简称为“主宰之天”。这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可以称作“神人合一”,较早出现在商周时代。一种是被动的,人完全听命于天帝;一种是主动的,通过政治的修为和道德的努力去维护天命的长久。
第二,“天”指大自然,即天地万物,可以简称为“自然之天”,这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可以称作“自然与人合一”。如荀子虽然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倡导者,但一方面主张“因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主张“爱自然”,在林木的生长期不要去砍伐,在鱼鳖的生长期不要去捕捞,通过维持生态平衡而为人类服务。又如道家反对“络马首”“穿牛鼻”等违背动物天性的行为,提倡建立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秋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庄子·养生主》),“好老庄之书”的鲍敬言主张建立人与动物之间互不相扰的和谐态势,“高巢不探,深渊不漉,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鳞群游于园地,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狐兔不惊”(《抱朴子·诘鲍篇》)。这种“天人合一”说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三,“天”指道德律令或道德法则,可以简称为“道德之天”,这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可以称为“道德法则与人的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说的核心内容,道德法则或张岱年所说的道德标准与宇宙本根是一体的,也是人的本性,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张岱年对“天人合一”的阐释抓住了“天人合一”说的主流,并对之进行了较为细密的梳理,也涉及“自然之天”,因为“天”在董仲舒那里既有主宰义,也有自然义。张岱年还补录了“天人有分”和“天人相胜”的内容,谈到了荀子和刘禹锡所说的“自然之天”。张岱年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也有微词,认为将人伦义理说成宇宙的主宰原则,犯了“拟人”的错误,但张岱年忽略了“主宰之天”与人的合一,可能是认为其不甚重要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