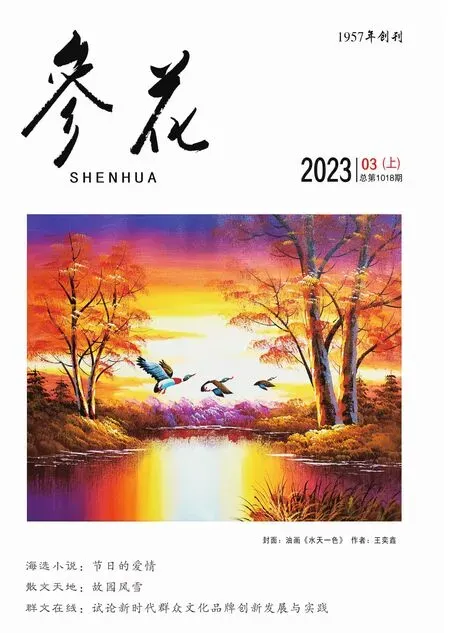先生的乡愁
2023-04-05杨文利
◎杨文利
想起来实在可叹,在燕园生活了四年,直至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才知道朗润园这个清幽、静僻的所在。一日,在宿舍独坐无事,隔壁的贾建良同学慌忙地闯进来对我说:“陈贻焮老师请你到他家里去一趟。”我听了此言,吃惊非小,忙问:“陈贻焮老师?”贾建良喘息稍定,便把自己请陈老师指导毕业论文,陈老师托他带话,欲邀班上三位湘籍同学到他家做客,一五一十,备细述了一遍。才出宿舍门,忽又探头进来加了一句:“陈老师是湖南新宁人。”
几天后,一个春阳和煦的星期日午后,我独自一人去朗润园赴先生之约。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体育馆,豁然别有洞天,遥见一岛,四围环水,湖中有荷,岸上多高柳。再北,过小石桥,行百余步,有几幢四层红砖楼房侧立道旁。循径行不远,便到了朗润园十二公寓,一零二号是一楼。轻轻敲了几下门,“呀”的一声,门开了,是先生本人。他眼光一闪,极快打量了我一番,不等我开口,便一迭连声说:“你来啦?欢迎,欢迎。”说罢,引我进了客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面如满月,状貌魁梧,淳朴有古风。他声音相当洪亮,满口湖南乡音,说话带笑声,透着一股爽朗之气。
礼毕,先生招呼我在沙发上坐定,含笑问道:“你们班不是有三个湖南同学吗?他们两个怎么没来呀?”我赶紧解释:“我们三人本来约定同来,不巧他俩临时有事,我就一个人先来了。”先生听说,“嗯”了一声,转身入厨房沏茶倒水。
见先生这般客气,我心中倒觉得不安。大二有一门必修课“中国古代文学史”,由葛晓音老师讲授隋唐五代部分,而葛老师是先生的开山弟子。论起来,我应当叫太老师才对。想不到先生学问极其渊博,性情又极其平易,一点教授架子也没有。正在想着,先生端来了两杯热茶,呵呵一笑道:“这是新宁红茶,尝尝滋味如何。”语毕,在沙发另一端坐下,自己也取一杯,轻轻啜了一口。我不懂得品茗,一尝之下,只觉其甘醇芳香,叹赏不止。
先生笑逐颜开,春风满面,殷殷询问姓名、年岁、籍贯,我一一告知。闲谈了几句,便渐渐地说到吾乡的地理、沿革。我所知不多,约略说了一点,先生听罢,拊掌笑道:“巧得很,我们俩的老家都在资江边上,只是新宁境内还不叫资江,叫夫夷江。”
忽又问起人物,我掰着指头列举:“有清朝的陶澍,有现代的周立波、叶紫,还有……”先生听毕,沉吟半晌道:“晚唐出过一个诗僧齐己,《全唐诗》收录了他八百多首诗。”停了一会,又道:“前几年出了一位莫应丰,是文学湘军中一员健将,可惜天不假年,走得太早。”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以前只知道先生以杜诗研究名重一时,哪里晓得他对当代文坛如此熟悉。
继而说到物产,才谈得几句,先生朝窗外望了一眼,又欢喜又感慨地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在家乡该上山摘三月萢了。”听见“三月萢”三个字,我激灵了一下,口水都流出来了。吾乡俗称三月萢者,是一种野生浆果,形略似草莓,色深红,多汁,其味甜酸,旧历三月始熟,故以名之。于是,一老一少,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说儿时摘食三月萢的情形,甚是相得。先生笑嘻嘻地说,小时候放牛,每当三月萢熟时,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到溪边去摘。吃得满脸满手都是三月萢汁,互相取笑一番,再捧起溪水洗净。三月萢树多刺,摘时须得格外小心,一不留神便会扎得嗷嗷直叫。
先生稍停一会,拿起茶杯呷了一口,我插嘴说道:“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多次写到三月萢,不过名字略为不同,不叫三月萢,叫三月莓。”先生听了此话,眼睛一亮,忙放下杯子,细问其详。我想了一想,把我所知道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丈夫》和《雨后》,一一说知。先生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地说:“三月萢多生于山谷溪涧,想必湘西一定不少。”我又告诉先生说:“他的小说中还写到过山莓,不知和三月萢是不是同一种野果。”先生听了接口道:“山莓是三月萢的别名,一名树莓,古称木莓。”
我忽然想起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谈及什么样的三月萢才好吃,对先生说了,于是话题转到采摘三月萢的诀窍。先生很在行地告诉我:“摘三月萢,就挑个儿头大的,鲜红的,有光泽的,保证又甜又香又脆。一粒入口,轻轻一咬,汁就流出来了。”先生兴致越发好了,手舞足蹈,开心得像个孩子,只觉人生之至乐,无逾于此矣。
由三月萢谈到家乡的野果,先生滔滔汩汩,一一道来:春天有刺萢、乌萢、蛇萢、茶萢、桑葚,夏天有杨梅、野樱桃,秋天有牛茄瓜、牛奶子、羊奶子、鸡爪枣、毛栗子、金刚刺、酸枣、毛桃、野梨、野柿子、野猕猴桃、野葡萄。一面说,一面咂嘴舐舌,若有至味。这些美味野果,敝乡处处有之,唯鸡爪枣闻所未闻。先生比手画脚,耐着性子解释道:“它结在树上,形如鸡爪,灰褐色,至秋成熟,味极甘美,可生食,浸酒尤佳。”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猛然一拍大腿,“对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拐枣。”先生讲了半天,我茫然莫晓。至今,我仍不知鸡爪枣为何物。这是题外话。
先生正说得起劲,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笑道:“只顾说话,倒忘了一件事。”不待说完,立起身便往厨房走。未几,捧出一盘切成四瓣的橙子,喜滋滋地说:“请你尝尝崀山脐橙,最后两只了。”少停,又用新宁话补了一句:“沁甜的。”脸上颇有得意之色。我剥了一瓣送进嘴里,果然甘香沁齿,其嫩无比。我一边点头咂嘴,一边用家乡话说:“沁甜的。”乃相与大笑。
赞叹了一回,先生向我眨了眨眼睛,抿嘴一笑道:“我给你吟一首诗吧。”我闻得此言,不觉又惊又喜。刚入校时,听一位学长说,先生娴习旧体诗,尤善吟诵,以传统吟诵调诵之,韵味十足。中文系学生都喜欢听他吟诗,引为乐事。我读中文系的时候,先生已升作博导,不再给本科生开课,惜无缘聆听,深以为憾,不期今日有此机会。
先生运了运气,清了清喉咙,随即晃着脑袋,拖着长腔,曼声吟哦起来,大有乡村塾师的气派。他半念半唱,吟了两首七绝,是先生自己所作,题为《回湘探亲》,其全首惜不能记忆,盖咏新宁风物。先生用湘音念诵,保留了中古音。其中一首,夕阳之“夕”、别趣之“别”,皆入声也。另一首,首句“人”、二句“津”、四句“春”皆押“真”韵。凡此之类,悉合格律。这种几于失传的老派吟诵,平长仄短,依字行腔,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极抑扬顿挫之致。
既罢,先生长长吁了一口气,笑着告诉我,年前回乡省亲,得偿夙愿,高兴之余,作了十首记游诗,适才吟诵的是其中两首。时隔半年,仍难掩喜悦和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谈起途中见闻,谈起新宁山川之胜,谈起崀山,谈起玉女岩,谈起夫夷江。先生娓娓道之,其眷恋之深自可想见。正说得兴起,不知怎的,突然顿住了,一言不发。默然半晌,幽幽地叹了口气道:“老喽,走不动了,回一次,少一次。”先生说这话时神情落寞,惘惘若有所失,我也不由得为之黯然。
出了一会神,先生抬起头来,启颜一笑道:“想不想听吹箫?”我听了这话,又是一惊,连声称好。先生顺手从旁边的小桌上取过一支竹箫,形似笛而长,色暗红,通身莹洁。先生略一寻思,点头说道:“吹一首郭沔作的《潇湘水云》吧。”言毕,坐正身子,头微微后仰,下颌抬起,深吸一口气,两手持箫,凑到嘴边。须臾,忽听得箫声悠悠响起,清越又浏亮,纡徐而婉转。先生沉浸在吹奏中,双目微合,神情端肃,吐纳之声可闻。吹着吹着,音调渐转凄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似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我在旁边听得呆了,心中暗想,张良一曲楚歌,或庶几乎此调。
曲终,先生把箫管一收,轻轻横于腿上,摩挲良久,委实喜爱到了极处。歇了片刻,复又谈起郭沔其人其作,说郭沔为南宋浙派琴家,永嘉人,值金兵南侵,流落湖湘,旅寓衡州。一日泛舟至潇湘合流处,但见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念故国之沦亡,感异乡之漂泊,作《潇湘水云》以寄意。此曲于潇湘之水光云影描写尽致,先生甚赏之,课余之暇,每喜吹奏。
又谈了几句,先生笑吟吟地说:“下次你来,我再吹一首《平沙落雁》,还有《梅花三弄》,这两支箫曲也跟衡阳有关。”先生随兴之所至,从《平沙落雁》谈到潇湘八景之一的回雁峰,从回雁峰谈到唐诗中的“衡阳雁”,最后,谈到杜甫的《归雁二首》。话到投机,越说越高兴。
言来语去,不觉日已沉西,方才起身告辞。先生执意送至楼门口,说了句:“得空常来耍。”我回了一声:“要得要得。”目送我上了大路,先生又直起嗓门喊:“叫他们两个一起来。”我闻言,诺诺称“是”,乃挥手别去。
光阴易逝,转眼到了离校的日子。我疏懒成性,把先生的邀约忘得精光,一见之后,遂不复见。刚毕业那阵子,因为工作关系,尝到朗润园拜访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三位老先生。有过几次,行经十二公寓,突然想顺道看看先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未曾请示,不敢冒昧登门,怕打搅了先生,而且几年不见,先生也未必认得我。那时的我对先生理解太少,而想得太多。那时的我万万想不到,几年之后,忽然听到先生溘然辞世的消息,愀然者久之。
后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读到,先生名片只印有“北京大学教授”,别无其他头衔,却特地印了一行字:“湖南新宁人”,倒有点像老派名士,见面先请教贵姓、台甫。这一下触动了旧事,始恍然悟先生当时热情相邀,无非是和几位同乡晚辈一起叙叙乡情,听听乡音,聊慰乡思而已。我深自愧恨,当初实不该爽约,辜负了先生一番盛意,而懂得先生心思时,斯人已去,遂至永失亲炙的机会了,虽欲悔之已无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