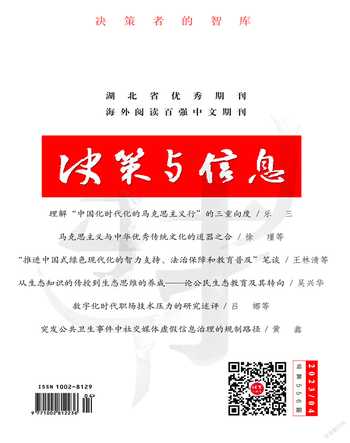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文化意义
2023-04-04黄赫男
黄赫男
[摘 要] 数据作为事实记录、学科构成基础以及技术是为人熟知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成为了生产要素之一,其重要性不断强化,但它作为信息、技术和符号所暗含的文化意义却常常被忽视。在日常生活中,数据在深入人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同时,也萌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数据不是单纯地记录现象、整理文本或提供决策依据的参考量,它常常蕴含抽象的文化符号或具体的文化意义,并且数据的流动性使其符号和文化意义进一步扩散。走出技术范畴的数据呈现了文化转向的态势,打破了文化资本建立的社会区隔,改变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数据的文化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数据是文化发展的载体,文化决定了数据生产及再生产的内容,数据的发展始终不会超越文化,因为文化的实质始终是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总和,总能与新鲜事象撞出时代的火花。
[关键词] 数据;文化转向;数据要素市场;数字经济;数据流动;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4-0057-11
一、引言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1],数据第一次作为生产要素跃入公众视野,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后第五大生产要素,其价值得到了上层建筑的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2]。202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3]。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再次突显了“数据”在当前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数字化在教育中的作用被强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文化的筛选、整理、传递、交流及创新。上层建筑的动态变化往往与经济基础直接相关,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时代,不仅改变了现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丰富了学界的研究内容、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影响着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数据”一词由“数”和“据”两个字组成,每一个字都有其具体的意义,“数”可以理解为“计数”,“据”则可以理解为“依据”或“凭据”,“数据”一词便是抽象和具体的结合。早在公元4世纪,就有人对“数”的问题进行了关注,到公元6世纪,古希腊许多卓越的哲学家、数学家开始对世界的本质进行探讨,从泰勒斯的“萬物是水”到毕达哥拉斯的“万物都是数”[4] 43,人类开始逐步对“数”进行探究。
而“数”发展成为“数据”,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丰富的文化意义。从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从机器的出现到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数的演算、叠加、记录、应用、推广……形成了各学科专业的符号、信息、知识和文化体系。数据无处不在,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形态的过渡。
“数据”在学术领域的广泛研究和关注,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这是近代数学创立与发展的时期,尽管数学这门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但是数据似乎一直没有随之获得相应的关注。众所周知,数据与数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息息相关,而实际上,数据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也关系密切,例如时间、农田、劳动力、人口、信息……数据无孔不入。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计算机学科的兴起和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数据的发展才出现了转机,数据产生了更强的冲击力、流动性和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数据(data)是对客观事物的符号表示,在计算机科学中是指所有能输入到计算机中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总称。它是计算机程序加工的‘原料”[5] 4,数据是计算机中的语言,“数据的含义极为广泛,如图像、声音等都可以通过编码而归之于数据的范畴”[5] 4。数据由此走入公众的视野,成为交叉学科间的“新宠”,并且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前,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数据”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出现了极大的扩展,也变得更加复杂。数据这种基于声音、文字、图像、符号等观察而来的结果,不仅成为了技术和生产要素,还成为了信息、知识和符号,数据的文化意义由此显现。过往对数据的研究只关注到了其技术属性和经济效益,忽视了数据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具体来说,数据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会区隔,改变了教育中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构建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规则,产生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二、数据自身的文化转向
数据是计算机语言中的符号总称,数据是技术体现在计算机每一次的信息处理过程中,人类基于电子设备的一切感受,都与数据这门技术密切相关。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数据与资本、技术等要素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例如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了车间的生产能力,数字农业则缓解了市场与需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前者暗含了企业文化的改变,后者则体现了数据对传统农业文化的改变;其二,数据还成为了消费品。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市场,无论是新媒体还是电子商务、短视频和直播等产业的蓬勃发展都使数据成为了文化符号的媒介和经济财富的载体。
无论是作为技术的数据,还是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都和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符号性是数据七大属性之一。“数据是一种物理符号或物理符号的组合,要依赖某种物理载体进行记录、传输或存储。这些记录、传输或存储数据技术的使用,通常是为了从数据中获得信息与知识”[6] 4。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关系十分密切,又有所区别。“数字、信息和知识都是对事实的表示,都具有符号表征,都或隐含或具有意义,都具有或长或短的时效性,这是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共同之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数据和信息的关系中,信息是世界的普遍性属性;数据是信息得以表现的符号形式,信息是数据的目的;经过数据处理后,有意义的信息得以表现”[6] 21。厘清三者的关系,可以发现,数据、信息和知识都具有符号指向性。
克利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曾论述过文化与符号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更多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它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混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7] 109。因此,符号在数据和文化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符号如同数据和文化的桥梁,基于它的存在,文化可以进行数据化的解读,而数据也因为符号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义。
数据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工具,在基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数据实践中,人类也创造了大量符号进行理解、互动。例如,在智慧医疗中,数据生产出“医生机器人”的符号,“医生机器人”既可以是实体的机器,也可以是虚拟的AR等数字技术设备,但都依靠数据来进行信息传导,方便患者就医;传媒产业中“流量”成为了标志性符号,“黑红也是红”“流量为王”使得夺人眼球的新闻层出不穷,与其说数据意味着阅读量、点击量,不如说数据衡量着传媒内容的价值;“小鲜肉”是娱乐业里的代表性符号,收获了前赴后继的拥趸,“粉丝”“应援色”“周边产品”……没有一个不依靠数据记录,没有一个不是符号,也没有一个不能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数据中的符号都具有文化属性,数据也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数据的发展出现了文化转向,生成了更为丰富的文化与现实意义。
文化转向原是翻译学领域中的词汇,由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共同提出,他们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提出“回顾西欧长期以来的翻译思维传统,我们意识到,相对较新的尝试将翻译的讨論局限于语言的限制,显然无法公正地反映问题的复杂性。此外,对传统——我们思维的谱系——的了解,帮助我们不仅关注与翻译本身有关的问题,而且还关注如何使翻译研究在一般文化研究中产生成效。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翻译应该在文化史上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目前它所处的位置”[8]。这意在说明,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对文化的理解以及在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意义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这也是文化研究中不可否认的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中也出现了文化转向。R.J.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第五次再版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增加了“文化转向”这一章节,其中包括了他对各类思潮所进行的汇编,包括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社会身份地位问题、文本与话语问题等,强调了社会问题的多样性与答案的差异性。“‘文化转向一词表达了二十年来不断强大起来的趋势,即将‘事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对于‘事实,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政治信仰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9]。翻译学中的差异化解读实际上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打破语言问题的限制,将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视野纳入讨论的范畴中。那么类似地,数据的文化转向则可以定义为:与数据研究收集、处理、存贮和反馈等过程有关的一切现象。其中不仅包括数据的本身意义、数据中的信息、知识与符号以及数据隐含的文化意义,还包括数据创造与运用等多个领域,还涉及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甚至地理学等多门人文社科学科。简言之,数据的文化转向就是技术维度之外的社会全域发展态势。
数据的文化转向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悄然持续进行着量的积累,直至数字经济时代,才呈现出质的转变。量的积累体现在一些文论甚至科幻小说中。例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从信息的角度,展望了数据对人类生活全域的冲击,“数字世界全球化的特质将会逐渐腐蚀过去的边界,有人感到深受威胁,我则欢欣鼓舞”[10] 248,《技术至死》则体现了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 与尼葛洛庞帝相反的态度,他关注到了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认为数据、互联网以及类似的前沿技术可能会颠覆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被颠覆,“它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而我们最好惟其马首是瞻,发现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当作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经验教训,相应地重新翻修我们的世界。如果这听上去像一个宗教,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11] 26。依照他的观点来看,数据所构建的互联网最终目的是建立广泛而绝对的信仰,人类对此盲从,就像一种新的席卷世界的宗教浪潮。
除此以外,波兹曼(Neil Postman)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德·穆尔(Jos De Mul)的《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贾森·默克斯基(Jason Merkoski)《焚毁书籍:电子书革命和阅读的未来》等书也分别从传统文化、赛博空间、电子阅读等方面讨论了数据与文化的关系。尽管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但为后人研究数据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参考借鉴。
2021年末,随着全球性的社交软件Facebook宣布更名为Meta(宇宙)这一现象级事件的发生,“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最早这一概念出现在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雪崩》(译者将“Metaverse”译为“超元域”)一书中。“超元域中的每个人其实都是软件,名为‘化身,是人们在超元域里互相交流时使用的声像综合体”[12] 44。“在这里,超元域这个虚拟空间中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逼真、多么美丽、多么立体化,都被还原成了简单的文本文件:电子页面上的一串串字母”[12] 437。而呈现在这电子页面上的一串串字母,以及人们互相交流的综合体就是数据,数据是元宇宙支持与运行的载体。这一想象在今天来看颇有科幻照进现实的意味,而不论“Meta”还是“Metaverse”都通过数据生成着意义,创造并传递着文化。所谓元宇宙(Metaverse),“从构词上看,Metaverse一词由Meta和Verse组成,Meta在希腊语中表示‘对……超出,verse代表宇宙(universe),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所谓‘超越现实宇宙的另一个宇宙。具体地说,就是指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运行的人造空间”[13],而在元宇宙中无论这些新生的文化究竟是否真正有价值,没人可以否认它们的存在,也没有人可以忽视它们与数据的关系。但难点是,要在元宇宙中认识人类文化与数据的区别和联结,把握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的价值观运用到数据的开发利用、文化的创新创造、元宇宙的维护建设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
近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世界各国陆续出台数据与文化的相关政策和战略,这无疑是数据文化转向的有力佐证。在中国,数据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信部在《“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3],数据的文化转向与中国国家政策紧紧契合,中国政府关于数据相关政策从政治经济方向逐渐朝文化与社会全域转移;在西方,欧美国家政府则从数据、技术和应用三方面推进大数据发展[15]。如美国发布了《联邦数据战略》[16],提出要运用数据开展好一系列具体实践,建立一套重视数据和促进公共使用的文化治理、管理和保护数据系统;英国政府在发布的《国家数据战略》[17]中则有一要旨——促进数据国际流动和共享;欧盟更是紧锣密鼓地发布了一系列用于指导欧洲适应数字时代的总体规划《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18]等。中国与西方在数据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这些规划和战略在无形中拉开了世界新一轮科技备战的序幕——一场没有硝烟的数据之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因为变革是呈指数发展的——昨天小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明日突发的剧变”[10] 12。
数据的发展变化是漫长的,从出现小小差异开始,发展至今,数据不仅成为了全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成为了一种可以定义事物的符号,其发展出现了数据文化转向的态势,生成了丰富的文化意义,随之带来的剧变冲击着社会全域。
三、数据打破文化建立的社会区隔
數据的流动性使其在世界的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发展空间,成为了全球化的资源,也因此使之具有类似文化的属性——“一种文化越是成为普遍的和公共的资源,它就越成功”[19]。数据也是一种可以广为利用的文化资源,适用的受众越多,范围越广,其价值就越高。而“在文化观点的发展过程中,单数的文化(culture)逐渐为复数的文化(cultures)所取代是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研究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20] 43。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与“他者”的区别,还暗含着文化的社会区隔,即“我”与“他者”的文化类型差别、价值区隔、认同归属、判断选择以及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过去,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曾从空间上打破了自然地理所建立的社会区隔,而在今天,无处不在的数据完全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前所未有地便捷,即时信息、同声传译、语音通话、共享画面、远程会议、社交平台等数据式的沟通,将时间和空间对于文化交流互动的限制无限缩小,随之人们寻求文化价值共识的理念、价值判断和社会行为选择也正在快速更新,这打破了阶级文化差异建立的社会区隔。阶级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个体或群体之间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悬殊,这导致人们审美存在明显差异,能获得趣味的文化选择也就不同。布迪厄(Pierre Bourdien)认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构成了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其结构是由其成员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分布确定的,每个阶级部分的特征是这种分布的某种配置,对应着某种生活方式,以惯习为中介”[21] 260。
斯沃茨(David Swartz)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文化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文化是有区隔的,“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22] 1。依照斯沃茨的观点类推,数据也属于符号系统,同样塑造着人对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的交往基础,并且帮助了数据掌握者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但是从符号的角度而言,数据与文化又不尽相同,数据不是传统符号,它的易复制性意味着它能够低成本地被使用,被再使用,甚至是被循环利用。数据是一种共享性的符号,随着它被使用的次数增加,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才越大,而其意义和价值越大,又会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影响范围。如果把数据看作一种传播现象,那么其受众一定是逐渐递增的,“受众的扩展源自两个因素:其一,随民主发展而来的普及教育的发展。其二,技术本身的更新”[23] 317。数据历史性的意义在于它的瞬时性和即时性,在数据的历史维度中世界每一秒钟都是崭新的,因此螺旋式的上升是数据扩张的逻辑,这也与文化发展的逻辑相符。
数据的扩张不仅打破了民族国家内文化的社会区隔,同时还在国家之间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我们经由电脑网络相连时,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将会改变,让位于大大小小的电子社区价值观。我们将会拥有数字化的邻居,在这一交往环境中,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而时间扮演的角色也会迥然不同”[10] 14。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使“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世界范围内国家价值改变的典例。截至2022年7月底,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文件的签署、合作的达成以及“数字丝绸之路”的构建,代表着中国的价值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么这一切与数据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试着去分析一下,首先,要进行中国和世界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才能够得出“一带一路”倡议;其次倡议的宣布经过了多重渠道的媒介进行数据传播;第三,中国建立了“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家‘一带一路数据分析与决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一带一路倡议研究院”等配套数据载体,便于世界获取“一带一路”的数据信息,包括“‘一带一路大数据指数”“中国数据”“各国数据”“地方数据”等等,这些数据的呈现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创造价值的记录,而不断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和组织由观望到加入的过程就是其价值发生变化的过程。当然数据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上述分析,这里强调的是数据影响了世界上国家和地区价值的变化。数据影响了国家间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的改变,由此可见一斑。
而“时间扮演角色的不同”,则体现在数据视域中时间的无序。“各种时态的混合,而创造出永恒的宇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自我维系,不是循环而是随机,不是迭代而是入侵;无时间的时间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为止可以提供的价值”[24] 403。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这段文字恰好是对尼葛洛庞帝预判的回应,数据即时变化性使事物进入到快速的流转中,以数据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将时间一同压缩了。而所谓的“无时间之时间”,实际上并不是说时间消失,“而是一种被挤压和集中的时间形式;时间不再是一种被动的缩减,而是在紧缩之后强迫事物的过程和内容的扭曲变化”[25] 362。
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流变中发展的,数据也不例外。但例外的是,数据作为一种工具,空前地改变了文化建立的社会区隔,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见证着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方式变化,见证着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也见证着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全球化的抵抗与妥协。与此同时,数据更对时空的存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空间成为了“没有地方的空间”,因为没有任何地方不存在数据,时间变化为“无时间之时间”,因为数据可以将时间压缩或者延展,尽管机械时间依然存在着。
四、数据改变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
人类一切生产生活的本质,都是具体时空限制下的行为。在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迈进,数据变得无所不在,不仅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会区隔,还打破了布尔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预设,改变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
布尔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设想适用于同质社会前提下的教育领域,他认为“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呈现在我面前的,这种假定能够通过联系学术上的成功,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26] 193。布尔迪厄肯定了人的知识或者能力本身就是时间与文化资本投资的产物的观点,同时也强调了在教育制度作用下,文化资本具有世袭传递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作出了贡献。但是布氏对文化资本的假设,基于人们处在同质社会中的前提,更具体一点来说,人们当时处于阶级划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样的同质社会里,教育行为或者说教育投资所依靠的就是家庭资本,“况且,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26] 194。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尤其是数字化的数据以及它最常见的载体——互联网,改变了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尽管阶级优越性依然存在,但是经济资本进行的教育投资不再是唯一决定性的方式,数据一步一步将过去“寒门难出贵子”的论断推翻。个体获取数据的渠道越多元,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知识、符号就越多,这为其文化资本积累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意味着普通人甚至是“寒门”在经济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文化资本的积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或许现今可以解读为,数据及信息是一位无形的老师,已经极大地流向个人,但是个体如何去学习,如何从师,则要看其思想的改变和行动力。这并不是说经济资本主导的教育投资在文化资本的获取中已经无足轻重了,只是金字塔顶层的财富拥有者毕竟是少数,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个体来说,触手可及的数据让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得以改变。
基于此,拥有数据的个体得以前所未有便捷地获得文化资本的积累。“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是它在有关场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26] 192,当个人通过数据获得了文化资本以后,他(她)便有机会进行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个人获得数据不是目的,而是借助数据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利用数据进行实践、生产、创造甚至是再生产,个人拥有的数据和企业、国家所拥有的数据一样也是生产要素。无处不在的数据还揭穿了文化資本的隐蔽性,数据作为一种符号,常常以某些多种多样具体的符号意义出现,而“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因此文化资本预先就作为象征资本而起作用,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只认为它是一种能得到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权威”[26] 196,因而数据也成为了一种文化资本。
数据是异质社会中的一种文化资本,它对过去阶级创造的文化和政治充满了质疑和挑战。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个人获取数据的渠道不再仅仅限于教育,个人运用数据的前提也不再完全受制于家庭教育投资,无处不在的数据改变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在瓦解同质社会的同时,铸造着数据化的异质社会。信息多样化、文化多元化是数据化异质社会的特点,而更为凸显的一点是,权力的分散,政治的日常化。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生存有四个强有力的特质,将会为其带来最大胜利。这四个特质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0] 258。数据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阶层,挑战着权威,个人在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社会政治参与和表达,数据将逐步改变“政治是少数人的游戏”的局面,使个体或群体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随着数据和网络技术的深入与推进,政治参与者不再仅仅是文化资本或社会(关系)资本、经济资本的持有者,而是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趋势,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即围观式政治参与。“所谓围观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虚拟聚集,以话语为主要行为方式,围绕一定的政治事件或议题,展开虚拟集体政治行动,影响政治决策,以实现自身权益与价值的政治活动”[27]。在数据化异质社会中,围观式政治参与越来越普遍,数据也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制度:它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公共权力、公共机构、普通大众的交往方式和交易之中,并在这些范围内得到了合法化。数据与政治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密切,政府为数据要素提供担保,数据的价值由此得到认可,这种价值的获得与数据自身的价值没有关系,而是依靠中央权力得以确认。数据的社会地位提高或者说公信力的提高表明,数据能够处理好一个群体内的中央权力与其他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数据也因为公共权力的认可,而更好地发挥了记录信息、传递信息和再生产信息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人们利用数据改变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同时也因为数据和信息的流通获得了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数据由个人的文化资本成为了群体文化资本。
五、数据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数据的即时性与流动性,既包含了数据的历史维度,又包含着向未来的动态展开的发展趋势。数据是可持续发展的,就像英语中的现在完成时语态一样,构建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方向,这意味着数据从过去的某一时间开始对新方向进行构建,一直持续到现在,或者刚刚终止,抑或仍然要继续下去。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很难给数据构建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则提出具体的步骤,但是它的引领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数据共享加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数据共享是数据要素市场中的核心环节,也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数据共享能将已有的信息获取门槛降低,提高数据供给能力,降低数据采集、信息获取、文化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在共享的过程中,数据能快速地进行文化再生产,在创作、传播、消费以及再生产等各个环节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也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渗透最广泛、创新迭代最快、效益最显著的应用领域”[28]。
遭遇数据的文化产业,迅速变为“数字文化产业”。原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有利于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29]数字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最大不同在于,数字文化产业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在被数据关注着,手机上的平台共享着收集到的关于“你”的每一条信息,新闻推送、浏览偏好、音乐推荐……都顺遂“你”意。数据共享在内容上具有呈现日常化、生活化的时代特征。这只是狭隘层面的数据共享,而从广义上来讲,数据共享的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生产与消费,包括但不限于文学作品、影视、游戏、音乐、直播、交友软件。在数据赋能下,文化产品有了更加丰富的形态,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数据+”出现在了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中,推动着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二)数据创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数据还是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数据对于整个国家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强于过去的媒介,并且数据和文化资本所产生的合力越大,适用范围越广,影响力越大,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越强。“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目的不应是通过实力的增强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中心,并在新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格局中去占据主导他者的地位”[30],而应该是凭借实力的增强来共同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创意涌动。例如以中国的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支付和消费方式,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世界各国接纳,既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又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自由的空间,中国的共建共享共治的文化理念也随之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认可。
数据创新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的应用要秉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即数据创新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国家文化是如何具体存在于世界的,致力于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以此共同构建更加繁荣的世界文化,而不是利用数据高位进行文化侵略和压迫。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强调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并将文化建设上升至引领全局的地位[31]。以数据共享为前提,充分调动国家文化发展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各方文化创意创造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从而更好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时代新征程准确地向国民,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价值,不断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三)数据治理增强世界文化安全
人类在享受数据带来的文化盛宴的同时也应当有所警惕,易复制的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正当利用数据或者滥用数据,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如侵犯个人隐私、窃取国家机密数据、数据破坏、數据侵权等等。
因此在利用数据构建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规则时,也要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应对办法:数据治理。数据治理依靠数据伦理和数据立法共同推动。所谓数据伦理,是指关于使用数据时判断行为是非的各种道德标准。“每个行为主体都应针对数据确立自身使用的道德规范,明确数据对自身的价值,重视数据中涉及的身份、隐私、权属及名誉等,在技术创新与风险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32] 17。然而仅仅依靠道德伦理的约束是不够的,因此数据立法呼之欲出。美国、英国、德国、欧盟、新西兰、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组织都制定并完善了数据的相关立法,旨在加强国家文化数字安全,强化企业与跨国组织的文化产权,保护个人数据隐私。
事实上,数据治理需要依靠所有数据受益者共同努力,夸张一点来说,人人都是数据的受益者。个人在数据伦理的监督和数据立法的约束下使用数据,就是为世界文化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六、总结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在科技、经济领域中创造了丰厚的价值,而且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解读数据的文化意义,能为未来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提供更多的可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记录着文化,转译着文化,用符号诠释着文化,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会区隔,改变了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参与并构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规则,这么来看数据似乎处于支配地位,实则不然。数据看似客观,处于支配性地位,但实际上,文化才是真正的主导者,文化决定了什么是数据,什么数据能够使用,只是这种影响以相对隐蔽的方式在发挥作用。数据无法“无中生有”地制造意义——因为“人为自然界立法”,万事万物经由人的判断后被赋予意义,人制定价值判断的标准,而人所持有的文化是价值判断的根源。
文化的存在是数据构建内容的基础,它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求选择了数据,就像过去文化选择了书籍、广播、电视、电脑等作为传播的方式一样。未来,瞬息万变的数据也许又会变成其他的事项,人们又会赋予其另外的名字或者含义,但是无论其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不会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一种文化或知识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导,那么,它所预言的或者推销的‘未来就将通过被它所导向的集体行为而几乎必然成真,于是,历史就变成提前写成的了。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终结”[19]。
因此,尽管数据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但是它并不应当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主导,应当警惕“数据主导文化”的声音,因为人类的大脑才是人类社会创造出灿烂历史文化、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尽管现在“数据化成为人们理解自身与社会行为的新范式,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33],但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文化的过程总会以最先进的技术为辅助。数据只是时下最为新潮的文化发展载体之一,它运用不同的媒介,为人类提供了认识文化、理解文化、生产文化的新方式,而文化的实质始终是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不是其他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一直动态发展变化,并总能与新鲜事物碰撞出时代的火花。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2020-04-09.http://www.gov.cn/zhengce/2020-04/09/content_5500622.htm.
[2]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2022-05-22.http://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4] 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严蔚敏,吴伟民.数据结构(C语言版本)[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6] 赵刚.数据要素: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7]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8] 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9] 唐晓峰,李平.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新版第八章述要[J].人文地理,2000,(1).
[10]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勇,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1]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M].张行舟,闾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12]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M].郭泽,译.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
[13]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中国政府网,2021-11-15.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1/art_c4a16fae377f47519036b26b474123cb.html.
[15] 大数据白皮书(2014年)[EB/OL].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4-06-18.http://www.cac.gov.cn/2014-06/18/c_1111184441.htm?ivk_sa=1024320u.
[16] FDS FRAMEWORK:Mission,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Actions[EB/OL].strategy.data.gov,2020-03-01.https://strategy.data.gov/overview/.
[17] UK National Data Strategy[EB/OL]GOV.UK,2020-09-09.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national-data-strategy.
[18]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data[EB/OL].European Commission,2020-02-19.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system/files/ged/communication-european-strategy-data-19feb2020_en.pdf.
[19] 趙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J].世界哲学,2004,(3).
[20]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London:Routledge,1984.
[22]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3]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铃,译.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24]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5] 刘少杰.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6]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7] 陆斗细,杨小云.围观式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2).
[28] 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1,(8).
[29] 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2017-10-1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230291.htm.
[30] 马翀炜.从边疆、民族理解国家文化软实力[J].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31] 钟晟.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J].决策与信息,2021,(1).
[32] Kord Davis,Doug Patterson.Ethics of Big Data[M].Sebastopol: OReilly Media,2013.
[33] 曾建辉.以纸抵心:传统阅读的算法嬗变与价值复归[J].中国编辑,2022,(9).
[责任编辑: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