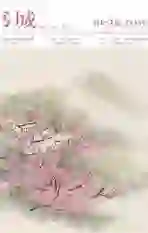一个比喻的讹传历程
2023-04-03何仍端(LucasHumbert)
[法]何仍端(Lucas Humbert)
一
王阳明(1472-1529)门人弟子所辑《传习录》中有个颇为有趣的比喻,即以一日之中的夜阑、晨旦、日中前后、昏夜之时来喻指古今世界各阶段—“羲皇世界”“尧舜世界”“三代世界”“春秋战国世界”,乃至所谓“人消物尽世界”。书中有云: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按,羲皇即伏羲)。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按,三代即夏、商、周,后世儒者常以“三代”指称完美的伦理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见《传习录》下)
从主体经验范畴来看,“不为气所乱”“常做个羲皇已上人”等,恐无实现之可能。一日之间,情绪变化多端,或通或塞,且不论疾病之害—诚如李贽(1527-1602)《复丘若泰》中所言:“此时正在病,只一心护病,岂容更有别念乎,岂容一毫默识工夫参于其间乎。”(见《焚书》第一卷)又如,夜里失眠而起身早者,晨间之景,竟若“人消物尽世界”,不得不以“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之状始一昼之业。然而,历经数个时辰的浑噩后,旦暮之间,亦会偶有突然而至的清醒时刻,甚至这片刻的“神清气朗,雍雍穆穆”,远胜于满满睡足一整夜后所得的心旷与神怡,盖以乐赔忧也。由此可见,阳明以“一日间的日升日落”这种客观规律性变化来类比中国远古历史发展的不确定变化并以此推导、演绎其内在规律的论述,有明显的主观性与巧合性之嫌,并非每时每刻都能得到印证。不过,其中教义却不无启迪之处:该比喻作为《传习录》中的指点语,道破了阳明弟子所求的修身方针。
若是日日亲体三代的更迭循环,无疑会提高我们对当下世事变化的洞察力,而此举也将遥远的三代圣贤之道纳入了《易传》所称的“百姓日用”范畴。如此一来,对该体认之道产生的种种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如阳明高弟钱德洪(1496-1574)提出的修身论便将此番体认混同于远古圣贤本身,认为“吾心之灵与圣人同,圣人能全之,学者求全焉”(见周汝登《王门宗旨》)。熟识朱子学的钱穆先生对此驳斥道:“夫人心之灵,固与圣人同,然谓吾心之灵同于圣人,有时或不如谓圣人之灵同于吾心。由吾心之灵去认识圣人,有时或不如从圣人之心反过来认识吾心之更便捷,更恰当。”(《略论王学流变》,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
心之灵既无法优于尧舜,何况羲皇呢!纵是如此,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对一种既有学说加以深化,乃至绝对化,本就是让思想史保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有鉴于此,钱德洪不算是《传习录》此篇的真正扭曲者。
二
阳明门人多以传承儒家“道统”为阳明本人的大事功。阳明门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所言及的“唐虞(按,即尧舜)君臣,只是相与讲学”以及“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语录》,见《王艮全集》第一卷),亦足以彰显他眼中的“我”与圣人的相近相类关系。王艮早岁亦有“父兄之愆,子弟之责。尧舜所为,无过此职”(《孝弟箴》,见《王艮全集》第二卷)一语,表明他的这些观点并非尽是受阳明影响所致。但同阳明的上述指点语一样,王艮对尧舜事业的具体化,旨在使之更为平易近人,以适用于门徒们的修身实践。其实,王艮的这般观点,皆具笑话、俏皮话特征,又像是某种特定情形下的偶发性比喻,显得既有理论支撑,又有其灵感渊源,而后者的引发或许更为奇妙。
无疑,王艮是了解王阳明的“一日间之说”的。但他对阳明单单强调人的内心状态却不甚满足,甚至觉得偏于狭隘,或者,他觉得这种具化了的道统不够豁达,尚保留着可再进一步拓宽的余地。正如其《年谱》所载:
会龙溪(按,龙溪即王畿,浙中王学代表人物)邸舍,因论羲皇,三代,五伯(按,五伯即五霸,泛指春秋、战国时期)事,同游未有以对。复游灵谷寺,与同游列坐寺门歌咏,先生曰:“此羲皇景象也。”已而,龙溪至,同游序立候迎,先生曰:“此三代景象也。”已而,隶卒较骑价,争扰寺门外,先生曰:“此五伯景象乎?羲皇、三代、五伯亦随吾心之所感应而已,岂必观诸往古?”(《年谱》嘉靖十五年丙申条,见《王艮全集》第四卷)
换言之,“列坐寺门歌咏”才是耐人寻味的“伏羲景象”。由此,阳明的“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便有了更具吸引力的化身;而“同游序立候迎”才是名副其实的“三代景象”,如是,阳明的“礼仪交会,气象秩然”,便得到了更具伦理意义的说明。“隶卒较骑价,争扰寺门外”才是有声有色的“五伯景象”,阳明的“神气渐昏,往来杂扰”便借此得到了一种“人化了的”描绘。在王艮那里,并没有无缘无故的内心与情绪表露可言。三代的更迭不同于饱经自律考验的纯粹自我,而是外在于内心的偶然事变,心之所感即事务本身。显然,王艮似乎并不善于捕捉心情的幽微变化,他对此的观点一如《礼记·乐记》所记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近乎抛却了阳明“心外无物”的重要命题。
作为一个当下立说的表现,王艮此言说得并没有阳明那么新颖:世间固然有乱有序,冠之以“道统”的帽子也无不可,却远不如直接讲乱、序。更何况,正因为此说不再局限于一日之间的个人经验范畴,那么,上述三种状态的顺序也不具任何必然性了,除非事事物物皆安分守己地依照早午晚等日程表而走下坡路,我们终究无从证成如此偶然的规律。即将入眠之人确然会呈现出一些颇显颓废的心靈迹象,也就是“心”进入掩蔽状态之貌;但自客观事物的角度来讲,心外之物或许仍处在“羲皇情景”中。对此,已入冥冥的“心”是无从知晓的。王艮此处所关注的对象,并非对情景的如实描述,而是拿“道统”作为主题,向在场各位儒者申说夏商周的历史流变及其在伦理层面上的意义。“尧舜景象”“人消物尽景象”之所以未被提及,正是因为外物没有出现符合这些比拟的情状。概言之,这番应景语纯是乘兴而发的,无此景便无此语。我们也不例外,只有在遇到与此相类的巧合时,才有理由援引王艮《年谱》此事。
三
对此掌故,明儒耿定向(1524-1596)《心斋语记》(“心斋”即王艮别号)中有个略异的记述:
蔡学博述:心斋王先生一日在白下联聚同志游某寺中。初,心斋同聚友觅蹇前往,维时诸友忘分忘年,熙然类聚。心斋指示之曰:“此个景象便是羲皇世界。”有顷,东廓先生(按,东廓先生即邹守益,王阳明得意门生,江右王学代表人物)偕泾野(按,泾野即吕柟,明朝关学巨山)诸缙绅长者悉至,时诸友以齿以分秩然列坐。心斋先生复指示之曰:“此个景象便是三代世界。”日暮将归,舆夫仆隶纷然抢攘。心斋先生又指示之曰:“此个景象便是战国世界。”
王艮的生平事迹早已在儒林中传为种种佳话,各类记载颇有出入,夹杂了不少夸张与捏造。又如,他早岁北上弘道,且在京引起了较大轰动,而对该事的记述不止一处,个中实情也不好说(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况且,耿定向本是一名喜于借题发挥、大发议论的儒者,因而,他的《心斋语记》并不止于纯粹的轶事叙述。且看下文:
叔子(按,叔子即耿定理,耿定向之弟,李贽好友。定向之见解,常受启于定理)曰:“羲皇时便有个羲皇出来提掇,三代时便有个禹汤出来提掇,就是战国时,也有个孟子出来提掇,不然不成世界。”余顾学博曰:“叔子此语良是,子能理会否?……吾弟所谓‘提掇’,羲皇等人即当日熙然、秩然、纷然时,众人不著不察,所以为众人也。即心斋此一指点,心斋便是当时羲皇、孟子等人矣。吾人从此一指点,便向里默识,即一识便是个个心中有羲皇、孟子等人矣。人心一日十二时候中,感应百交,安能保得时时俱是羲皇时光景?顾时时须认得此种有个羲皇、孟子在,便不是混世人,此是大关窍。”近日友朋人不信当下而别求光景,此便是混倒在战国时而想象羲皇时景象,不知一提出孟子作主宰便是了。有种猖狂自恣者,冒认谑浪怒詈都是天机,是在战国世界上打混,而不认得时有孟子乃命世人知宗而主之也。(《心斋语记》,见《耿定向集》第八卷)
耿定向借耿定理之论并参照蔡学博之言,阐发了他对王艮及羲皇光景的见解,认为上述列代并不只是个广义上的天下,而是以某一人物为代表或最优,将其视作正道的化身。从而,定向提出了对阳明“一日间之说”颇有见地的异议,也就是,一个时代若无此类代表或最优人物来倡导时代精神的萃华(耿定理所谓“提掇”),这个时代则称不上真正的时代(耿定理所谓“不成世界”)。悟得这一精神萃华,并依《论语》所倡的“默而识之”行事,以免《孟子》所贬的“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之弊,这些有关自省的修身方针,皆系前人未曾发之意。后文中,定向却转而大骂这些“不信当下而别求光景”者与“猖狂自恣者”,虽不知所骂对象姓甚名谁,但影射意图明显:矛头所指应是以聂豹为代表的心学“归寂”思想及“浙中王学”抛却个人功夫的为学倾向。如此语境下,于我们而言,这些詈骂之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耿定向对这个比喻的阐发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指向“心性学”问题(此处可简化为纯心理问题),一是指向历史哲学问题。从第一个向度来讲,耿定向所言“人心一日十二时候中,感应百交,安能保得时时俱是羲皇时光景”,其实与本文第一节对《传习录》中这一比喻所提出的疑问相合,颇近乎我们的心理常识:今人无从回溯至羲皇的平淡境界,正如我们在困意十足时无法保持早晨的蓬勃与畅快。王艮对此讲得不像耿定向那么直截了当,可能与其对外在“景象”的兴致有关。至于定向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性阐发,可以总结为:我们哪怕是身处衰世之人,仍可寻得一种值得令人向往的道德化身,一是伏羲,一是大禹、成汤,一是孟子。原始阶段的道统英雄(如伏羲)呈现出一些令人羡慕的飘逸“景象”;晚期阶段(如孟子)则更多在于严格的道德修养要求。最初是恰如其分地平安无事,最后则处于失道的天下中,不能不进行道德反思,如孟子在战国时刻意潜心于“义利之辩”。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讲,晚期阶段的实践方式只不过是谨慎而行,这一如耿定向所钦佩的邹守益(1491-1562)“戒慎恐惧”之学。
每个时代都呼吁一种独特的学说,正如我们的情绪需要一种对症下药的律己方式。如此,“心性学”与历史哲学得到了本质上的统一。但是对于阳明原来的“一日间之说”而言,耿定向的新说意味着什么?哪怕心绪不佳,我们还务须表现得心态良好?精神魄力受挫时,还得寻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类的安慰话,拿孟子的思想来慰藉精神状态之萎靡?不可否认,定向所指,确实体现了与“阳明—内心”“王艮—事变”不同的视角:不僅是对于日常经验与三代更迭,当下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思想史—亦显露出衰退的迹象,其危险也最为可怕可怖。因而,定向之语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归圣”或“道统在此”,而是“正统何在”。在他那里,回答则是:遥敬伏羲!效仿孟子!
四
阳明对孟子虽是推崇备至,但基于一些“治天下”的考量,他始终是以尧舜为先的,如云:“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见《传习录》上)论及王艮,此处无须过多赘言,简言之,他对孔孟的周流天下有莫大的取益,这限制了他对伏羲、尧舜的向往。至于耿定向,既承认“三代”一去不复返,又对“乱”表示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在他眼中,最合宜的做法其实不是“戒慎恐惧”之学,也不是永久的内心警惕,而是对异端的严格排斥。明代思想史学家皆知,耿定向对儒家道统的理解具有浓厚的消极意味,竟以消灭历代异端为首务。他曾说:
昔三代以降,学术分裂,异端喧雇。高者鹜入虚无,卑者溺于繁缚,乃夫子出而单提为仁之宗……逮至战国,功利之习薰榻寰宇,权谋术数以智夕牛驰,益未知所以求仁矣。孟子出而又提一义。……下逮晋、魏、六朝,时惩东汉以名节受祸,或清虚任放,或靡丽蔑质,德益下衰矣。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后承传者又失其宗,日束于格式形迹,析文辨句于训话之余,而真机梏矣。乃文成(按,文成即王阳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示应试生》,见《耿定向集》第五卷)
仲尼振周室,孟轲斥纵横,宋儒辟佛老,阳明警朱门。但这里耿定向的矛头所指,实是阳明逝后以王畿(1498-1583)为主的“王学末流”,微词尖锐,此不必究。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察觉到,在定向眼中,该时期的救赎者,盖是其本人。由此,足见其野心之大、关怀之宏。当然,《示应试生》中的道統观及《心斋语记》里的种种说教也不乏先人依据,确保了它们在儒学里的正当性。如宋朝二程曾云:
学者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按,颜子即颜回)陋巷子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见《二程集》第二卷)
用典不止于此,且不赘述。
五
耿定向以其与李贽的通信论战而著名,自二十世纪初李贽受到了学界注视以来,定向常被诸多学者骂为“伪道学”的代表。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称之为“主张维护封建道德的道学家耿定向”,可谓是当代学界无法直接采信的过火评价。耿定向的人格与思想实属其时最为错综复杂者之一,泰州学派(嵇文甫所谓“左派王学”)与江右学派(嵇文甫“右派王学”)通过他的学说而得以集于一身,吴震教授命之为“一种奇妙的组合”(《耿定向论》篇,见《阳明后学研究》),亦不为过。耿定向一贯自视为明朝诸流派的纠正者与监督者,从上文来看,这是不难想象的。笔墨有限,这里我们无法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更翔实的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南开大学博士张斯珉《卫道之学:耿定向思想研究》进行的细致分析。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还刊印了傅秋涛点校的《耿定向集》,珍贵文献出炉,勇敢的读者不妨亲自比照。
笔者曾以为,哪怕对耿定向的学术“昭雪”有其公平之处,自己恐怕仍无法对其人产生由衷的同情。同时,不少学者曾对他的生平事迹捏造过纯粹的冤假错案,多起无凭无据的官司,竟激起了笔者为之鸣不平的念头。但若不是经了这番偏颇的官司,我们又如何能够提炼出对他的正确评价来呢?古人的“轻罪”,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出合理的评定呢?本文以为,王阳明与王艮的论述,各有其旨趣,皆体现出明人与今人在主观经验上的某些共性。至于耿定向,其论则像一位老塾师的呵斥之言,味同嚼蜡,但反而可能更让人清醒,正如严师的苛责会有益于勤学苦练的学习生涯。孰真孰伪,实在难言,只怕是耿定向说得最实用。实际上,王阳明亦曾说:“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见《传习录》上)耿定向继承了这一说法,却忘了它与“常做个羲皇已上人”的命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在于,第一文是就人文历史展开而言,第二文则是就个人心态起伏而言。耿定向混二为一,以历史的不可扭转为吾人良知的内在局限性。如此一大误会,通过王艮的具体化说法,竟得到了自圆其说的机会:如若“一日间”的诸多问题皆外在于我们的内心,那么,“伏羲景象”的飘逸世界,很大程度上则意味着一种无法追回的人间乌托邦,修身功夫于此无益。于是,阳明的比喻就沦为了一种奢侈、难以企及的迷人对象,且不论王艮的笑话、俏皮话与乘兴语。这未免让人心里产生一种深切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