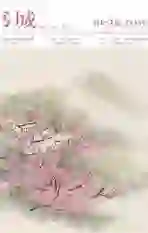汪曾祺的旅美心史
2023-04-03李怀宇
李怀宇
最近重读汪曾祺先生的书信集《飞鸿传书寄真情》(译林出版社2021年),他从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写给妻子施松卿的信,所写正是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之事。
一九八七年九月,汪曾祺应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1908-1991)之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汪曾祺写了散文《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对这一段岁月有动人的回忆。而汪曾祺在爱荷华生活的点点滴滴,更多的是写在给施松卿的家信里。写这些信时,汪曾祺有意留下这段生活的第一手记录。他到了美国给妻子的第一封信里说:“稿纸带少了。可以写一点东西的。至少可以写一点札记,回去再整理。我写回去的信最好保存,留点资料。”果然,后来他写了散文《林肯的鼻子》和《悬空的人》。
汪曾祺的信札,有明人之风。因为是写给妻子的信,说的是体己话,如叙家常,笔调比散文更轻松。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写的文字,自然流露了汪曾祺当时的心境。如今将这批信重理一遍,可见汪曾祺这一段“旅美心史”。
一、生活的气味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汪曾祺刚到爱荷华,洗了一个脸,即赴聂华苓家的便宴:美国火锅。汪曾祺喝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宴后,主人给汪曾祺装了一瓶威士忌回来。安格尔把《纽约时报》杂志上汪曾祺的全版大照片翻印了好几份,逢人就吹:这样的作家,我们不请还请谁?
汪曾祺擅书画,特意带了画和对联送给聂华苓,安格尔一看画,就大叫:“Very delicate!”汪曾祺对聂华苓说:“我在你们家不感觉这是美国。”到爱荷华的第一天,汪曾祺就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说:“这里充满生活的气味,人的气味。”
汪曾祺住在五月花(Mayflower)公寓八楼30D,很干净,无噪声。他开始琢磨厨艺,利用美国厨具,做中国菜。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不仅自己做饭,还为朋友献厨艺。
“国际写作计划”每星期派车送作家去购买食物。汪曾祺发现:蔬菜极新鲜。只是葱蒜皆缺辣味。猪肉不香,鸡蛋炒着吃也不香。韩国人的铺子里什么作料都有,生抽王、镇江醋、花椒、大料、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应有尽有。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易碎。有几个留学生请汪曾祺吃饭,包饺子。但留学生都不会做菜,要请汪曾祺掌勺。汪曾祺发现美国猪肉太瘦,一点肥的都没有,嘱咐留学生包饺子一定要有一点肥的。不久后,汪曾祺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他说: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白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
蒋勋住在汪曾祺的对门。蒋送了汪好几本书,汪送了蒋几张宣纸、一瓶墨汁。蒋原籍西安,汪便给他写了一副字:“春风拂拂灞桥柳,落照依依淡水河。”
中秋节晚上,聂华苓邀请汪曾祺及其他客人家宴,菜甚可口,且有蒋勋母亲寄来的月饼。有极好的威士忌,汪曾祺怕酒后失态,未能过瘾。美国人不过中秋,安格尔不解何为中秋,汪曾祺不得不跟他解释,从嫦娥奔月到中国的三大节,中秋实是丰收节,直至八月十五杀鞑子……他还是不甚了了。月亮甚好,但大家都未开门一看。
十月十二日是安格尔七十九岁生日,晚上请大家去喝酒,谢绝礼物,但希望大家念念诗、唱歌、表演舞蹈。安格尔家的门上钉了一块铜牌,刻字两行,上面一行是“Engle”,下面是中文“安寓”。汪曾祺给安格尔写了一首诗:“安寓堪安寓,秋来万树红。此间何人住?天地一诗翁。此翁真健者,鹤发面如童。才思犹俊逸,步态不龙钟。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弯腰拾山果,投食食浣熊。大笑时拍案,小饮自从容。何物同君寿?南山顶上松。”
十月中,陈映真八十二岁的父亲特地带了全家,坐了近六个小时汽车来看中国作家,听大家讲话。晚上陈映真的妹夫在燕京饭店请客。宴后陈映真的父亲讲了话,充满感情。吴祖光讲了话,也充满感情。安格尔抱了陈映真的父亲,两位老人抱在一起,大家都很感动。汪曾祺抱了陈映真的父亲,忍不住流下眼泪。后来又抱了陈映真,汪、陳二人几乎出声地哭了。
汪曾祺说:“我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十月二十日,他写信给妻子:“昨天董鼎山、曹又方还有《中报》的一个记者来吃饭(我给他们做了卤鸡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汤、水煮牛肉,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曹又方抱了我一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德熙说我在美国很红,可能是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写信告诉他的。王渝说她写信给巫宁坤,说:‘汪曾祺比你精彩!’她说那天舞会,我的迪斯科跳得最好,大家公认。天!”
二、有画意的小说
在爱荷华,汪曾祺改写《聊斋》故事,这便是后来的《聊斋新义》。他说:“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
汪曾祺也喜欢作画送人。有一次作家们存款的银行请客,聂华苓想要有所表示,安格尔让她跟汪曾祺要一张画,请所有作家签名。汪曾祺让作家们就签在画上,作家们说这张画很好,舍不得,就都签在绢边上。
九月二十日,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会上发言。谈到“空白”时,汪曾祺说,宋朝画家马远,构图往往只占一角,被称为“马一角”,翻译者译成“一只角的马”。这份发言在九月二十九日整理出来,汪曾祺独抒己见:
中国画家很多同时也是诗人。中国诗人有一些也是画家。唐朝的大诗人、大画家王维,他的诗被人说成是“诗中有画”,他的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我的小说,不大重视故事情节,我希望在小说里创造一种意境。在国内,有人说我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有人说是诗化的小说。其实,如果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那我是会很高兴的。可惜,这样的评论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
大概从宋朝起,中国画家就意识到了空白的重要性。他们不把画面画得满满的,总是留出大量的空白。马远的构图往往只画一角,被称为“马一角”。为什么留出大量的空白?是让读画的人可以自己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一个小说家,不应把自己知道的生活全部告诉读者,只能告诉读者一小部分,其余的让读者去想象,去思索,去补充,去完成。我认为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一篇小说,在作者写出和读者读了之后,创作的过程才完成。留出空白,是对读者的尊重。
李欧梵在爱华荷听了汪曾祺的这次发言后说:“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是一种很新的理论。”
十月十八日“我为何写作”讨论会,汪曾祺以为可以不发言,结果每个人都得讲。汪曾祺略加思索后说:
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从小数学就不好。
我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希望我将来读建筑系,当建筑师—因为我会画一点画。当建筑师要数学好,尤其是几何。这位老师花很大力气培养我学几何,结果是喟然长叹,说“阁下之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几何要一步一步论证的,我的几何非常简练。
我曾经在一个小和尚庙里住过。在国内有十几个人问过我,当过和尚没有,因为他们看过《受戒》(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看过《受戒》)。我没有当过和尚。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打到了我们县旁边,我逃难到乡下,住在庙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之外,我只带了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选集》。我直到现在,还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十月三十日下午,汪曾祺给妻子的信记录了他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起首说:“我的女儿批评我,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我自己的。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这篇讲话,汪曾祺并没有带稿子,而畅所欲言:
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小说是回忆,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
在讲话现场,汪曾祺还加了几句:“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肯德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十月三十日这封家信的最后,汪曾祺说:“我回来要吃涮羊肉。在芝加哥吃了烤鸭,不香。甜面酱甜得像果酱,葱老而无味。”
三、艺术之旅
这一年秋天,汪曾祺旅行了半个月。路线是爱荷华市—芝加哥—纽约—纽海芬—费城—华盛顿—马里兰—费城—波士顿—芝加哥—爱荷华市。
在芝加哥,汪曾祺和蒋勋去看艺术博物馆。汪曾祺看了凡·高的原件,才真觉得他了不起。凡·高的画复制出来全无原来的效果,因为他每一笔用的油彩都是凸出的。高更的画可以复制,因为他用彩是平的。莫奈画的睡莲真像是可以摘下来的;有名的“稻草堆”,六幅画同一内容,只是用不同的光表现从清早到黄昏。毕加索的原作,有一幅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画《母与子》,很大,好懂;也有一些他后期的“五官挪位”的怪画。汪曾祺说:“这个博物馆值得连续看一个月。可惜我们只能看两小时。”
旅行的归途中经过海明威的家乡。有两所房子,一处是海明威出生的地方,一处是海明威开始写作的地方。两处都没有明显的标志,只是各有一块斜面的短碣,刻了简单的说明。两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人家,也不能进去参观。汪曾祺感慨:“芝加哥似乎不大重视海明威。”
在纽约的第二天,金介甫夫妇开车带他们去看了世界贸易中心。汪曾祺说:“这是两幢完全一样的大楼,有一百多层,全部是不锈钢和玻璃的。这样四四方方、直上直下的建筑,也真是美。芝加哥的西尔斯塔比它高,但颜色是黑的,外形也不好看,不如世界贸易中心。”
汪曾祺在纽约住王浩家。他回忆:“我和王浩四十一年没有见了,但一见还认得出来。他现在是美国的名教授。他家房间颇多,但是乱得一塌糊涂,陈幼石不在。但据刘年玲说,她要在,会更乱。这样倒好,不受拘束。王浩现在抽烟,喝酒。我给他写的字、画的画(他上次回国时托德熙要的),挂在客厅里。”
王浩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汪曾祺写《金岳霖先生》一文,谈到王浩是金岳霖最得意的弟子。上课时,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汪曾祺在文中还说:“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没想到此文写后几个月,汪曾祺就和王浩在纽约重逢了。
在费城,汪曾祺住在李克、李又安夫妇家。他到宾州大学博物馆参观:“昭陵六骏”的两骏原来在这里!晚上看了馆藏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 on the River”,汪曾祺告诉李克,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李克在第二天汪曾祺的演讲会上做介绍时特别提到这件事,以示汪曾祺很渊博。
在华盛顿,汪曾祺觉得在航天博物馆开了眼界。阿波罗号的原件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玩意,登月机看来很简单,只有一辆吉普那么大,轮子是钢的,带齿。他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在这里毕加索已经成了古典,展品大都看不懂。有一张大画,是整瓶的油画颜色挤上去的,无构图,无具象,光怪陆离。门口有一大雕塑,只是三个大钢片,但能不停地摆动。美国艺术已经和物理学、力学混为一体。
在波士顿,汪曾祺去市博物馆参观,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汪曾祺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出来的。中国的矿物颜色太棒了!他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刘年玲带了汪曾祺去看一个加勒夫人的博物馆。刘年玲说这里的沙拉很有名,大家都叫了沙拉,原来是很怪的调料拌的生菜。在国内,沙拉都有土豆,可是这种“恺撒沙拉”一粒土豆都没有,只有生菜。汪曾祺对刘年玲说:我很怀疑吃下这盘恺撒沙拉會不会变成马。
十一月二十二日,汪曾祺去參加“美国印象座谈会”。他讲了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并说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没有人的鼻子是神圣的。会后,好几位女士都来摸他的鼻子。
此时,汪曾祺已不想去西部旅行。他说:“我游兴不浓,因为匆匆忙忙,什么也看不到。我连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的大概方位都不清楚,只是坐在汽车里由别人告诉这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凡·高、毕加索、宋徽宗的画。”
四、文化之根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写信感谢聂华苓:“我本来是相当拘束的。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这也是你们的影响所致。因为你们是那样感情奔放,那样聪明。谢谢你们。”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的不只是华文作家。汪曾祺和外国作家也打成一片。有一晚,汪曾祺十一点回到五月花公寓,几个拉美作家强拉他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们说,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汪曾祺。
汪曾祺还给一位墨西哥诗人画了一张画,见他不在家,便塞进他的门缝,他夜里两点钟敲门道谢。聂华苓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洋人会喜欢汪曾祺,而且有些事会为汪打抱不平。汪曾祺说:“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用很坏的英语跟他们聊了一晚,他们的英语也不好,居然能讲通。”
正当汪曾祺为回国作准备之际,有两位黑人学者请他去聊了一晚。一个叫Herbert,一个叫Antony。Herbert在一次酒会遇到汪曾祺,就对他很注意。以后汪曾祺每次讲话,Herbert都去听。Herbert认为汪曾祺是一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Herbert读了四个学位,在教历史,研究戏剧。Herbert跟汪曾祺谈了一个剧本的构思,汪给他出了一点主意,他悟通了,非常感谢。
谈了五个小时后,汪曾祺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以上就不知道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从非洲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来的。他们想找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美国的其他移民都能说出自己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德国、荷兰来的……他们说不出。
汪曾祺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汪曾祺说了自己的感觉。他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Herbert说《根》那本书是虚构的,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
在起身告辞时,Herbert问汪曾祺:“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汪曾祺说:“既然找不到,那就从我开始。”这一晚的谈话,汪曾祺后来写成了《悬空的人》一文,他在文中说:“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就在聊天的当夜,还发生了一件事:汪曾祺的房间失窃了。小偷不知是怎么进来的。就在汪曾祺熟睡时,小偷搬走了屋里的电视机,偷了他六百美元现款。除了这些东西,小偷把汪曾祺的毛笔、印泥、空白支票本以及桌上不值钱的小玩意都拿走了。小偷还把汪曾祺的大半瓶Vodka拿走了。后来汪曾祺发现,小偷把陈怡真送他的一个英国不锈钢酒壶也拿走了,壶里有聂华苓给他灌的威士忌。
事后,聂华苓给汪曾祺开了一张六百美元的支票。聂华苓听说陈怡真送他的酒壶丢了,高兴极了,说:“我正想送你什么好,这下好,我再买一个送你!”她知道他的皮夹子也丢了,说:“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皮夹子。”
此时,汪曾祺离回家还有一个星期。他心情轻松,就看看书吧,看安格尔的诗、聂华苓的小说,还有不少美国华人作家寄给他的作品。汪曾祺读海外华人的作品,颇有意思,有的像波德莱尔,有的像D.H.劳伦斯。他们好像打开了汪曾祺多年锈锢的窗户。不过看起来很吃力,汪曾祺得适应他们的思维。他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曲终人散一惆怅,回首江山非故乡。一九八七年年底,汪曾祺回国。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