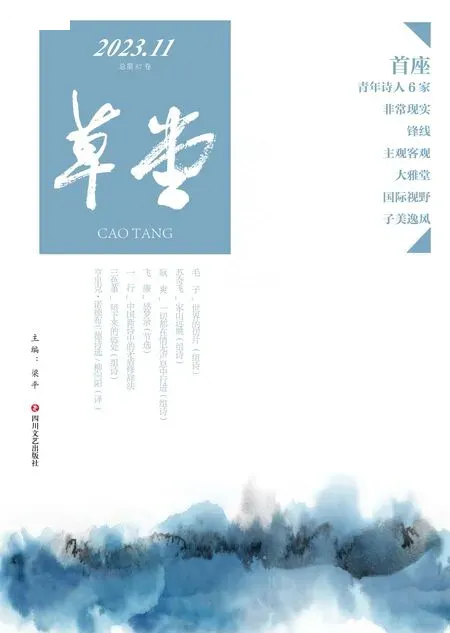中国新诗中的矛盾修辞法
2023-03-24一行
一 行
1
“矛盾修辞法”(oxymoron,本义为“敏锐的愚蠢”)是文学中的常见手法之一。在严格定义中,它是将两个相互排斥、冲突的词或词组连在一起形成有特定效果的短语,诸如“冰冷的火焰”“真实的谎言”“深刻的浅薄”;如果做扩展的理解,它还可以包括悖论式表述(paradox),亦即主词与谓词性质相反、或者有两个彼此矛盾的属性谓词(或陈述项)的句子,比如“那歌声既遥远又切近”“儿童是人类之父”“它从未是它而只是它所缺失的”。矛盾修辞法能造就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句(epigrammatic)风格,深合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洞察:“相反者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从赫拉克利特这句名言来看,矛盾修辞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格或机智的语言游戏,它有更深的根源——“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词表面,而是存在于语词、心智和实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自波德莱尔《恶之花》以来的现代主义诗学中,矛盾修辞法因其体现出了“现代心智”或“现代主体”的内在张力和复杂性(“恶之花”这一矛盾修辞即是其象征),而得到众多诗人的青睐。中国新诗作为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诗歌运动和语言形式,自然也不例外,但新诗作者们运用矛盾修辞时的语境、方式和所要实现的诗学意图多有差异。本文试图在简要说明矛盾修辞法的哲理根据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不同时期中国新诗作者们对这一手法的运用方式,来呈现修辞技艺中隐含的精神史线索。
2
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矛盾修辞法有其哲理上的深刻根据。如果进行观念史的回溯,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种言说方式首先是用于对“终极实在”(“天道”或“神”)的形容,然后才逐渐用在对普通事物的复合性质的描述中。由于“道不可说”,终极实在超逾了人的理智能力和言说能力,因此所有对“道”(或“神”)的言说都必然呈现为“说不可说”的悖谬,这种不得已的言说只能用矛盾和悖论来暗示“道”的超越性。《道德经》中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都是著名例证。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大师、库萨的尼古拉等人也用类似的矛盾修辞(“非存在的存在”“无意愿的意愿”“有学识的无知”)来形容无限者之超语言、超逻辑性,以及人与终极实在之间的距离。而一普通事物所具有的相互矛盾的性质,不过是分有了终极实在之内在悖谬性的结果。
按沃格林的观点,人是一种“居间性”的存在,亦即以爱欲的方式活在各种张力之间,这些张力包括内在与超越、人类秩序与神性秩序、有朽与不朽、无知与知识等等。“矛盾修辞”最初用于呈现终极实在的超越性,但在后来的历史中,“矛盾修辞”逐渐内在化,成为了对人之处境和生命状态的表述方式。中国与西方在这一“内在化”的进程中,大体沿着以下方向展开:在中国,是庄子的“无用之用”(《庄子·逍遥游》)和列子的“不射之射”(《列子·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在西方则是“世界的荒谬”(诺斯替主义的教义可概括为“最美丽的世界也不过是一个黑暗、混乱的垃圾堆”)和“精神的自我否定”(黑格尔说的“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依然保持自身的完整”)。庄子和列子所要抵达的是一种不被固定目的所束缚的自由,“无用之用”与“不射之射”都有一种依循“天”之自发秩序而忘我的姿态;而诺斯替主义和黑格尔的矛盾言说则透着一种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感,精神与世界的冲突呈现为“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黑格尔重新勘定了“矛盾”的起源位置:“矛盾”的出现并非因为终极实在不可言说,相反,“矛盾”是作为终极实在的“绝对精神”的必然环节和运动方式。“实在”并不在语言和概念之外,而就显现为“概念的概念”或“概念整体”,通过概念的自我否定来展开和实现自身,一切矛盾在体系的完成中获得和解与统一。于是,“矛盾修辞法”就成为了“概念的辩证法”:“A 是A 也是非A,因为A 在自身中包含自相关的否定性。”
在现代哲学和文学中,矛盾修辞法得到空前规模的运用,这是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危机、分裂和冲突,而且这是不再能获得和解的冲突——现代人始终要面临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总体、生存与理性、永恒与瞬间、内在与超越之间永无止息的对峙和斗争。青年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论断就贯彻着矛盾修辞法:“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在马克思之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自身的矛盾”朝两条不同路径发展:其中一支往晦暗里行进,成为了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的“生存的荒诞和自我的悖谬”;另一支则往光亮处走,变成了爱默生和惠特曼式的自我宣言(“我自相矛盾,因为生命是无限丰富的”)。巴塔耶《内在体验》开篇处所引的尼采箴言“黑夜也是一个太阳”仿佛是这两条路径的汇合处。
以上简要的观念史溯源,基本涵盖了“矛盾修辞法”建基于其上的“真理内容”的主要形态。在中国新诗中,有难以计数的诗人以此种言说方式来呈现“终极实在的神秘”“无用之用”“世界的荒谬”“精神的自我否定”“现代主体的内在分裂”和“生命难以穷尽的丰富性”。但是,诗的演进并非只是观念或哲学的注脚,它总是与诗所诞生于其中的历史处境和诗人个体的生命气息有着密切关系。在具体的考察中,我们仍然能发现中国新诗在一些重要时刻,用矛盾修辞法显示了更复杂多样、也更具切身性的历史和生命境遇。
3
在新诗的多重开端中,鲁迅《野草》以一种强劲的黑暗之力确立了“现代主体”,并提供了如何有效运用矛盾修辞法的典范。《墓碣文》中的名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听起来和本雅明《论歌德〈亲合力〉》的结尾“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极为相近。不难看到,《野草》中的全部矛盾修辞是由其“题辞”奠定基调的,它由双重对峙或双重张力的交错构成:其一是“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张力;其二是“生命”(生长)与“死亡”(朽腐)之间的张力。前者构成了诗的语言境域(一种深黑色的、荒凉的语调),后者构成了诗的实质内容(对生命和死亡的双重肯定)。《野草》的言辞生长于“沉默”这一荒野之上。它既吸收了中国古典传统对“沉默”或“无言”的领会,又偏离了这一传统。尽管《野草·题辞》中的“沉默”仍然是形而上的,但其情调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古典那种白色的、悠然恬静的、通向自然之无限境域的无言,被置换为一种黑色的、充满张力的、灵魂内倾朝向的沉默。“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世界、自我和语言之间的冲突关系,使得鲁迅的矛盾修辞具有了表现主义的情调。
真正继承了《野草》的内在张力的诗人,是穆旦。像《我向自己说》(“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恶毒地澎湃”)和《出发》(“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喜欢”)这样的诗作,显然延续着鲁迅笔法的血统。穆旦与鲁迅一样致力于塑造“现代主体”,但与《野草》中的抽象场景书写不同,穆旦有许多诗作处理了更为具体的战争年代的现实人群和情境(如《小镇一日》《洗衣妇》《野外演习》《农民兵》等)。像《森林之魅》中“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或《农民工》中“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这样的矛盾修辞,在穆旦诗作中并不少见,其中蕴含着穆旦对人性、对战争的曲折而辩证的观照方式。正如王璞《新诗深入内陆》一文所说的,穆旦用一种“非中国性”的写法,恰恰写出了他那个时代的紧张、痛苦、黑暗和不确定的中国经验。这种“非中国的中国性”的辩证法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穆旦笔下的“中国”并非传统中国,而是正在血与火、死与生的斗争中成形的现代中国的“国族共同体”。为了书写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国族,穆旦必须用一种体现了现代性之分裂、对峙、冲突的悖论性句法去呈现其中包含的斗争和紧张。
4
早期新诗所构建的那个“现代主体”在不久以后的历史中被摧毁。很长一段时期里,“矛盾修辞法”的使用只具有语言的表层意义。而要重新确立起“现代主体”,需要等到“今天派”那一代诗人登场。北岛的诗在今天看来显得粗糙、单薄,但就重塑“现代主体”这一方面而言仍然有其历史重要性。《结局或开始》(以及《宣告》)试图“代替另一个人”发言,将“死者的声音”吸纳到自身之中,它确认“主体”的存在总是“与死者一起共在”。矛盾修辞法在《结局或开始》中服从于道义批判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虽简单却直接有力。而在另一首诗《十年之间》中,北岛试图使“诗歌之看”容纳一种“盲人的目光”:“而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这位“盲人”睁开眼睛时的视力,正是“昨天那盏被打碎了的灯”的转化物,并且变成了对罪恶的指证。从诗歌伦理的角度来说,北岛承担起了其历史使命:对“死者的声音”和“盲人的目光”这类提示着欠负之物的汲取和内化,是新的诗歌主体得以存在的条件。
相比之下,多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下的诗中虽也有对“死者声音”和“盲人目光”的书写(如《从死亡的方向看》和《火光深处》),但他对矛盾修辞的运用是更为戏剧化的,甚至有一种顽劣少年的恶作剧气质。常被人津津乐道的《我姨夫》(1988 年)充分显示了多多绝妙的戏剧想象力:“我姨夫常从那里归来/迈着设计者走出他的设计的步伐/我就更信:我姨夫要用开门声/关闭自己——用一种倒叙的方法”。这里出现的“用开门声关闭自己”固然是“倒叙”产生的吊诡结果,但如果结合《我姨夫》的意图,亦即用超现实主义笔法为某个特殊年代中产生的“唯我论强迫症狂人”画素描,那么,“用开门声关闭自己”恰好精准地呈现出这类人的精神状态——貌似开放、无所不能和对一切感兴趣,其实只是为了更好地自我封闭。《为了》(1993年)中“用失去指头的手指着”所产生的戏剧效果则是另外一类,“无指之指”似乎只是为了指向缺失本身的存在。多多高超的语言天赋和他对诗歌精神强度的不懈追求,使他在这一时期诗作中的矛盾修辞具有了一种耀眼的魅力。
5
不过,以上这些诗人对矛盾修辞法的使用仍然是局部性的。在当代新诗中,将矛盾修辞发展为自身的风格标志的诗人只有一位,那就是欧阳江河。大致以1996 年为界,欧阳江河的写作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时期:1996年以前,他诗作的基调是抒情性的,在抒情底色之上进行玄学、政治和社会学的思辨;而1996 年以后,他的诗的基座则被更换为“材料主义”或装置性,写作的目标是利用所有可能的材料来制造综合性的语言装置。在这两个时期,他都将矛盾修辞当成诗的主要方法或策略之一,但不同时期它承载的诗学功能是迥异的。早期名作《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1986 年)中的警句“真正恐怖的枪杀不射出子弹/它只是瞄准”,毫无疑问包含着对现代政治的深度经验。《我们》(1986 年)的结尾以一种令人震悚的诡异语气陈述了“反面乌托邦”的荒诞状况:“他年轻时,我们的祖先不敢老去/当他老了,我们的儿子不敢降生。”这些诗作都有强烈的对身体感受、身体性的恐惧的指涉,因而能迅速唤起读者的类似经验。《玻璃工厂》(1987 年)对事物的玄学思辨则带着马拉美和瓦雷里式“纯诗”的影响痕迹,但最终来说仍然是抒情性的:“但还有另一种真实/把我引入另一种境界:从高处到高处。/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而火焰是彻骨的寒冷,/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玻璃”“石头”“火焰”的真实物质性被抽掉,剩下了词语的纯粹质地,一种硬朗、高贵、寒冷、空旷、美丽且易碎的质地。但通过将词的质地与“事物的眼泪”相连,身体性又被召回,它将人引领向崇高又忧伤的状态。在《一夜肖邦》(1988 年)中,有关“弹奏”和“倾听”的矛盾修辞反复出现(“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可以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在弹”“可以死去多年但好像刚刚才走开”),最终通向的是一个极度抒情的结尾:“真正震撼灵魂的狂风暴雨/可以是/最弱的、最温柔的。” 《哈姆雷特》(1994 年)更是将矛盾修辞与重复句法叠加在一起,强化了诗的感染力:“衰老的人不在镜中仍然是衰老的,/而在老人中老去的是一个多么美的美少年!”可以认为,欧阳江河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位抒情诗人,矛盾修辞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以身体经验为根据的几种质感或生命状态的对比,来形成诗的情感氛围。《智慧的骷髅之舞》《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这些诗中的矛盾修辞也都可以作为这种抒情性的例证。
而从1996 年写下的《感恩节》和《国际航班》开始,欧阳江河的诗歌机制发生了内在转换:词、物与身体之间的连结被弱化,修辞学性质的语言景观逐渐占据诗的中心,一些类似于纽约时代广场广告屏幕的诗歌装置在他的写作中竖立起来。“警车快得像刽子手/快追上子弹时转入一个逆喻,/一切在玩具枪的射程内。车祸被小偷/偷走了轮子,但你可以用麻雀脚/捆住韵脚行走”(《感恩节》),“一个有身孕的过气港姐在减压时/昏了过去,班机降落后,胎儿/仍然奇怪地逗留在天空中”(《国际航班》),这些过于机智、光滑的句子削弱了诗的严肃性,但又没有构成真正的喜剧,而只是停留于诡辩和俏皮话的层次。《毕加索画牛》《时装店》《那么,威尼斯呢》也都有类似的倾向。中断写作近十年之后,2007 年正式重新提笔的欧阳江河,打算将诗当成“装置艺术品”来经营——这给他的诗带来了浓浓的“装配感”。矛盾修辞与材料拼接术一起,构成了其诗歌装置的核心工序。长诗《凤凰》(2010年)中写道“一分钟的凤凰,有两分钟是恐龙”,这个集古今中西各类知识、观念、媒介信息材料和废弃物于一身的“凤凰”,指向一种从高处俯瞰尘世的神性之物(“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它固然将“破坏与建设,焊接在一起”,并使得“一堆废弃物,竟如此活色生香”,但其“崇高性”是空洞的,按照冯强《新诗现代性的技艺和崇高问题——以欧阳江河诗歌为例 》一文的分析,其中不包含身体性,也基本抛弃了普通人的感知尺度。
在近作《鸠摩罗什》(2023 年)中,欧阳江河对材料的组装和处理能力更加老练,修辞也臻于圆熟,但阅读时给读者带来的审美疲倦却更深了。这样的诗作为大型景观诗或装置诗,看上去里面什么都有。从形式诗学的角度来看,它在观念赋形方面做得不错,但在感受性的赋形方面做得并不好——诗的感受形态是完全散乱的、碎片化的、不连贯的,也没有贯通性的情绪和情感氛围。从动力诗学的角度来说,这首长诗的气息是断的,读下来很勉强、没有推动性,几乎就是规划性的强行书写的产物。一首诗必须在多重层面上完成赋形:观念的、叙事的和感受的,观念形式不能取代叙事形式和感受形式。欧阳江河早年的诗在观念性和感受性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很平衡(《一夜肖邦》《咖啡馆》《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特别是《1991 年夏天,谈话记录》),叙事性是他一直以来的弱项;走向材料主义的装置诗之后,他基本放弃了对感受性的挖掘,只满足于语言的修辞质感,而不再在诗中呈现经验的实际感知或事物的情境质感,这使他的诗完全失衡,变成了只有观念形式这一根柱子的大厦。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现在的写法是向当代艺术中的装置物靠拢,可是,装置物是有真实的物质性和空间限定的,一个装置自带一种物与空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感受形式;而装置诗只是语言作品,它并不直接具有装置艺术的物性和感受性。语言本身是观念性的,因此语言要获得感受性,就必须突出词与身体、身体与情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知觉连续体,继而诉诸身体性的情绪和情感氛围。
6
在后期欧阳江河的诗中,矛盾修辞法是作为一种语言景观被不加节制地运用的。它既脱离了与“身体主体”的关联,也不再指涉世界的荒诞。修辞一旦丧失实在根据和感受基础,就会成为一种可以无限繁殖、衍生的拟像。在我们时代,矛盾修辞被广泛运用于广告文案的写作,它向景观转换的迅速性和便捷性,导致它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有一种深层的同构性。一些更谨慎的当代诗人警觉于此,开始主动减少或放弃矛盾修辞。萧开愚的早期诗作也曾有过集中使用矛盾修辞的情形,比如《日本电器》:“它的画面和声音如此清晰,/证明我们一直生活在模糊中。/甚至更坏。DVD 将要/证明那些好音乐是扼杀过的,/眼前的白天是黑暗的。”但在后来的写作中,这样的句子几乎再也见不到了。矛盾修辞的另一个弱点是,它本质上是依靠相反词项的结合、并置而制造效果的警句写作,但其诉诸“相反”或“对立”的逻辑结构却并不能涵盖世界和实在的全部范围。如德勒兹所看到的,世界主要不是由“相反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是由“相异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矛盾”并不能将所有的“差异”都包括进来。在德勒兹思想中,由“微分差异”构成的连续体才是我们真实经验的先验条件。因此,“矛盾修辞”制造出的警句往往是较为粗糙和简化的心智产物,当代诗人需要更微妙的感受力来填充被“矛盾逻辑”所忽略的经验区间。这种诉诸对“微分差异”之感受力的诗作,可以在臧棣、哑石、朱朱等人的作品中看到。
进入21 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除了欧阳江河的写作之外,矛盾修辞法在当代诗中的出场频率明显减少,大多数成熟诗人都不再将它当成重要的修辞手法。但这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无论矛盾修辞存在哪些局限,它都是诗歌获得语言张力和强度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完全放弃矛盾修辞,诗或许可以变得更微妙,但诗的强度也同时会有所丧失。这构成了当代诗的两难困境之一:过度追求微妙感,诗就很可能不再有那种浓烈的刺激性和惊艳感。因此,诗人并不一定就要将矛盾修辞作为一种失效的修辞手段完全扔掉,而最好是在保持警觉性的同时重新建立起矛盾修辞与实在、与身体感受之间的真切关联,并用诉诸差异性的修辞去包裹和平衡它。在我看来,多多、王君和郑越槟是试图在当代语境中重建矛盾修辞的三个诗人例证。
多多《拆词》(2022 年)这部诗集中的作品与他早期诗作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基本放弃了早期诗作中的微型戏剧场景和情节(只保留了一些动作和表情),同时,早期诗作中的画面感和完整形象序列也接近于消失(只剩下松散的、碎裂的形象),被高度抽象的沉思和冥想所取代。这种抽象化的代价,是通过形象产生的感性力量流失了很多,而其收获则是诗的内聚力得到强化,并呈现出更浓缩的语言强度(“讨论诗歌,就是讨论炸药”)。这种写作方式高度依赖于警句,因而矛盾修辞就是重要手法之一。在最好的状态下,多多能以他自身的方式召唤出“实在之神秘”,如下面这首《读伟大诗篇》:
这童话与神话间的对峙
悲凉,总比照耀先到
顶点总会完美塌陷
墓石望得最远
所有的低处,都曾是顶点
从能够听懂的深渊
传回的,只是他者的沉默
高处仍在低处
爱,在最低处
让沉思与沉默间的对话继续
这首诗建立在由两组相近词语(“童话-神话”,“沉思-沉默”)的对照所打开的语言空间之中,这种对照由语义的微妙差异构成。而“对峙-对话”则是第三组形成对照的相近词语:从紧张的“对峙”到和解性的“对话”的转变,是由“悲凉”“对他者的倾听”和“爱”带来的,它们将整个语义空间中的运动收束到一个导向同感心的方向。在诗的行进中,第二段出现的“低处-顶点”“(听懂和传回的)声音-沉默”“高处-低处”这三次矛盾修辞,带来的并不是“对峙”张力的加剧,相反,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平缓向下、汇入“最低处”(“爱”)的引导性的斜坡,降低了从“顶点”到“深渊”的语言势差。在多多这首诗中,矛盾修辞是从属于“微妙差异”的对话逻辑并被后者包裹的,因而读者感觉不到强制性和紧张感。另外,在《拆词》这部诗集中,大量关于“存在与无”“言说与沉默”“人与无人”“消失与显现”的矛盾修辞都表明多多试图重建“当代诗的超验维度”,这一在当代世界中仍执着于朝向“终极实在”(尽管它已碎裂为“无词、无物和无人”)的写作姿态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专注力。
王君的写作根源于其长期的宗教修行和严格系统的意识观想训练。他对矛盾修辞的使用方式明显受欧阳江河影响 (如《幻化》中“我飞在我不能为鸟的不能里”,《蝴蝶苔藓》中“一只蝴蝶的非眼”),而他对“感知的微分差异”的言说方式则借鉴了臧棣(如《颗粒琴》中“宇宙的琴”与臧棣《芹菜的琴丛书》有类似之处),但这两方面的语言技艺都被王君以“词与物的观想法”所统摄,并重新铸炼为独一无二的风格。《海市蜃楼》可以部分说明王君的观想方式,某种力量“动了一下原子的/结构和次序,物质的大厦轰然倒下”,一切事物都被融化为“光与气”的微粒的重组和变幻形态:
世界由银碗组成。
从银碗的边沿流出金黄色的牛奶,
群山互为奶酪,它们浓稠得
让光线化不开海鸥。而海鸥的两个轮子
飞起来是滚动的木桶。
气,在木桶里
是比寂静滚动得更快的木桶。
气的左手递给右手一个酒杯:
以虚无,嘴啜饮到这葡萄的瀑布。
竟然还有……精神追不上的光亮。
边界的融解导致了事物的互相转化(在“银碗”“牛奶”“海鸥”和“木桶”间反复变幻),这种以微分差异的连续性形成的“液体”或“流体”的观看方式在当代诗中并不少见。但这首诗的特殊性在于后面那句“竟然还有……精神追不上的光亮”,此即是说,诗中发生的物的变形并不是诗人主动想象的结果,而是由某种从外部到来的力量(“他”)展现给“我”、让“我”看的结果。“我”试图追逐、理解和把握这一光亮或事件,却追不上。因此,观想乃是主动地进入到一种被动状态中,将意识交给从深处涌起的无意识过程,在此过程中事物将逐渐消融为空无状的种子或微粒。这就是王君诗中多次出现的“能与不能”“物之存在与非在”等矛盾修辞的实在根据。这首诗中的“飞翔-滚动”“虚无-啜饮”的并置也由此而来。王君凭借这一从宗教经验(主要是禅宗、藏密和道教)中获得的观想法门,成功地将矛盾修辞转换为意识与无意识过程之间的对话。
郑越槟是当代罕有的神秘主义诗歌天才,他将济慈式的“消极感受力”与里尔克式的对“超验”的领悟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有的诗歌气息和精神性。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如此强劲、密集和庞大的神秘主义渴望,仿佛有一些潮水般的声音终年在他灵魂的群山之间来回晃荡,而他的诗歌句法只是对相互交叠的多重回声的记录。在他那里,并不需要刻意运用什么修辞手段,那些惊人的句子就会自动像泉一样汩汩冒出来。比如《扫地僧日记》的下面这一节:
有些爱抚产生了彻底的理解,有些
爱抚则由彻底的理解产生。世间
冰块一定是因为被倾听了才消融的
决不是别的原因,风中劲草开始
以摇来晃去为细小宗教。我在夜里
随意走着,难免会走到世界和世界的
空无必须互相照顾的至暗处,就算
不是火,我也得熄灭了。人走着走着
也该哭了吧一样突然哭了,那种泪
至今依然只由大雨和无形的姐姐擦拭
在那被秘密和热泪遗忘的空旷之地,诗人和自己的灵魂发生着对话,或者说,“灵魂”就是这场对话本身。或许“我们”都在期待某种“无手的爱抚”,而“我们”注定的归处却是“无火的焚燃和熄灭”。与王君诗作有着明确的宗教传统来源不同,郑越槟的神秘主义灵视是完全个体化的,因而也更为脆弱、更容易绝望。这是一种在风中摇曳的苇草所拥有的“细小宗教”,它的内倾和晦暗性,使得诗人在绝对孤独中时刻面临着崩溃的危险。那潮水般的声音和回声塑造出来的个体灵魂空间,总是一再地在内部构筑、摧毁又重建。这一不断自我构建又自我摧毁的主体形态,与穆旦《诗八章》中不断“变灰又新生”的爱欲主体有相似之处,但处境更为危急(郑越槟写道:“不知塌陷后/仍有个坚实的新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只能期待诗人在一次次的自我摧毁中能够终于形成一个不可摧毁的核心。
以上对新诗历史和现场中部分诗人的重述,并未穷尽“矛盾修辞法”在新诗写作中的所有可能性。在重述中,作为一种诗歌手法或技艺的矛盾修辞始终是次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矛盾修辞所映现出的生命在世界中的处境,以及语言、精神和实在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否将其当成自己的主要诗歌手法,无论这一手法具有哪些局限和缺陷,我们都不能否认它所带来的语言和精神强度。正如多多《读伟大诗篇》所显示的,面对着现代世界的荒诞和我们自身的内在分裂,矛盾修辞除了是对这一时代状况的揭示之外,也可能构成一种特殊的疗愈。事实上,无论是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还是海德格尔的“作为争执的真理”,都有一个从斗争向和解、从对峙向对话的转化。通过观想与沉思,通过差异感知对辩证法的补充和包裹,诗或许能帮助我们重建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平衡,在新的历史处境下返回与终极实在的亲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