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现史料看中央特科的活动情况
2023-03-24■杨田
■杨 田
1934年9月26日,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公共租界枪杀叛变的特科原成员熊国华。此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联合上海市公安局对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进行大搜捕,抓获红队成员多名并查获多份资料。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外事科科长丘比罗斯的建议,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副总监命令情报处勤务警部助理伊姆·高尔德,根据被捕人员的供述、查获资料及多年来侦破的涉中央特科的案件,撰写中央特科的活动情况报告。12月6日,高尔德完成报告——《中国共产党特务队的活动情况》。1935年7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将该份报告从英文译成日文,并刊登于《外事警察报》 (第156期),标注密级为“特密”。
因工作性质特殊,中央特科没有留存档案,这为后来的党史研究留下一大难题。近年来,关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2021年,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也于上海建成。但是,关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更多的是依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当年租界巡捕房及国民党有关机构保存的口供。日本《外事警察报》中刊载的此份报告,虽然是翻译资料,但应该是目前已知的早期比较系统地介绍特科的资料之一,而且是出自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之手,其内容可信度较高。现将有关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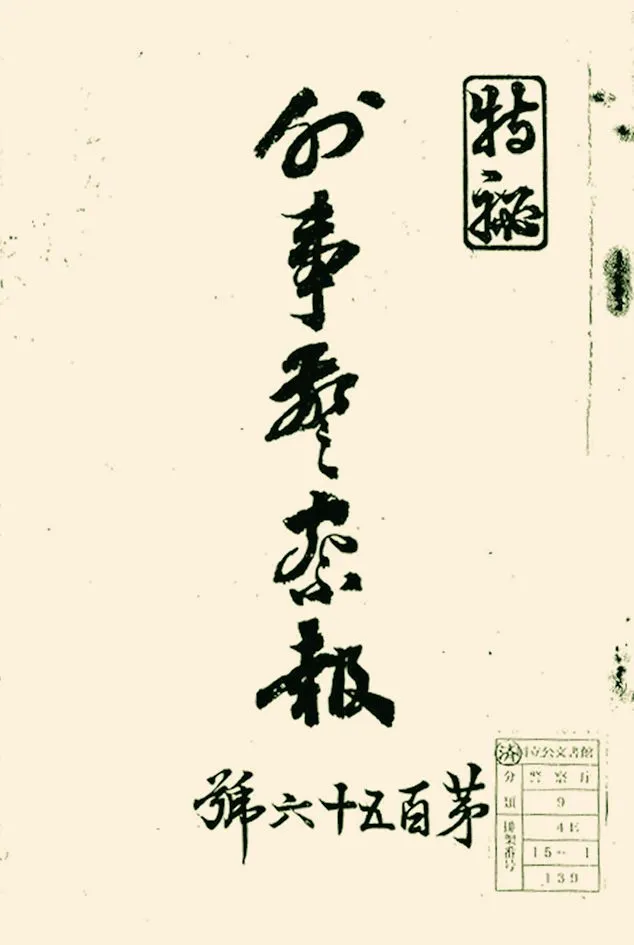
日本《外事警察报》 (第156期)封面
关于中央特科的名称及中央特科红队开始活动的时间
该份报告通篇没有出现“中央特科”或“特科”的称谓,而是使用“中共特务队”。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名称,故用自创的“中共特务队”来代指“中央特科”;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知道“中央特科”的名称,但由于是中译英翻译问题,使用了某一特定英语词汇,后来日本译者从英文翻译为日文时,译成了“中共特务队”。
从中日语言翻译的惯例来看,“中央组织局特务科”这八个汉字在日语中都存在,如当时日本译者知道“中央特科”这一组织,肯定会直译为“中央特科”,而不会另译为“中共特务队”。基本可以判明,至少在1935年之前,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尚不知道中央特科的具体名称。
从报告内容来看,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注的更多是特科的行动,对特科的总务、情报和无线电通信并不关注,所以该份报告中的“中共特务队”指的主要是特科的红队。报告中专门提到了中央特科红队开始活动的时间,是这样表述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格别乌,即中共特务队的成立时间,目前有用的信息不多。不过据中共特务队的前领导人顾顺章介绍,大约在1928年秋天,中共特务队开始在上海活动。自1925年至1927年间,中共也组织过一些惩处活动,但那都不是中共特务队所为。中共特务队是中共在原有保卫力量的基础上,补充精干力量并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后形成的一个专门的行动机构。”
报告中还列出了两个表格,表一为1925年至1934年中共在公共租界内开展惩处行动的日期、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及被逮捕人数的数据统计。表二为中共组织的惩处行动的日期、死亡者姓名、行动地点,以及被逮捕人数的数据统计。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1929年后,除1931年受“爱棠村事件”影响外,每年“死亡人数”较1927年、1928年明显下降。在表二中,1927年的惩处行动达到顶峰,共计28起。这应该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残酷的斗争形势有关。但特科在1927年11月14日才成立,所以此年度的绝大多数惩处行动应与中央特科无关。1928年惩叛锄奸行动10起。进入1929年后,每年的惩叛锄奸行动直线下降至两三起。
根据已知史料,红队自特科成立伊始就已组建,从未被授予过任意行动、滥杀的特权,每次采取制裁行动,都要经过严密侦察,掌握确凿证据,并且须报经党中央、中央特委批准,执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综合报告中提及的顾顺章关于红队开始活动的有关表述,以及表一和表二中红队1929年前后惩处行动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红队自1928年秋季开始在上海开展惩处行动的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

《外事警察报》 第156期刊载的《中国共产党特务队的活动情况》 报告
特科红队开展惩处行动的细节
根据报告所述,红队开展惩处行动大致分为前期准备、具体实施和后期收尾三个阶段。
一、前期准备阶段。“死刑执行部部长向暗杀组下达惩处指令,附带行动目标的照片或者画像等。执行部部长从成员中挑选出一到两位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此次惩处行动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整个行动。”“组长到惩处目标的住处进行踩点,确定便于惩处且容易撤退的地点,并做好准备工作。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组长向执行部部长汇报行动方案。执行部部长审核行动方案,确定具体实施时间。”
报告中的“死刑执行部部长”应为中央特科红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制裁行动由党中央、中央特委批准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才会挑选具体人员参与惩处行动。根据报告所述,红队成员人数应较为可观,每次可根据不同的惩处任务确定不同的人员构成。而且确定好人员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还会确定一名或者两名成员担任组长,由其负责整个惩处行动。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具体行动方案还要履行审批手续,由红队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才能具体实施。可以看出,惩处行动在具体实施前都要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相应地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在报告中公共租界巡捕房评价红队的惩处行动:“惩处行动比较缓慢,但是组织良好,而且成员大多为忠诚的中共党员,所以行动成功率非常高。”
二、具体实施阶段。“在行动的前一天,暗杀组组长或者受其指派的成员会提前到行动地点附近,以假身份在两个不同的旅馆内各开一个房间,或者租借两处房屋,一处用于行动前集合,一处用于行动后会合。在行动前一个小时(有时也为两个小时),所有参与惩处行动的成员会到其中一处房间或房屋内集合,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所有人不携带武器。最后由死刑执行部部长或者部长的代理人将武器送到集合点。武器平时藏在部长的家中,运输时采用两人前后掩护的方式。探路人在前,运送人紧随其后二三十米。如果突遇警察盘查,探路人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运送人立即掉头逃走。到达集合点后,运送人将武器分发给每名成员,然后大家散去各就各位,按照预定方案执行惩处任务。两名成员不参与惩处行动,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往返骑行,如果发现成员被捕,这两人会立马逃走,告知执行部部长人员被捕情况,同时告知其他未参与行动的成员迅速变换住所。”
报告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红队开展惩处行动的细节。一是执行制裁任务时,会提前在行动地点附近物色两处临时住所。二是红队队员平时不带武器。武器由红队队长保管,只有在执行惩处任务时,红队队员才能拿到武器。此外,报告中还提及“基层成员最近(1934年9月熊国华被惩处之后至该报告撰写期间)每人还配备了一把锤子,主要用于自卫”,也从侧面证明红队队员平时不携带武器。三是武器双人运输。前面的人负责预警,后面的人负责运输。四是在行动现场,除参与执行惩处任务的成员外,还会安排两名成员全程观察,如任务失败,可第一时间预警。
三、后期收尾阶段。“当行动顺利完成时,所有参与人员会到租下的另一处房屋或者另一家旅馆的房间会合,将武器交出后立马各自离去。”
中央特科的保密手段
报告中提及:“中共惯用的保守秘密方式,不适用于特务队。特务队的保密要求更高。”这与党的隐蔽战线比党的其他机构保密要求更高的史实相符。报告列举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要求:
(一)禁止前往茶馆等复杂场所。
(二)禁止与非成员交友。
(三) 非成员,如无特殊理由,不得进入特务队成员的房间。
(四)进门后,房门必须反锁。
(五) 会面时,要使用约定暗号联系,如吹低音笛子或者往窗户上扔硬币等。
(六) 邮寄物品必须使用假名,严禁邮寄涉密文件资料。
报告还提及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手段。如,使用不同颜色的信封代表不同含义。公共租界巡捕房在工作中发现,“中共特务队的很多信封内部并没有任何东西,仅靠收件人的写法和信封的颜色就可以传递信息”。又如,使用特殊的暗号传递信息。报告中提及:“中共特务队成员在住处被外方巡捕逮捕后,普遍会请求巡捕打开窗户透透气。欧洲人不喜欢长时间待在不通风的房间内,如果被捕人员提出类似要求,外方巡捕一般都会答应。后来巡捕房逐渐认识到,打开窗户就是特务队成员约定的一种暗号。一旦看到某位成员的窗户开着,就意味着该成员出事了。其他同伙自然不会再靠近。”“从窗户边伸出一根小竹竿意味着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则是指出事了。”“在窗户上贴一张小的正方形的纸片,意味着自己在房间里。”
在大街上碰面时的暗号也是多种多样:摘下帽子,用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用左臂或者右臂夹着包;摘下帽子,擦帽子内檐的汗;手里拿个手绢或者用手绢包着手;假装牙痛,用手捂着脸;等等,不同的动作代表不同的含义。
中央特科红队的经费来源和武器来源
根据报告中“中共特务队的经费来源至今不明”这一表述,基本可断定公共租界巡捕房当时并不掌握中央特科的经费来源情况。不过报告中提到了1934年10月4日法租界法方巡捕在麦琪路麦琪公寓34号查获的《1934年4月中共特务队支出情况》。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份文件,同时结合被捕人员的口供,判定中央特科日常运行仅使用现金,不会开立账户或者使用支票等。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一个细节,“中共特务队有一个姓叶的副队长。1934年9月27日在成都路被逮捕的邝惠安曾用邝奇的化名从这名姓叶的副队长手中领取了自己及下属队员的现金津贴”。此位姓叶的同志具体是谁,根据现有史料还无法确定。当时很多特科的同志都用化名,至于是否真的姓叶也很难确定。不过,邝惠安是特科后期红队的主要负责人,从他领取现金津贴的细节来看,基本可以断定这位姓叶的同志应为特科内较重要的一位领导或者负责财务的同志。
公共租界巡捕房对中央特科的武器来源有一个认知转变的过程。在前期,公共租界巡捕房认为中央特科的武器都是从苏区通过秘密渠道运到上海来的。但是,后来随着侦破案件的增多,以及被捕人员的口供,公共租界巡捕房逐渐查明,中央特科使用的武器基本是从上海等地购买的。其中有部分武器甚至是国民党军队看管军火库的士兵从军火库中偷出来,然后卖给中央特科的。
中央特科红队的培训
报告中提及了“中共特务队”的培训情况,但从培训内容来看,主要指的是红队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一是上海城市概况。让队员熟悉公安局、政府部门、主要道路和车站位置等。
二是跟踪训练。主要练习跟踪和识别目标人物。
三是熟悉旅馆及出租房等的内部结构。
四是模拟演习。分成两组,一组为观摩组,另一组为行动组。演习前,观摩组到预定行动地点就位,观摩整个演习过程,积累经验,查找不足。行动组完全模拟实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实施行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回之前预定地点。在整个演习期间,安排专人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来回骑行,对行动进行监视。
五是寻找指定地点。教官要求培训人员去寻找某一旅馆或某一出租屋等。培训人员自行前去寻找,找到指定房屋后,要将周边情况及居住人员的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回来报告。寻找练习有时间限制,而且还会受到教官的监视。
六是“弄内斗争”培训。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撰写报告时对“弄内斗争”培训的具体情况还不掌握,仅是在1934年9月27日搜查到的一份文件中发现了“弄内斗争”的有关文字,猜测可能它与利用上海狭小的弄堂开展惩处行动有关。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对特科成员的评价
报告中对特科成员的评价较高。“现在中共特务队的成员大多是从红军中精心挑选的。他们是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坚信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并且愿意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去冒任何生命危险。中共特务队成员清楚地知道自己早晚会被逮捕,但依然毫不畏惧地继续冒险犯难。在对特务队成员进行审讯时,他们的供述也充分体现出上述特点。如,当被问到某某是不是你杀的,他们会很痛快地回答,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但如果被问到你们的领导是谁,他们肯定不会透露任何姓名或住址,甚至会胡乱编个荒唐无稽的人物来糊弄你。1934年9月27日,我们逮捕了一批特务队成员,相信他们与未归案的特务队成员肯定有联系,但他们却没有招出任何一人,导致我们到今天也没能抓到其他人。”
报告中提到的1934年9月27日逮捕的特务队成员,其实就是邝惠安、孟华庭、赵轩和祝金山等特科红队领导和成员。根据报告内容,可断定上述人员在狱中是坚贞不屈的,没有泄露任何秘密。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中共特务队中党员数量很多,他们没有私心,信仰坚定,能力突出”,“中共特务队成员并不是从上海党组织中补充的,而是来自红军,所以即便冒再大的危险,他们也会严格执行命令。与在沪共产党员相比,除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中共党员共同的目标外,红队成员与他们没有任何相同点”。
报告有贬低上海党组织的中共党员之嫌。由于报告是站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立场,这种认知自然不具有客观性。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央特科,特别是红队的成员并不是从上海党组织中补充的,而是从各根据地的红军中补充的,他们都是信仰坚定、能力突出的红军战士。
该篇报告的最初版本是英国人用英语撰写的,后来由日本人从英语译成日语。笔者在写作此文时又将日语翻译成中文。通常来说,一篇文章,每被翻译一次,内部的细节就会丢失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英文版报告还尚未发现。相信英文版报告会还原更多中央特科的细节,对我们研究中央特科的历史将大有裨益。期待这一报告的英文版能够早日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