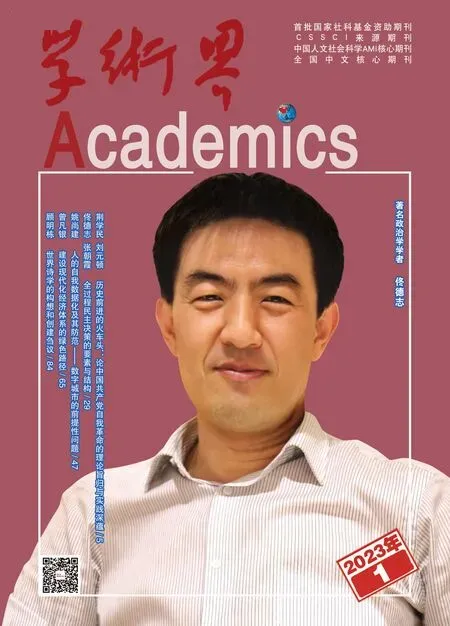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
2023-03-22陈丹丹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陈丹丹(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当代全球化进程、数字革命以及由此而不断增强的跨文化交流,使歌德在19世纪初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构想褪去其乌托邦色彩,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益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热门话题。世界文学的崛起呼唤世界性批评体系、世界理论和全球美学,这样的学术内驱力引发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一些文论家秉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对“世界文论”“全球美学”的议题展开了极具启发性的探索:华裔学者刘若愚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建构了融合中西诗学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美国学者孟而康综合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文学传统,进行了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的尝试,在走向总体性文学及文论研究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中国学者乐黛云、叶朗、倪培耕、王宁等沿着前人的足迹提出“世界诗学”的概念,倡导建构一种有着共同美学原则和普适标准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可以看出,学者们希望冲破文论的地缘性,在跨文化论域中进行对话,寻求公约元素,最终建立普适框架。他们走在“世界文论”的前沿,提出了极具意义的前瞻性思考,但是,不得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理论建构的草创阶段,尚未真正建立起一种跨文化美学的融合型框架。因此,在中西二元范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论和美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华裔学者顾明栋的新著《中西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视域的融合》〔1〕对比较文学、文艺研究中极富时代性、挑战性和开创性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较为全面的考查,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启发下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论诸问题展开分析、批判和反思,主要目的是对实现世界文论及全球美学的构思和做法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的缘起及意义
全球化的进程及电信科技的急速发展大大缩小了东西方的地理距离,使得人员、物资、智力资源和知识的洲际流通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让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从构想走向现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提出了“世界文学”观,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丹穆若什通过研究文学作品在离开源语境流向广阔的国际空间时发生的“变异”及其过程和方式,证实全球化对文学国际化以及对促进文学文本在国际流通中构建“世界文学”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2〕其他不少理论家、学者也看好“世界文学”的前景,为建立与之适应的世界批评、世界理论和全球美学而付诸努力。从世界文学走向世界文论在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一个堪称划时代的事件。2008年,美国文论家文森特·里奇等编著的《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改变了历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编辑政策,打破了只收录西方文论家的惯例,在新版里加入了来自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非洲、拉美等非西方传统的文论家,其中就有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核心论文。〔3〕尽管文选的编辑承认,文选根本上还是以西方为中心,但是这一举措无疑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开创了收入非西方文论家思想的先例,从而在文论全球化的道路上建立了一座里程碑,〔4〕成为美学视域融合之路上的开拓者,激发我们对于世界文学可能性的思考,为走向全球美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探寻文学的世界普适性特征、方法和范式,尝试搭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中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带着建设“世界文学”的初心,成为了弥合中西方美学领域鸿沟的早期摆渡人。朱先生1936年的《文艺心理学》〔5〕和刘先生1975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文学理论》〔6〕都是建构“世界文学”的前瞻性思考,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然而,“世界文论”的构想并没有随着先驱者的步伐和全球化的浪潮而迅速实现,建立“世界批评”“世界理论”“全球美学”由于文化差异和知识惯性,注定不可能是百米冲刺跑而是马拉松障碍赛。全球语境下的美学发展历程中,英国美学家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在其文艺哲学研究方面撰写了开山之作《美学史》,但非常遗憾的是,他选择性忽略和放弃了整个东方的传统美学思想,认为东方无审美意识,或者说东方的审美意识因缺乏反思特质和无系统性建构特征而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准。〔7〕在鲍桑葵眼中,东方艺术,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不可与西方相提并论的“异类”。
鲍桑葵所处的20世纪之交是殖民主义鼎盛的时期,如果说他的视角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在全球化缩小了东西方地理屏障的今天,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看到,情况有所改变,但分歧依旧存在,且不容乐观。全球化对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西方)文艺比较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促成中西学术对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西方审美的不相容性也有所缓解,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仍显著存在,对此甚至生成了一些新形式、新观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话语,但是在“文化相对论”框架下,中国被视为西方的终极“他者”,因而很难找到跨越东西方文化鸿沟的概念性基础。在后现代时期,文化相对主义更是呈现出激进的态势,一股让中西方走向对立而非融合的力量掀起文艺理论界的浪潮将中国和西方推向相反的方向,中西方历史、语言、政治、诗学、美学、形而上学等方面截然分开,很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东西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也以相互无法理解的方式差异性地存在着。正如张隆溪批评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片面地认为,东西方的知识体系应该与另一方保持相当的距离。〔8〕显然,学界众多观念仍然落在鲍桑葵认为东西方美学互不兼容的“认识型”窠臼之中。
在“文化相对主义”和西方霸权话语的影响下,中西方不相容的显性特征逐渐形成了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在文艺研究领域,基于二分法的对立范式出现了。自此,二分法和对立范式成为中西比较研究的普遍框架,互为支撑,相互巩固,似乎成为中西方之间的坚不可摧的屏障。华裔文论家周蕾认为,对于中西方概念化的二分法究其根本是对西方观点和范畴的先天性的“臣服”,〔9〕这种“先天臣服”使得学界的思想及研究状况非常复杂,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也认同中心二元范式,有意识、无意识地接受二分法并承认其信度和效度。比如前面提到的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构想的是普通文艺理论,而实行的却是二分法原则,表达的也是类似于鲍桑葵的中西美学不相兼容的观点:无论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10〕认为非西方学术传统因其朴素的形而上学和肤浅的宗教感知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暗指中国几乎不存在美学和哲学,即使有,也不可与西方的相提并论。持类似观点的屡见不鲜,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就曾将国内学者的中西美学二分法予以概括,并一一指出其偏颇之处。〔11〕中西美学的二分法往往以中西哲学的差异为概念性支撑和论据。比如,华裔学者欧阳敏认为“中国没有西式的哲学”,因而也不需要跟西式哲学攀比。〔12〕即使是思想观念十分开放包容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在中国是否有哲学的问题上步黑格尔的后尘,认为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后特有的文化产物,中国的儒道思想只能算是一种人生智慧,而不是基于抽象推理和精神意识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能算是哲学。〔13〕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中西方二元对立范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以下论点:造成中西文艺比较研究中二分法对立性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哲学的异质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美学及批评理论学者,不论来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其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中西对立/差异范式。从表面上看,该范式来源于西方知识霸权或文化相对主义,但是从其深层结构来看,还是生成于对人类不同发展模式的历时认知和对中西方思想差异形而上形成的概念。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明过去到现在呈现的是一种连续模式,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断裂模式。从思维方式看,中国以关联性思维为主导,而西方以分析性思维为特征。从形而上学模式看,中国思想重整体的一元论模式,而西方是分离式二元论模式。西方传统是建立在自然和文明的分离格局之上,而中国传统则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连续体。西方有一个创造一切的创造神,而在中国传统里没有创造神,中国宗教是泛神论的,因而缺乏深沉的宗教性。因此,西方的世界观在人神二分之间显现出悲情式张力,而中国人所看到的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和谐宇宙。〔14〕
在这一系列二分结构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讽刺。文化相对论意在抵抗文化普遍论、挑战欧洲霸权话语、扭转强加于非西方文化的西方意识形态。然而,现实却与初衷背道而驰,诚如印度学者明确指出,不论是在吉卜林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还是在我们所处的后殖民主义时代,那些捍卫东方差异性的人和那些贬低东方差异性的人在最重要的描述性推定上出奇一致,不同的只是评述性话语。甚至那些一直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作斗争的人竟与其声讨的敌手共享大部分的思想观念。〔15〕因此,激进的相对主义本该打击跨文化研究中的西方文化优越性,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实际上,在已建立的中西方之间的二分模式中,不论对中国的学术话语是褒是贬,一种或隐性或显性的偏见已植入其内部结构。对二元对立进一步观察后发现,它们实际上隐含着一种等级结构,其中中国学术总是处于较低的地位。
二元对立范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形成格局,对中西对比研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二分法虽然有其历史和学术的发展渊源,但是刻意地去制造对立和二分则让该范式受到质疑,对中国文化持异质论的观念也应受到批判性审视。对于中西方学术研究的对立范式引发的争议,很多学者参与其中。有些对这种对立范式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却认为此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正确和有效的。这种棘手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的问题:首先,如果我们采用对立范式,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中西方研究?它能否指导我们厘清中西方语言、文学、艺术的真实质态?能否为中西方人文科学间的真正对话提供理论框架?其次,如果我们摒弃对立范式,那么有什么样的替代范式能够促进中西方学术传统交流?又以何种方式让中西方语言、文学、艺术和思想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富有意义的对话?最后,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如果想要将中西方语言、文学、诗学、美学、形而上学等方面的差异重新概念化,进而推动中西方审美视域融合,就需要一个共同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
比较文学著名学者张隆溪教授写过一部中西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力作《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该书旗帜鲜明地反对东西方文艺二元对立的观点,并以大量实例分析证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在概念构想和表现上的共同之处,展示出两大传统不期而然的契合和同工异曲之妙。与其他学者不同,张先生没有落入二分法对立范式的窠臼,而是富有创见地对传统的跨文化研究的学科壁垒和思想概念的分割进行剖析,找出东西方间超越差异的契合与同质,并在文化同质基础上探讨两者关系,他认为只有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才能有开阔的眼光,只有从东西方比较研究跨文化的视角,才能获得某些批评的洞见。〔16〕正如张先生指出,东西方差异客观存在,不能简单丢弃,也不会随着全球化和数字通讯的加强而逐渐消失。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异曲”而忽视“同工”,如果我们对原有的范式和方法抱残守缺,就不会有理论的突破,中西方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思想的交流继续处在西方话语的单方控制之中,中国学界充斥着西方话语(即便是中国化的西方话语),中国美学传统在汹涌的西方美学思想面前集体“失声”,最终沦为西方美学的附庸或者说是西方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中西方研究中的两种情况就会持续存在:第一,中西方美学截然分开,固守各自的框架和体系,两者之间的联系仅停留在表面,肤浅且零散;第二,两种学术传统在一种虚假互动中展开,中国素材沦为证实西方思想及理论的原始资料和数据。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从事文艺研究的学者应该怎么办呢?
面对中西对立范式和西方文论一家独大的话语格局,需要对中西方研究中的一些固有观点提出挑战,深入思考中西方研究中的二分法,在中西文论和美学的核心议题上,展开对思想表达新模式的开放性探讨,尝试建构中西方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范式。华裔学者顾明栋教授认为中西方对话障碍的根源在于一系列能够让人明显意识到的感性差异(如语言、文化、概念、审美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形成整个认识论的分裂。这个论断是极富价值的。为了弥合裂隙,必须梳理文艺研究领域的一些核心问题,分析异同,找出共通的概念性基础,努力建构中西方学术研究的新型理论框架。由此,促进中西方研究范式转向,设计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以跨越中西认识论的鸿沟。此外,在构建中西方话语双向交流框架中,既需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又要追求真正的普遍价值。受已有关于世界文论的启发,笔者试图结合顾著的相关论述对以下问题作出粗浅的思考:“世界文论”“全球美学”是否可能?“世界文论”“全球美学”如何可能?
二、“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是否可能
“世界文论”“全球美学”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从语言、诗学、文论、美学等核心批评视域对此展开研究,顾著的基本思路首先是对各视域中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批判性反思,论证语言的同质性、比喻的普遍性、摹仿的普适性,并从中发现视域融合的根本——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揭示两大传统可能存在的共同基础,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中西语言、诗学、美学等方面的差异,尝试从多维度视角跨越中西思想的鸿沟,进而试图建立带有普适价值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范式,为“世界文论”“全球美学”铺路。笔者认为,此研究思路对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鱼”指研究结论,可以回答“世界文论”“全球美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渔”指研究方法,可以回答“世界文论”“全球美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整部作品所呈现的“渔鱼”过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令人钦佩的范例,不仅带来洞见,而且也引发思考。接下来,笔者在对语言、诗学、美学视域融合的学术反思中谈谈对“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是否可能”的看法。
语言视域融合建立的观点是:第一,中西语言都是从图像起源,在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语境中演变并逐渐分野,沿不同路径形成两套成熟的语言体系:象形表意文字与语音字母文字;第二,两种语言系统的表征差异不应成为完全割裂其联系的鸿沟,符号学、语言哲学等学科框架为其提供了概念性同质基础,使中西语言鸿沟的融合成为可能;第三,结合汉字“六书”与语言符号、认知科学发现新的符号类型,由此构建汉字分析模型,对世界符号理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不得不说,语言融合在理论构建上是成功的,但可能也只停留在理论上,而缺乏可操作性。我们认为,顾著所建构的语言鸿沟的弥合点一个在底部一个在顶部,即,中西语言的表层符号在人类底层心理及认知中的相同建构机制,以及中西语言符号在形而上的思考空间中的概念性弥合。的确,文字起源的图像性是人类认识、构建世界的本能和一种自然顺序,从图到字的发展是人类心理的普遍能力,但是,这种本能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自发性的,而中西在各自语境中语言发展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这些选择因素对文字体系的最终成形具有重大作用,所以这部分可能也是分析中西语言异同的不可忽视的部分。同样,对文字的符号性质的形而上思考是一种极度抽象的概念凝结,而在中西语言发展路径中的具体操作及原因也是中西语言异同分析的主体部分。如果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西语言间的异质元素虽然存在同质的概念性基础以及视域融合的可能,但是历经若干世纪在众多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的两大体系在现实中将仍然按照各自的路径发展,任何企图以表意维度去重构字母语言体系,或是从语音维度去重写汉字体系,抑或是创造一个统一框架将字母语言和表意语言全部纳入其中都难以成功,而且也没有必要。尽管如此,“语言视域融合”的构建对语言进行根源性探索,得出创新性启发性结论,为中西视域融合作出了有益尝试。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原创理论需要大胆突破原有框架,走出传统视域的藩篱,这种研究之“渔”是创建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中西语言文字的本质性差异使得语言文字层面的融合只能局限于语言哲学的领域,诗学视域融合部分显得更为卓有成效。在实证层面,利用文本细读对一些学者的论证进行批判性反思,对大量中西诗歌的用喻实例进行建设性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推翻长期存在于中西比较研究中的二分法及其隐含有价值导向的论断,指出中西比喻的共同特征:高度抽象性和创新想象力;在概念层面,发现西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逻各斯(Logos)”与中国庄子的“道”具有中西哲学思想的普世之“一”、《周易》中的“道”“器”分离与西方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分”共同蕴含的二元思想,揭示了中西比喻可以融合而非分离的形而上概念基础;在重构层面,创建多学科融合框架,一度被踢出“比喻”范畴的“兴”被重写为“转喻性比喻/比喻性转喻”的混合质态,“比”与“兴”走向融合,中国“比兴”与西方“比喻”走向融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比喻的符号化模型,为比喻的普适性奠定概念性基础。以上的这些见解非常深刻,可以激活人们的思考能力,抛开固化的二分体系重启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新创的比喻符号模型,确实可以作为中西比喻的分析框架,在这个符号体系中,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比喻,都可将漂浮状态的能指/喻体和所指/本体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意指空间,它们在想象的压力下,在“延异”所释放的意识空间寻找“落锚点”和“契合点”,从而形成比喻的开放性阐释,不仅为中国的比兴带来新的洞见,而且对普遍的比喻也具有重要意义:本体、喻体意指过程的潜在空间拓展了阐释的多种可能,进而带来“比喻的复活”;比喻得以突破传统的表层结构模式,从述谓结构到零述谓结构,其存在的语法单位从句子、小句甚至可以到短语,比如定语中的比喻等等。由于比喻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要素,展望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不仅可能,而且能为世界文学艺术带来更多思想的火花。文论和美学的视域融合涉及诗学、美学的众多议题。笔者认为,将研究视域拉回到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后,就回到了比喻的原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共同的摹仿本能;对于二分论者始终纠缠的摹仿论的文化决定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哲学思想“道”的超验与内在的双重性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文学双重发生论:文学既源于自发生成也源于摹仿再现,并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的两种趋势:自发表现论为主流,摹仿再现观为支流,这种双重性不以分离而以互补为特征。审美视域则从形而上学视角,探讨艺术之源及审美的终极理想,指出神/神性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神明的审美理想型仍然与当今的艺术创作有关,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终极审美标准——“入神”(entering the divine)观念可能是艺术创作中激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适用于各文学传统普遍的最高审美理想。通过对艺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证明了中西美学思想根源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应该成为跨越中西思想鸿沟的概念性基础。这一点对于建构中国诗学和全球美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此外,如果能建立中国摹仿理论的一套完整体系,无疑是击垮“中国无摹仿论”的致命一拳。因此,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著作中寻找中国思想家的一些摹仿洞见,梳理中国批评传统主要领域里的摹仿理念,在此基础上,厘清其内在联系和结构,从中国摹仿的本质、摹仿的趋势、摹仿的内容、摹仿的对象、摹仿的类型、摹仿的目的、摹仿的技术性问题、文学源头摹仿说、文学艺术的摹仿本质、中国摹仿的形而上学等维度创立中国摹仿论的框架,以此勾勒中国摹仿理论全貌,建立宏观系统的中国摹仿理论,同时也可成为中西摹仿比较研究的框架,进而为全球美学提供方法论的有益补充。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笔者认为,对于“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中西语言的确存在共同的概念基础,而“可能性”就是建立在中西视域的同质性根基上,中西语言、诗学、美学的共同根基使“世界文论”“全球美学”成为可能。
三、“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如何可能
“世界文论”“全球美学”的最大障碍是学术研究的二元对立范式及其概念基础,因此,解答“世界文论”“全球美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必须实现范式转向,其核心就是寻求替代范式、建立新的方法论框架。方法论的推陈出新带来理论的突破和学术发展,同时能够改变当前学术界的一种瓶颈现象——缺乏新思想的机械模仿和简单重复。如何做到?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新型理论框架的建构:一是突破原有的框架模式,以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洞见;二是力图实现学科、理论、方法等多方面的视域融合,开发新的阐释空间,显示学术研究的无限可能。由此,建立融合语言、诗学、美学批评视域的“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
笔者认为,顾著对中外研究汉语汉字的偏颇现象的批判、从比较的视角重新思考中西方符号的生成对新范式的构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语音中心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语言视域中二分法的认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在场先于缺场,口头言语是在场,书面文字是缺场,因此,言语优于文字,文字是言语的奴仆。在此逻辑下很自然地推导出西方以语音为主的语言是优势语言,而汉语不如西方语言文字,导致中西语言一直处于一种二元对立中,而且是一种强弱不均的二元对立,久而久之,这种范式形成一种“认识型”,成为语言研究中的“汉学主义”,并长期影响和主导着学术研究,导致研究结论不能反映普遍真理,甚至沦为判定文化优劣的标准。那么,跳出语音中心主义的泥沼,在更大的理论视域下,不仅得出了科学客观的结论,而且在中西理论的真正对话中,视域得以融合,生成新的阐释空间。例如,许慎的汉字六书与皮尔斯的西方书写三分法的接合突破原有表音/表意二分法,重新分类文字符号,发现新的符号类型,实现理论飞跃。再如,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与汉字构字原则结合,揭示从图到字的共同心理机制。这种研究方法对文学艺术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成功地将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神经学、计算机科学等相结合,为全球化电信化时代的人文研究开辟了新领域。〔17〕因此,这种论证之“渔”极具价值,告诉我们将研究放置在更大更广的学科联系中,学科视域的融合会打开一个新空间,研究将具有开放性,显现出令人激动的无限空间。
在比较诗学视域,陈旧的研究框架仍然是割裂中西比喻使其彼此不容的主要因素,放眼该领域中学术研究的局面,我们发现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的,部分学者有意强调和深化中西差异,常常预设研究结论,为迎合其心理期待刻意选择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和研究结论的相互加持中巩固捍卫二分体系,因此一些陈旧老套的研究框架成为他们的温床,对更多的研究可能视而不见;另一种是无意识的,对知名学者盲目崇拜,缺乏反思的学术素养和创新精神,因此陷入泥沼而无法自拔,这一点可以作为“汉学主义”的一个现象。美国著名文论家卡勒教授(Jonathan Culler)在一次影响深远的探讨比喻的国际性专题讨论时指出,在比喻的概念性研究中,有两大研究方法:哲学路径和修辞路径。〔18〕而在中西比喻研究中就存在着这两种路径的分离,即使在诗歌的常规修辞分析研究中也存在着比喻与转喻的分离,导致中国比兴与西方比喻的差异持续放大且固化为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要想实现理论突破,就必须跳出研究的舒适圈,将哲学路径和修辞路径相结合,在人类普遍心理和认知机制中发现中西比喻的交汇点:即心理符号学视域中的诗性想象。接着,在索绪尔(Saussure)的“意指”理论、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以及雅各布森(Jakobson)和拉康(Lacan)的比喻/转喻理论的合力下,融合比喻与转喻,融合比兴与比喻。再通过德里达(Derrida)的“延异”概念对符号语言学的补充融合,建立了中西比喻的符号模型。
在美学视域,一些研究者对产生摹仿的文化条件和美学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认识误区,使得中西美学思想分属两个阵营,相互对抗。在论证摹仿普适性时,将关注点拉回到摹仿的原始概念,顾著指出摹仿的条件是模型和复制的二元性,而不是西方超验与内在的分离等文化先决条件,从而发现了中国摹仿的双重性,因此,中西摹仿论并不相悖,而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融合状态。面对抒情表现与摹仿再现的中西二分法,从历时角度进行分析,在文学体裁与审美思想的互动中勾勒出中西美学思想源流及转向,揭示中西的“再现”在其传统伊始就呈聚合状态,经历发展和转向后两者都形成了不同强度的表现与再现的交融,进而将艾布拉姆斯著名的“镜”与“灯”〔19〕的独立范畴重写为“镜中灯”/“灯中镜”的融合视域。
四、结 语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随着电信技术的日益发展,世界逐渐浓缩为地球村,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应该制造壁垒相互排斥,而应该走向对话促进融合。然而在西方霸权的长期影响下,西方理论话语仍然唱着“独角戏”,非西方世界却集体“失语”,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在制造一些二分法,进而形成一种“无意识”,影响、操控世界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建构。对于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二分法,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考查,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对话。在对一系列二分法原则进行研究分析后得到的大量概念性批评证据表明,尽管存在语言文化差异,中西学术传统在美学思想方面仍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现有的洞见可以指引我们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进一步拓展路径去跨越中西方鸿沟,从而建立中西两种美学传统的“视域融合”。笔者相信,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来看,世界文论和全球美学不仅应该存在,而且在将来完全可能实现。
注释:
〔1〕Mingdong Gu,Fusion of Critical Horiz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1.
〔2〕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1-36.
〔3〕参见Vincent Leitch,et al.,eds.,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Norton,2008,“Preface”。
〔4〕顾明栋:《〈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及中国文论的世界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
〔5〕参见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6〕参见James J.Y.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7〕Bernard Bosanquet,A History of Aesthetics(1892),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6,p.x.
〔8〕Longxi Zhang,Mighty Opposites: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xvii.
〔9〕Rey Chow,ed.,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Reimagining a Field,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10.
〔1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1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6页。
〔12〕Min Ouyang,“There Is No Need for Zhongguo Zhexue to Be Philosophy”,Asian Philosophy,22(3),2012,pp.199-223.
〔13〕Haifeng Jing,“From ‘Philosophy’ to ‘Chinese Philosophy’:Preliminary Thoughts in a Postcolonial Linguistic Context”,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37(1),2005,pp.60-61.
〔14〕Mingdong Gu,Fusion of Critical Horizon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Poetics,Aesthetics,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1,pp.5-6.
〔15〕Parrick C.Hogan,and Lalita Pandit eds.,Literary Ind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Aesthetics,Colonialism,and Cul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6,8.
〔16〕张隆溪:《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序,第2-4页。
〔17〕参见顾明栋:《从“小文学”走向“大人文”——“后文学”时代文学新概念的理论探索》,《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
〔18〕Jonathan Culler,“Commentary”,New Literary History,6(1),1974,p.219.
〔19〕“镜”与“灯”是艾布拉姆斯(Abrams)以大脑思维的两种方式来类比摹仿再现和抒情表现的两种基本文学书写形式。参见M.H.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New York:Norton,1958,p.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