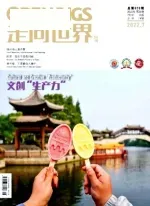两个幸运儿
2023-03-21佟予
佟予
每年的高考牵动着无数考生的心。某种意义上,它确实能改变人的命运,让人改头换面。
1979年,我走进了大学校门。原以为工作后参加的高考我会是班里的“大龄青年”,谁知比我年龄大的起码还有20个。
刚恢复高考时考生年龄参差不齐。当年我们班里最小的同学不到17岁,最大的已过30岁,而且那些“大龄”的真实年龄谁也不知道。同宿舍有位老大哥自报年龄26岁,怎么看也不像这个岁数,觉得40岁都不为过。后来有同学解释说,整日在地里干农活日头晒、秋风吹的人长得老相点也正常,村里好多人见了以为是爷爷辈的,一说年龄发现叫他们一声大叔都冤得慌。這位老大哥寡言少语,除了学习很少参与同学活动,更别说星期天凑钱外出打个牙祭之类的。当年学校礼堂放电影很便宜但老大哥从不去看,每次问他都说看电影头疼,但大家在宿舍里讨论电影时他听得比谁都入迷,还时不时追问几句。时间常了,大家私下都说他是“葛朗台”。
他最大的快乐是收到老家来信,但从不在教室里打开看。别的同学收到信件总忙不迭地打开,他每次都塞进口袋匆匆赶回宿舍。好几次我回宿舍就能看到他在看信,那认真的神态甚至都没听到我的脚步声。我猜想他或许有对象,因为他这个年纪在农村早该成家立业了,于是总有意无意地问他“是家里的信吗?”他总笑笑应答再无下文。也有淘气的同学跟他开玩笑,拿着来信说:“交待吧,是不是嫂子来信了?”他马上涨红了脸十分紧张地看着大家,然后乞求对方:“别胡闹,是俺爹娘的信。”“骗谁啊,撕开看看。”同学继续逗他,他脸色顿时由红变紫让人看了害怕。逗他的同学也就此罢手,小心地把信递给他,从此再无人敢跟他开这种玩笑。
毕业前的一个月的某个周末,不知谁动了那根神经,非要请老大哥去参加同学聚餐。老大哥一个劲地拒绝,但同学也扭上了,不达目的不罢休,并一再言明不让老大哥出份子钱。或许是盛情难却,或许是感到马上要各奔东西再难有机会凑一起,反正那天他去了而且喝得一塌糊涂,直到半夜才回宿舍。第二天一个爆炸性新闻在同学中悄然传开:老大哥早已结婚,还是3个孩子的父亲,那个所谓的二十多岁的入学年龄肯定注了水。
面对投来的异样目光,老大哥可能意识到酒后失言。他逐个向那晚在场的同学作揖,恳请大家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别去辅导员那儿报告。他还找到那些有可能知道消息的同学,支支吾吾却又不得不哀求手下留情。尽管不少人知道了实情也在议论纷纷,但最终无人去做“犹大”,辅导员那儿也没见动静。不知道是老大哥找过他还是他明知却佯装不知,反正直到毕业老大哥都安然无恙。后来,老大哥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并被分配到所在县最好的中学教语文,他在农村的媳妇和3个孩子也由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
从毕业分别再没见到老大哥,也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只是偶尔一次说到他,有知情的同学说他已经退休了,而那时我们同学中的绝大多数依然还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之上。
现在老大哥在做什么不得而知,也许儿孙满堂正享受着天伦之乐,也许和媳妇在自家小院里忙活着种种菜、栽栽花。无论怎样,有一点我相信,他一定会庆幸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会感激40多年前那次高考,感谢那张来之不易的文凭。因为有了它,他和他家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惠及后代。
说完老大哥,又想起另一位大姐,她是城市姑娘。
1977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母亲最要好的同学也是“闺蜜”——谭大姨来到我家。她带来了那个好消息:要恢复高考了!
在中学当教师的谭大姨跟母亲是女子中学的同学,关系非常铁。在我眼里她很“特别”,一是因为她的气质与众不同,爽朗中带着高雅;一是她住的地方有些“神秘”,当时市政府的好几位领导住在那一带。谭大姨的女儿,我们叫她姜姐,小提琴拉得很好。上世纪70年代,初中毕业后的姜姐曾去考过山东“五七艺校”,当时100多人报名只取4名,姜红过五关斩六将最后以第二名的成绩被确定录取,可到了开学仍没接到通知书。她一个人跑去了省城找到“五七艺校”,当时院领导告诉她:“我们专门开会研究过你的事,但很遗憾因为你父亲的问题,我们没法下决心。”姜姐懵了!父亲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姜姐又急忙返回青岛去父亲的单位问个究竟,答复莫衷一是。直到后来,她父亲的事才有了论断,被答复:“没人说你父亲有什么问题啊!”可当初就因为没有肯定的答复,断送了姜姐的艺术前程。
艺校去不了,倔强的姜姐决定上山下乡。家人很担忧她一个妙龄姑娘在贫穷落后的农村该如何度过。好在姜姐是个适应力很强的人,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她却跟男知青一样扛着撅头在田间泼辣地忙活,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娇惯”长大的城市女学生。后来姜姐加入了生产大队成立“铁姑娘”队,当时能进“铁姑娘”队的凤毛麟角,是件很让人羡慕的事,因为队员不仅要表现好、肯吃苦、能干,还要是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姜姐农闲时还会在田间地头用小提琴给拉《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红色歌曲老乡听,她小提琴拉得好很快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公社宣传队、县文化馆都来借调她去参加各种演出。那阵子姜姐又兴奋又累。兴奋是因为自己的才艺有了用武之地,累是因为演出后回到村里依然要下地干农活。一年后,大队党支部书记找姜姐谈话问她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姜姐不知怎么回答是好,眼泪“啪嗒啪嗒”落下来,书记听完姜姐含泪述说后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但姜姐并没因此灰心,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中去。在“铁姑娘”队里她是最能干的队员之一,抢修河堤时,黑灯瞎火不见亮光,男社员都犹豫不决,她二话不说“扑通”一下子就跳进浑浊的河水里;暴风雨来临前抢收小麦时,本来说好清晨5点集合,可不到4点她就叫上知青女队员来到田间挥着镰刀弯腰干起来,等其他人赶到时地里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大片。
3年后,有个政策让姜姐离开了条件艰苦的农村,顶替母亲到学校工作。姜姐兴奋极了,她很喜欢当老师,梦想着有一天像母亲一样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传授知识。然而分配工作时,又迎来一盆冷水——别的顶替者可以当老师,她只能到校办工厂,原因自然是“你懂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姜姐代一位生病的老师当了几天临时班主任,她的才能显露出来,校领导干脆装糊涂顺势让她继续干下去。那年市教育局选拔优秀教师到师范学校进修,姜姐满怀期望地写了申请,但第一轮审查就被淘汰,原因还是“你懂的”。伤心欲绝的姜姐感觉自己是大千世界里“多余的人”,她扑在妈妈怀里大声痛哭。无奈的谭大姨只能一边叹着气一边抚摸着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所以,当谭大姨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找母亲商量让不让姜姐去报考。“考啊,为什么不考,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母亲毫不犹豫地大声说道。
1979年,姜姐走进了山东师范大学院的校门,从一个学校工人变成了一名外语系的学生。尽管那年她已经过了23岁,不再是“妙龄”,但她的身上无处不散发着青春的光彩。她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学习空余时就拉上一段。那轻松、欢快、优雅、美妙的旋律犹如高天上飞逝的流云、大地上奔腾的河水,充满了激情和动感,仿佛是她幸运而激动的心声在飘洒、在流淌。大学毕业后,姜姐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圆了自己的梦想,新的人生也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