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妖史与捉妖记
——《西游记》导读(上)
2023-03-14施战军
■施战军
每到假期,电视总爱重播电视剧《西游记》。我们感觉得到,《西游记》在各艺术形式下的衍生能力都非常强,这在我国古典名著中是非常特殊的。无论是经典的1986版电视剧,还是电影《大话西游》、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更有我们这代人看过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一直到几年前的《大圣归来》等,都深入人心。无论是何种表现形式,我们如今对经典名著的诠释维度和深度相较于从前扩展了很多,可以将它各显神通地充分艺术化、形象化、动感化,可以从各自的阅历体验加以辨认和重识。《西游记》的主干故事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唐僧陈玄奘的锦襕袈裟在小说里格外醒目。在古典四大名著中,迄今为止,它的外文译本也是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的。
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初期,前辈们曾有过激烈的文化论争,即东西文化大论战。这场论战的阵地是《东方》杂志,当时的主笔杜亚泉提出了“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这一对概念。他认为西方是动的文明,我们东方是静的文明,是更高级的文明。当然,这不应该是“绝对论”。今天,我们就大致借助这个维度切入,来猜想、讨论《西游记》。
一、动静之辨:不安分的“打”“闹”与更高的“制动”力量
动静之辨,我觉得是研读《西游记》的第一组密码。
这部小说里天然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动”的。古典文学中“动”的元素也不少,《三国演义》《水浒传》明显都是“动”的,《红楼梦》是静的吗?也不能讲得这么绝对。那么,在接近大众的表达、叙述,以及学者所认为的“民族本质”之间,四大名著的呈现,有着看似微小、实则明显的差别。《西游记》这部作品,“动”的背后确实有“静”,这是一种虚静。就像《红楼梦》的热闹和“空”的关系一样,《西游记》也是整个小说以空、静做底色的,就像大圣名以“悟空”。这“空”和“静”,实际上源于先秦时代的老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特征。
相对于“静”而言,《西游记》的“动”体现得更加明显。首先是“闹”。“闹”在《西游记》里是个关键词。大闹地府、大闹天宫、大闹五庄观、大闹盘丝洞……有的是打闹,有的是吵闹,有的是玩闹,反正主题都是“闹”。其次是“打”:打上天庭,打翻老君炉,打破妖洞门,孙悟空的棍子、猪八戒的耙子说举起来就举起来,每个人好像都随时出手开打,唐僧一旦念咒比打还凶……另外,《西游记》还有很多元素中带着“动”的节奏。比如风——妖精出现的时候往往狂风大作;再如水——美猴王数次念诀入海欺负龙王,沙僧、白龙马从浪涛里出来,千辛万苦取来的经书被掀翻到水中等,都说明水是影响故事发展的重要“动象”。
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人物设置不可能都不安分。如来、菩萨等形象,就是对种种“动”的“制动”力量。他们镇定、自信,关键时刻能出来“制动”,但其实最难捉的妖精都是他们“放”出来的。这种“制动”因果运行的最高力量,决定了无论故事态势如何发展,怎么往前走、往后退,怎么摔打、塑形,纵使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静”就在于掌控的、恒定的某种力量。西天取经之路让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纵使孙悟空有七十二变,猪八戒有三十六变,这种发展着的、变化着的“动”,也始终是被“静”的力量所掌控的,只不过,“制动”也是一种“动”。而唐僧是动静之辨的“路由器”“变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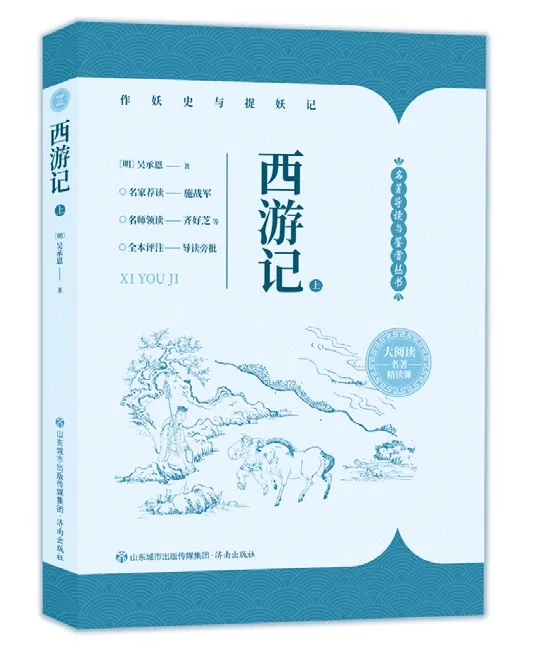
二、生死之辨:“杀生”与“护生”的冲突
第二组密码,更贴近文本自身,是生死之辨。
无论是唐僧、菩萨,还是“老祖”“老君”“古佛”,他们都是慈悲为怀的“护生”者,但小说中更多形象有着说杀人就杀人的“无底线”特性,因此“杀生”与“护生”就构成了矛盾。孙悟空在章回题目中被称为“心猿”,即使由猴子变成心猿,他依旧是个不稳定因素,没法确定他是否会听话。有这样的形象存在于身边,使唐僧一行的取经之路充满活力,但这个保护神又是个惹事精,也会随时带来大大小小的危机和事故。《西游记》对取经生活的设定是不顺的,甚至是动的、乱的、闹的,宗旨即在闹的情形下寻找恒定。把孙悟空取经之前和他成为斗战胜佛之后的部分对比阅读是非常有趣的,有深意存焉。
第十四回,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此时已经叫作两界山,这一座山的两个名字也很耐琢磨)下救了出来,上路时,突然窜出六个人来,分别叫“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即“六贼”。关于这“六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是从民间文化中总结得来的。巴金曾翻译了一本外国书叫《六人》,从国外六位著名人物的分析中展示了六条人生道路。虽然这跟我们中国文化追求“六根清净”不是一种路数,但都是训示为人之大道。西方成长小说成熟的年代当然比《西游记》晚多了,在《西游记》中,对主要“人物”心理结构、日常生活、规则结构的思考,就都包括在“六贼”出没之中了,中国古典文化确实了不起。这一回中,孙悟空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毫不犹豫抬手就把这六贼打死了,此刻唐僧才意识到,这泼猴是个杀人狂,于是顺理成章就有了观音菩萨送来的紧箍咒。孙猴子就成了有了管束的“心猿”。
这是悟空打了老虎穿上虎皮成为“行者”,踏上取经之路后正式展开的第一个故事,在小说中非常重要,相当于迈开了西游之旅修炼正果的第一步,由此也成就了这部标准的“成长小说”模式的关键环节。接下来所有的矛盾与冲突都是由此转折而生发出来的。“杀生”与“护生”之间的冲突,所有约束与自由,都建立于此。后来取经路上孙悟空起杀心、灭妖怪的时候,唐僧屡次念紧箍咒,这其中大都出于正确选择,但也有诸多误解。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故事之外还有叙事,情节下边还有情结,思考周遭还有思想,精彩背后更有精妙。像这样有着丰富的言外之意的书写,巨大吸引力和无尽生发力兼具的故事,才堪称经典作品。
三、妖佛之辨:“捉妖”也“作妖”
研读《西游记》的第三组密码,是理解初心和多面性的关系,也就是妖佛之辨。
人都有童心、初心,在长大的过程中,思维不断被成人世界修改,被各种各样的力量管束牵引着。按理说孙悟空岁数太大了,他自己也常常跟人显摆自己的“资深”,但是在人们的一般印象里,“猴子”永远都是“皮孩子”。
很多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标准是让孩子将来达到家长的程度就可以,也就是“你可以长大,但是长到像我为止,你也不可以成为自己,你必须成为我”。孙悟空走的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路,他的家长不只有唐僧,还有佛祖、菩萨,果然最后长大成为斗战胜佛,小说只好结束,无法再写下去。但结尾时有个细节很调皮。当他们最后修成了正果,孙悟空却又对唐僧道:“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儿咒》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这时候,孙悟空作为一个已经成了佛的尊者,说的还是猴话。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沉重的肉身”,也可以看成不变的初心。孙悟空为什么从始至终都可爱?是因为他的初心一直没有被摔坏、没有被粉碎,猴性还在。
孙悟空是在“群治”规训中成长,他作为大圣存在的时候,身上最让人无限向往的,就是自由。他学会七十二变,还有分身法、定身术,这些厉害的本事为他赢得了自由的本钱。后来,他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这个自傲到自恋的高手也不得不求人帮忙了,所谓的七十二变只能作为他战胜八十一难的工具,没人合作帮忙也办不成事。
这种个人自由与群体规约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始终都在面对的古老话题。孙悟空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虽然他以猴性为基本特征,但他要完成宏大使命的责任,要求他必须同时具有神性。这种猴性和神性之间的不断拉扯、推搡,让孙悟空身上有了“人味”,人性就是两者碰撞中出现的。因此,一个成功的形象,肯定不是单纯神性的化身,也不是某种单纯动物性的化身,而是两者之间碰撞化合的产物,我们暂且叫它人性。人性所有的优点、缺点,在孙悟空身上都是充分的,既“作妖”又“捉妖”,这样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学名著的经典形象中,完全可以位列前三甲,这也是《西游记》被誉为伟大的创作的重要原因。
在孙悟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西方成长小说更高明的另一种范例——如来给他的考核评价极高,是“全终全始”。而事实是,他长成以后依然在成长,是不结束的可持续成长。小说全篇就像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又像一个老式银镯子,镯子是有接口的,中间可以张开。小说为悟空的成长留出了缝隙,开辟了空间,使他没有完全成了定型的甚至走向固化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