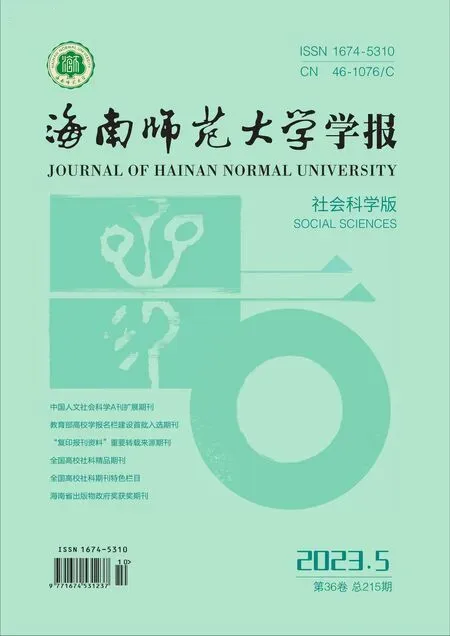红色文艺“现代性”的体制特征
2023-03-13宋剑华
宋剑华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体制化”既是红色文艺的本质属性,也是其“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现在学界对于“体制化”文艺存有一种偏见,认为这种文艺“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依照我们的文学常识,举凡经典都是出自于自由个体的精神创造”①刘勇:《“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体制化”在“极左”年代的确曾对文艺创作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彻底抹杀它作为一种保障机制的历史贡献和正面意义。因为文艺创作并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空间里所展开的精神活动,文艺工作者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自存在。如果一定要摆脱“体制”去强调绝对个人的“绝对自由”,那么“追求不同目的的自由人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②[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所以,“体制化”文艺是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其政治导向,去建构一种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体制”文化的受益者和真正主人。百年红色文艺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体制”文化的保障作用。
一、体制化与红色文艺的保障机制
“体制化”文艺的一大优势,就是对文艺生产者提供生存保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在教育部下面成立了一个“艺术局”,直接领导苏区辖地的文艺工作。除此之外,中央苏区还在瑞金创办了“工农剧社”和“蓝衫剧团学校”等文艺组织,在湘、赣、闽、粤、鄂等根据地广泛开展“俱乐部”与“列宁室”运动,建立了一套报刊杂志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发行系统,③《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之六)》(1931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并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和管理“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剧团等等的工作”的重要性。①《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决议案(节选)》,江西文化厅、福建文化厅合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不仅如此,苏区还在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文艺工作大力支持,甚至还派部队去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像湘鄂赣省委的“万铜丰剧团”,“全团有导演、琴师、演员共四十三人,”军分区不仅拨款3000 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还“成立一个直属红色警卫连,有枪七十余支”,陪同剧团到部队和农村去进行演出活动。②参见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比如,“1937—1948年,整个延安时期,共存在过至少75 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 大类”③王克明:《〈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而“延安时期的文艺家绝少有,甚至没有散兵游勇式的个体创作活动,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社团和组织”④高杰:《延安文艺运动中的社团组织及其流派风格》,任文主编:《延安时期的社团活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9年,第1页。。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工作者给予了很高的生活待遇,在当时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还投入大量资金出版刊物、进行戏曲公演、举办美术展览等活动,以确保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能够得到发表。延安时期,“每月竟有了近乎几十万字底文艺作品产生”⑤萧军:《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21页。,同时成立有十多家文艺团体,上演过大约300 多部剧目。因此,延安文艺的“体制化”实践,为新中国文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层面上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宣部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把关者,文化部和出版总局是文艺演出、文学出版的行政管理者,“文联”与“作协”是文艺创作的业务组织者,可以说新中国文艺的生产过程,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体制化”的优越性,首先是使数十万流散于民间的戏曲艺人,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在文化上逐渐脱盲、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生活上有了保障,就像老艺人马彦祥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艺人追求进步的热忱逐日高涨,学习已成为艺人自觉自愿的要求”⑥马彦祥:《1951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和存在的问题》,《人民戏剧》1951年第8期。。而文学作家也大都职业化,不仅挂靠在“作协”领取固定的工资,还可以依靠版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生活水准也远在普通民众之上。如果没有“体制化”所起到的保障性作用,新中国文艺绝不可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妄谈民国时期文化人的生活待遇,这是一个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荒谬之见。民国初期,的确有极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收入很高,像胡适、鲁迅、张恨水等都收入颇丰、衣食无忧。比如,老舍说他在青岛大学教书时,除了薪酬还有稿费,“我自己还保了寿险,以便一口气接不上来,子女们不至马上挨饿。此外每月我还能买几十元的书籍与杂志”⑦转引自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37页。。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像刘雪苇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叶紫病重无钱医治只能返乡等死,这才是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生活境况更是一落千丈,无论名气大小都只能是艰难地活着:老舍“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就靠着那不规则的稿费”,经常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但他还必须坚持写下去,“不写,全家喝西北风”。⑧胡絜青:《读书添新知 生活更灿烂》,胡絜青、舒乙:《散记老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26-127页。张恨水在陪都重庆照样陷入了生活困境,只能是哀叹“入蜀三年未作衣”“瓦盆久唱食无鱼”⑨张恨水:《浣溪纱(四阙)》(原载1940年4月26日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剪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为了一家老小能够填饱肚子,也是在靠倒卖布匹来维持生计。闻一多更是不得不替别人刻印章,尽量多赚点外快以补贴家用。
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延安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生活境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延安地区的物资匮乏,但中共却给予他们最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仅吃穿与中共高级干部同一标准,而且还有稿费和额外津贴。故尽管延安的生活艰苦,可他们却经常下馆子大吃二喝。仅以萧军为例,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远不如老舍、张恨水等人,可是当老舍为了生存到处去“蹭饭”、张恨水在贫困中哀叹“食无鱼”时,萧军却在延安过得十分安逸:“萧军那时很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不过他最爱吃的还是甲鱼,一只重约5 斤左右,一块钱一斤萧军也在所不惜。①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10-115页。日本反战同盟的小林清在延安时曾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人每个月的津贴都很低,“士兵一元五角;排连级三元;营团级四元;师级以上,包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五元”②[日]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88页。。因此,中共领导人的简朴生活同延安文化人的大肆挥霍,便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照。我查阅了1941 年的《萧军日记》,仅这一年就记载有他下馆子吃喝20 余次。例如,4 月13 日:“晚饭请罗峰全家和舒群夫妇、芬,在西北菜社晚餐,出乎意外,竟费去十七元多,他们真太贵了”③萧军:《萧军日记》上,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10 月3 日,“夜间在俱乐部内把十五元答周扬文章的钱用十一元和烽,群,张仃等喝酒了!”④萧军:《萧军日记》上,第303页。一顿饭便吃掉了一位中共领导人近3 个月的津贴,这恐怕是老舍和张恨水在重庆想也不敢想的奢侈生活。延安文化人之所以敢于高消费,一言蔽之,就是拜“体制化”所赐。因为萧军在延安时期并没有写多少文章,稿费很少,固定津贴也非常低,其主要经济来源还是靠边区政府的高额补贴。比如,他在1941 年12 月18 日的日记中便记载:“参议会送来300 元”⑤萧军:《萧军日记》上,第356页。。如果没有这种高额补贴,他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大肆挥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有了固定收入。戏曲艺人和文学作家不仅有了事业编制,每月可以领取高于普通民众的固定工资,而且演出有酬劳、创作有稿费和版税,完全摆脱了民国时期那种窘迫的生活状态。老舍就深有体会地说,解放后“我写出了不少的东西来,主要的是话剧剧本和通俗的宣传文艺小段子”,加上《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重印后的版税收入,“在精神上我得到尊重与鼓舞,在物质上我也得到照顾与报酬。写稿有稿费,出版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⑥老舍:《生活,学习,工作》(原载1954 年9 月20 日《北京日报》),《老舍全集》第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541页。1956 年,全国实行工资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艺工作者非常尊重,毛泽东的工资是500 元左右,但著名文艺家的工资待遇却远远高于这一标准:如梅兰芳月薪2100 元,周信芳月薪2000 元,俞振飞月薪2000 元,马连良月薪1800 元,张君秋月薪1500 元,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600 元。地方上的文艺工作者,工资待遇也普遍高于党政干部,像河北京昆剧团演员宋德珠月薪400 多元,青年演员安荣卿月薪300 多元。就连邯郸地区豫剧团的胡小凤、河北梆子剧院的裴艳玲等十五六岁的小演员,月薪有90 多元。⑦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83页。文艺工作者除了固定工资,还有剧场的演出收入。比如,马连良一场演出就要1000 元,彭真对此表示可以理解,他说马连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不能对他要求太高。⑧彭真:《对马连良不要要求太高》,《共产党员》2007年4月3日,第46页。
这一时期,作家的收入则更为可观。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文集》的版税收入是239 620 元,《茅盾文集》的版税收入是192 266 元,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的版税收入是107 400 元,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税收入是70 248 元,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的版税收入是58 000 元等等,而那时候中国人的月平均工资也只有40 元左右。“也就是说,一部小说倘若成为官方确定的‘经典’,或成了新时代作家的‘优秀作品’,那么,它的价值就是一个普通职工100 年的收入,甚至更多。”⑨张柠:《上世纪60年代作家的待遇》,《共产党员》2011年第8期。其他人像梁斌、刘知侠、吴强、曲波、杨沫、罗广斌等人,在当时都是10 万以上的文坛“富翁”。许多作家都用稿费或版税买下了房屋,如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在煤炭胡同买了一套房子,田间在后海附近买了一座小四合院。⑩阎纲:《作家与稿费》,《文史博览》2004年第10期。即便是刚刚出道不久的刘绍棠,稿酬也有18 000 元,他说自己把这些钱“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 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 元,相当于一个12 级干部的工资”①刘绍棠:《我是刘绍棠:刘绍棠自白》,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16-117页。。所以,郭小川就认为:“现在作家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是高出工人、农民甚至一般的工作干部的”②郭小川:《沉重的教训——1957年10月11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57年第28期。。孙犁说得更为直白:“我可以断定:在十年动乱时,有些作家和他们的家属,遭遇那样悲惨,是和他们得到的稿费多,有直接关系。”③孙犁:《谈稿费》,《远道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72页。尽管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文化人都曾受过迫害,但他们在“极左”年代的生活情况却超乎人们的想象。比如,陈白尘、张天翼、张光年等作家在“蹲牛棚”期间,他们经常在周末结伴去到东来顺“涮羊肉”“烤子鱼”、喝“大曲”,后来怕别人背后议论就把东西买回来在住处吃,其中包括有“火腿”“大排骨”“烤子鱼”“啤酒”“大曲”等美食美酒。④参见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9页;陈白尘:《牛棚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50页。
“体制化”不仅对于国家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关爱备至,对于那些个体化经营的民间艺人也是一视同仁,一方面,视他们为“祖国艺术的宝贵财富,是我国整个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在他们遭遇生活困境时,拨出巨款“帮助他们解决目前最紧迫的生活上的困难”,1956 年,文化部还做出了明确表态,力争“在今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和民间职业艺人基本上安排妥当”。⑤《文化部关于对民间职业艺术团体和民间职业艺人进行救济和安排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 年8 月4日,第954-955页。这一切都在说明,“体制化”是新中国文艺的根本保障。其实对于“体制化”文艺的诸多好处,文艺工作者都心照不宣、缄口不言,只不过由于“极左”思潮的心理阴影,使他们不愿意去承认罢了。然而,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感受去否定客观的历史真相。仅就“体制化”文艺而言,无论《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还是《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每一部红色经典的生产过程,从投入到产出都离不开“体制化”的保障功能。所以,“体制化”文艺应被纳入到纯粹的学术范畴中去加以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问题去横加指责。对此,我们应以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正确对待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
二、体制化与红色文艺的协调机制
“体制化”文艺的特殊功能,就是它具有“调动”与“整合”社会资源的协调能力。“体制”是一种系统化的组织结构,它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调配人力与财力,去共同打造文学艺术的经典作品。在百年红色文艺运动发展史上,从中央苏区到当下社会,这种协调机制一直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那些大型文艺作品的创作方面,“体制化”的协调能力要远大于“商业化”的金钱效应,因为“体制”可以参与文艺生产的全过程,这是“商业化”运行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从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系列电影如《大决战》,甚至包括北京亚运会和奥运会开幕式等超大型公益活动的文艺演出,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作为支撑和保障是很难完成的。所以,“体制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百年红色文艺的本质所在。
《白毛女》从歌剧到芭蕾舞剧的经典化过程,就是“体制化”文艺运作方式的成功范例。“白毛女”原是具有多种版本的民间传说,周扬却从中发现了它在革命启蒙方面的艺术价值。⑥参见任颖:《回忆王大化》,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于是,他决定让“鲁艺”来改编这一故事,并运用“鲁艺”院长的职权,调集“鲁艺”所有的优秀艺术人才,集中起来去共同创作:从文学系抽调贺敬之和丁毅写剧本,从音乐系抽调马可和张鲁等人搞音乐创作,从戏剧系抽调王滨、陈强、林白、王昆等人担任导演和演员,从美术系抽调师生来进行舞台背景设计和道具制作,可以说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几乎动用了“鲁艺”最好的艺术资源。贺敬之说《白毛女》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鲁艺”内部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合作,在剧本、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院上下的鼎力支持,“若不是集体力量的相互合作,《白毛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①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歌剧本《白毛女》,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第8-9页。《白毛女》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也是一种“体制化”运作。芭蕾舞剧《白毛女》最早是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科排练的一个毕业作品,后来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因此专门调集了上海文艺界的精英共同参与,目的就是要将其打造成一部经典作品。例如,导演是上海“人艺”的黄佐临;舞美设计是歌剧院的朱士场、“儿艺”的胡冠时、“人艺”的程漪芸等名家;音乐伴奏是上海“儿艺”和上影乐团;剧本唱词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杨永直创作;喜儿的唱词由上海歌剧院的朱逢博演唱;杨白劳的唱词由上海合唱团的简永和演唱;大春的唱词由上海电台广播合唱团的朱均雄演唱;全场的伴唱是上海广播乐团合唱队。由此不难看出,倘若没有“体制化”的高效运作以及众多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歌剧《白毛女》和芭蕾舞剧《白毛女》,也不可能成为一部艺术完美的红色经典。
谈到红色文艺的“体制化”运作,最令人震撼的还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 年7 月,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 周年国庆献礼,周恩来提议创作一部大型舞台节目,形象化地再现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并成立了一个以周扬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东方红》确定的表现形式,是把音乐、舞蹈、戏剧、诗歌、朗诵、美术结合为一体,向全世界去展现红色文艺的巨大魅力。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 个,革命歌曲39 首,诗朗诵18 段,不同的场景33 个,整台节目从排练到演出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国庆期间上演时,“现场的那种氛围是其他观看形式无法企及的,那种热烈、雄壮、沸腾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狂热和沉醉”②黄卫星:《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文化研究》第11辑,第187页。。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国家体制的强有力保障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为了创作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精品,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担任总导演,中共中央宣传部坐镇指挥,一共调集了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文工团等七十余个文艺单位的3500 多名演员,仅合唱队员就有1000 多人。为了在天安门广场那一幕能够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时代主题,周恩来还专门派飞机从新疆等地接运少数民族演员。③袁成亮:《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记》,《文史月刊》2004年第11期。1964 年10 月15 日,周恩来陪同日本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的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带领他们到后台去参观。当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得知这台节目是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完成的,都非常惊讶地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④南山:《总策划、总导演——周恩来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党史文汇》1997年第5期。。实际上,日本艺术家不仅是在向周恩来个人表示敬意,更是在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敬意。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体制下,国家总理才会亲力亲为,出面去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否则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像《东方红》这样的艺术奇迹。对于这一点,当年参加过《东方红》创作或演出的艺术家们,更是记忆犹新、感同身受,他们说:“《东方红》是部不朽的经典,是特定历史时期,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下打造出的艺术经典。只有那个时代的中国能够出现《东方红》,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产生《东方红》”⑤黄卫星、孟兆祥:《一位军队艺术家眼中的周总理——基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一次访谈》,《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因为“像这么重大的题材,这么大的规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没有领导同志的亲自参加是不可想象的”⑥陈亚丁:《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人民音乐》1964年第Z2期。,而这正是新中国文化自信与体制自信的一种表现。作为“20 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情感记忆。比如,著名音乐家时乐濛就曾这样认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一座丰碑,其规模之宏大,技术之精湛,影响之深远,中国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一部音乐舞蹈作品能与之相媲美!自她诞生以来的28 年间,尽管有人低毁过她,贬低过她,但是她的舞,她的歌,却从来没有一天在中国老百姓中消失过,绝响过”⑦熊华源:《周恩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东方红》被拍成电影之后,还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大唱革命歌曲的社会热潮,像《农友歌》《情深意长》《赞歌》等歌曲,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中传唱,至今仍然热度不减。
“体制化”文艺的高效运作,在革命军事历史题材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1952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故事片《南征北战》时,陈毅、粟裕等军委领导亲自过问剧本的创作情况,并向主创人员讲解当年华东战场的真实情境,中央军委还专门调派了1000 多名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坦克、火炮、枪支和服装等供拍摄使用。当时参加拍摄的解放军指战员,都是刚刚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战士,他们具有极高的思想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每一个战斗动作都表演得十分到位,确保了整部影片反映战争真实性的艺术质量。以至于后人不无感叹地说,电影《南征北战》所表现的真实程度,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标杆’”①何倩、张凡:《回望波澜壮阔的战争岁月——重温红色经典影片〈南征北战〉》,《新疆艺术》2021年第6期。。1986 至199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史诗性电影故事片《大决战》三部曲(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则是“体制化”文艺成功运作的又一典范。
1985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明确指出,一定要“写三大战役,我看是不是不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分开写,而是要把三个战役连起来,一气呵成地写出来。只有把三大战役的内在联系写出来,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战略思想和他运筹帷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宏大气魄”②转引自明振江:《中国银幕上的战争史诗——回忆电影〈大决战〉的创作历程》,《炎黄春秋》2021年第8期。。1986 年1 月,杨尚昆把胡耀邦的谈话批转给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然后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文,成立了一个由解放军三总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五个大军区、十个省市领导同志组成的《大决战》影片摄制领导小组,这无疑是一种大规模“体制化”文艺的运作方式。剧本创作小组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徐怀中担任组长,成员有史超、王军和李平等人。他们首先是熟悉军史和查阅三大战役的有关文献,并多次登门请教参加过三大战役的老同志,甚至还虚心听取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黄维、侯镜如等人的意见和建议。从1986 年1 月到1988 年末,《大决战》剧本在3 年时间里经过了8 次修改,最终由总政治部审查通过,并开始拍摄。关于《大决战》的资金问题,杨尚昆公开表态说,为了“拍三大战役,要舍得花钱,可能要一个亿。就是一个亿,也该花”,他还语重心长地嘱托全体主创人员:“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拜托,拜托,再拜托了!”③转引自萧穆:《战争史诗〈大决战〉的操作和拍摄》,《百年潮》2014年第6期。《大决战》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电影故事片,由于当年还没有数字特效合成技术,故整部影片在技术层面上,只能是依靠真人实景进行拍摄。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战场情景,摄制人员从部队到群众演员,他们先后在东北、西北、中原、淮海等广阔的空间地域里,战严寒、斗酷暑,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将其拍摄成了一部代表中国电影摄制最高水平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像这种大规模的拍摄场面,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难以复制的。④梁晓雯:《揭秘经典电影〈大决战〉:不可复制的军事巨片》(2011 年6 月8 日),https://ent. sina. com. cn/m/c/2011-06-08/02193327897.shtml.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一组数字:“全国共有14 个省市自治区的50 几个市区县为《大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拍摄条件;5 个大军区所属的陆海空军以及武警部队,有25 个军级单位、33 个独立师团单位出动了13 万余名干部、战士参加了拍摄工作。参加拍摄的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累计共达345 万余人;此外,还动用了大量的飞机、舰艇、坦克、火炮、车辆等大型军事装备。其中,有许多重要场景是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和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拍摄的。应该说,《大决战》的拍摄,是在全国全军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⑤转引自萧穆:《战争史诗〈大决战〉的操作和拍摄》,《百年潮》2014年第6期。在道具使用方面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烟火:设置炸弹3500个,梯恩梯炸药160 吨,黑白烟幕70 吨,服装:解放军棉服5823 套,国民党军棉服4331 套,日式钢盔700顶,美式钢盔667 顶,牛皮美式腰带2500 条,青天白日小帽徽6699 个,解放军胸章6000 个。……车辆:美式、日式装甲车20 辆,可炸汽车100 辆,真坦克50 辆。枪弹:空炮弹170 多万发,真炮弹1 万多发,假枪支6000 支,效果枪5 支,刺刀6000 把。”⑥胡国达:《电影〈大决战〉知多少》,《中国民兵》1991年第12期。在这些具体数字的背后,反映的正是“体制化”文艺的优越性。
“体制化”不仅是新中国“十七年”文艺创作的主要保障,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强大支撑。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为了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先后动用了部队演员6900 人、地方演员10 829 人,让全世界数十亿人领略了红色中国的艺术魅力。仅仅是开幕式的保安工作,国家就动用了“10 万警力和3 万多的部队士兵,加上北京市本身已有的25 万保安员和开幕式现场的安防人员,总的人数差不多40 万左右”①陈保华:《奥运安保是2008北京奥运的第一块金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背后故事》,《中关村》2008年第9期。。因此,当西方媒体在赞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历史上“最美的奥运会开幕式”时,他们当然懂得这种“体制化”的运作程序,只能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具有可操作性,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商业化运作是根本完不成的一项艰巨任务。
三、体制化与红色文艺的生产机制
“体制化”文艺的基本特点,就是集体化创作的生产机制。因为“协调”强调共同参与性,故群策群力便成为了红色文艺的明显特征。集体创作是红色文艺的普遍现象,它与自身队伍的构成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无论中央苏区还是新中国“十七年”,红色文艺创作队伍的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如果只凭借低文化水准的个体创作,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的艺术精品。因此,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去创作同一文艺作品,这无疑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红色文艺的集体创作,可以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凑戏”现象,一种是署名作者背后的“潜作者”现象。
“凑戏”现象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的业余创作,像《庐山雪》《工作在箱子里》《东洋人照相》《扩大红军》等剧目,都是由红军将士们在战斗间隙中,坐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凑”出来的。而延安时期的许多艺术作品,像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小放牛》等等,也都是由“鲁艺”学员集体“凑”出来的。李波在回忆当年创作《兄妹开荒》时曾说:“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更没有什么形式约束,思想特别活跃。一开始就七嘴八舌地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结构起来。觉得这儿用唱好,就唱;觉得这儿用说好,就说。一个不到20 分钟的小节目,有说有唱,有舞,还有快板。”②李波:《往事的追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83页。歌剧《白毛女》也是由“鲁艺”人在一起“凑”出来的,贺敬之本人坦承:“仅就剧本来说,它所作为依据的原来的民间传奇故事,已经是多少人的‘大’集体创作了。而形成剧本时,它又经过多少人的研究,批评和补充,间接或直接地帮助与参加了剧作者的工作”③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歌剧本《白毛女》,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第8-9页。。陈强则回忆说,《白毛女》的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先把每场戏拉出提纲,再分场细谈,以王滨主说,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我们大家补充,贺敬之把它记下来再文字化、歌词化,写成一场就找人谱一场曲,一场一场就这么写下来了”④陆华整理:《张庚等四同志关于歌剧〈白毛女〉创作过程答张拓同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张庚也说,《白毛女》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作品,在排演过程“大家热心地提意见,每排一段,每支曲子,都有各种不同的讨论”⑤张庚:《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创作演出》,《新文化史料》1995年第2期。。除了“鲁艺”的主创人员外,“院内的首长、教员、同学和勤杂人员,以至附近的老百姓都对这个创作表示极大的关心,并且都热情地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可以说这个作品自始至终是在大家的关切下,以集体的力量完成的”⑥马可:《〈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6期。。延安文艺集体化的创作倾向,很快便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普及推广,像《穷人乐》《繁昌之战》《围困蒲阁寨》《老乡上战场》等作品,都是抗日根据地集体创作的经典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戏改”的所有成果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特点。现代“戏改”的真实意图,源自于毛泽东本人对于民族传统艺术的忧患意识。他在同文艺工作者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说:“为什么要让你们演现代戏呢?因为爱看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观众都快不在这个地球上了,你们要为将来的青年服务,青年人是肯定爱看现代戏的,所以让你们演现代戏。”⑦和宝堂:《自成一派:赵燕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1-222页。因此,在现代“戏改”中,集体创作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之所以能够成功问世,是因为前有电影《自由后来人》、后有沪剧《红灯记》为它铺路,经过电影剧和沪剧的早期创作,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故翁偶虹和阿甲改编起来就得心应手了。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创作过程中,不仅众多京剧艺术家纷纷献计献策,而且周恩来对杨子荣的唱词和唱腔,也提出过具体的修改意见。剧中“小分队”骑马、滑雪的场面,“深山问苦”和小常宝这一人物,也是根据贺龙、刘志坚等人的意见后来添加上去的。其他像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作品,几乎都是由集体智慧凝聚而成的艺术精品。①张雅心口述、画儿整理:《离样板戏最近的人》,《中国摄影家》2007年第12期。
“潜作者”现象是新中国“十七年”小说创作的一大奇观,我们不妨也将其视为“凑戏”现象的文学翻版。“潜作者”是指作者的初稿还达不到出版标准,只好由编辑们亲自去动手对其进行加工或修改。几乎所有的文学编辑都在感叹,做一个责任编辑非常之“难”,他们“对于一部作品的加工是使用手术刀,就是去掉多余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也是去腐生肌,编辑要给作品输血,又要植皮。有些书就是贫血,有的地方需要修饰,需要植皮,还有的地方需要针灸。”②钱振文:《〈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所以,每一位编辑就是要“把自己的事业融化到别人的事业中去,甘心做文化走廊中一颗铺路石”。③张羽:《我的编辑和写作生涯——指1983年》,《张羽文存》下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806页。新中国早期的红色作家,虽然他们都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但是文化程度却都很低,比如曲波只读过小学,陈登科只读过私塾,故他们作品的初稿都十分粗糙,距离出版标准还相差很远。罗广斌等人虽然曾读过大学,可他们缺乏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同样靠责任编辑倾力相助,否则小说《红岩》也难以问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十七年”所有的“红色经典”,没有一部是由署名作者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其背后都有一个“潜作者”的影子存在。
小说《红岩》原稿有80 万字,责任编辑张羽读后,觉得题材不错,但却布局零乱、结构松散,写得满纸都是血腥味。为了使这部作品能够顺利出版,1961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罗广斌、杨益言请到北京进行修改,先是由责任编辑王维玲和张羽等人在小说的“结构和布局”“开头和收场”“暴露和歌颂”“英雄群像”“江姐和许云峰”等几大方面,都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然后,再由张羽同罗、杨二人一起进行修改:杨益言改第一遍,罗广斌改第二遍,张羽改第三遍,直到12 月9 日才最后定稿。据张羽本人的编辑记录,小说《红岩》经过了几次大修改后,从80 万字压缩到40 多万字,如第四稿总共删掉了33 000 字,增补了11 000 字;第五稿删掉了20 600 字,增补了40 000 字等等。张羽说,在小说《红岩》里,有10 万字是由他写的,不过,1960 年代,团中央经过核查,得出的结论是两万多字。即便是两万多字,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因此,罗广斌在60 年代多次对人讲,张羽是《红岩》这部小说不具名的作者。”④钱振文:《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陈登科的小说《风雷》也是如此。这部小说的初名为《寻父记》,讲述主人公祝永康在解放以后到淮海故地去寻找救命恩人的故事。为了使这部作品能够顺利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样约了陈登科和责任编辑一道对作品做过两次大修改。第一次是江晓天、张羽二人同陈登科在北京西山,用了一周的时间对作品“从主题思想到结构布局,人物描写,逐人分析,逐章研究”⑤黄伊:《张羽的编辑生涯》,本社编:《无名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后来,江晓天又同陈登科一起进行修改。江晓天自己回忆说:“作为一个编辑,《风雷》在我处理过的长篇小说稿子当中,是花费时间最长、精力用得最多、最为精心谨慎的……40 多万字的稿子,大动起来,可不是容易的。登科找来耿龙祥同志给他当助手,在炒豆胡同招待所住了下来。我们采取流水作业,交错进行。我每看完三五章,就送回给他,谈谈具体意见,出点主意让他进一步修改补充。登科受演义、章回小说影响,分章不分节,叙事、状物、抒情、议论、对话,一股脑儿写下来,我帮他顺顺理理,把层次、眉目分清。有的章节,改动多些,就请他看后让小耿重抄一遍。”⑥江晓天:《〈风雷〉的旋风》,《江晓天近作选》,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5-68页。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用了8 个月的时间,作者与编辑才终于一起把小说《风雷》修改完毕。
与《红岩》和《风雷》相比较,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对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所付出的辛苦劳动,就更能说明“潜作者”的存在价值了。曲波把书稿刚送到出版社时,用龙世辉的话讲就是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稿纸还大小不一。他起初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可仔细一读,又被其中的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龙世辉认为这部作品虽然文字粗糙,但如果加以修改一定能够成为一部优秀作品。于是,他便把曲波约到出版社,和曲波一道商量修改事宜。但曲波自己修改了一个月后,却怎么也达不到要求。曲波“自谦地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改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恐难达到要求,只好委托编辑部全权处理。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老龙同志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工作的责任心,毅然接受了作者的委托。老龙回忆说:‘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我的浑身解数都使上了!’”⑦参见黄伊:《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介绍老编辑龙世辉》,本社编:《无名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136页。龙世辉用了三个月时间,对作品逐字逐句地修改了30 多万字,就连作品名称也从《林海雪原荡寇记》改成了《林海雪原》,并且作品中有许多内容也都是他添加上去的,比如小白鸽白茹这一人物,曲波的原稿中是没有的。龙世辉设计这一艺术形象,既是要用鸽子去象征和平,以表达革命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的思想主题;又可以用小白鸽美丽活泼的人格魅力,去冲淡残酷战争的紧张气氛,增强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和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曲波为了表达自己对于龙世辉的感恩之意,特地送给龙世辉一本精装本《林海雪原》,并在扉页上深情地写道:“在英雄们事迹的基础上,加了您和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友谊和它一起诞生”①黄伊:《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介绍老编辑龙世辉》,本社编:《无名集》,第136页。。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责任编辑这些“潜作者”的无私贡献,又哪里会有“十七年”“红色经典”的辉煌成就呢?
现在学界都把注重“人”的价值,视为20 世纪世界文艺的现代性特征,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体制化”文艺的显著的特点,同样也是在集中凸显“人”的价值——只不过它的关注重点不是个人的存在价值,而是人民大众这一社会群体的生存权与幸福感。因为这种文艺体制“有着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的特点,以组织方式通过挤压社会空间不断把文艺纳入体制内,在意识形态上张扬人民美学的价值诉求,以合力建构了‘人民文艺’及其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所追求的人民性,以艺术的人民性应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人民审美创造的追求,形成了“十七年”时期文艺审美的崇高风格”②范玉刚:《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东岳论丛》2017年第10期。,所以,“以人民为本位”的红色文艺,恰恰体现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文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