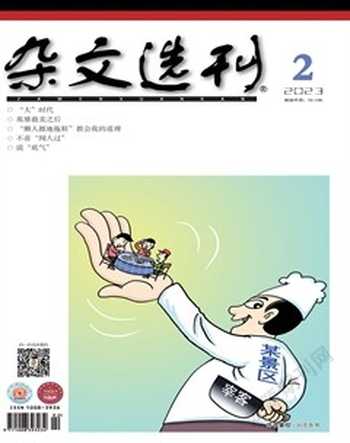请把我的声音还给我
2023-03-13南桥
南桥
最近在看兩本毫不搭界的书,可是不知道怎么想到了一块儿去。一本书是肯塔基一位地方作家的家族回忆录。这个作家津津有味地描写她祖辈多少代生活在肯塔基东部的一些趣事,之所以觉得有趣,是因为这是个普通家族既不是望族,也不是名门,可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如何在时代的变迁中跌宕起伏,才是让人回味的地方,就好比余华的《活着》。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是一个以前被我称为“黑三角”的地方,当地有人称之为“黑洞”。怎么叫黑洞呢?因为人若是生于此地,日后哪怕跑出去,最终还会被“吸”回去,因为离不开那里的山山水水和淳朴而有趣的民风。当地的人,基本上自得其乐,好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似的。
另外一本书是一位美国作家和一位苏丹难民阿恰克·邓合写的一部阿恰克·邓的传记,《什么是什么》(What is the What)。这个苏丹难民在自己的传记中,坦诚而诙谐地描述了他在苏丹以及非洲其他难民营的经历,还有后来到美国的遭遇。有一些经历,平时我们见到听到,可能颇为不屑,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或许会觉得难为情,太土,太俗,不想说,可是被他们两个一写,突然觉得妙趣横生。
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是作者都找到了各自的声音,从而能够自得其乐,津津有味地描述各自的遭遇和环境。社会学里有个说法,叫“给声音”。有了声音就有了力量,就有了归属,不然一切都是虚无的,都活在影子中,甚至干脆就是隐形的。一些群体,一些地域是没有声音的,有的是自己放弃的,有的是被世界的繁华给淹没的。
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声音,那么在表达的时候、消费的时候就容易走向同质化。回老家,看到街道边的墙上有和央视同样的产品广告,就气不打一处来。赵树理式的“山药蛋”还有没有呢?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会知道有些“进步”,不过是自我的丧失呢?对于一个地域的独特性没有足够关注,若这个地域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精神,就会陷入自卑,到最后像贾樟柯好多电影里反映的那样找不着北。一些小地方已经找不到自我,基本上是跟小城市学,小城市跟大城市学,大城市跟上海北京学,搞到最后,跑到偏远的地方,也会看到很多对那些所谓榜样的拙劣模仿。这可能和大众传媒也有关系,尤其是一些电视台,通过节目,广告,潜移默化地告诉人们它欣赏什么、爱好什么、同情什么、鄙视什么,不知不觉中将一些扭曲的好恶播种了下去,老少皆种。真该发明一种过滤软件,过滤这样的电视节目。
各地其实都有一个人文的富矿。这未必是檀香扇、文房四宝、京剧昆曲之类的国粹,而是对自己民俗的认可和赏识,是一种对自己所处生活的自得其乐。有的人很土,但是他很超前。有的人很时髦,其实他不过是一老土,世界它就是这么辩证。有时候有人会向我问起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可是我一说,他们反没了兴趣。我家孩子在学校,很多作业我看都很乡土。比如上学期,老师在教室里放了一个用来孵小鸡的保育箱,在里头放了二十几个鸡蛋,小孩天天观察,看鸡蛋是怎么变成小鸡的。还有一只小鸡掉下来,差点儿摔死,孩子们都哭了,后来居然活过来了。孩子们天天观察,还写笔记啥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可是这不是我们当初在农村接受的教育吗?
如果这些还不够东拉西扯的话,我索性再讲个美国律师的故事:
有个律师去乡下打猎,“砰”一枪,一只鸟掉下来了,掉到了农民的地里。农民拿走了,律师去索要,农民说:“掉到我地里,我就有权不给你。”律师说:“我是律师,信不信我把你告得倾家荡产,不要说鸟我能拿到手,就是你这地,我也能给夺过来。”农民说:“在你们地盘上这话我信。不过入乡随俗,在我们这里,我们遇到什么纠纷,不是这么解决的。”律师问:“是怎么解决的?”农民说:“大家轮流踢,每人每回踢对方三脚,踢到最后谁受不了谁认输。你先来吧。”
律师想,也不知道这踢是真是假,让他先来好了,轮到我,加倍奉还便是。于是他让老农先踢。老农便开始踢了起来,第一脚,踢到了律师裆部,律师一下子就趴下了;第二脚,踢到了律师头部,律师就如同被鲁智深暴打的镇关西,眼前全是红红绿绿的星星;第三脚,踢到了律师的肚子,律师差点儿把三年前吃的东西都吐出来。律师勃然大怒,心想,轮到我你死定了。于是他叫老农准备好。老农说:“你赢了,鸟你拿走。”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有的比赛,或许你像是赢了,却赢得很惨。
【选自《你该懂些世故再老呀》】
●江苏南京 王世全荐
插图 / 争夺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