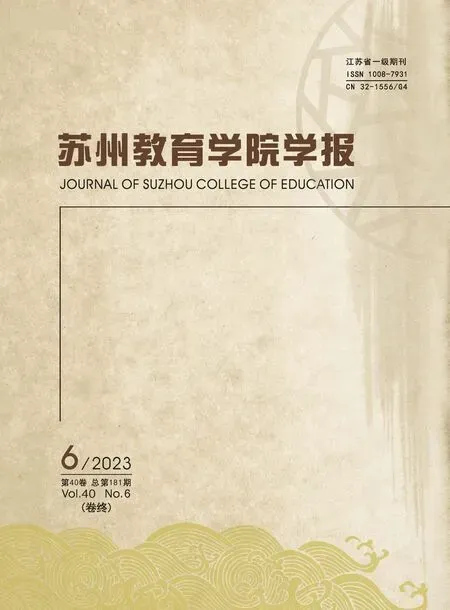从向恺然看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评韩倚松《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2023-03-12李瑞翾朱全定
李瑞翾,朱全定
(太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体量庞大、受众甚多的通俗小说走入了学者们的视野,范伯群先生提出的“文学双翼”发展之论,如今也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民国时期的通俗文学辉煌一时,其中曾经引领民国时期武侠之风的《江湖奇侠传》及其作者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享有“现代武侠小说鼻祖”之名的向恺然为何获此殊荣,引起了美国华盛顿大学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教授的注意。韩倚松致力于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研究,为探索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之源,他将目光投向了平江不肖生。2019年,其著作《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The Unworthy Scholar from Pingjiang:Republican-Era Martial Arts Fiction)[1]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①本文所引外文文献皆为作者自译,下文同,不另注。一书,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评价道:“韩倚松是武侠小说领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将向恺然置于民国这个更广大的文化政治版图中,探索武侠小说体裁的复杂性。本书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坛上被忽视的研究角落作出‘极富价值的’贡献。”②John Christopher Hamm:The Unworthy Scholar from Pingjiang: Republican-Era Martial Arts Fiction,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 2019,封底。在这本专著中,韩倚松以小见大,第一章呈现了平江不肖生的生平与所处历史背景;第二、三、四章观照武侠小说的本质、内容和市场表现形式,旁征博引,论证精彩;第五、六章以《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为例,对照前三章的小说理论成果,分析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作品特色,主要侧重于叙事内容和作品结构框架;最后一章将作品中表现出的中国现代性置于世界现代性的经纬中进行观照。本书与2013 年出版的《平江不肖生研究专辑》[2]相比,研究路径由一人设计完成,又增添了许多2013 年后有关平江不肖生的研究成果,故论证更具整体性,研究视角也更开阔。韩倚松用西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全面立体地分析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对作品的研究也结合叙事学、文体学和诸多社会商业因素,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在第二章中,韩倚松分析了平江不肖生如何看待写作、如何进行有效的写作实践,从而展现出前现代小说的一些共性特点。韩倚松从短篇故事《三只猴儿的故事》中的一段作者自述里,提炼出平江不肖生对小说的本质、目的和作用的理解—在小说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作者兼叙述者的角色、记录与传播的作用、娱乐的目的和对奇的痴迷这四个方面。[1]42平江不肖生的笔下汇集了众多趣事,作者的声音在叙事时若隐若现,引导读者转换视点视角,进行思考,这是在小说转型时期作者对传统说书人身份的转化和顺应读者阅读习惯的折中之选。而平江不肖生的创作从最初的文言短篇转变到后来的白话长篇叙事,表现出作者顺应文坛潮流的能力,这也是其作品成功出版的保障。
第三章将小说的范畴缩小至武侠这个文类,韩倚松以有关武侠小说文类发展的翔实史料,分析了平江不肖生给武侠小说发展带来的活力。尽管在轰轰烈烈的“小说革命”中,武侠小说并不是被推荐的“新”题材,但它却在这样的背景中实现了复兴。1905 年,《新小说》的“小说丛话”栏目提出了“武侠小说”这一说法;1916 年,由技击类故事辑成的《文言故事集》出版,武侠小说这一概念得以形成。然而,武侠小说这一文类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形态,直到沈知方以敏锐的市场嗅觉邀请平江不肖生写书后,武侠小说才形成了更稳定、更具辨识度且适销的文类特征。韩倚松通过还原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的激烈竞争论证了以上观点。世界书局发行的《侦探世界》与大东书局发行的《半月》的栏目构成十分接近,在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争夺市场时,世界书局将侦探小说视为一个重要战场,它对构建小说流派形象具有极强的“造星”能力。世界书局在逐渐形成期刊规模后,又将这种成熟的模式复制到《红杂志》《红玫瑰》的内容布局中。汤哲声曾言:“流行小说的创作与期刊的文学定位是互为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创作作品不断地强化期刊的特色,另一方面期刊的特色也制约着创作作品的价值取向。”[3]105不过韩倚松通过对比发现,在武侠小说领域,世界书局拔得头筹,其旗舰杂志《红杂志》《红玫瑰》率先设置了武侠小说的评论、赏析栏目。此后,读者和刊物的互动增多,无形中强化了杂志社对市场、读者的引导。此外,世界书局的另一高明之举便是捆绑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来吸引市场关注,此举不仅顺应了当时阅读市场上社会言情类小说为主、其他文类小说较弱的情况,也借用了侦探小说业已形成的成熟品质,使特定文类与特定作者联系起来,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出版之后,再加上电影市场的推动,这种捆绑的优势愈发明显。汤哲声认为:“此时武侠小说的创作如此之热,这里面有商业的炒作,更主要的是武侠小说开始展示出了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读者。”[3]85《江湖奇侠传》为何成为当时武侠小说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第五章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第四章从文体角度阐述武侠小说发展的市场环境。韩倚松认为,世界书局突出了章回体小说的特征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生产的特定语境之间的协同性,换言之,将章回体连载小说形式认定为特定的媒介形式并无不妥。而为何章回体被选中,韩倚松从这一文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脉络说起,直到20 世纪初,文坛将之确立为一种中国小说的类型。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知识分子推崇的短篇小说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有所发展,不过,作家、评论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有所不同,作家认为短篇小说是“新”的,由西方词汇“fiction”翻译而来,而编辑只是以篇幅长短对小说进行分类。长篇小说始终与“旧”文化捆绑在一起,尽管如此,通俗文学更受市场欢迎,长篇小说在短暂的短篇小说热潮过后再次占据市场。长篇小说的发展离不开章回体,韩倚松参考了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对中国连载出版物的研究成果,认为杂志将文本结构与连载形式联系起来不是自然的演变过程,而是编辑选择的结果。[1]100编辑对连载的长篇小说进行单独的页码设计,以区别于同一杂志上刊发的其他作品,此外,出版社又通过增加插图等小设计使章回体小说与杂志连载行为实现完美契合。在本章中,韩倚松对比了世界书局旗下以武侠小说为特色的《红杂志》《红玫瑰》和其他出版社的杂志,旁征博引地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使读者穿越回那个繁荣的市民阅读市场,尽情纵览当时出版社激烈竞争的景象。韩倚松从《新歇浦潮》看到世界书局刊登长篇连载小说的规律性,再深入比较《红杂志》和《红玫瑰》对平江不肖生的作品《江湖奇侠传》的刊登形式的变化,从而发现世界书局的长篇小说连载规律具有前后连贯性。自《江湖奇侠传》停载后,接棒作品姚民哀的《龙驹走血记》在出版形式上有了少许变动,但上述的连载规律依旧是杂志一以贯之的标志。韩倚松又将《红玫瑰》与其他杂志刊发姚民哀作品的出版形式进行对比,发现世界书局实为有意为之,意图将《红杂志》和《红玫瑰》构建成出版长篇武侠小说的标杆,从而引导此类小说的创作范式的建构。通过对比,韩倚松发现出版社编辑对作者创作风格和市场接受具有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章回体小说被改造为更适合杂志连载的形式后,出版社将杂志上连载过的小说直接编订成集,推出流行小说的全册书,进行2 次出版,无形中与连载文本相辅相成,使文学市场热闹非凡。
第五章着重分析了《江湖奇侠传》的奇幻魔力。《江湖奇侠传》遭遇了读者处于两个极端的反馈,而争论的核心便是向恺然以“奇”为著述纲领。那么,奇的核心是什么?奇又为何备受争议?韩倚松从电影《火烧红莲寺》谈起,在那个提倡理性、反对迷信的时代,影片中颇具迷信色彩的故事情节使其遭到当局的强烈制裁,韩倚松又结合直接描写迷信的《江湖怪异传》和平江不肖生的其他短篇小说对迷信的态度,观察当代社会中的非正常精神。作为前现代小说的核心的“奇”,旧式小说十分适合表现这一议题。平江不肖生写小说的关键,不在于他大胆陈述自己对迷信的看法,而在于其文本把小说阐释作为认知世界的基础方式。韩倚松认为,平江不肖生对小说诗学要素重新进行微妙的定位,使读者在接受的同时存疑,因此更容易受到抨击。韩倚松又以书中主要人物为例,对平江不肖生所写的故事与赵苕狂续写的情节进行比较,分析《江湖奇侠传》之多重奇态,从柳迟、蓝法师和刺马事件分析作者的叙事方法、写作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意义。在作者兼叙事者的视角下,这些故事形成了复杂、多层次的嵌套结构,表现出的奇不仅各具特色,还有一些相似性。柳迟的故事之奇在于它引出了小说发展的江湖环境,即不为人熟悉的边缘化的世界,这里的奇表现在与儒学仕途截然相反的求道、学“剑术”、成“剑仙”的人生追求,以及与血缘社会相对的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此引出该小说的另一个核心议题—传承。蓝法师的故事表现的奇在于边缘社会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此外还有动物、性与欲、超自然现象等,它们看似无关,却在作者的笔下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圈。此外,在传承问题方面,卢瑞和柳迟对血缘传承的不同反应与方绍德招徒传本事的对比,可见两种传承体系之间的矛盾。而刺马事件的奇则在于法外之徒的兄弟情谊,借此故事表现出小说传播的重要目的,即维护绝对的历史性。而赵苕狂所续写的章回的故事结构更加紧凑,内容增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性话题,赵苕狂运用的寓言写法实则是对小说历史性的破坏。
第六章聚焦《近代侠义英雄传》表现的武侠与现代性的相遇。自李小龙扮演陈真演绎《精武门》后,中国武侠电影开始走入西方观众的视野。但是,以霍元甲为主角的武侠电影却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叙事侧重有所不同,电影侧重于民族情绪引发的复仇心理,而小说则不然。韩倚松认为,小说中霍元甲并没能与外国强人真正进行武术较量,这更接近历史。在此前提下,韩倚松从霍元甲与现代性的相遇这一主题入手,研究小说的主题和结构以及平江不肖生对长篇小说创作结构的看法。现代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都市生活中,韩倚松从《留东外史》的东京到《近代侠义英雄传》的上海,关注两地与中国人有复杂关系的日本人,分析中国人在寻找身份认同时的不同表现。为此,韩倚松也对比了同时期其他中国作家对相似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表现了部分中国人的自卑敏感心理;而平江不肖生笔下的人物黄文汉,虽然常利用武术满足个人私欲,但也在剑术比赛中赢了日本人,从而获得了尊重,表现出中国人的另一种姿态—积极表达自豪感。在平江不肖生心中,武术可以用来表达并维护民族自尊心。这一发现丰富了国内已有的论述,我国学界一般认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书品”之高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其高明之处便是作者对“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充分肯定:‘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学’而不‘媚外’”[4]。霍元甲因为相信武术而认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弱,他为给中国人争面子,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广交豪杰,并挑战外国大力士。面对上海的都市生活,他在好友农劲荪等人的帮助下,适应了都市的商业、法律、社交及媒体等新事物,成功改造了传统擂台—虽然擂台改造未能打破传统的门派观念,最初的挑战目标也因洋人逃窜未能实现。但在此过程中,霍元甲身体力行地突破了武术传承的传统,开办学校,打破门第局限,尽管所教内容不涉及自家“迷踪艺”,却在武术传播形式上有了新突破。韩倚松认为,这是武术适应现代性的一个突破,是历史中武术进步的投射。但是在创作手法方面,韩倚松认为平江不肖生叙事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对霍元甲为实现武术愿景而努力的描写。由于这方面的叙事不够深入,加之“受害是现代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形式”[1]211,影视作品和小说的主题产生分歧。关于小说的作用,平江不肖生认为写小说和为国效力的工种无可比拟,小说也并无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所相信的力量,所以他侧重于小说的娱乐功能。
最后一章把中国现代性置于世界现代性的经纬中,找到与世界相通的参照系和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这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新视角。在时代转型期,平江不肖生创作的数部作品所表现出的过渡性,是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和读者期待,小说的体裁、语言、形式、主题、表现方式、叙事结构、叙事声音等都不是由作者的独立意志决定的。韩倚松将平江不肖生的文学活动作为一个例子,揭示了他所参与的关系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构成的系统,通过这种以木见林的方法,还原了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发展历史的微观细节和宏观生态。向恺然的成功与资本的注入分不开,从而当时的市场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武侠小说分类鼻祖身份。正如《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封面上的平江不肖生的肖像照所示,猴子把玩着手中的水果,行为似人非人,有论者认为这很像是一种暗喻,暗示作者因商业小说作者身份而受到资方限制。韩倚松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该意象与现实社会市场大环境中的平江不肖生的作者身份形成呼应。平江不肖生因参加革命被迫前往日本求学,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和日语环境对他的白话文创作形成的影响、他对武术的痴迷以及风趣幽默的性格使其文学创作形式丰富多样。在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时代,他用丰富的写作素材储备和精湛的写作技巧,适应市场需要进而改变市场风向,推进武侠小说的发展,也推动了武术教育的进步。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本土产物,小说中蕴含的侠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发展,对这一文类的研究是我们探寻通俗文学本质的一个重要路径。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断形成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新视角、新方法、新结论激起大陆学界的层层波澜,那些曾经因种种原因被遮蔽、被边缘化的作者、作品渐渐得到关注。比如,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令人振聋发聩,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五四”之前那段通俗小说盛行的历史。
长久以来,韩倚松先生对华夏文化与通俗小说深感兴趣,并在中国通俗文学的细分文类里深耕。《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以平江不肖生为中心,辐射民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跨越媒介形式,还原了那个特殊时代对武侠小说转向的推动。不过,本书对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分析略有不足,缺少对此时期武侠小说作者的对比研究,从横向来看,缺少对与平江不肖生同时期的武侠小说名家赵焕亭的介绍,赵焕亭有其独特的叙述格局,也是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史中独具一格的作者;从纵向看,平江不肖生、赵焕亭之后的“北派五大家”(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对武侠小说的发展也有所贡献,若将笔墨留一些给其他武侠小说作家,那么对此时期的武侠小说呈现可能会更全面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本书呈现的研究路径非常值得推荐,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武侠小说已是难得,对关注中国侠文化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民国早期的文学生态。若结合阅读中国学者的武侠小说研究成果,则可以形成纵横网络,丰盈这个文化坐标的内涵,将会对理解、传播中国侠文化有更好的推动作用。
许多汉学家对本书的评价颇高,安如峦、白睿文、夏维明、雷勤风等都认为韩倚松先生的研究方法高明,他们从不同角度赞扬了以平江不肖生这位重要的武侠小说家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有助于读者了解作家、认识中国近代文学世界还未被重视的领域,引人深思,甚至可以改变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对中国武侠小说发展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平江不肖生在国外却鲜为人知,这不由得引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面临的困境和今后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等问题。在《平江不肖生: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到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渺小,但个人仍然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本书不仅为喜欢武侠小说的中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史料,还奉献了精彩的历史分析方法和结论,其中,中、西研究不同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碰撞和互补,相得益彰,可为中外读者带来诸多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