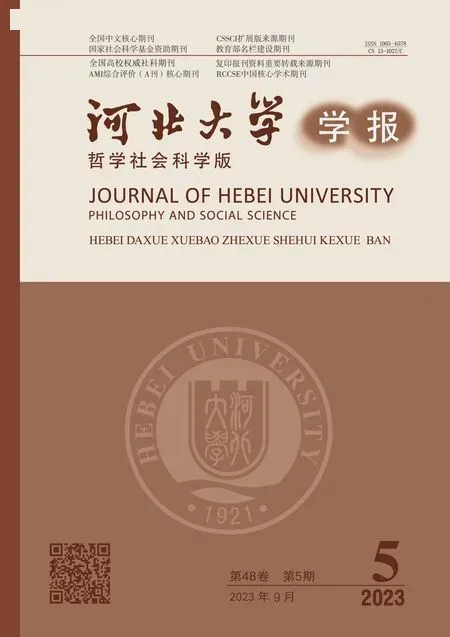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研究
2023-03-12杨高凡
杨高凡
(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官司出入人罪法主要是指唐宋以来用于规范司法官员因故意或过失而导致量刑不当行为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官司出入人罪首次出现于《唐律疏议》中,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发展、完善。现今学界对其研究成果主要有:季怀银《宋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1],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2],伍天翼《中国古代出入人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构造》[3]、李晓燕、李麒《我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历史演变》[4]、马玉臣《宋代官吏失入死罪法规初探》[5]等。在这些成果中,关于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发展、内容、特点、评价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拟通过对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全面研究,厘清其发展脉络、特征、不足之处等,以期为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的官司出入人罪包括故出入人罪和失出入人罪,它作为一个独立罪名首次正式出现是在《唐律疏议》“断狱”篇[6]中,这是中国古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展的重要阶段。但作为规范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具体规定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史记》载晋国人李离因“过听杀人”妄杀无辜,晋文公欲为之脱罪,但李离坚持“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最终“伏剑而死”[7]。李离自裁证明当时晋国是有追究法官失入人死罪责任的。秦朝的“纵囚”“不直”和汉代的“故纵”“故不直”即是当时官司出入人罪具体罪名。延至唐朝,《唐律疏议》“断狱”篇正式对此类犯罪行为有了详尽的规定。在唐朝发展基础上,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宋初:出入人罪法沿袭唐律无变化
北宋初年修订律典《宋刑统》时几乎照搬了《唐律疏议》,成为宋代最早的官司出入人罪法:
诸官司入人罪者(谓故增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有恩赦,而故论决,及示导令失实辞之类),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即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各又减二等。所司已承误断讫,即从失出入法,虽有出入,于决罚不异者勿论。[8]486
这一规定将概念、种类和处罚原则混同在一起,且有其他相关法规散见于《宋刑统》其他篇章中。总结起来,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基本概念、分类和处罚原则如下。
1.官司出入人罪的概念与分类
依《宋刑统·官司出入人罪》规定,宋代的出入人罪分四类。
第一,故入人罪。司法官员故入人罪又可分为“故增减”“故论决”和“示导令失实辞”三种情况。“故增减”,是指司法官员“虚立证据”“妄构异端”,即“虚立”“妄构”不利于罪囚之情状,加重罪囚罪责;“故论决”,宋代赦降活动频繁,对罪囚多所减免,故相关官员在已知将有赦降而判决的行为无疑属于故入人罪;“示导令失实辞”,司法官员“示导”或“恐喝”导致罪囚“改词”者。
第二,故出人罪,即“增减情状之徒,足以动事之类”。司法官员故意“增减情状”足以减轻判决结果者。
第三,失入人罪,即司法官吏因过失而导致罪囚处罚加重的犯罪行为。相对于故入人罪而言,失入人罪没有犯罪故意的意图,只是因为客观原因或失误导致案件判决加重。
第四,失出人罪,即司法官吏因过失而导致罪囚处罚减轻的犯罪行为,与失入人罪一样,失出人罪者无故意犯罪的意图。
2.处罚原则
第一,故出入人罪者处罚重、失出入人罪者处罚轻。
宋承唐制,刑罚分为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死(绞、斩)五刑二十等,其五刑又可以划分为身体刑(笞、杖)、劳役刑(徒、流)、死刑(绞、斩)三个级差。司法官员在不同级差之间与同一级差之内出入人罪处罚不同:其一,不同级差间故出入人罪者,以全罪论。即司法官员将“本无负犯”者,“虚构成罪”;笞杖入徒流或死刑,徒流入死刑;从死罪出至徒流杖笞,从徒流出至笞杖,甚至无罪开释,皆以所出入罪之全罪责之。其二,同一级差内(含同一刑等内)故出入人罪者,其刑责以司法官员出入人罪之所剩罪论处,即“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从徒入流,亦以所剩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若司法官员故出入人罪,以全罪或剩罪论,处罚较重;若乃失出入人罪,则是在故出入人罪剩罪、全罪基础上,“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处罚,过失犯罪处罚轻于故意犯罪。
第二,减等处罚原则。
特殊情况下,出入人罪者可减一等论处:“未决放”,即故入、失入死罪及杖笞罪未实施者;故出、失出死罪以下未放或者“已放而更获”者;“囚自死”,只要囚徒死亡,不问死因,皆减一等论处。但司法官员若非原审官员,仅“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8]487,即充使别推者出入人罪,可减二等处罚。
宋初的官司出入人罪法沿袭唐制,几无变化,另有其他律条散见于《宋刑统·名例律·同职犯罪》《宋刑统·名例律·八议》《宋刑统·名例律·请减赎》《宋刑统·名例律·以官当徒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宋刑统·断狱·遇赦不原》等篇目中,一方面造成司法实践操作不便,另一方面因特权法的存在,司法官员犯罪后所受惩戒有限,直接导致这一法规形同虚设。
(二)宋太宗、真宗、仁宗朝:失入人死罪法初步发展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规范司法官员司法行为、维护法制健全公正的需求日渐迫切,“时天下甫定,刑典弛废,吏不明习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9]卷一九九《刑法一》,第4968页,出入人罪案件增多,因此进一步发展、完善官司出入人罪法的需求逐渐提上日程。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判刑部张佖即上言:“果州、达州、密州、徐州官吏枉断死罪,虽已驳举,而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非少峻条贯,何以责其明慎! 按《断狱律》,从徒罪失入死罪者减三等,当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望自今断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削一任,更赎铜十斤,本州判官削一任,长吏并勒停见任。”宋太宗下令“从之”①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2页。又见《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71页。二处记载文字略有不同。。即失入死罪者不再按照旧律,全罪减三等即徒二年半后,再享受官当、例减、赎等特权,而代之以长官(知州、通判)勒停现任、检法官削一任罚铜十斤、判官削一任的行政处罚,官当等特权取消,法律“少峻”,有利于强化司法官员的责任意识,减少出入人罪案件发生。
宋太宗雍熙三年的诏令显然触动了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故宋真宗咸平初年新修《咸平新删定编敕》时被迫删去。随后,“长吏渐无畏惧,轻用条章”[10]卷六十,景德二年七月辛亥,第1349页,失入死罪案件又增多。景德二年(1005),上封者提出折中建议:
刑部举驳外州官吏失入死罪,准《断狱律》,从流失入死罪者减三等,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定断官减外徒二年半②“二年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七月辛亥,第1349页)误作“三年”,《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九(第8482-8483页)误作“二年”。据《宋刑统·同职犯罪》(第79页)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若通判官以上异判有失者,止坐异判以上之官)”。其责任顺序为长官、判官、检法官、主典,“各以所由为首”,即若是主典检法有失,则主典为第一从,判官为第二从,通判官为第三从,长官为第四从;若是判官判断有失,则判官为第一从,通判官第二从,长官第三从,主典第四从,失出死罪为全罪减三等徒二年半,则第一从判徒二年半,第二从判徒二年,以此类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谓“定断官”即案件的最终决断者乃“为首者”或第一从,应是徒二年半的处罚,对应行政处罚是“追官”,“余三等徒罪”则是其余第二、三、四从的处罚结果,对应的行政处罚皆为赎铜。,为首者追官,余三等徒罪,并止罚铜。伏以法之至重者死,人之所保者生,傥官司不能尽心,则刑辟乃有失入。盖幕职州县官初历宦途,未谙吏事,长吏明知从坐,因循不自详究。雍熙三年七月敕,权判刑部张佖起请,失入死罪不许以官当赎,知州、通判勒停。咸平二年编敕之时,辄从删去。臣以为若依格法旧条,似亏惩劝;或准张佖起请,又未酌中。欲望自今失入死罪不至追官者,断官冲替,候放选日注僻远小处官,系书幕职州县官注小处官,京朝官任知州、通判,知、令、录、幕职授远处监当,其官高及武臣、内职奏裁。诏可。[11]刑法四之六九,第8482-8483页
景德二年(1005)诏令折中了《宋刑统》过宽和宋太宗朝过严的惩处原则,详分类型、区别对待,其为首者即应徒二年半者,追官;其余 “失入死罪不至追官者”即第二、三、四从官员亦不再依据《宋刑统》规定可以赎铜代替徒刑,而是断官充替,及放选日注僻远小处为官处罚;高阶文官、武臣、内职者,则上奏朝廷裁决。此次敕令温和、有效,责轻者罚宽,特权者宽贷,适应当时的政治现状,既坚持了行政处罚、限制特权法原则,又不至于沦为激烈抵制下的无效法令,此后宋代的失出人死罪法一直沿袭此趋势发展。
(三)宋神宗朝:失入人死罪法成熟完善期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颁布诏书,规定:
十二月十一日诏:“今后失入死罪,已决三名,为首者手分刺配千里外牢城,命官除名编管,第二从除名,第三、第四从追官勒停;二名,为首者手分远恶处编管,命官除名,第二从追官勒停,第三、第四从勒停;一名,为首者手分千里外编管,命官追官勒停,第二从勒停,第三、第四从冲替。以上赦降、去官不免,后合磨勘、酬奖、转官,取旨。未决者,比类递减一等,赦降、去官又递减一等。内使相、宣徽使、前两府,取旨;大卿监、閤门使以上,比类上条降官、落职、分司或移差遣;其武臣知州军、自来不习刑名者,取旨施行。”[11]刑法四之七五至七六,第8486-8487页
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员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编管,二人远恶州军,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后法寝轻,第不知自何人耳![12]
熙宁二年(1069)诏令明确区分官员、吏员分别失出死罪一人、二人、三人在已决、未决不同情形下不同处罚标准以及可否享有赦降、去官不追责之特权等规定。且高品文官即使相、宣徽使、前两府和武臣知州军、不习刑名者可以取旨处理,特殊照顾。这一敕令总结了北宋建立以来失入人死罪法的发展成果,并将之纳入海行敕中,标志着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展到成熟完善时期,故熙宁六年(1073)修订《熙宁编敕》时将之纳入其中,《元丰编敕》沿用,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时,这条敕令被删除,旋即恢复:
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尚书省言:“左司状:‘失入死罪未决并流徒罪已决,虽经去官及赦降原减,旧中书例各有特旨。昨于熙宁中,始将失入死罪修入海行敕,其失入流、徒罪例为比死罪稍轻,以此不曾入敕,只系朝廷行使。近准朝旨,于敕内删去死罪例一项,其徒、流罪例在刑房者依旧不废,即是重者不降特旨,反异于轻者,于理未便。’本房再详,徒罪已决例既不可废,即死罪未决例仍合存留,乞依旧存留《元丰编敕》全条。”从之。[11]刑法四之七七,第8487-8488页
《宋会要辑稿》此处记载的熙宁二年敕令仅仅适用于失入人死罪者,而未提及失入流、徒罪官员的处罚问题,但据元祐元年尚书省上言可知熙宁二年敕令中必含有失入徒流罪规定。考《宋史·刑法三》:
未几,(宋神宗)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隶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9]卷二0一《刑法三》,第5022页
可以肯定,此处宋神宗的“复诏”与《宋会要辑稿》所载熙宁二年敕令是同一个诏令的后续补充,二者记载各有偏重,《宋史·刑法三》所载失入人死罪不及《宋会要辑稿》详尽,但其关于失入徒流罪之记载却弥补了《宋会要辑稿》之疏漏。二者相互补充,完善了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①失入人罪减故入人罪三等处罚,故司法官员失入杖笞罪的犯罪行为基本可以忽略。,此后宋代司法官员失入人罪法一直沿袭至南宋,是两宋一直通行的失入人罪法。
(四)宋哲宗、徽宗朝:失出人罪法立而复废
元祐七年(1092),有臣僚上书言:“伏见法寺断大辟,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断徒、流罪,失入五人则责及之,失出虽百人不书过。常人之情,能自择利害,谁出公心为朝廷正法者! 乞令于条内添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宋哲宗诏令“从之”“著为令”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七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六,元祐七年八月丙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38页;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一《刑法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23-5024页,三处史料对此皆有记载,文字略有不同。。自此,宋代失出死、流、徒罪行为正式立法。惜此诏令实施时间不长,绍圣四年(1097)改为“失出死罪或徒流罪各三 人,比 失 入 一 人”[10]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一月丁丑,第11705页,元 符 三 年(1100)五 月 宋 徽 宗 初 即 位 后 即 废止[11]刑法四之七八,第8488页,此后失出者不罚,失出之法被废止,延至南宋灭亡,宋廷再未立失出人罪法!
(五)宋孝宗朝:县级官员被纳入官司出入人罪法规范范畴
南宋初年,官司出入人罪法沿袭北宋旧制,“如祖宗法”[11]刑法四之七九至八0,第8489页。孝宗朝起,县级官员出入人罪亦被纳入立法范畴:
淳熙元年六月四日,敕令所言:“大辟翻异,后来勘得县狱失实,乞止依乾道敕条科罪;如系故增减情状,合从出入法施行。”从之。《乾道敕》增立“县以杖笞及无罪人作徒、流罪,或以徒、流罪作死罪送州,杖一百;若以杖笞及无罪人作死罪送州者,科徒一年刑名。”先是,臣僚言县狱失实,当将官吏一等推坐出入之罪。刑寺谓县狱与州狱刑禁不同,故是看详之。[11]刑法四至九五,第8502页
宋代县级官员无审断徒、流、死罪之权,但他们必须甄别区分所辖范围内所有案件,其中杖笞刑直接审决,徒流死刑则负有侦查、初审权力和义务,之后上报州府审断。若县级官员误将杖、笞、无罪之人作徒、流、死罪或误将徒、流罪作死罪送至州级司法机构者可依乾道敕令处罚,若为故意为之,可依出入人罪法科断。
自唐以来,官司出入人罪法管辖范围一直不包括县级官员,宋孝宗乾道年间敕令虽对县级官员出入徒流死罪行为有所规范,但亦未将之纳入出入人罪法范畴。淳熙元年始将县级官员故出入人罪纳入管辖范围,这是宋代出入人罪法进一步完善的一个表现。
(六)宋宁宗朝:失入人死罪法之调整、定型
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修订《庆元条法事类·出入罪》,进一步调整官司出入人罪法:
诸官司失入死罪,一名,为首者,当职官勒停,吏人千里编管,第二从,当职官冲替,事理重吏人五百里编管,第三从,当职官冲替,事理稍重吏人邻州编管,第四从,当职官差替,吏人勒停;二人,各递加一等(谓如第四从依第三从之类),为首者,当职官追一官勒停,吏人二千里编管;三人,又递加一等,为首者,当职官追两官勒停,吏人配千里(以上虽非一案,皆通计),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未决者,各递减一等(谓第三从依第四从,第四从三人依二人之类)。会赦恩及去官者,又递减一等(以上本罪仍依律,其去官会恩者,本罪自依原减法),即事涉疑虑,若系强盗及杀人正犯各应配,或中散大夫以上及武官犯者,并奏裁。[13]
相较于熙宁二年敕令,《庆元条法事类·出入罪》弥补了前者对官、吏第三从、四从责任划分不明晰、处罚等级无区别的不足,且总体上减轻了熙宁二年敕令的处罚力度、增加了享有特权的官员范围,官司出入人罪法自宋神宗后“法寝轻”[12]矣。
二、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特点
官司出入人罪法首次出现在《唐律疏议》中,但在此后的二百多年时间内,唐朝统治者一直未曾对其进行修订、补充,延至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发展尽管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其中故出入人罪法进步明显,且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
(一)形成独立适用的特别法
官司出入人罪法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但一直到唐代为止,都未能形成独立的特别法,其主要法规散见于《唐律疏议》之《断狱律·官司出入人罪》《名例律·同职犯罪》《名例律·诬告比徒及出入罪比徒》等不同篇目中,《宋刑统》几乎完全照搬《唐律疏议》,使得这一法规在实际操作中诸多不便。且宋代官员的法律素养普遍较低,“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9]卷一五五《选举一》,第3618页,因而“刑罚失中”就成为普遍现象,司法官员出入人罪亦为多见。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尤其是失入人死罪法建立起以行政处罚代替五刑本刑的处罚模式,取代了唐律以五刑本刑判、以官当、减、赎等特权法执行的处罚传统,标志着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形成了独立的特别法,这与唐代官司出入人罪法从法律适用、罚则、责任划分等皆混同适用一般法则的司法实践形成鲜明对比。
(二)发展的不平衡性
官司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入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四类犯罪种类,司法官员所出入之罪轻重亦不等,含死、流、徒、杖、笞五刑二十等、三个级差(身体刑、劳役刑、死刑),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不等,故官司出入人罪法涵盖内容丰富。但规范四类犯罪行为的法规并非同步发展,而是各自独立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其中故出人罪法、故入人罪法沿袭唐律未见变动;失出人罪经历了短暂的立而复废反复后继续沿用唐律;失入人死罪法发展充分。经由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发展、反复,宋代的失入人死罪法最终在宋神宗朝发展成熟、完善,区别于《唐律疏议》《宋刑统》用“同职犯罪”条区分司法官员责任的规定,熙宁二年敕令将相关司法官员直接分为承担主要责任者即为首者、第二从、第三从、第四从,明确区分各自的责、权等级;又将相关吏员群体亦纳入规范范畴;区分已决、未决分别处罚;依据入罪人数多少分类处罚等,这是官司出入人罪法在宋代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一进步成果直至宋亡一直沿用,《庆元条法事类·出入罪》仅在惩罚力度上、责权等级方面稍有调整,其基本原则、内容未有变革。但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明显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宋代的失入徒、流罪、失出人罪、县级官员出入人罪法等虽有所发展,但远远逊色于失入死罪法的完善、发达,更不用提故出入人罪法沿袭唐制略无变化了。
(三)法律适用对象扩充
中国古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规定皆是针对司法官员而制定,地位低下的吏人群体从未被纳入其规范范畴。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首次将之纳入其中,熙宁二年敕令和《庆元条法事类·出入罪》皆将吏员群体与官员群体同等规范,依据其责任轻重、失入人数多少、判决是否实施等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标准,这是唐代乃至此后的明清二朝皆未能达到的高度。
大量的吏员群体活跃在中国古代各级政府机构之中,对于吏治、法制是否清明的影响不言而喻,但其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升迁空间狭小,故他们利用熟悉业务和地方人情世故之优势谋一己私利就成为普遍现象。官员多儒家知识分子出身,听讼本非所长,再加上政务生疏,故“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9]卷一九九《刑法一》,第4968页的现象经常出现,吏员营私舞弊、愚弄上司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以能吏著称之包拯亦不能避免: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号呼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14]
民有徒罪当受脊杖,吏违法受贿后诱使长官包拯误判以杖,为失出人徒罪。在案件的最终判决中,此吏员之作用极其明显,依宋律,收受贿赂数额较大为赃罪,数额较小则为故出人徒罪。包拯所处时代为宋仁宗朝,熙宁二年敕令尚未颁布,此吏员若受赃数额不足以构成赃罪,则此吏人之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受法律制裁。猾吏如斯,廉能如包拯者亦不免为之所欺,庸碌、无知之主官受制于吏员之普遍现象可想而知,故将吏员这一影响巨大、数目众多之群体纳入法律规范范畴之内本身即是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一大显著进步,是其法制完备的重要标志。
(四)高品阶文官、内官、武将等享有特权
宋代自雍熙三年规定“自今断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后,司法官员皆不得再享受“官当”这一法律特权,终宋一朝,这一原则一直被严格遵照执行。较唐代而言,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更严格,对司法官员更有约束力,遭到官员的反对更激烈,故其具体内容多有立而复废、不断修订经历。经过反复斗争、修订,从宋真宗朝“官高及武臣、内职”①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2-8483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七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49页,二者记载略有不同。,至宋神宗朝“使相、宣徽使、前两府”“武臣知州军、自来不习刑名者”[11]刑法四之七五至七六,第8486-8487页,再至宋宁宗朝“中散大夫以上及武官犯者”[13]皆上奏皇帝裁决的规定,高品文官、武臣、内职者的司法特权得以保留,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中依旧保留有一定的特权法残留。
除了高品文官、武臣、内臣等依旧享受特权外,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的特权法特征还体现在失出人死罪之官员所受处罚远远低于吏员群体的处罚,且受罚官员经过一定时限或赦降即可叙复,而违法吏员则无此待遇,这是整体官员阶层特权法的体现,亦是中国古代法制等级制本质的体现。
三、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达原因及其评价
经过持续的修订、反复,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规则细密、管辖范围扩充,发展到了前代所未能达到的高度,甚至后世的元明清亦未能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
(一)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达原因
因社会进步、经济发达、儒家思想盛行等因素影响,宋朝社会法制健全、制度完善、司法实践活跃,这是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发达的直接原因。
其一,法制发达是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完善的时代背景。宋代是一个法制文明高度发达的朝代,徐道邻指出“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达到最高峰”[15],“成就最辉煌”[16],其制度完备、法规细密,叶适言其“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17]。如此昌盛的法制文明大背景孕育出了完善、发达的官司出入人罪法。宋代“多明法之君”[18],尤其是宋神宗“思立法度以宰天下”[19],在位期间制定了大量的法令法规①据郭东旭《宋代法律与社会·宋代编修敕令格式一览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305页)统计,两宋共编修法典263部,其中宋神宗一朝共92部,占比三分之一略多。。梁启超评价中国古代立法概况云:“其真可称为立法事业者,惟神宗时代耳!”[20]正是基于此时代背景,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高峰,较其前之唐代更加细密、操作性更强,惜其后的元明清法制未能继承这一传统,进一步发展。
其二,出入人罪案件增多客观上需要宋廷制定完善、健全的出入人罪法。宋代私有观念发达,为维护其私有财产,宋人诉讼活动的需求量随之增多,“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21]“有开讼学以教人者”[22]宋代甚至还出现了专职助人诉讼的讼师,“讼师哗徒”“饵笔之人”“讼师哗鬼”等记载在史料中时有出现,地方上诉讼案件增多,州县官员日常工作量增加,但他们多为儒生出身,甚或有武人出身者,“远方官吏于文法既疏,于职事亦怠,故刑罚失中”[11]刑法六之五八至五九,第8562页,官员不能胜任其职责,则“势必委之于下,老胥猾吏得以为奸”[23]5015,冤假错案增多:
五代以来,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金州民马从子汉惠无赖,尝害其从弟,又好为敓,闾里患之。从与妻及次子共杀汉惠,防御使仇超、判官左扶,悉 按 诛 从妻 及 次 子。上 怒 超 等 故 入 死 罪,令 有 司 劾 之,并 除 名,杖 流 海岛。[10]卷二,建隆二年五月戊寅,第46页
绍兴七年十月九日,知信州永丰县事李景山上书:“伏见黄冈强盗初无事发之日,复无被盗之人,彼警捕之官贪功妄作,悉系平民二十有五人,违法锻练,致诬服者十有三人。有司观望,肆其惨毒,卒成其罪。审问之吏,属之武人,既不能辨其冤滥;议法之官,公事诞慢,又不能条其可否。而奸吏得以舞文,不俟闻而诛戮……移邻路别勘,委监司亲鞫,果皆平人而释之。”[11]刑法四之九四,第8501页
地方官员不亲其职、吏人从中渔利,甚至连最基本的司法程序都不遵守,导致张冠李戴、错杀嫌犯:
(绍兴)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臣僚言:“知泉州富直柔因本州奏勘杀人海劫黄□□,州院官吏将合断配陈翁进作陈进哥,领□□□重杖处死,却将陈进哥作翁进解押上州。……臣契勘直柔身为前执政而不亲郡事,致僚属弛慢如此。”[11]刑法四之八二,第8490页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七日,大理寺丞石邦哲言:“伏睹《绍兴令》,决大辟皆于市,先给酒食,听亲戚辞诀,示以犯状,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举行,殆为文具,无辜之民至有强置之法。如近年抚州狱案已成,陈四闲合断放,陈四合依军法。又如泉州狱案已成,陈翁进合决配,陈进哥合决重杖。姓名略同而罪犯迥别,临决遣之日,乃误以陈四闲为陈四,以陈翁进为陈进哥,皆已决而事方发露。”[11]刑法四之八三,第8491页
知泉州富直柔误将陈翁进作陈进哥处死、知抚州误将陈四闲作陈四处死,如此严重的失误显然是当职官员敷衍公事的恶果,此种现象应该不是个案,“今之勘官往往出入情罪,上下其手。或捶楚煅炼,文致其罪;或衷私容情,阴与脱免。虽在法有故出故入、失出失入之罪,几为文具”[11]刑法四之八四,第8491页,司法官员懒政、不作为、放纵吏员弄法,致有几多冤魂枉死! 因此,制定出完善、细密的官司出入人罪法规范司法官员、吏员的司法行为就成为宋廷必须完成的任务,这应是官司出入人罪法在宋代发达、完善的客观需要。
(二)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之评价
就法律制度设计的角度分析,宋代的官司出入人罪法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与宋之前、之后各朝代相比,它显然是最发达的,远非唐、明清所能媲美。尽管如此,在政治斗争激烈、司法官员专业素质整体不高以及频繁赦降影响之下,就最终实施效果而言,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与其他朝代类似,其司法实践效果有限,我们不应该对其评价过高。
其一,宋代官员相互之间因私人恩怨、党派之争等导致出入人罪之案件的判决或复审多不能依法进行,致使制度设计上的自我纠错功能失效,未能在司法程序最后一个环节中阻止出入人罪结果的最终形成。
福津尉刘莹携酒肴集僧舍,屠狗聚饮,杖一伶官,日三顿,因死。权判大理寺王济论以大辟,经德音从流。知审刑院王钦若素与济不相得,又以济尝忤宰相张齐贤持法尚宽,钦若乃奏莹不当以德音原释。齐贤乘其事,断如钦若所启,济坐故入,停官。[10]卷四七,咸平三年五月甲辰,第1018页
权判大理寺王济审断福津尉刘莹杖杀伶人之事,并无不当。但知审刑院王钦若、宰相张齐贤因私人恩怨在核准此案时枉断王济故入之罪,人为地制造出一例故入人死罪案。
有宋一代党争不断,双方“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24]卷5《边备政策》,第151页,必然导致官司出入人罪法沦为党争之工具,失去其本真价值。如熙宁初年,反变法重要成员宰相韩琦任相州(今安阳)知州期间处决了3名劫盗。多年之后,韩琦已去世,变法派、刑房堂后官周清提出“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入死罪”,从而引发牵连大理寺、刑部、御史台、谏院、审刑院等诸多官员在内的一场大纷争,案件最终以变法派、原知谏院蔡确拜相,而原宰相、反变法派吴充罢职为结案标志,“牵连得罪者数十人”,“狱成,人以为冤。”①此案牵连极广,散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庚子,第7025、7034页;卷二九〇,元丰元年六月辛酉,第7090-7091页。自始至终,双方争论的焦点皆非案件本身,而是借此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和借口,是否为失入死罪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胜出一方的身份,法制败于政治,其法设立之价值难觅矣。
其二,赦降太频导致犯罪官员所受处罚等同虚设,官司出入人罪法之实际震慑效果有限。宋代赦降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大赦、曲赦、德音、录囚、特赦等,释放有罪官员等罪囚是其内容之一。因大赦、曲赦、德音、录囚各自赦降等级不同,其减免、宽宥等级亦不同,大致可分为五个等格,其中第一等格的赦降可减免包括出入人罪之司法官员在内的所有罪囚,而经由二次第二等格的赦降受责官员亦可免罚,因此,犯罪官员经过等级不一的赦降后即可恢复官员身份。虽然第一等格的赦降有限,但宋代第二等格的赦降则比较普遍,据统计,北宋168年间,大赦、曲赦、德音、录囚共计425次,针对一人一事的特赦则无数。频繁的赦降严重干扰了司法公正,许多犯罪官员得以逃脱惩罚,“徒紊国家之纪纲”,“益令群吏慢于奉法,且使天下有以窥时之尚姑息”[25],直接导致“虽在法有故出故入、失出失入之罪,几为文具”[11]刑法四之八三—八四,第8491页的现象。如哲宗绍圣四年,李适任职临江军判官时失入三人死罪,依律当追两官勒停,恰好两遇大礼赦而减免惩罚,宋哲宗特下诏书令李适免勒停,仅与小远处差遣[11]刑法四之七八,第8488页。类似记载极多,违法官员“虽暂废,他日复得叙官”[23]4996,出入人罪法徒为文具,失去其应有约束力和震慑效果。
四、小 结
宋代儒家思想盛行,其慎刑、法治等思想直到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官司出入人罪法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一抹异彩。但其不足之处亦不能忽视,如特权法依然保留,高阶文官、武臣和内臣依然享有“奏裁”的特权,多数能够逃避制裁。而频繁的赦降则是所有犯罪官员的特赦机会,经过若干次赦降,犯罪官员即可全免或减降惩罚力度,既而叙复为官,如除名者六年后即可叙复、冲替者一年可得差遣等,宋仁宗朝敕令“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9]卷一二《仁宗四》,第251页的规定显然只是一纸空文。宋代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全体官员群体的权益自然是法律保障的重点,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宋代官司出入人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有限,与其制度设计相对发达并不完全匹配,无法真正起到维护司法公正、听讼清明的目的,这大概是帝制时代不可避免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