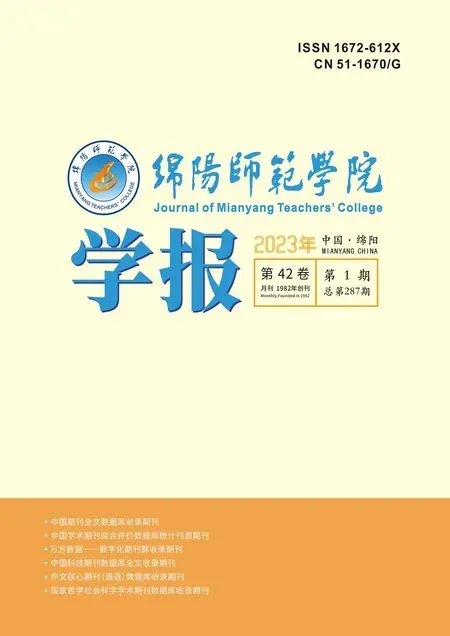马端临对“文献”的认识与运用
2023-03-12刘学伦
刘学伦
(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韶关 512005)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2466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1]2466郑玄虽未对“文”做直接解释,但从他把“献”作“贤也”解,再从“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一句可知,郑玄把“文”解释为“文章”,“献”解释成“贤才”。尔后注解《论语》的学者,如皇侃、朱熹、刘宝楠等人,所用的语词虽有殊异,但所作的解释与郑玄的说法没有太大的差异,皆将“文”释为“文章”或“典籍”,将“献”释为“贤才”。
马端临(1254—约1334),字贵与,号竹村①,江西乐平人。其所著的《文献通考》是现存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并专研文献的典籍。其《自序》云:“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以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2]自序,2对“文献”的认识有别于传统的注疏。因此将马氏所谓的“文献”加以厘清有益于我们对《文献通考》的研究。
前人对马氏“文献”观的看法各有差异,大抵可分作四类:一是文献分别为不同的材料来源。如杨琳认为《文献通考》中所谓的“文”指历代诸子经史中的记载,“献”是历代群臣奏议及学士名流的议论[3]103。二是文献为文字记载或载体。如张大可和俞梓华就主张马端临只认定文字记载才是文献,非文字记载的知识载体就不是文献[4]3。三是偏向“典籍”之意。如林申清认为,马端临对文献的理解是从兼指“典籍与贤才”向专指“典籍”演变的过渡[5]。四是叙事为“文”,论事为“献”。如杨燕起和高国抗就抱持着“文为叙事,献为论事”的观点[6]3。
诸家的阐释虽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皆是根据《文献通考·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有关“文”“献”的叙述,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既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以“文献”命名,且为专研文献的典籍,那么在探讨马氏的文献观念时,就不能仅从《自序》的叙述着手,更应当结合马氏在《文献通考》一书中对文献的实际运用,才能全面了解马端临的文献思想。
一、马端临对“文献”的认识
(一)传统和创新兼容
笔者认为,马端临将“叙事”材料视作“文”,把“论事”材料视作“献”,是他自己独创的见解。《自序》中除了上面引述那一段有关“文”“献”的叙述之外,还有另一处容易被人忽略,而与“文献”相关的文字:“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2]自序,2其中“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指的是“典籍”,“趋庭之问答”指的是“贤才”的回答,这正是以往对于“文”“献”的传统观点。
显见马端临不但自己能提出新的文献观点,同时也保留、承继了以前对文献的观念,突显出他兼容并蓄的文献思想。探其原因,“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对它的解释本属于注疏之学的范围。宋代经学的特色之一是疑经改经的风气盛行,在这种学风之下,马端临对旧有的注疏重新进行省思,提出己意,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动态的文献思想
马端临认为“文”“献”,并非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可将同一书籍的内容、相同性质的资料,因“叙事”或“论事”的需要而有所转换,甚至有时同一则材料也是如此。《国语·周语》中的“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之语,在《封建考》中,被视为是受封于天子的各个诸侯、蛮夷与天子之间由亲疏远近关系决定其该当行何种形式之礼节的“叙事之文”[2]卷260,16,但在《宗庙考》中,则是被当作议论“日月时岁之祭”的“论事之献”[2]卷96,8。据此,我们可以将马端临对文献的掌握运用,视作为一种“动态”的文献思想。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他对文献的认识,充分体现在对文献的运用上。
二、马端临对“文献”的运用
(一)叙事为文,论事为献
《文献通考》是主述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史书,共三百四十八卷,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全书综罗文献,根据《自序》可知,只要是“信而有证”的经史、历代会要、百家传记,皆属于“叙事之文”的取材来源;“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的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纪录,均属于“论事之献”的取材来源,由此可见《文献通考》征引的资料十分丰富。
以元代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刊后至元五年(1339)刊刻的《文献通考》余谦修补本为例,大抵将“文”顶格书写,“献”低一格或二格书写,马端临“考”之按语则低三格书写。根据这个格式,再对照征引的材料,可以发现,马氏常将同一书籍、臣僚奏疏……等,有时作“文”,有时作“献”的格式征引。笔者举例如下:
1.同一书籍
(1)《尚书》
《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二》顶格书写:“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恊于中,时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2]卷162,1视其为“文”。但在同卷该“文”之后续引:“《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2]卷162,1则低一格书写,视其为“献”。
(2)《公羊传》
《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一》顶格书写:“《公羊传》曰:自陜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2]卷261,1视其为“文”。而《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三》于“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之“文”后,低一格征引:“《公羊传》:其辞成矣,则其称纪季姜何?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2]卷253,5视其为“献”。
(3)《孟子》
《文献通考·卷七》顶格书写:“《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2]卷7,15《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一》于“虞舜践帝位,乃载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谨以子道”之“文”后,低一格书写:“《孟子》:咸邱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不识此语诚然乎哉?’……《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2]卷251,1视其为“献”。
(4)《史记》
《文献通考·卷十四》征引:“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巿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卷14,2《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七》征引:“帝颛顼生子曰穷蝉。”[2]卷257,1皆顶格书写,将其视为“文”。而《文献通考·卷四十》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之“文”后,征引:“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励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2]卷40,8-9《文献通考·卷八十四》于“秦始皇既即帝位,三年,东巡狩郡县,祀驺峄山。……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灭文学,皆曰‘始皇上泰山,为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云”之“文”后,征引:“太史公曰:自古受命帝王,尝不封禅?……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2]卷84,1-2皆低一格书写,视其为“献”。
(5)《后汉书》
《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征引:“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2]卷35,17《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三》征引:“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槀人。……二十八年薨,葬北芒。”[2]卷253,12皆顶格书写,视其为“文”。而《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三》于“献穆曹皇后,名节,魏公曹操之中女。……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禅陵”之“文”后,征引:“范晔论曰: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其安思,顺烈以下,皆依而加焉。”[2]卷253,15《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于“东夷有九种,曰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千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武帝元封初,杨灭其国,迁其人于江、淮,虚其地。自后,虽人庶复集,遂为郡县矣”之“文”后,征引:“范晔论曰:《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若箕子之述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2]卷324,1-3皆低二格书写,视其为“献”。
2.臣僚奏疏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征引:“长寿二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于朝堂列列拜,则金帛羽毛升于玉阶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可。”[2]卷29,4《文献通考·卷四十》征引:“桓帝延熹五年,太学西门自坏。襄楷上疏曰: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2]卷40,20皆顶格书写,视其作“文”。
《文献通考·卷十八》顶格书写“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之“文”后,低二格征引:“右拾遗李珏上疏谏曰:‘榷茶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訾,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巿者稀,不可三也。’”[2]卷18,2视其作“献”。
《文献通考·卷四十二》顶格书写“齐王正始中,刘馥上言:‘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一十余年,而成者盖寡。……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之“文”后,低一格征引:“明帝时,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堕也。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2]卷42,2视其作“献”。
从上面引述的各例可以发现,若按照马端临在《自序》所说的“文”“献”材料来源,《尚书》《公羊传》《孟子》是经,《史记》《后汉书》是史,当为“叙事之文”;臣僚之奏疏当为“论事之献”。但《文献通考》书中的实际运用却并非如此,“文”“献”材料的来源,经史之书并非全然为“叙事之文”,臣僚之奏疏也绝非只是“论事之献”。
那么,应该怎样来理解马端临所谓的“文”“献”呢?从马氏自己辑录征引的方式来看,可证明笔者所说的,马端临所言的“文”“献”,就只是“叙事”和“论事”的区别而已。尤其是在史书上的征引特别明显。以《史记》《后汉书》为例,举凡顶格书写者,皆是叙述史实之“文”,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后汉书》的“范晔论曰”,这些都是作者议事的言论,马端临皆以“献”的格式书写。
依照这个观点来审查《文献通考》辑录征引的内容,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以上述所举之例,在经书方面,例如征引《尚书·吕刑》的原文,可以当作是用来补充说明刑制的议论。《公羊传》“其辞成矣,则其称纪季姜何?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之语,可以理解成是用来解释说明“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的议论。至于臣僚奏疏,“文”的部分亦仅止于叙事,“献”的内容,即是对前条之“文”的议论。探其原因,臣子上奏、上疏之文,除了叙述事件以外,更需提出议论之己见,才能得到上位者的认可,终以实行,因此很难纯粹只有叙事或论事的内容而已。因此马端临《文献通考》取材的资料,引述作“文”或“献”,端看实际情况而决定,叙事时征引作“文”,论事时征引作“献”。
(二)综罗文献
此外,马端临在“文”“献”的运用上,有“综罗文献”的特点。宋代史学有综罗大量历史材料的倾向,尤其在司马光撰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之后,更是达到高峰。如王钦若、杨亿编纂,取材自正史、实录的史学性质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和《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等,都是“综罗文献”的具体呈现。
马端临之父马廷鸾著有《读史旬编》,其书《四库全书总目》云:“尝仿吕祖谦《大事记》之例,作《读史旬编》,以十年为一旬,起帝尧元载甲辰,迄周显德七年庚申,为三十八帙。”[7]1411董萼策等修、汪元祥等纂的《乐平县志》,说该书“本康节邵氏《经世书》、南轩张氏《经世纪年图》、朱文公《通鉴纲目》,畧仿吕氏义例,而为《读史旬编》”[8]2223。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一是由先列历史事实的“事目”和之后作阐述的“解题”,共同组成的“谱”,做为本书的主体。二是“通说”,属于序言的性质。三是“图”,将各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史事,以图表的方式呈现,使其条理化、形象化,使人一目了然。四是“历代之首”,是以邵雍《皇极经世书》数考其气运之推迁。可见亦是一部以“综罗文献”为特点的史学著作。《读史旬编》之《自序》云:“姑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9]147说明此书的用途之一是给予后辈讲学之用。又言:“不可不令儿辈觉也。”[9]148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提到的“先公曰”“先公……曰”或“先君曰”的文献,大多是从马廷鸾的著作中征引而来,或是“趋庭之问答”时对马端临的指导,其中应当有征引自《读史旬编》一书,成为他撰写《文献通考》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外,马端临师承朱子后学曹泾,吴怀祺云:“朱学在宋代末年的变化,有一个方面,是重文献综罗、考证和训诂。”[10]434马氏在学术思想上自当有所承继。
可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所以“综罗文献”,乃是深受家学、师承和当代学术思潮影响所致。
三、小结
笔者认为,马端临对“文”“献”的认识和运用,皆是宋代疑经思潮下的时代产物。宋人对经书的作者、内容的真伪等方面皆大胆提出质疑,马氏受此风气影响,对《论语》中的“文”“献”,能有别以往,提出“叙事为文”“论事为献”的新观点,是对传统注疏之学反思的结果,但他并不反对旧有“文”指典籍、“献”指贤才的说法;并将这种新观点运用在“综罗文献”上,把同一书籍的内容、相同性质的材料,随着“叙事”“论事”的实际情况而予以调整征引,以将“叙事”材料顶格书写为“文”,“论事”材料低一格或二格书写作“献”的格式来呈现,充分反映出马端临兼容并蓄以及“动态”的文献思想。
注释:
① 历来文献多皆载马端临,号竹洲,今据《扶风马氏宗谱》所录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