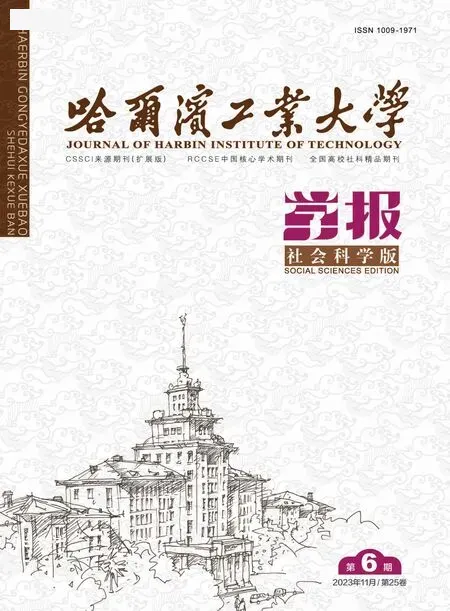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2023-03-09赵彬
赵 彬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17 )
宋、金灭亡后,科举制度亦随之而被废弃,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得以重新恢复。 科举废除现象,引起了元初众多文人的关注。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科举的弊端:如董文忠即认为科举为“亡国余习”[1]3502,赵文则更是明确指出“科举累人甚矣”[2]59,而谢枋得甚至高呼“科举士误天下”[3]33。 另一方面,其中亦不乏支持科举推行之人,如程钜夫既承认“有科举之累”[4],又不吝赞赏科举,并于皇庆二年(1313)为元仁宗草拟《科举诏》,足见他对科举并非持完全否定态度。
从历时维度考察发现,元初持“科举累人”观的文人,虽处于宋、金、元易代之际,但他们对于科举的看法却与其自身政治倾向关系甚小,反而是主张“文”与“道”,即“文统”与“道统”相折衷的观念。 纵览目前学界对于元代科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举兴废与文学、理学盛衰消长的关系,至于科举兴废背后所蕴藏的元人思想观念,鲜有深入挖掘。①参见任红敏《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中州学刊》2018 年第2 期;李兵《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故本文拟从元初“科举累人”的论断切入,探析产生此现象原因,揭橥元人主张“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想实质。
一、“科举累人”的表现
元朝初期,因自隋唐以来施行的科举制度未能继续推行,致使当时文人入仕之途基本中断,科举随即成为明日黄花,昔日之辉煌也一去难返。身处在一个没有举业压力的时代,文人能够开始理性反思科举,于是,探寻“科举累人”具体弊病所在的诸种说法由此生发。
科举骤然遭废的元代初期,在断绝当时文人仕进之途的同时,亦在一定层面促使他们能够重新审视科举,掎摭其利病所在。 在此审视中,人们看到了科举的弊处,提出了“士累于科举”“科举累人”等论断,认为科举的废除具有一定合理性。 而“科举累人”的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举有碍文学的发展
元初不少文人看到了科举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不良的影响,不但削弱了文学创作,且对文学良好风尚的形成同样产生阻碍作用。
1.科举阻碍了文学的创作
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名家元好问,就曾指责:
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 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 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5]1455
他批评金代泰和、大安年间文人追求通过科举而登“荣路”,除了科举“程文”的写作外,鄙薄其余“翰墨杂体”,其中诗赋创作更遭轻视,严重消解了诗赋发展的力量。 与之相反,牟巘看到了科举的废除,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兴盛:“场屋既废,为诗者乃更加多。”[6]595在这一点上,刘辰翁与牟巘持相似看法:“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7]177认为没有了功名的羁绊后,士人能够无所顾忌地投入到诗歌创作当中,而这样的创作投入,反过来推动了元代文学发生由衰落到复兴的转向。 由此可见,科举的废除,于文学创作而言,具有积极的作用。
科举的废除,使它完全脱离了士人日常生活的范围,不再是士人追求的人生中心与目标,赋予了士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看清科举兴与废的差异。 经过对比科举的往昔,元初一些文人认识到:当士人奋力于科举时,往往不愿花费精力进行诗文创作,乃至于鄙薄诗文,视诗文为末流。 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吴澄在《出门一笑集序》一文中,通过“近世”诗与唐诗创作状况的对比,认为唐代“能诗者众”,近世“能诗者寡”的原因,除了因为“江湖游士为之又多不传”之外,更是因为“场屋举子多不暇为”而导致:
场屋举子多不暇为,江湖游士为之又多不传,其传者必其卓然者也。 往年鉴溪廖别驾以名进士为学子师,既宦游遍历岭表,始有诗曰《南冠吏退》。其从子业举子,未仕,亦有诗曰《月矶渔笛》。 《吏退》之语清而韵,《渔笛》之声奇而婉。 虽不传于人,吾固知其诗也。 云仲亦别驾君从子,自选举法坏,而其业废,遂借父兄之余为诗。 且韵且婉,锵然不失其家法。[8]250
他认为近世诗人稀少的原因是文士忙于“举业”而无暇作诗从而导致近世诗歌难以企及唐代。 《南冠吏退》诗语“清而韵”,《月矶渔笛》诗声“奇而婉”,两者虽然可称为诗,但其作者不免有“累于科举”的嫌疑,而云仲无科举之累,全心致力于创作,诗风融通父兄神髓。 可见,在吴澄眼里科举确实妨碍了文学的创作。
另如戴表元的《陈晦父诗序》、赵文的《诗人堂记》、何梦桂的《清溪吟课序》、邓剡的《翠寒集序》、曹泾的《重修休宁县学记》、舒岳祥的《跋王榘孙诗》、任士林的《书蒋定叔诗卷后》、陈栎的《吴端翁诗跋》等,均论及科举废而诗出或场屋废而诗复兴的观点,足见元初文人清醒地认识到科举阻碍了文学的创作。
2.科举文章对文风产生不健康影响
元初诸多文人,经历改朝换代之痛,亦见证过科举的盛衰兴废。 他们在冷静的思考中,注意到科举文章对于文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他们看来,科举以诗文为考试科目,士人会迎合“有司恪守格法”①《金史·赵秉文传》载:“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 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参见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2427 页。的趣味,从而导致文气卑弱。 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到金人张行简长期主持科考,“以格律痛绳之”的“苛甚”做法,致士子“不成语言”,乃至“文风浸衰”[9]97的可悲现实。 阎复《谢解启》一文,亦载科举之文的写作:“拘之以声律之调畅,检之以对偶之重轻。 以窘边幅为谨严,以粘皮骨为亲切。 描题画影,但知一字之工夫。”[10]234赵孟頫作为元代前期非常有影响的名家,同样看到了科举影响文风的弊病,他在《第一山人文集叙》中,指明宋朝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 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 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11]“有司”墨守成规取士,士人为求一第趋之如骛,从而文章出现“缀缉新巧”“模题画影”“旁搜为奇”“远引为博”“文体破碎”“诗体卑弱”等弊端。 吴澄则在《聂咏夫诗序》中激赏聂咏夫诗无“场屋举子气”,与俗流不同,得诗学要旨。二是士人为求利禄希冀在文章中对权贵阿谀奉承以换取前程,换言之,文人本身的气节低下造就了文风萎靡不振。 方回《读宏词总类跋》曰:“凡有司之命题与试者之作文,无非力诋元祐,以媚时相。 四六于是愈工,而祖宗时文章正气扫地,天下文人才士心术蛊坏,知猎一时之荣,而不恤万世之有公议。”[6]171宋代科举阿谀之风既来自政治高压,又来自文人迎合“时宰”所好,因此,宋代程文堕落不堪,文风根本不可能出现“雄健浑厚”的新气象。
(二)科举有碍经学发展
宋、金两朝的科举,都曾以经义、诗赋作为考试内容。 举子习经义、诗赋,是为应举,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且充满功利性。 因此,元人认为,科举对经学的阻碍与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是相似的,其有害影响有二:一是影响经学健康发展。 宋、金时期,出现士人为了应付科举,在阐释经典时,无所顾忌,破碎六经,即使承讹习舛也不以为意的乱象。 戴表元曾严厉抨击此种现象:“场屋腐生,山林曲 士, 因 而 掎 摭 微 文, 破 碎 大 道, 为 可 悯叹。”[12]155认为“场屋腐生”们,为名利曲解经典、“破碎大道”的行为,丝毫无益于经典的传承与传播,反而产生了非常有害的作用。 元人朱晞颜则通过回顾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士人为迎合“时宰”而曲解经义、牵强附会的史实,批评王安石“作相”时,为推行“新法”,不惜利用手中权柄,“以私学取天下士”,毫无顾忌地“作经义,去笔削,一经目为断烂朝报,任情穿凿,牵合不伦”,致使“海内翕然,慕而一变”[13]的有害做法。 二是科举占据时间,无暇治学。 关于此,元人刘坦的《尚书纂传序》、戴表元的《左氏窥斑序》等文,均有论及若无科举之累,方可有暇著述文章,钻研经义之言。
(三)科举有碍理学的发展
科举对于理学发展的妨碍,在元人看来,最为鲜明地体现为科举占据大量时间,士人无法专注于研读程朱理学。 理学兴起于宋,元时得到进一步传播与接受。 而当士人耗费大量精力、时间浸润于科举时,无疑会分散其在理学方面的注意力。故而,元初之人对此问题亦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明确看到了对于研习理学时间的占用,进而批评之。刘壎在《再举谢段知军》《谢监试通判(旧座主)》中,就非常鲜明地指出“科举妨义理之学”。 赵文于《学蜕记》中,也清晰地指明:“士欲舍科举而专意义理,势有所不能,科举义理之学两进,日有所不给。”[2]106认为人的精力有限,科举、义理二者不能兼顾,科举废正好全心于理学。 同时,舒岳祥也强调:“士无科举之累,而务问学之实。”[14]226他此处所说的“问学之实”,即程朱理学,要求士人应该把精力专注于理学的探索而不是博取虚名。 可见,科举对于人的牵累之苦,早就成为元人的普遍共识。 在元初之人看来,只有摆脱“时文掇拾之劳”“场屋得失之累”,“士之读书者”才能够真正做到“心胸旷然,开卷之顷,圣贤之蕴,天地之心,轩豁呈露”[2]95。
(四)科举取人的偏颇
经过对科举的重新审视,元人发现科举所铨选的部分士人只会考试而无真才实学。 刘祁《归潜志》载金章宗时,宋使进贡枇杷,章宗命文人赋诗,状元王泽因不识枇杷而无法成诗。 王泽虽有状元之名,却局于“举业”,不能多读书,对生活日用不甚了解,可见其“任事”能力的不足[9]72。 方回同样认识到士人虽凭借科场文章“致位卿相”,却深受所习科举“时文”之误,导致“奏议无一篇可观”[6]193,徒有虚名,足见其人能力之欠缺。 陆文圭在《选举》中,也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认为科举之士,以文中举,而文章却“拘于声病,止于雕刻,言语尚未能也,况于文学。 珉中玉表,巵貌蜡言,文学尚未能也”,更何“况于政事。画饼充饥,谈河止渴,政事尚未能也,况于德行”。 而此状况的出现,均“盖科目之弊极矣!”[15]他在《送马伯亨序》中,进一步揭示元朝废除科举乃是以前代为殷鉴,“斥去浮华”,追求实效的进步表现。 吴澄也看到了业进士者往往只会举子业,而缺乏处理实际政治问题的才能,无法与有家学的世胄相提并论:“方且以科第自高自荣而骄世胄,抑孰知彼家庭之所见闻、官府之所经历,监旧章,视已事,明习法令,有非孤寒乍跻仕路者之所能及哉!”[16]尽管此看法存在一定的偏狭之处,认为世胄子弟政治才能高于孤寒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所抡选的人才也并非全有实学。 相较于陆文圭对于科举之人缺少处理实际政治问题的担忧,胡衹遹则明确批判科举是听其言而信其人,无法真正考察一个的真实才能,他说:“至于科举之取人,千载一辙,岂非听其言而信其人乎?”[17]302
由此可见,元初文人对科举铨选人才出现的弊端有深刻反省。
(五)科举对个人的消极影响
在元初文人看来,科举不仅对社会层面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它同时会对个人产生消极影响。它一方面会影响亲友情感和谐。 赵文就批评举子们因为忙于仕宦,不能对家庭、朋友尽到应有的责任:“修廊夜铎,收灯掩卷,敦其独宿,不知二亲千里外亦已睡否? 睡不念其子否? 盖科举累人甚矣……无科举之累,有读书之闲,无客外之苦,有养亲之乐。”[2]59-60这种家庭、朋友间责任的缺失,又会影响其情感的和谐。 另一方面,科举对人身心的损害。 科举对士人身心的折磨也是巨大的,举子冒风霜雪雨,千里赴试,身体上受到了折磨,在科考过程中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时间,若科考不中,无疑是晴天霹雳,造成心灵创伤。 戴表元讲述自己为求名利而跋山涉水的艰辛,《芷屋记》云:“然方是时,不免为科举利禄之役。 既以不资之身,争得失于千万人喧呼之场,冲风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陆,以干斗升之粟。”[12]99。 “冲风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陆”,对身体、心理的考验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元初文人清醒地看到了“科举累人”的弊病,并概括出其具体弊病的表现。 不过,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他们在体认到“科举之累”的同时,其实又并未完全否定科举,甚至同时还能够看到科举的益处,认可其具有的积极作用,当然,此问题,暂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
二、金、宋、元易代对于“科举累人”反思的影响
元初持“科举累人”观点的多为经历宋、金、元政权更迭之人,就其政治身份与倾向而言,大体可分为金代遗民、南宋遗民、金莲川藩府文人三个团体。 此三个团体成员对科举的态度,是否受到所处政治立场的影响,颇为值得探讨。
(一)金代遗民的反思
金代末期,北方因长期战乱金源士人或死于战乱,或转投地方世侯,或出仕元朝,真正的遗民数量较少,对科举发表过批驳观点的遗民有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人,他们仅是对科举做出客观评判,并无鲜明的遗民政治色彩。 相较于南宋遗民与金莲川幕府文人集团,金代遗民对于“科举累人”问题的反思分量非常轻。 因此,关于此问题的探讨重点是在南宋遗民与金莲川藩府文人。
(二)南宋遗民的反思
南宋灭亡后,其原属文人如程钜夫、赵孟頫等积极出仕新朝。 他们虽由宋入元,却很少抒发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悲,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遗民。 而赵文、何梦桂、邓剡、谢枋得、戴表元、胡次焱、刘辰翁、刘壎等,宋亡后心怀故国,或隐居不仕,或短暂出仕即归隐,他们属于遗民。 这些南宋遗民批判科举以赵文、谢枋得最具有代表性。 如谢枋得就曾借好友方伯载之口表达其观点:“吾岂不能为场屋无用之文,所以胶口不肯道者,愿为大元之逸民。”[3]30表面看起来,谢枋得认同方伯载以遗民的立场批驳科举程文为无用之文,实际上,他批判的不是科举本身,而是为通过科举求名利而心无家国天下的士人:
因道前朝四十年遗事:宰相之仁鄙,将帅之知愚,军民之苦乐,兵财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无问不知,如响斯答……始知东南科举士,误天下苍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将家子不习时文者,可与谈天下事。[3]33
在谢枋得看来,东南科举士致力科考而心无家国,坐视赵宋灭亡,严重辜负了苍生的期望。 所以,误天下苍生的从来不是科举本身,而是那些“科举士”。 南宋因多重原因而走向灭亡,谢枋得将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科举士,虽然有些偏激,却可以看出当时士风之猥陋。 他于《程汉翁诗序》既肯定科举为读书人提供“行其志”的作用,又批评“科举程文之士”以“学术误天下”[3]35。 客观来说,谢枋得本对科举士期望甚高,认为他们应该承担“家国天下”的重任,“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文之事,皆大言无当也。”[3]14他以张载的格言期许程文之士,期盼他们能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而亡国后的切肤之痛,让他认识到程文之士的鄙陋不堪,由此产生失望进而批驳科举。
刘壎与谢枋得有相似看法,其于《答友人论时文书》中,追述了南宋朝廷在面临由“樊陷而襄已失”所肇始的一系列生死存亡危机之际,南宋士人们却仍醉心于“解试”“省试”“类试”,将科举应试下所掩盖着的重重危机抛却于九霄云外:
痛念癸酉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已失矣。 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于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 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 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 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2]221-222
“癸酉之春”,即1273 年春。 此时距宋、元襄樊之战已有五年,而襄樊正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其一旦陷落,元军便可迅速控制长江中游,进而顺江而下扫荡东南,到时南宋的覆灭便难以挽回。刘壎严厉批评科举程文之士在国破家亡之际,“爱文而不爱国”,一心求取功名富贵,“家国则置度外”。
多次言及“科举累人”的元初文人赵文,一度将科举视为“书生分内事”,即使是在宋亡后,一面认同科举的益处“国家往时以科举收天下士,自胜冠以往”,“高者坐幕府”“小者犹不失参军尉簿”,并又以长者身份向友人之子赵渊如倾囊相授科举的应试技巧“不失韵,不触讳忌,即可举、可第”[2]83-84。 同时,又痛惜宋亡后“科举既罢”,使得众多像赵渊如一样的有才士人“无致身之望”[2]83-84。 因而,他鼓励如赵渊如一样的读书人当以读书为本,不必去追求元代的功名。 由此可见赵文是以遗民心态审视科举的。 这样的遗民心态,赵文在《诗人堂记》更是表露无疑:“而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 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马队之间者鲜矣。”[2]108宋亡后,科举时文的废除,使所谓的诗人骤多,而赵文所认可的诗人不是那种为求仕途抛弃节操,阿谀新贵的人,更不是身处山林而心在名利场的文人,这同样是其遗民心态的具体体现。 赵文晚年时,其遗民信念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从其《文苑英华纂要后序》一文中见出:
圣天子下诏,求经明行修之士,试六经、古赋,治诸章表,以观其所学;试时务策,以观其所能……崇儒重道之风,古之菁义,不啻过矣,习科目者,熟精此书,鏖战文场寸晷之下,能使朱衣人暗点头,则题雁塔、跋铜章,特拾芥耳。[2]74
是文作于延祐元年(1314)冬后一日,而在此之前的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已下颁布诏书恢复科举。 写此文时,赵文生命已接近尽头,已经不大有阿谀元朝以求富贵的可能,他称呼元仁宗为“圣天子”,对恢复科举表示支持,并认为熟精《文苑英华纂要》可以题名雁塔,从中可见他对元廷、对科举的看法有明显改观。
以遗民的身份批判科举毕竟是少数,而且遗民的思想也是呈现动态变化。 戴表元曾指出,随着元朝统治日久,南宋遗民日渐减少,遗民思想日渐消解:
余初学儒时,见世之慕利达者宗科举。科举初罢,慕名高者宗隐逸,隐逸之视科举有间也。 当是时,犹各有大儒遗老、有名实者为之宗,学者赖以不散。 岁月推迁,心志变化,昔之为宗者,且将销铄就尽,而士渐不知其宗,吾为吾道、吾类惧焉。[12]309
他所说的“吾道、吾类”即指遗民以及遗民思想。 南宋遗民的减少乃至消亡是大趋势,遗民或凋零故去,或因现实问题而放弃坚守,故而遗民思想不能成为元初出现“科举累人”说的主要原因。
(三)金莲川幕府文人的反思
相较于前文所述原南宋、金之文人,金莲川藩府文人对科举的态度亦不统一。 忽必烈即位前于金莲川藩府,延揽人才,形成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 藩府文人帮助忽必烈经略漠南,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以及后来元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藩府文人的政治见解、治国理念对元初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他们对于科举的见解却是不一致的。
作为金莲川藩府文人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王鹗认识到“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众多士人被迫转谋他业“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才能不得施用,这完全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与发展,进而提出其观点:“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1]2017。 与之相似,女真人赵良弼也看到了废科举之学的不利方面,主张:“宜设经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1]3746
与王鹗、赵良弼两人对于科举所持的积极看法不同,元初重臣许衡对科举则持批判态度:“科目之法愈严密,而士之进于此者愈巧,以至编摩字样,期于必中。”[18]85他更多地看到了科举之士无真才实学,只会投机取巧,为应付科考“编摩字样”的弊处,认为科举未能实现“先王设学校,养育人材,以济天下之用[18]85”的初衷,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而作为金莲川藩府文人中重要一员的郝经,也同样认为科第不足道,对于科举文章自己虽能为之,但“弗好”[19]1852。
同为金莲川藩府文人的董文忠,对科举也有着相应的看法。 据《元史·董文忠传》载,至元八年(1271),女真人徒单公履想奏请忽必烈“行贡举”:
知帝于释氏重教而轻禅,乃言儒亦有之,科举类教,道学类禅。 帝怒,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 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文忠对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 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事遂止。[1]3502
至元八年(1271),徒单公履了解到忽必烈崇信藏传佛教,用科举比喻藏传佛教,道学为禅宗以求打动忽必烈而实行科举。 董文忠为宿卫出身,他深知忽必烈是实用主义者,便从实用的角度批驳徒单公履的科举观,认为科举无用,无益于修身治国。 董文忠对于科举的看法虽一定程度可以代表自己,但更多的代表了忽必烈。 因此对比金莲川藩府文人对科举兴废产生的分歧发现,他们是从各自的角度去阐释观点,并未从政治立场的视域去观照科举,足见其观点与自身政治立场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
需要说明的是,元朝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其疆域越度前古,其族群众多,其整体文化特征以交流交融为主要趋势。 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文人也加入了对科举的讨论。 大致而言,从现有的资料看,少数民族文人中不乏有对科举持以肯定态度,如前文所述的女真人徒单公履、赵良弼。 此外,元太宗时期的契丹人耶律楚材①《元史·选举一》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参见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2015 页。、元世祖时期的蒙古人火鲁火孙②《元史·选举一》载:“至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十一月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 帝曰:‘将若之何?’对曰:‘惟贡举取士为便。 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爲学矣。’”参见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2017-2018 页。,以及后来的色目人贯云石③欧阳玄《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载:“会国家议行科举,姚公已去国,与承旨程文宪公、侍讲元文敏公数人定条格,赞助居多,今著于令。”参见欧阳玄《欧阳玄集》,岳麓书社2010 年版,第110-111 页。、高克恭④邓文原《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载:“公在台言圣代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参见邓文原《邓文原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9 页。等人均支持实施科举。 可以说,少数民族文人对科举的认同,不仅仅是他们受到中原文化熏陶的表现,也是元代时期多元文化进行交流交往交融的注脚。总之,从本质上来说,多数元初文人是以理性的态度看待科举的。
实际上元初文人深刻认识到科举弊病在于人的趋利性,科举制度本身并没有错。 他们意识到科举制度本身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其弊端产生的根源在“人”。 这些“人”既包括举子,也包括统治者。 就举子而言,他们受利禄诱惑,一心专意举子业,除此之外毫不关心,自然会出现上述各种被“累”状况,犹如张伯淳所言:“乡举里选降而科目取士,其弊则专意举子业。 文未尝弊也,而弊之者人。”[20]就统治者(当权者)而言,他们的好恶决定了士人的趋向,这一点从女真人赵良弼与忽必烈的对话中即可揭橥:
帝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良弼对曰:“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如耳。 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1]3746
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当权者的喜好引领了风尚,“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人从之”。
三、“科举累人”之下:文道合一的回归
中唐韩愈作有《原道》篇,勾勒出道统谱系,以表明儒家之“道”的传承从未断绝。 嗣后,宋人在此基础上形成道统与文统两阵营。 其论文者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其尚理者宗周(敦颐)、张(载)、程(颐、颢)、朱(熹),导致文与理析而为二。 而元初文人则主张调和文统与道统的矛盾,希望统一文、理。 他们所论及的“科举之累”,恰是文统与道统折衷的体现。
许衡、杨恭懿是元初理学家,他们纯粹以理学家视角批判科举。 许衡的观点上文已有论述,而杨恭懿在面对忽必烈询问徒单公履提出开科取士的看法时,其回答与董文忠相似。
元好问则是完全以文统观念看待科举。 其在《闲闲公墓铭》中批评金朝初年沿袭辽、宋以经义、诗赋开科取士,士人为钓高官厚禄,无暇通经义、创作文学的现象,而赞许赵秉文与众不同,以道德、仁义、性命自任,其文章出自“义理之学”。他将赵秉文比作韩愈、欧阳修,认为赵秉文传承的是韩愈、欧阳修的统绪,“道之传,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则非一人之功也。 唐昌黎公、宋欧阳公身为大儒,系道之废兴,亦有皇甫、张、曾、苏诸人辅翼之,而后挟小辨者无异谈。 公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 主盟吾道将四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5]272
元初有更多的人折衷文统与道统,主张文与理合一。 如郝经,其《文说送孟驾之》云:“而有宋氏兴,欧苏周邵程张之徒,始文乎理而复乎本”[19]1764,他以“理”的视域,将文统纳入道统,把欧、苏、周、邵(邵雍)、程、张并列。 并于《文弊解》云中强调:“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19]1588进而批评“事虚文而弃实用”的金末遗风,认为“三代无文人”,“六经无虚文”,以“以实为用”为基点调和文统与道统。
再如,金末人王若虚认为即便是“科举之文”,也需要“尽其心”而“造其妙”,做到“辞精”“意明”“势倾”,为此,就须:“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 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敌功无勍,可以高视而横行矣。”[21]他为经义程文开出药方:以欧苏菁英、《语》《孟》渊源为文,做到有气象,勿怪勿僻勿猥,文从字顺。
另外,阎复、陈栎、王恽等人对此问题同样表达了相应的看法。 阎复主张辞章与义理兼备,以此革除场屋弊病,进而使诗赋归复到“丽以则”的本真:“俾削拘挛之态,庶还丽则之风。 格虽守而必文辞之可观,辞虽尚而亦义理之为主。 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内;取古今气,艳于程文规矩之中。”[10]234-235陈栎对程文的基本要求是:以明经为本,文不绮靡,文字通顺。 而为实现这样的基本要求,他认为应坚守文与道的合一,他特别强调,文与道,实非二致,而具体做法则是:“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渊源,以词章壮其气骨,文于是乎无弊矣。”[22]
王恽也主张调和文统与道统,他本人虽未经历科举,却对科举认识颇深,一方面批驳科举之士痴迷功名,对家国大事懵然不知,甚至毫不关心:“迨魏晋隋唐以来,慕高尚者以虚无为宗,干利禄者以科举为业,其视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为何事。”[23]2430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及金祚垂亡,其伏节死义者皆前日之进士也”[23]3074之事实,故此并不抹杀科举的益处,且积极主张恢复科举:
迨隋,始设进士科目,试以程文,时势好尚,有不得不然者。 至唐有明经、进士等科,既明一经,复试程文对策,中者虽鲜,号称得人,至有“龙虎将相”之目。 其明经立法敷浅,易于取中,当时亦不甚重,又别设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经为经义。 其赋义法度严备,考较公当,至于金极矣,后世有不可废者!然论程文者,谓学出剽窃,不根经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谊蔑闻,亷耻道丧,甚非三代贡士之法……愚谓为今之计,宜先选教官,定以明经、史为所习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拣俊秀无玷污者充员数,以生徒员数限岁贡人数,期以岁月,使尽修习之道。然后州郡官察行考学,极其精当,贡于礼部,经试、经义作一场,史试、议论作一场。 廷试策兼用经史,断以己意,以明时务。 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不习之史,进退用舍,一出于学,既复古道,且革累世虚文妄举之弊,必收实学适用之效,岂不伟哉?外据诗赋,立科既久,习之者众,亦不宜骤停,经史实学既盛,彼自绌矣。[23]1762-1764
王恽看到程文成为虚文的原因是由“时势好尚”导致,责任不在科举制度本身。 对于前代科考内容他并没有采取偏激的态度,而是理性看待:经义科,在宋朝“法度严备”,考较公允,在金代,士子破碎六经固不可取,但对于经学的传播起到一定作用,故不可以尽废;诗赋,在理学家眼里本是无用之物,但考虑到立科既久,其存在有合理的地方,他也认为不可骤然废停。 他主张开设科举当以经史实学“革累世虚文妄举之弊”,若士趋向于实学,则“必收实学适用之效”,并建议礼部贡举“经试经义作一场”,“史试议论作一场”,廷试则“兼用经史”。 王恽较为积极地主张调和文统与道统,“至唐踵上代之衰,理弛文弊,道统益微,及韩愈氏出,以道济自任,隄障末流,廓清义路,盖皇皇如也。”[23]2822同样,他以“文道合一”的立场称赞韩愈“黜邪觝异”,“以道济自任”,重振“道统”,扭转“理弛文弊”的困局。 其《追挽归潜刘先生》云:“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23]734王恽追挽刘祁的诗歌中明确主张,“伊洛之学”与“韩欧古风”并用,文与道并重。
元初提出“科举累人”的文人,其中主张调和道统与文统者汇辑如下:
方回:学海者何?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垂世立教,董、韩、欧、邵、周、二程、朱、张之著书立言,皆是也。[6]301-302
刘辰翁:故尝谓韩欧当平世,崇辨拒邪,又在关洛之先,杨墨之外,为学校功宗。 皆所谓天地立心者也。[7]100
吴澄:若他文(朱熹文章),则韩、柳、欧、曾之规矩也,陶、谢、陈、李之律吕也。[8]267
王义山:学致于道;造乎孔孟颜曾;言发而文,蔚若欧苏韩柳。[14]45
胡衹遹:唐士气卑陋极矣,而生韩文公、李翱、张籍、皇甫湜。 陵夷于五季,至宋而生周、邵、欧阳、曾、苏、程、张、朱文公。 今之学者幸而无科举利禄之诱,凡有城邑皆设学校、树学官,当此之时而不学,趋末利而隳大德,凡庸自弃,可羞之甚也![17]235
刘将孙:盖欧、苏起而常变极于化,伊洛兴而讲贯达于粹……紫阳于文得其缠绵反复唱叹之味,故其论说则辞顺而理明。”[24]
从中不难看出,元初文人充分认识到文统与道统是互相协调的关系,所以采取文、理综合的态度,打破了“文道为二”的局面。 同时,诸多文学家本就是理学家,而诸多理学家又身兼文学家。也正因如此,由元入明的宋濂编撰《元史》时,将元代理学家与文学家统合于《儒学传》中,可谓是对元初文人文统与道统合一的思想进行了深刻体认。
结 语
要之,元初文人批驳“科举累人”的本质是折衷道统与文统的体现。 正是如此,元人对科举有特殊定位,“夫道一而已矣。 科举所以崇道义,非欲徼利达;经术所以淑性分,非欲资口耳;文辞所以敷心术,非欲饰葩藻、长浮华。”[2]6科举、经术、文辞都是服务于道的,文即是道的外显形态,道是文的内隐本质,文道两者不可分离,因此科举作为道的一种载体,体现了文与道的结合。 元代科举考试第一场经问的选取文章标准即是文道合一,“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1]2019由此看来,延祐复科的意义不仅是元朝统治者“以夏变夷”的深化,也是南北文学、学术思想融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