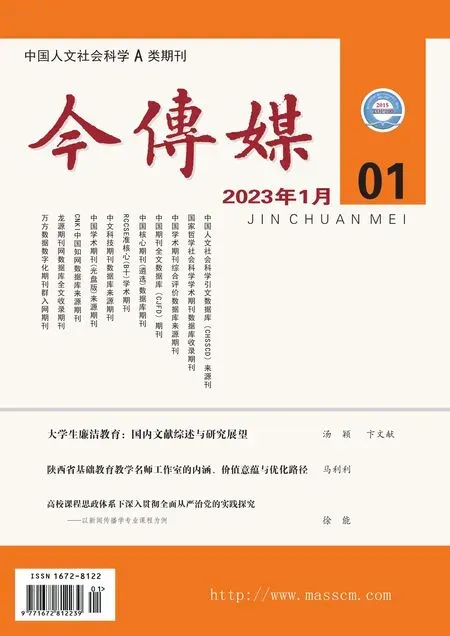短视频的使用与乡村社会图景建构
2023-03-06卞琳琳
卞琳琳
(西藏日报社,西藏 拉萨 850000)
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到如今的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大众传播媒介愈发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和个人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丹尼斯·麦奎尔将传播、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大众传播被视为 ‘社会’现象,又是 ‘文化’现象,大众传播机构是社会机构的资讯组成部分,它的技术基础是经济和权力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传媒所传播的社会思想、形象和资讯显然是我们文化的重要方面”[1]。如今,传播媒介已然成为了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乡村社会生活而言,这种影响更为突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闭塞结构逐渐被打破。在今天,中国乡村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容量接受着来自外部的、城市的、现代化的大量信息的冲击,而这些信息大部分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
媒介社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对外界的认识不断更新并与时俱进,但是,相对而言,人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处于忽视和停滞的状态。新媒体出现后,技术赋权使得乡村社会有了对外传播与表达的平台和能力,尤其是当下各类短视频APP盛行以及手机功能不断丰富,录制并向外界展示乡村生活的短视频开始流行起来,成为了展示和了解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
一、乡村短视频内容类型分析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赋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多元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蓬勃发展、相互融合。与此同时,随着新媒介技术等传播基础设施在乡村的普及,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农具”成为了乡村社会个体展演、形象宣传、营销增收的重要工具。短视频的繁荣已经对乡村文化和经济建设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并且形成了自身的题材类型、美学风格和生产模式[2]。目前,学界对乡村短视频并未有明确、权威的定义,本文分析的乡村短视频指以乡村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短视频,视频制作者或上传者通过视频记录、展示和传播个人的乡村日常生活、地方特色美食或家常美食、地理风貌以及民风民俗等,传受双方通过视频内容联系在一起。
目前,活跃在微博、抖音、西瓜视频和哔哩哔哩等平台的乡村短视频制作者有很多,许多视频制作者甚至在“三农”领域已有较大的影响力,比如,“牛二条”“川乡小妹”“滇西小哥”“野居青年”。这些视频制作者通过展现不同地域的乡村生活,向受众呈现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原生态内容,而这些内容也为受众进行群体划分奠定了基础。
如今,各个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上的乡村短视频内容多样,较为常见的类型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乡野美食制作
食物来自于大自然,是人与自然最直接的联系。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尤其是对生活在城市的受众来说,直接从田野到餐桌的食物是他们很难获取的,而视频制作者却可以在田野上、深山中、大海里轻松获取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因此,受众会乐于观看此类短视频,以满足自身渴望亲近自然、获取自然馈赠的精神需求。在这类短视频中,视频制作者一般以获取原生态食材、制作家乡传统美食为主要拍摄内容,他们不仅仅是呈现一种简单的美食和制作方法,更重要的是让受众接收到不同于自身生活的文化冲击以及身临其境的真实体现感和满足感。
(二)日常生活呈现
乡村短视频的聚焦点在于乡村,因此,乡村的日常生活、邻里相处也是视频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日益紧张的快节奏生活和强调距离感的人际交往给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而乡村短视频正是以制作者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为主要内容,其中所呈现的亲情关系、邻里的和睦相处、日常生活的平淡温馨是吸引受众的亮点,这种呈现不仅给予受众视觉上的享受,帮助受众放松心情、释放压力,更给他们带来了心理和情感的满足。
(三)特色资源展示
广袤的土地孕育了不同的风景、物产和习俗,这些均是乡村的特色资源,对当地的受众而言,家乡的特色资源是一种情感的归宿,对其他受众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在乡村短视频中,视频制作者家乡的特色资源能够增加视频内容的趣味性,更容易激发受众的好奇心,比如,当地的景色风光、特色农产品以及逢年过节时的特色民俗。同时,乡村特色资源对远离家乡的游子而言是难以割舍的乡愁,更易引发情感共鸣,因此,特色资源也是乡村短视频吸引受众的又一重要元素。
二、乡村短视频的关注图景与内容偏向
(一)符号化的乡村短视频与乡村生活
法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在 《符号学原理》一书中结合叶尔姆斯列夫的含蓄意指符号学,界定了符号意指的两个系统,即直接意指第一系统和含蓄意指第二系统。他认为,“一个被含蓄意指的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且“在含蓄意指的符号学内,第二系统的能指是由第一系统中的记号所组成”[3]。
在乡村短视频中,一方面,“乡村生活”一词与视频内容 (包括视频中的具体人物、生活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人物的行动等)构成了“乡村生活”的直接意指第一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乡村生活”一词为能指,具体的视频内容为所指。即乡村短视频的关注图景与内容偏向包括原生态食物和传统美食、乡村日常、地方美景、特色民俗等具体而直接的元素,它们是当下众多类型的乡村短视频最能直接表现出的语言和符号,共同构成了“乡村”和“乡村生活”的直接意指第一系统。
另一方面,具体视频内容所拥有的特质、特色与形象标签丰富了“乡村生活”一词的内涵意义,构成了含蓄意指第二系统。比如,在田野、深山和海洋里寻找食材被贴上了“原生态”“绿色”的标签;乡村美丽的田野风光展现被赋予了“贴近自然”“远离世俗”等含义;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场景被认为具有“温馨”“温暖”等感觉。于是,在含蓄意指这个层次上,“乡村生活”一词的内涵得到了广泛拓展,它的所指不再具象化地集中在某一具体生活场景上,而是泛化地指向了乡村社会生活所共有的某些“特质”。
(二)乡村短视频关注图景与内容偏向的构建
目前来看,乡村短视频的关注图景与内容偏向所指向的乡村生活“特质”大多具有正向、积极、美好的意义,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乡村生活场景进入城市生活,而城市生活中激烈的竞争给人们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焦虑,人们渴望“逃离”城市,走出当下的困境。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环境更加宜居,因此,人们希望能够在乡村中获得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并根据既有印象赋予了“乡村”和“乡村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其次,在当下愈发完善的乡村环境下,乡村短视频打破了以往受众对乡村的刻板印象,这种反差和冲击使受众更加向往美好的乡村生活。最后,短视频制作者在呈现内容时不可避免地会迎合受众的心理和需求,对美好乡村生活的关注和强调进一步强化了受众的观念。
乡村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文本,以特有的记录形式表现了乡村文化之外的受众对“异域”的想象 (即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以及乡村社会生活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媒介所呈现出的乡村生活图景符合目标受众的生活经验和美好想象,是一种群体归属与精神寄托,代表了一种文化和身份认同。传播者通过媒介和乡村短视频的形式对外传播并建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为了迎合部分群体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和期待;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乡村通过短视频形式进行的一种对外表达与传播。
乡村短视频作为呈现和建构乡村社会的载体,包含了乡村生活的诸多方面,从美食制作、田间劳作到地理风貌、民风民俗以及视频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内容由一个个具体的表意符号组成,其背后蕴含着制作者和传播者对乡村社会的理解。并且,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性,它是在人们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完成意义的赋予和增殖的。因此,制作者和传播者利用表意符号呈现乡村社会景观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受众的影响。
综合来说,乡村短视频所呈现和建构的乡村社会图景是在传播者与受众的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内容诉求、不同爱好倾向以及不同思维观念的综合作用下,通过媒介开展交流与互动,逐渐磨合并共同塑造出来的虚拟图景。
三、乡村社会生活:虚拟与现实对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某种程度来说,乡村短视频所展现出的乡村社会图景与实际乡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出入和差距,或者说,乡村短视频所呈现的是一个“拟态”的乡村社会,是一种被美化和强调的“乌托邦”式的乡村生活图景。在乡村短视频的呈现和建构中,许多乡村社会问题被弱化或忽略了,短视频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存在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同时,这种虚拟图景与现实的乡村社会生活又相互影响。
(一)虚拟图景:美好祈愿与情感寄托
在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是被表述的“沉默的他者”,乡村是被凝视的“隐秘的角落”,短视频激活了农民和乡村的“可见性”,完成了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出场”,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作为农民所处的“背景”被嵌入了叙事结构中[4]。
乡村短视频兴起之初,内容质量参差不齐,不乏有一些以低俗、猎奇、搞怪为卖点的内容。在这类短视频的叙事结构中,乡村是“落后的”“愚昧的”“低俗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部分受众对乡村的旧有印象。但是,经过几年的筛选和过滤,这种猎奇乡村短视频的关注度明显降低,甚至会引起受众的反感,原因在于低俗、落后、愚昧与当前乡村的发展方向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众通过媒体的宣传以及人们的口耳相传和亲身感受,对乡村的印象已经改变。同时,短视频的兴起不仅拓宽了外界观察乡村的渠道,也让乡村能够更为顺畅、真实地“表达”自己,使得乡村形象和生活图景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生活其中的人,还是外界的受众,都对乡村有了更多期待。乡村短视频中构建起的虚拟乡村图景,对乡村生活美好特质的展现、赋予和强调,更是一种美好祈愿。
人类拥有漫长的乡村生活史,人类早期文明的孕育与演化都是从乡村开始的,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大多是乡土社会环境的产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乡土、乡村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感,乡土中国的社会联系纽带和文化习惯依旧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维系着社会的团结与协作关系。在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人们对乡土的记忆和情感凝结为一种乡愁,传统乡愁的实体通过互联网媒介转化为精神上的追寻,这是一种放弃了地理差异、文化返乡的情感活动。因此,短视频中的虚拟乡村图景之所以会被构建,更大程度是一种情感寄托的体现。
(二)回归现实:身份认同与乡村发展
无论是乡村短视频的制作者、传播者还是受众,他们都认为短视频中的内容要源于现实生活。正如孙信茹教授在谈及网络民族志时所提到的,“网络媒体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5]。媒介社会化背景下,网络媒体的介入为受众或者说媒介使用者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空间,尤其对乡村社会而言,媒介的使用与普及、城乡人口快速流动、大量现代化信息的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闭塞结构,乡村传统文化也逐渐被消解。但是,短视频的火爆逐渐将实体地域空间虚拟化,制造出了庞大的虚拟空间群像。农村网红们的田园短视频借此成为了人们心灵的可栖息之所,媒介的介入和新的信息也同样在创造和建构着新的乡村社会图景以及新的乡村文化[6]。
将短视频中对乡村图景的建构放置于现实中来看,它最根本的价值就是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身份认同。一方面,乡村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发布视频,发现了以往被忽视的乡村生活现在正被高度关注和正向肯定,创作者和传播者在获得受众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话语权,可以更充分地进行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乡村短视频吸引了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焦虑、渴望回归平淡生活的受众,它不仅寄托着受众的焦虑、不安与痛苦,也让聚集起来的受众发现自身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个例,从而获得了共鸣和认同。
乡村短视频的兴起让视频创作者获得身份认同的同时,也让他们和乡村看到了更多的发展可能。现在,短视频正在以一种新的生产资料的形式提升乡村生产力,推动乡村振兴,从售卖特色农副产品到创办企业、带动当地群众就业,从传播乡村文化到提升农民文化自信、推进乡风文明,乡村短视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让无数人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在为乡村振兴聚民智的同时,也推动了短视频中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
四、结 语
社会发展、技术赋权,乡村短视频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乡村真实面貌的平台,也让乡村有了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积极的因素推动乡村和农民通过短视频不断提升自己,也有消极的因素使乡村和农民在互联网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迷失。因此,如何更好地抓住媒介和技术带来的机遇,不断减少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我所用,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