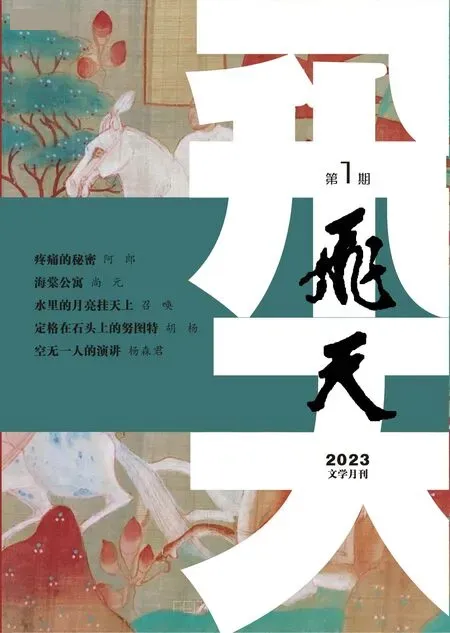宁家庄:深埋与流淌
2023-03-06吕敏讷
▶吕敏讷
1
像中国西北地区所有的村庄一样,宁家庄朴素、安详、憨厚,藏在山窝里,一条河流边。它像一个坐标,用名字指证了它的气质和环境。
这三个汉字站在一起的时候,看着有些随意简单,它身上却潜藏着时间的厚度。它们身后隐藏着无数的意象,这些意象叠加起来就会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在那里有可以看得见的人类上古文明,也有人类历史长河中贝壳一样散落沉潜在泥沙中的物质遗存。
西汉水与大柳河交汇之地,形成一个三角台地,宁家庄就在这两条河流所形成的臂弯里安坐。这一条臂弯,伸向哪里,哪里就有一连串的房舍、祠堂、学校、树木、田块;也会有一连串的阳光、果蔬、清风、脚步、欢笑。这条由水流形成的臂弯,柔软明亮,为村庄涂上一层光晕,也把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和现存的一切都揽入怀抱。农耕传统顺着水势,从远古一直流向这里,在土层里积淀沉潜,在村庄保存完好。这里土地平旷肥沃,气候温润分明。在群山绵延的陇南山地,宁家庄却显出独有的一份空旷之感。在今天,这座东西长约500 米,南北宽约350 米的袖珍土地上,人们保持着春种秋收,耕读传家的秩序,劳动并且读书,在与泥土万物的亲近中渗透着文化的张力。一座屋舍俨然的现代化的村庄,依然流露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浓厚气息。村子里随处可见的戏台,文化墙,照壁,处处有文人辞赋、对联书法,村间小道散发着墨韵书香。
路边有百年的五培子树,参天而立,把一座寺庙庇护在它的身下。寺庙红色的外墙上刻着“道法自然”四个大字,好似在诠释着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某些规律。田间,一切秩序井然,田畴像一幅画卷在房舍周围展开,菜蔬密密麻麻,枝上果子繁盛。随意走进一户人家,辣椒串挂在屋檐下,苞谷堆在院边。也有日光温棚,是现代化规模化的蔬菜产业。一幅农耕生活的美好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村子里建起了笤帚加工厂,用高粱秆编制笤帚的农妇农夫,就地取材,在家门口勤劳致富,他们手脚并用,麻线在指尖和脚尖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把固定装置绑在腰间,还让牙齿来帮忙,让高粱秆的材料顺从地变成一把把大小不一形制各样的笤帚,工厂墙壁上有一行字:一双巧手绑出幸福生活,一把笤帚扫出窗明几净。他们做工,欢笑,简简单单地生活。这些手工,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又显示出了一份弥足珍贵。恍惚间,我觉得这些做工者,是从某个遥远的朝代穿越而来的,他们是农耕时代的原住民。
在当地方言里,“宁”字读作入声,它像村庄的姓氏,走在村庄的前头,是村庄的领队。而事实也是这样,村子里的人就是以“宁”为姓。在用来当做一个姓氏放在人名前面读出来时,它是铿锵有力的,刚正果断的,而写成汉字,在纸上见到它的字形时,我依然感受到的是这个汉字后面所包含的安静从容。像一个人,时光在他身上堆积出大密度,褶皱起伏不平,露出沧桑,有些肃穆,但有质感,少去了一些浮华躁动,多了一些沉稳,呈现一股厚重的力量,因而显出镇定自若,安宁不慌张。这是安静的内涵带给人的美感。宁家庄恰好给人这样的美感。我喜欢厚重而安详的东西,在最深厚的时光积淀中尽显岁月静好,流露出一份大安宁。
隔着一条西汉水,就是秦早期先祖的墓冢所在地,名扬中外的大堡子山。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时的战地故垒祁山堡,也酷似一架巨轮,停靠在西汉水的另一边。
人类沿河而居,生存离不开水,内心世界亦离不开水。水的现实意义是孕育人,滋养人,水的精神意义是利万物而不争。水有现实功用,水也代表时间长河。水和时间的共性是,储量丰富,永不回头,带走一切,也留下一切。人类文明起源似乎都离不开河流,最初的发祥地都在一些大河流域,长江、黄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如此想想,两条河流围成的臂弯里的宁家庄,是河流领会了上天的旨意,让它们前来缔造这个村庄,并在时间的河流之上,早已为这里要发生的一切设定好了细节。
2
大柳河,的确是一条被柳树裹敷的河,虽然河水已经变瘦,但从宽阔的河道和石块流沙可以推测出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数千年之前河水的宏大气象。两岸垂柳绿云堆积,给河水镶嵌出两道可以随风飘摆的花边。河边有一个叫川口的地方,据说,曾经人们沿着古道去往四川,就是从这里出发。川口,是远行的一个起点,它像陇蜀古道上的一个眉眼,照见远方,作为一个旧码头,川口承载了无数的出发与归来,它让大柳河一度熙来攘往。这条被《水经》称作鸡水的河,在它的17.17 公里处完成了使命,在宁家庄那里注入西汉水。
西汉水,一条在商末周初的三千多年前孕育了诗经的河流,在更加久远的史前时代就参与了人类探路阶段的生生不息。人类数百万年的生存锻造出优越的自然禀赋,早在五六千年前,宁家庄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西汉水也同样孕育了宁家庄。时间的河水从遥远之地轰鸣而来,裹挟着宏大的叙事,带来人类历史演进中无数奇幻而又珍贵的讯息。今天的宁家庄地面及断崖上,随处可见暴露灰层、红烧土、陶片等,一些石器、红陶、黑陶器文物出土以后,经学者考证,它们属于仰韶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先民们刀耕火种,达到史前文化的巅峰。宁家庄是陇南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遗迹,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也能在这里找到依据。
人们喜欢用河流来比喻时间,逝者如斯永不回头。我沿着时间的河流朝上游走,据说,在这里的土层里,现在还能捡拾到彩陶的碎片,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史前,让目光在宁家村跟不同时代的文明来一次华美相遇。
历史书里关于出土文物的文字介绍,总是让人觉得遥远而又生硬,毕竟,只言片语的概括显得太苍白,不能让我真正感知数千年时光的神秘和厚度。但是当我走进宁家庄历史博物馆,看到展柜里各式各样的彩陶、灰陶、红陶、绿釉陶、酱釉、青釉、彩绘,我一下子就把今天和过往联系起来。这些展品有单耳红陶罐、双耳灰陶瓮、陶鬲、灰陶钫、灰陶熏炉、灰陶漏碗、灰陶盆、灰陶鸡狗、陶仓、灰陶灶、灰陶水井、灰陶皈依塔、彩绘牡丹纹砖、酱釉碗、齐寿瓷枕、青釉吼狮……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汉、唐、宋、元……在这些器物面前,我仿佛看到了时间的流淌,它们像承载时间的一个个容器,时间被烧制成不同的形态和体貌被保存下来,通过土层留给后世,让后来的人可以目睹时间存在的意义。不同的展品,身上都带着泥土的本色和气息,可以看出,人类的早期,一切器物主要满足于实用需求,造型随意,外形朴素,颜色质朴,线条简单,纹饰是自然界的草叶或者鱼鸟蛙,泛着一种原始的朴拙之美,可以想象那时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人类对于美的追求没有止步,一旦满足了实用需求,修饰和美化就从未歇脚,磨光、涂刷、堆纹、刻纹、雕镂、彩绘,让器物不单是一个实用意义上的器具,还有了艺术层面的美感。对于造型、纹饰、手感、工艺的追求,让器物成了一个审美载体。事实上,很多器物很难分辨它是用来实用的还是用来审美的,比如,我在那个汉代的灰陶熏炉前,久久站立,想象如果古人将香料点燃,袅袅香气从顶部的孔隙缓慢飘出,在那些山峦一样起伏的线条图案间缭绕着一层白雾,此时,谁能说得清它更美还是更香呢。那些兼具实用和审美的事物,经由时间之手,变成一件件珍贵的文物。
因此,博物馆更像是一个保管时间的地方。宁家庄博物馆,让我生出这种感念。人类早期文明的碎片,就变成这些陶器,作为最具有见证性的一种符号,供我们参观。我们透过它照见上古的生活场景,它们是时间之河的上游捎来的礼物。
大地像个神秘的容器,善于包容也擅长保管,它是天然的艺术家和史学家。宁家庄就是大地之上一个幸运的村落,它承载、接纳、安放了时间的秘密。
3
在一截高出地面的土垄前,我看见标示牌上的文字:宁家庄遗址文化层,是现存较为完整的古遗址文化层,距地表一米左右,暴露明显,遗存丰富,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把目光投向面前黑褐色的土层,这土层里出土过着大量的陶罐、陶盆、陶钵,石斧、石刀、石铲,我想象到上古时期的生活场景,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以泥土为原料,烧制陶器生活用品,用它们舀水、盛饭、储存、祭祀;以石头为原材料,打制尖利的工具,用来切割、砍伐、取火、开垦。先民们用他们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在属于他们的赛道上奔跑,加速文明的演进,还培植了“五谷”,驯养了“六畜”,建造房舍,创制祭礼。
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些彩陶碎片,像上古的时间遗落在土层的某种语言,携着一道道光,来到今天的宁家庄面前。也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穿越时空,与先民进行一次次对谈。
百年之前的1921年7 月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开幕,它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而正当此时,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正带队准备前往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三个月后,他到达那里,受到时任县知事的亲自迎接。安特生时任世界地质学会的主席,是当时中国政府聘请的地质学家,他和中国地质学家,奥地利古生物学家一起对仰韶村落下考古学的第一铲。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瑞典人的到来,竟成为改变中国考古学领域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此次开掘揭开了仰韶文化的面纱,以这个村子命名的一种人类史前文化——仰韶文化诞生,现代中国考古学也从此诞生。学者们认为,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命名,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距今七千到五千年的史前文化的样貌如何,我们从何而来将去向何处的追问,答案就藏在地下。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与1921年安特生的那一铲遥相呼应,时隔六十年之后,西汉水上游的宁家庄,一个农夫手中的铁锨在土层里落下,作为一个重大的补充,这一锨,为仰韶文化添加了新的内容。
4
1982 年3 月的一个清晨,大地复苏,泥土松软。宁家庄一个叫宁万顺的人,在村子北侧自家的宅基地里劳作,他要为建造新房打土基做准备,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埋头面对土层,对泥土做着精细的手工。漫长的劳作,他脚下的土层慢慢出现一个浅浅的凹坑,这些土,在他的铁锨、镢头翻耘过后,拥有了恰当的干湿度和粘度,常年与泥土打交道的手,对泥土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土堆在模具上慢慢变成一块又一块长方形的土基子。打土基需要大量的土方,宁万顺的铁锨继续向土层深处开挖,这一次,当铁锨从土层里拔出来时,宁万顺察觉到土质的颜色和质地有所变化,他知道那种灰层土并不能制作出坚固的土基。他的铁锨在灰层土里翻动清理,此时,一个扁圆球体状的土疙瘩来回滚动,在散落的土粒当中,它显得与众不同。宁万顺将这个圆土疙瘩捡拾起来准备抛向旁边的石堆,就在触碰到的那一刻,他的手敏感地掂量到这个土疙瘩里包裹的并不是一块石头。在当地,人们认为土层里挖出来的是墓葬品,因此有所避讳,很多东西都会遭遇丢弃或者砸碎的命运。当宁万顺清洗掉表层的泥土,这个扁圆的袖珍球体上泛出一种柔和的橙黄色泽,仔细打量,隆起的表面还有黑色花纹,线条简单舒展,颜色古旧朴拙,这一切让宁万顺都觉得非常舒服,他看着这个圆融饱满中空、上下有圆孔、对称美观、色泽莹润的小器物,凭直觉是一个吉祥之物,就把它当做摆件,放在自家最显眼的地方——堂屋简陋朴素的八仙桌上。
1982 年的村庄,普通人家的八仙桌上,应该还没有一件像样的摆件。这个叫宁万顺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或许对泥土有着一种天生的审美,他是一个真正的有心之人。
奇妙的是,这个被大地包藏了几千年的器物,在土层深处穿过无穷暗夜,自从它重见光明,再一次获得呼吸,接受一个农夫之手的摩挲和目光的端详,它就拥有了一份幸运和福祉。如同一粒被黑夜包裹的珍珠,在等待命运的转折。时光积淀,有一天,它摆放的位置,也从一个农家木桌一跃变成聚光灯下的展柜,历史为它预留已久的这块专有展台,早就在那里等待一个主角归位。
甘肃省博物馆的华美展柜里,一件彩陶文物,像一个表演者站在盛大的舞台之上,灯光聚焦在它身上,观众的目光凝结在它身上。它在世人面前展示出的端庄外形,高雅质地,柔和色泽,时光印痕,无数次吸引观瞻者和研究者的目光。下方的标注牌写着:彩陶权杖头。
我在宁家庄新建的村级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是这件文物的复制品,它的上方有放大了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彩陶权杖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982 年西和县长道镇宁家庄遗址出土。高7.6 厘米,大口1.9 厘米,小口1.3 厘米,最大腹径12.6 厘米。器身通体彩绘,上半部释弧线勾叶纹,下半部以十字形均分四瓣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考古学者许永杰认为,宁家庄的彩陶权杖头是氏族或部落的原始宗教崇拜信仰物,为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或酋长专用。这可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权杖头。
被这段文字注释的那件真品文物,它从宁家庄出发,去往县城文化馆,再到达省城博物馆,还一次次赶赴了国外的展出。
有人高度评价这件文物在全省乃至全国彩陶文物界的广泛影响,认为它是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里的一件扛鼎展品。国家一级文物。它的体积之大,国内绝无仅有。
5
再说回这件文物当年的身世,巧合的是,它的命运传奇仍然与姓宁的两位前辈有关。一位是宁家庄的宁文举,他是一位教师,是大书法家。他在宁万顺家串门偶然见到桌子上的这个摆件时,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直觉,断定了它的非同寻常,但他只是嘱咐这位邻居好好保存。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同为教师和书法家的好友宁世忠时,两位宁老师不谋而合,相约一起立即找文化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的同志,并一同去了宁万顺家。这件器物,被当场确认是一件出土文物,宁万顺表现出一个农民特有的憨厚质朴,将器物立即上交。宁万顺只说了一句话:文物是国家的,我上交是应该的。
这个器物被带到文化馆保存后,工作人员对它的用途及命名各执己见,难以定论。它像生活用具,但上下穿孔,不能盛装食物;像编织工具纺轮,但体积和穿孔较大,不易旋转;它造型优美,但体型较大,也不是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于是约请甘肃省和天水市博物馆的专家对器物的形制、纹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形略同于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及秦安大地湾发现的权杖头,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评估,鉴定,确定宁家庄出土的这枚器物是一枚彩陶权杖头,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氏族或部落的首领或酋长手杖上的专有镶嵌物,它是权力的象征。
据说,后来的表彰大会上,县文化馆奖给宁万顺一个搪瓷洗脸盆,用以表彰他深明大义的精神。
两位姓宁的前辈,早已作古,而他们的墨宝像他们在书法文化方面的盛名一样永久留存。宁万顺也已经年近古稀,在村子里安安静静生活着,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某一天能到省博物馆看看当年的这个土疙瘩。
这枚彩陶权杖头像一个桂冠,戴在宁家村的头上,成为村庄的荣耀,也让村子在文明与文化传承的光影下,拥有了一份独特的气质。
6
宁家庄的幸运还在于,赶上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这样的好政策,青岛市投资援建宁家庄时,并不像大多的投资者,只看到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坚硬苍白的空壳,砌墙、修边沟、修路、引水、筑防护栏,让钢筋水泥简单代替土木构架的村庄,相互模仿,千村一面,以牺牲村庄的精神内在特质为前提搞形式意义上的表面翻修。宁家庄的建设,能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把宁家庄仰韶文化遗存这个重大的文化层面凸现出来,它像一面高高竖立起来的旗帜,扛起了村庄的精神高地,彰显出村庄本来拥有的文化气息。村子里建成一座宁家庄历史文化博物馆,宁家庄由此也成了一个东西协作示范村。这个隐匿在大山深处的小村,揭开了裹敷其身的繁复外衣,曾经被土层埋藏的都经由时间之手还给这里的土层,曾经由人类创造的都经由时间之河还给人类。村庄被厚重的历史文化熏染,一朝涅槃,便展现出它应有的气质,站在时间的水墨中。
这一天,参观完宁家庄博物馆,我在村子里某一个照壁前,一字一句阅读由宁弋撰文,年轻的书法家沈澎先生书丹的《宁氏家训》碑刻。
祁山之阳,汉水之旁。
有古人类,仰韶荣光。
我宁家庄,源远流长。
稼穑耕读,繁衍顺昌。
先贤海清,望重一方。
其母贤淑,施粥送粮。
与弟祷天,舍己救娘。
孝感天地,后辈敬仰。
……
文字顺畅,书法高古。宁弋是宁文举先生的侄子,好书画诗词赋,也善民俗研究。也是村子里文艺范的婚礼主持人。受宁老先生的影响,村庄出现了宁弋、宁兴源、宁勇一批书画家。沈澎是宁文举先生的外孙,家就在邻村,是清华大学书法研究生,书法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在宁家庄,书法家画家学者,文人辈出,文风兴盛,手工艺人代代相传。稼穑耕读,读书与种田相得益彰的宁家庄,让我明白,文明、文化和文脉也像一条河流,是一种可以流淌延续的事物。
正是深秋,土层依旧用上古的深厚广博接纳承载着每一个人,田里劳作的人和来此观瞻的人;鸟儿用史前的叫声向我打招呼,水用传说中的柔软照拂诗经、唐诗、宋词和现代流行风;风从七千年前吹来,吹红了枝头的苹果,吹绿了菜地,停驻在这一片活色生香的土地之上。
土地,是深埋人类历史的温床。土地,是人类文明的纸张,它是最忠诚的历史官,不会因个人喜好爱憎漏掉某些真实的成分,也不会在人类的蝇营狗苟面前扭曲掩藏雕饰。我想,假如时间中存在过的一切终将在记忆中消失,那么,我相信最后剩下的真相,一定都埋在脚下的土层里,并且,在我们不易察觉的地方汩汩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