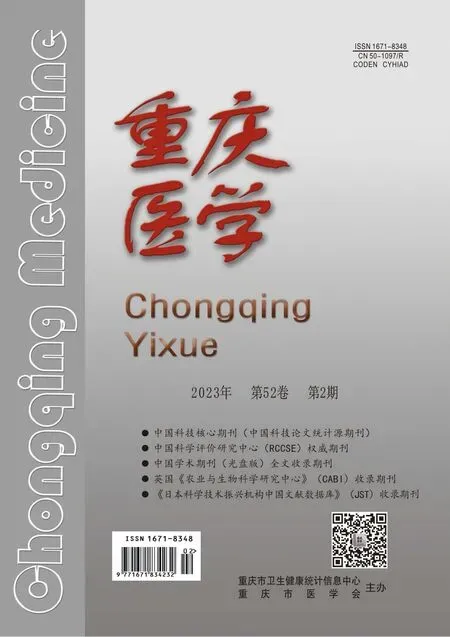免疫治疗时代下肺结核对肺癌发生、发展及治疗策略的影响*
2023-03-05倪婷婷综述审校
李 燕,倪婷婷 综述,唐 菲,张 瑜,3△审校
(1.遵义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贵州遵义 563000;2.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科,贵阳 550002;3.国家卫生健康委肺脏免疫性疾病诊治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02)
结核病是全球单一感染源致死的头号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987万,而中国是全球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患病人数居全球第2位[1]。近年来免疫治疗的应用使得肺癌的治疗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肺癌仍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症,2020年中国肺癌死亡人数近71.5万,占全部癌症死亡率的23.8%[2]。结核病可以发生在人体的多个部位,其中80%发生在肺部,而肺结核患者的肺癌发病率是非肺结核人群的2~4倍[3-4],合并肺结核的肺癌患者的死亡率是单纯肺癌患者2.36倍[5]。在高发病率及高死亡率的疾病负担下,深入探索肺结核与肺癌发生发展的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重点与难点。肺结核和肺癌都涉及免疫逃避策略的过程,这些免疫破坏机制促进了肺结核和肺癌的发展,本文对免疫治疗时代下肺结核与肺癌的相互作用机制及治疗策略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合并肺结核的肺癌患者寻找有效干预靶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肺结核是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1.1 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的慢性感染及组织修复促进肺癌的发生
肺结核是由MTB引起的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这种长时间的炎性反应及其伴随的肺组织广泛重塑可能是肺癌发生的原因之一[6-8]。有研究显示,慢性MTB感染会诱导细胞发育不良和鳞状细胞癌,且这种诱导是肺组织特异性的,提示肺结核与肺肿瘤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9]。一方面,MTB可直接诱导被认为具有促癌作用的炎性介质的释放,例如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2、IL-12等[10-14]。另一方面,活化的巨噬细胞、白细胞会募集到MTB感染部位并产生大量活性氮和氧、组织破坏性蛋白酶、前列腺素、细胞因子等,引发严重的炎性反应,导致组织损伤和基因组改变,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15]。此外,MTB感染在导致肺组织损伤的同时会激活组织修复机制以控制病原体,在组织修复过程中,结核肉芽肿附近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化及瘢痕。研究发现,肺癌可以从结核瘢痕(瘢痕癌)发展而来,结核腔的上皮可发生化生并在旧的结核病灶中向恶性病变发展[6,16]。总体说来,长期感染MTB的肺组织经历了多个炎症和组织损伤/修复过程,这为肿瘤发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增加了肺癌发展的风险。
1.2 MTB感染后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可能促进肺癌发生和发展
MTB可在宿主体内长期存活,这期间会激活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免疫细胞的改变可能会促使免疫微环境发生恶性转化[17],有研究认为,肺结核患者肺癌发病率的增加可能与MTB感染后免疫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状态密切相关[18]。
巨噬细胞是MTB的首选宿主,受MTB感染的巨噬细胞不仅可通过氧化应激产物诱导其附近的肺组织DNA损伤,还产生上皮调节蛋白等生长因子刺激正常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的增殖,导致鳞状化生和肿瘤发生[9]。有研究显示,在与MTB 感染的人单核细胞共培养后,人肺腺癌细胞的侵袭性明显增强并出现上皮间质转化特征。此外,巨噬细胞产生的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IL-6、IL-10 和 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可直接作用于上皮细胞,诱导肿瘤的发生并促进肿瘤持续生长[19-22]。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是肿瘤微环境中浸润的主要免疫细胞之一,通常分为 M1及M2型,其中M1型TAMs与肿瘤的良好预后相关,而高度M2型TAMs的浸润与肿瘤进展、侵袭、转移和对肿瘤治疗的抗性密切相关。在肺结核的早期,巨噬细胞可通过上调M1表型以增强吞噬作用、增加促炎细胞因子分泌水平以清除MTB,然而,随着感染引起的炎症增加,M2型TAMs在肺结核晚期中逐渐占优势[23]。据报道,M2型TAMs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s)募集到肿瘤微环境中,且M2型TAMs表达更多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和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从而削弱了T淋巴细胞消除癌细胞的能力。此外,M2型TAMs可促进IL-10、TGF-β等分子的表达,这些分子在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及血管生成中发挥作用,直接影响肿瘤进展。因此,肺结核中M2型TAMs表达的上调可能是导致肺肿瘤形成的原因之一[24-27]。
T细胞活化是抗肿瘤免疫的关键因素,当CD4+T细胞减少时,机体免疫监视功能降低,免疫逃逸增加,从而促进肿瘤的形成[18,28]。与其他肺部感染相比,MTB感染后T细胞反应延迟,主要表现为CD4+T细胞缺乏。meta分析表明,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肺结核患者体内CD4+/CD8+T细胞比率明显降低,尤其是新诊断病例[29]。此外,肺结核患者的T细胞信号转导蛋白CD3ζ和NF-κB的表达降低、组成型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磷酸化激活,这可能是这类患者发生T细胞功能障碍从而逃避免疫反应的原因之一,在肿瘤患者中同样观察到了相似的变化,这种共通的免疫抑制机制可能与结核病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30-32]。
程序性死亡受体(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PD)-1和PD-L1信号通路激活可导致T 细胞的功能受损及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形成,阻断该信号通路可恢复T细胞功能、逆转肿瘤免疫微环境并增强内源性抗肿瘤免疫作用[33-34]。活动性MTB感染患者的CD4+T细胞上的PD-1表达同样增加,且患者接受抗肺结核治疗的有效性与效应T细胞上PD-1表达减少相关[35-36]。近期研究发现,肿瘤抗原和MTB抗原共同刺激可使小鼠T细胞上PD-1及PD-L1的表达均增加,且MTB感染小鼠的肺转移数量及体积较未感染小鼠明显增加,但在PD-1敲除小鼠中并未观察到这种差异,提示MTB可能通过PD-1/PD-L1信号通路抑制免疫反应并促进肺癌转移,可见,PD-1/PD-L1免疫调节通路可能成为未来研究肺结核和肺癌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靶点[37]。
2 肺癌所致免疫抑制增加MTB的感染或诱导潜伏感染再激活
2.1 肿瘤本身引起免疫功能低下促进肺结核发生
多项meta分析显示,与普通人群相比,癌症患者患肺结核的风险明显增加,肺癌患者患肺结核的风险比一般人群增加约6倍[38]。肿瘤患者通常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状态,肿瘤对免疫系统的损坏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激活淋巴细胞来启动适应性免疫反应发挥抗肿瘤作用,而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外周血和淋巴结中DC的数量和功能都会降低。此外,在NSCLC中发现的骨髓抑制细胞可浸润肿瘤引流淋巴结并抑制初始T细胞的启动,这使患者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39]。另一方面,由于能量代谢异常、抗肿瘤治疗致胃肠道毒性反应、营养摄入受限、胃肠道吸收功能障碍、感染、心理精神因素等原因,肿瘤患者常常呈现营养不良状态[40],而营养状况决定了免疫系统的细胞和分子成分的产生和功能,这些成分负责人体对包括肺结核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的抵抗力。研究证实,患者针对MTB感染的免疫反应会因营养不良明显下降[41]。
2.2 细胞毒性化疗所致免疫抑制促进肺结核发生
已有研究证实抗肿瘤治疗是肿瘤患者发生活动性肺结核的独立危险因素[38,42]。针对肺癌的抗肿瘤治疗,尤其是化疗常常导致免疫抑制,使患者更容易受到机会性病原体的感染。化疗药物可明显杀伤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重要的免疫细胞,包括NK细胞、吞噬细胞、T细胞及B细胞等,如氟尿嘧啶可明显抑制抗感染的关键细胞——中性粒细胞的迁移,导致感染MTB的风险增加[39]。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影像学上陈旧性肺结核与抗肿瘤化疗是肿瘤患者发生肺结核的重要危险因素,且二者似乎对活动性肺结核的发展具有协同作用,该研究中,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的癌症患者在影像学上观察到陈旧性肺结核的比例高达90.9%,而在未合并活动性肺结核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6.5%。因此实体器官恶性肿瘤患者活动性肺结核的发展更有可能归因于MTB地再激活而不是再感染[42]。
2.3 免疫治疗后机体免疫功能改变促进肺结核发生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是晚期 NSCLC 的突破性疗法,在选定的亚组中具有提高总体生存率的巨大潜力,其基本原理是使调节性免疫途径受控地下调,启动和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从而导致免疫介导的癌细胞识别和破坏[43]。如前所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中CD4+T细胞上的PD-1表达增加,理论上来说,使用ICI阻断PD-1/PD-L1对抗T细胞耗竭,增加CD4+和CD8+T细胞活性将同样有助于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治疗肺结核,然而,在MTB感染中,PD-1/PD-L1通路的作用是有争议的。体外实验显示,阻断CD4+T细胞和巨噬细胞上的PD-1/PD-L1通路增强了它们对MTB的吞噬作用和细胞内杀伤作用,表明该通路在MTB感染中具有负调节作用[36]。然而,体内实验显示,在慢性MTB感染的情况下,阻断该通路不足以挽救效应T细胞的功能,缺乏PD-1的小鼠对肺结核的易感性和致死性均增加,这可能与肺部过度炎症和不受控制的细菌增殖有关。据报道,来源于CD4+T细胞的γ-干扰素(IFN-γ)负责脾脏中80%的细菌清除率,抑制PD-1可限制CD4+T细胞产生的IFN-γ,加重MTB感染和早期宿主死亡率,这提示CD4+T细胞中PD-1下游信号传导在小鼠MTB感染期间发挥保护作用[44-46]。
在真实世界中,一系列病例报告描述了肿瘤患者在使用PD-L1阻断治疗后发生了活动性的肺结核[47],近期一项回顾性分析显示,297例接受ICI单药治疗的肺癌患者中有5例在治疗期间发展为活动性肺结核,目前其发生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但现有数据显示,MTB 感染的症状和体征多数在使用 PD-L1抑制剂后6个月内出现,考虑为潜伏性肺结核感染再激活的可能性大[48]。与之相反,一项来自韩国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在接受ICI治疗的5 037例肿瘤患者中有0.4%的患者在治疗开始后的中位时间2.2个月时被诊断出患结核病,并且80%为肺结核,但在调整了潜在的混杂因素后,ICI治疗与结核病风险增加没有明显相关性,该研究认为,ICI治疗所致高结核病发病率可能是由于潜在的恶性肿瘤导致而不是暴露于ICI,此外,使用免疫抑制药物(如皮质类固醇)来管理ICI给药后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也可能导致该患者群体发生结核病[49]。另一项队列研究针对接受一线化疗的晚期NSCLC患者,其结果同样显示加用ICI并没有额外增加患肺结核的风险[50]。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来确定接受ICI治疗对肺癌患者肺结核发展的影响。
3 抗肿瘤治疗与抗结核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3.1 细胞毒性化疗联合抗结核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抗结核药物如异烟肼和利福平,可导致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并损害肝功能,而这也是抗肿瘤化疗可能导致的常见不良反应。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合并肺结核的肿瘤患者同时进行抗结核和抗肿瘤化疗时,在临床反应、影像学改变及毒副反应方面与普通肺结核患者均没有区别,提示细胞毒性化疗并不是治疗肺结核的障碍[51]。近期的两项研究显示,加用抗结核治疗并不会改变肺癌患者对抗肿瘤治疗的反应率、中位生存时间及副作用,提示在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的肺癌患者中,同时进行抗癌和抗结核治疗是安全且有效的。但目前几乎没有研究可明确抗结核治疗与化疗的最佳开始时间。据报道,抗结核治疗2~4周后痰菌转阴,这似乎是开始化疗的合适时间,也有研究显示化疗与抗结核治疗同步进行是安全可行的,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52-53]。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均是针对活动性肺结核而不是潜伏性肺结核的肺癌患者,而我国作为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潜伏性肺结核的人群庞大,是否应对合并潜伏性肺结核的肺癌患者进行预防性抗结核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抗肿瘤治疗前对高危患者常规进行肺结核筛查是必要的。
3.2 免疫治疗联合抗结核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由于担心ICI可能导致宿主免疫失衡并发生irAE,肺结核患者常常被排除在ICI临床试验之外。近期一项来自中国的队列研究中纳入了45例、21例和32例分别被诊断为活动性、潜伏性和陈旧性肺结核的肿瘤患者(其中NSCLC占总人数的79.4%),3组患者接受抗PD-L1治疗的反应率、中位生存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同时接受ICI和抗结核治疗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73.3%,其中13.3%为3~5级,未出现意外的毒性作用,其中仅3例患者出现肺结核复发[54]。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报道了13例肺结核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安全性,研究认为,免疫治疗对合并潜伏性肺结核的肺癌患者相对安全,未发现潜伏感染地再激活及活动性肺结核的进展,但其中1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因严重irAE死亡[55]。目前在肺癌免疫治疗期间治疗活动性肺结核的临床经验有限,尚无循证推荐,但建议在抗PD-L1治疗前进行结核筛查,在合并活动性肺结核的患者中应更加谨慎地监测irAE。此外,另一个重要的临床问题是,在活动性肺结核的背景下,ICI和抗结核治疗的顺序、间隔和时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4 小 结
肺结核与肺癌共存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是一项重大挑战,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机制亟待更深入的研究。在肺癌治疗前,对高危人群如既往曾患结核病、长期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患者进行肺结核筛查是必要的;在肺癌治疗期间,应对高危人群进行重点监测,尤其是当患者出现无法用肿瘤解释的临床症状或影像学表现时,应早期进行肺结核的排查。此外,对于合并肺结核的肺癌患者,就现有的研究而言,抗肿瘤治疗联合抗结核治疗是相对安全的,但必须高度重视疾病的监测、治疗措施的相互影响及抗肿瘤治疗的毒副作用管理,尤其是免疫治疗等新治疗策略的应用时,应综合权衡治疗利弊,力争为患者提供最佳的精准治疗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