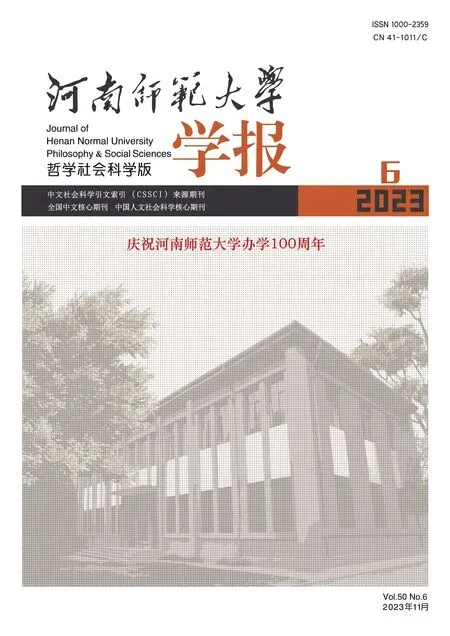国际法中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研究
——基于国际法院实践样本的分析
2023-03-04王玮
王 玮
(北京交通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91)
一、问题的提出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145, para. 290.。早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签订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1条中(2)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rticle 1.,即规定各缔约国承担着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且尽量避免诉诸武力解决的国际法义务,要求各国竭尽全力以保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宪章》第1条(3)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 Article 2.,要求会员国以和平方法且依据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在第2条中要求各会员国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协商谈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重要方法,善意协商谈判义务也是国际法中一项重要的义务。《不扩散核武器公约》(NPT)第6条明确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针对核裁军问题进行善意协商谈判(4)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rticle 6 “each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undertakes to pursue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on effective measures relating to cessation of the nuclear arms race at an early date and to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on a treaty on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rmament under strict and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ntrol”.,国际法院甚至在多个过往案例中确认善意协商义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义务并且明确表示该义务已经构成习惯国际法,例如在1996年关于使用核武器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中(5)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96, p.226.,作为主席的贝贾维(Bedjaoui)法官在判决的个人宣言中,同国际法院的相关论述一致,再次确认了善意协商义务的重要性,认为该义务并非限定存在于NPT第6条之中,而是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在国际法上存在着事实上的双层一般国际法义务(two-fold general obligation),国家不仅在行为上有义务寻求善意协商,并且在结果上应当达成期望的成果,这样才算符合善意协商义务的双层标准。他明确指出,通过各国在该领域内的一致和正式的同意,该寻求善意协商和达成明确结果的双层义务在过往的至少50年间,已经取得了习惯国际法的地位。 但“善意”这一概念具有天然的模糊性,在国际法上何为“善意”?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条约解释方法中,以及在协商谈判义务上加入“善意”的要求涵义为何?在国际法院的其他案例中,国际法院如何界定善意协商义务,如何对该义务进行考量和具体适用,国际法院对善意协商义务的态度和倾向又是如何?善意协商义务是行为义务还是结果义务,是否要求协商各方必须达成一定的成果?
二、国际法院实践中对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情况概述
从国际法院官方公布的所有案例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6)List of All Cases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cij.org).,国际法院在所呈现出的全部163份文件中,对善意原则这一大类有所涉及的案例在所有案例中大约占比23%。在这些案例中,国际法院将善意原则分别具体适用为善意协商义务、程序性事项中的合理时间内通知义务以及诉讼前置条件中的善意协商和外交沟通、禁止滥用权利和禁止反言、条约解释的指导规则、单方承诺的效力等类型。在不少案例中,国际法院仅仅强调善意原则的重要性和地位,阐述了条约必须遵守与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性和价值导向,而无展开论述与深入探讨。纵观国际法院所有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发现国际法院针对善意原则的三种适用类型给予高度重视,在多个相关案例中进行较大篇幅的详细论述。这三种类型,首先是善意协商义务,占所有涉及善意原则案例的37%之多;其次是程序性事项中的善意协商义务,占比27%;再次是禁止滥用权利。综合来看,国际法院针对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高达64%。在这三个类型的案例中,尽管存在个别法官的不同意见,但整体上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善意原则,并给出了相对详细的标准和较为明确的观点和立场。而在其他类型中,国际法院更多的是对善意原则的浅层涉及,例如条约解释和单方声明的效力类型。相对于国际法院对善意原则的涉及情况,常设国际法院(PCIJ)对善意原则的重视程度明显较低。在常设国际法院官方所呈现的所有案例中,只有5个案例对善意原则有所涉及(7)Series A/B: Collection of Judgments, Orders and Advisory Opinions (from 1931)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cij.org).,除了“赫尔佐工厂”一案(8)PCIJ: Chorzow Factory Case (Merits) (1928) A.17, p.29.,在其他案例中均没有详尽展开善意原则的适用问题。总体来看,常设国际法院对善意原则的适用主要集中在善意协商原则这一类型上。
三、国际法院在具体案例中涉及善意协商义务的适用方法分类探讨
(一)在案件实体判决中对善意协商义务进行定义与考量
国际法院倾向于将国际法中较为笼统的善意原则直接等同于或具体化为善意协商义务,并强调其在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在国际法院对善意原则有所涉及的案例中,该种适用类型占比最大。针对善意协商义务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国际法院几乎在每一个涉及善意协商义务的案例中都对善意协商义务在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肯定,例如在渔业管辖权案中(9)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Iceland),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aras.78, 79.,国际法院就明确在判决主文中表示:“解决争议的最合适办法,明显就是协商谈判。”针对善意协商义务是否可以单独创设法律义务这一问题,国际法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但整体来看,国际法院的倾向为善意原则虽然是一项基础性的国际法原则,但并不具有独立创设法律义务的功能,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在尼加拉瓜边界行动案(10)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5, p.665.以及1998年海洋与陆地边界案(11)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8, p.275.中,国际法院均认为是否违反该种善意协商义务要结合个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针对善意协商义务是行为义务还是结果义务这一问题,国际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的态度并不一致。国际法院在关于太平洋主权许可善意协商义务案(12)Obligation to Negotiate Access to the Pacific Ocean (Bolivia v. Chile),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8, p.507, para. 86.中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根据国际法院的观察,善意原则并不包含一种具体的承诺,不要求产生具体的后果。而在1996年的使用与威胁适用核武器咨询意见(13)Th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f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C.J. Reports 1996 (I), p.264, para. 99.中,国际法院的立场则是针对该项义务给出了更高的要求,设定了更高的门槛。正如前文所述,认为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6条中所规定的针对核裁军的善意协商义务为双层义务,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求各方进行积极寻求协商谈判的行为,同时还要求各方基于这种协商行为达成一定的结论和成果。从这点来看,相对于单纯的行为义务,国际法院明显在该咨询意见中给出了一个更高的结果要求。从相关国际法院案例的整体倾向分析来看,国际法院更倾向于在非核裁军领域内认为善意协商义务仅仅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在核裁军领域内对善意协商义务采取更高的结果义务标准,可能是由于关于核武器的使用和核裁军等问题事关重大。针对善意协商义务的具体审查要求,国际法院在多个案例中给出了自己的审查要点和标准,例如北海大陆架案(14)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I.C.J. Reports 1969, p.47, para. 85.、爱琴海大陆架案(15)Aegean Sea Continental Shelf (Greece v. Turkey),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8, p.3. para. 20.、渔业管辖权案(16)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Iceland),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aras.78, 79.等等。总结来说,国际法院要求各方在出现国际争端时应当积极寻求协商,并且必须是真诚而有意义的协商,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程序要求或达成诉讼前置条件走形式。在协商过程中要考虑对方的合理利益,不能固执己见,要准备作出妥协和改变。在纳米比亚咨询意见(17)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71, p.16.中,国际法院不同于以往模糊的态度,少有地明确认可了联合国在一个长时间段内作出的一系列努力,认为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联合国在积极寻求协商谈判的一系列行为中并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尝试妥协和修改自己原有的立场,寻求各种解决争议的提议供双方协商,是符合善意协商要求的。在该案中,国际法院鼓励了一种充足的协商努力行为和诚恳的协商态度,将当事人在公众场合作出的一系列发言与行为中所体现的态度作为考察是否满足了善意协商义务要求的重点。在渔业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提到引导各方进行善意协商也是国际法院的一项司法功能,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引导各方进行协商,并为各方提出了善意协商的一些阶段性目标。
国际法院尤其重视当事国的善意协商义务的具体履行情况以及协商态度,要求当事国必须在协商谈判的过程中展现真诚的态度和愿意改变自己立场而作出努力的姿态,在一些特定案例中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审查标准,例如细致考察当事国各方之间的外交沟通记录和谈判细节。在纳米比亚咨询意见(18)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71, p.29. para.79.中,国际法院就对联合国的善意协商行为予以高度认可,并认为对方拒绝沟通或者不愿意变通、商量与妥协的态度是违反善意协商义务的。虽然国际法院在过往的案例中并没有直接明确一国违反善意协商义务的法律责任是什么,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善意协商义务的违反会对该国产生各方面的负面影响。
从具体案例来看,国际法院在一些案例中提出了对善意协商义务的考察标准。在2011年“临时协议适用案”中,国际法院重点讨论了善意协商义务,认为善意协商原则要求各方不仅要进入协商谈判的状态,而且要有明确的目的,尽可能地推进谈判进程。国际法院考察了本案中双方之间沟通协商的详细记录,认为通过行为可以体现一国的善意态度、是否具有开放性等。如果一方固执己见不准备进行任何意见调整和立场妥协,或者无视谈判议程和程序,都是违反了有意义谈判的要求。另外,国际法院在本案中认为善意协商是一项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不能仅仅因为没有达成阶段性成果就认定一方违反了善意协商义务。在这一点上与1996年核武器咨询意见相悖。该案也对这种行为义务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考察标准,例如是否不合理延迟协商,是否无视双方已经达成的协商议程与程序,是否拒绝沟通,是否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是否完全坚持己见不作出妥协,等等。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对什么是“有意义”的善意协商谈判提出了具体考察标准。在1984年“缅因湾地区海上划界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双方应当进行善意协商,以最终达成有效的成果为目标,同时认可善意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观点。在1980年“国际卫生组织与埃及协议解释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要求各方应当进行善意合作,无论何时都应遵守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进行咨询和协商。此外,还应当共同处理后续安排和新的地点的确定等事项,并指出各方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对方利益的变动行为之前,应在合理时间内通知对方。在1978年“爱琴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要求各方对善意协商义务的履行不能是浅层次的、表面的、走程序的,而是充分而真诚的。在1974年“渔业管辖案”中,国际法院明确指出协商谈判是解决国家之间争议的最合适途径。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对各方提出了善意协商义务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例如确认各方之间的目标是划分关于渔业利益的边界,做好各方利益的平衡;要求谈判应当至少涵盖几个基本的问题,例如如何划定捕鱼权范围、如何确定捕捞限制额度、如何限制和分配各方的捕捞额度和权限,各方在针对这些目标和问题进行谈判时必须秉持善意的原则。国际法院在该案中梳理和引述了其过往案例中对善意协商义务的认定和论述成果,重申善意协商应当具有意义,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程序性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国际法院同时认为,指导和指示各方进行善意协商也是国际法院应适当履行的司法功能之一。在1971年“纳米比亚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给出了独特的针对是否满足善意协商义务的考察方式,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国际法院针对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管理机构存续争议,详尽考察了联合国与南非二十多年间的沟通交流,并认为联合国在过去长时间内没有固执坚守一开始的立场,而是以达到双方一致为目标,考虑对方的合理利益,并一直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设立特别委员会来促进沟通和解决。国际法院通过考察联合国的一系列行为和决议内容,最终给出了明确论断,认为联合国在针对该项问题上的表现和努力“毫无疑问”地符合了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但对方体现出来的协商谈判态度是固执原先立场,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和改变,因而也是违反善意协商义务的。
国际法院在一些案例中强调了协商义务的重要性以及习惯国际法地位。在2020年“豁免与刑事诉讼程序案”中,国际法院提示善意协商义务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要求各国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遵循国家之间友好和平共处原则。同时将善意协商义务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联系起来,提到合理性、非歧视性等原则,也提到善意原则作为条约解释的指导原则。在2010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咨询案”中,国际法院同样确认善意协商义务的重要性。在1995年“东帝汶案”中国际法院确认各方承担着善意协商与合作的义务。在 2019年“贾达夫案”中,国际法院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的内容是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在善意原则的指导下解释国际条约已经取得了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即使一方当事国不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当事国,也并不妨碍这项习惯国际法义务对所有国家产生约束力。国际法院也在本案中提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的必须遵守的义务,认为各国有义务善意地履行在国际条约项下的义务,并且有义务进行善意协商。国际法院认为应当结合和审查所有相关情况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善意。例如巴基斯坦从程序开始到结束,没有向国际法院提供过任何有关贾达夫在其国家的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的相关材料的行为,即体现出善意原则和公正程序的缺乏。在1988年“总部协定案”中,国际法院提及各国应当作出善意协商谈判的努力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善意协商谈判应当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项重要方式。在1996年“武装冲突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核心武器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作出了关于善意协商义务的重要论述,依据NPT第6条的内容,认为NPT所指的针对核裁军的善意协商义务是一种双重义务(two-fold obligation),要求各方善意寻求协商谈判,但不能仅仅满足于协商谈判的行为,而是要求各方协商谈判出一个结果。在马歇尔群岛诉核大国的一系列案例中,申请方马歇尔群岛主要基于1996年核武器咨询案中国际法院对NPT第6条的认定,国际法院则重申1996年咨询意见中的观点,认为针对核裁军的善意协商义务是双重义务,不仅仅是行为义务。然而这一针对核大国的起诉最终以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告终,所以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国际法院并没有对起诉书中涉及的核裁军善意协商问题作出具体回应。
(二)在案件程序性事项中适用善意协商义务
针对第二大类的程序性事项中的善意协商义务适用,国际法院倾向于在以下三个细分类别中具体讨论善意协商义务:
第一类为跨境环境污染案件,各方在行动前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测并及时通知对方,并做到信息共享与合作沟通。在这类案件中,国际法院将善意协商义务等同于一种纯粹的程序性义务,具体可以细分为通知义务、信息共享义务、合作义务、沟通义务等等。例如在2015年“圣胡安河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在相邻国家之间进行工程建造项目可能造成跨境环境风险的时候,施工方应当首先进行环境影响评测(EIA),并按照程序性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及时通知利益相关方,并且及时分享信息(19)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15, p.665.。 在2010年“纸浆厂案”中,与上述2015年“圣胡安河案”相类似,国际法院重点阐释了善意协商义务包含通知利益相关方的要求,要求在进行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行为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测(EIA)并及时将情况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各方,并使用“特别利害相关方”(specially-affected states)的概念。在1993年“磷酸盐土地案”中,国际法院对善意协商义务的认定类似于前述的2015年“圣胡安河案”与2010年“纸浆厂案”主要是将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具体细化为应当在工程可能造成跨境环境污染和影响时及时通知利害相关方并及时分享相关信息。
第二类为关于国际法院管辖权建立中的善意协商义务。例如喀麦隆与尼日利亚之间陆地与海洋边界案(20)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Judgment, I.C.J. Reports 2002, para. 244.与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与准军事行动案(21)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I.C.J. Reports 1984, p.421, para. 65.等,国际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对善意原则的核心要求是,一国不能为了规避被诉而紧急撤回和修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在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与准军事行动案中,国际法院认为美国在短时间内通过修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来规避尼加拉瓜针对他的起诉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也是缺乏善意的。Ajibola法官在喀麦隆案的不同意见(22)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8, p.275.中的观点值得注意,认为在不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后立即提起诉讼的行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这会导致双方之间的诉讼与信息优势的不平等,有违善意原则和公平原则。Ajibola法官在该案中举出一个友好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范例,鼓励各国在诉至第三方争议解决机制之前,双方应当直接达成特别协定(Special Agreement)(23)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Dissenting Opinion, Judge Ajibola, p.397.,各方同意任何一方在合理给出通知后都有权诉至国际法院,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前通知对方诉讼意愿和相关行动,并且不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如在“庇护案”中当事方的做法,这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善意协商义务具体要求的,该立场可以算作Ajibola法官个人对何为善意行使“诉权”以及满足善意协商义务的一种理解和标准。国际法院在此案中对善意协商义务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主要是关于管辖权确立阶段,一国仅为在国际法院起诉他国而临时修改管辖权声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行为是否违反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引述了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与准军事行动案中的论述,认为在尼加拉瓜案中美国为了逃避针对自己的起诉而提前几天修改针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在喀麦隆诉尼加拉瓜案中不能完全类比这种判断,国际法院并没有认定喀麦隆的行为是明显违反善意协商义务的,虽然如前述个别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认为喀麦隆的行为也是不能被接受的。起诉方认为对方违反国际法院颁发的临时性程序措施指令的行为是违反善意原则的,国际法院仅仅认为临时性程序措施的指令具有创设法律义务的效力,对双方是具有约束力的,但没有直接回应起诉方认为违反国际法院指令是违反善意原则的观点。
第三类为关于起诉前置条件是否为双方直接的协商谈判与外交努力。国际法院在有些案例中认为双方之间协商谈判穷尽后提起诉讼是满足善意协商义务要求的,但对何为“穷尽”以及何为“谈判进入死局”的标准认定并不统一。有四个此类重要案例值得注意,分别为1924年常设国际法院的马夫马提斯案(24)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Greece v. U.K.), Preliminary Objections, 1924, P.C.I.J. (Series A) No.2, p. 15.、1962年西南非洲案(25)South West Africa (Liber v. South Africa;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I.C.J. Reports 1962, p.319.、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行动与准军事行动案(26)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I.C.J. Reports 1984, p.420, para. 63.和2011年CERD案(27)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Qatar v. United Arab Emirates), Judgment, I.C.J. Reports 2021, para.78.。这一系列时间跨度较大的案例体现了国际法院对诉讼前置性协商问题从宽到严的立场转变。早在1924年常设国际法院的马夫马提斯案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起诉方给出起诉的通知即可,不强制要求各国诉前的外交救济手段被穷尽。在接下来的西南非洲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争议方在公共的或多方的场合例如通过联合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即为满足各方诉讼前置性外交努力的条件,甚至两国在起诉前完全没有直接外交交流的情况下,国际法院也认为满足了特别协议中所述的前置性谈判要求,可谓门槛极低。在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又将标准降低,否认了美国认为尼加拉瓜在起诉前没有进行充分的解决问题的外交努力的观点,认为尼加拉瓜在起诉时抄送美国并向美国给出关于争端的通知这一事实即足够确立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但国际法院这种针对诉讼前置条件门槛松弛和开放的风向到2011年的CERD案出现改变,国际法院在该案中认为没有满足诉前善意协商义务的条件,因而不可确立条约中约定的管辖权,与之前态度相反,国际法院认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仅仅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沟通并不符合诉前充分的外交努力和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对作为诉讼前置条件的善意协商义务和外交行为设立了较高的门槛和标准。国际法院的这一态度转变又回到其在另一些案例中认为充分的善意协商是解决条约最有效的方法,而诉至国际法院应为最后一道防线等观点。但即使国际法院在该类问题上存在不一致立场,也并不妨碍CERD案可能引发的一些重要影响。根据国际法院在该案中表现出的倾向,国际法院很可能会在后续有关涉及诉讼前置条件的满足问题上,认为善意协商义务和外交努力并不是简单地通知对方争议的内容和诉讼信息,而是鼓励各方首先要尽全力通过直接协商谈判来解决争议,以此来满足善意协商义务的要求。但在2020年ICAO理事会管辖权案中,各国签署的《芝加哥公约》第84条明确规定了提起诉讼的前置条件为完成善意协商义务。国际法院要求各方真诚地付出努力进行协商,但对善意协商义务的完成作为起诉前置条件的达成条件的认定并不苛刻,只要达到谈判出现死局或达成协议的标准即算完成。国际法院认为经过几轮谈判之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则可以认定为前置条件达成。国际法院的态度又形成了不一致的演变。另外在 2000年航空事故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院管辖权的确立与各方持续善意协商谈判义务并不冲突,即使不能建立管辖权,也不妨碍各国继续善意寻求和平解决争议的方案并作出努力,认为善意协商义务的满足是诉至国际法院的前置条件。
(三)其他类型案例中的适用
在其他类型的案例中,国际法院对善意协商义务的认定和描述更多是一笔带过,倾向于将善意原则这一概念作为一顶“帽子”,一项“平衡性”或“兜底性”的国际法原则,仅仅强调其重要性或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论述。在有的案例中,当事方在诉状或答辩状中明确提出对方的行为违反了善意协商义务,而国际法院对该观点不作直接回应与详述。
四、结语
善意协商义务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重要部分和具体表现形式,在国际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具有天然的模糊性。因此有必要详细考察国际法院对该义务的认定态度与立场。关于善意协商义务的具体要求,国际法院在过往案例中分别考察了几项要素,包括:(1)各方是否真诚、有意义地进行了谈判协商的系列活动,国际法院倾向基于各方沟通记录与历史、公开场合表态等内容进行判断;(2)各方是否愿意考虑到对方的合理利益并且不固执己见愿意作出相应的妥协和退让;(3)各方是否不合理拖延协商,不考虑与尊重已经商定好的谈判协商议程;(4)是否拒绝沟通;等等。关于善意协商义务到底是行为义务还是结果义务,是否要求达成相应的谈判结果才可算作满足善意协商义务这一点,国际法院在几个案例中体现出相悖的立场,在1996年核武器咨询案中,国际法院认为NPT第6条的善意协商义务为双重义务,不是简单完成协商谈判的行为即可满足该义务,而是要求达成一定的成果;而在另外的案例中,例如2011年临时协议适用案中,国际法院又认为善意协商义务仅仅为结果义务,不涉及对协商谈判结果的要求。然而,尽管国际法院并非在每一个所涉及善意原则的案例中都对善意协商义务给予重点关注并提出细化的审核要点,也并非在相似问题上的观点保持一致,而是可能出现完全相悖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院对善意协商义务较为重视,其对善意协商义务的判定与倾向,对中国的国际法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各国也都应当在国际法实践中重视对善意协商义务的实践与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