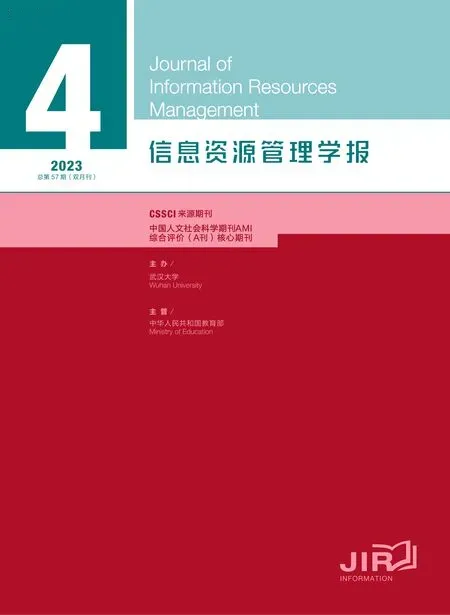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历程、挑战与展望
2023-03-03陈传夫朱传宇彭敏惠
陈传夫 朱传宇 彭敏惠 吴 钢 陈 一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2.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430072)
自1920年至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过百年,在这百年间,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也经历了兴起、稳定发展、繁荣、专业化四个阶段。从印本时代到今天的智能环境,图书馆学教育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专业人才与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者。但是,在瞬息变化的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了学科生态环境、学科建设模式、学生就业能力等新挑战,面对新文科教育的发展机遇,迎接这些挑战,总结图书馆学教育百年成就,探索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培养新一代图书情报领导者的方法与路径,对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历程
根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图书馆学教育活动特点,本文将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1 第一个三十年(1920—1949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
20世纪初以来,全球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中国结束封建统治,民众对文化的渴求加快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等顺应历史变化,多名图书馆学教育先驱,筚路蓝缕,初创了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1.1.1 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图书馆学教育兴起背景
国际上,工业革命掀起了欧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高潮。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向公众开放借阅、为公众教育服务是时代潮流,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主流机构。麦维尔·杜威于1887年1月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教育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国内,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积弱积贫,民众识字率较低,据估算调查,当时文盲达3.3亿人,占总人口的75%,并有5000万儿童正在成为文盲[1],迫切需要推广社会教育。虽然清政府在1908年发布了《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计划到1914年识字人口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当时时局不稳,政府无力,教育难以维系。因此,多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组织、公益性机构兴办识字学校、学堂、夜校等,湖南、浙江等地政府也将图书馆作为民众的教育机构,古越藏书楼等中国古代传统藏书楼系统也从封闭式转变成了对外开放式。19世纪末,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藏书楼,1905年之后,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图书馆,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民国初年颁布了《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图书馆事业得到发展,图书馆学教育逐渐兴起。
1.1.2 文华图专: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开端
新图书馆运动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图书馆事业发展需要专业人才,这对图书馆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李大钊先生说发展图书馆学教育“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2]。
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等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兴起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20年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是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的教育机构,标志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开端。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1861年8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曾任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The 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首任馆长,1899年来到中国,先后募款创办文华公书林,为民众阅读提供服务。她促进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并将其用于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办文华大学图书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1926年,她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出席ALA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1927年,她代表协会出席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发起成立国际图联的决议上签字,使中国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的创始发起国之一。沈祖荣是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的留学生,担任文华图专校长达20余年,主要著作有《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等,1929年,他作为中国图书馆业界的代表,参加了在意大利举办的IFLA的第一次大会。胡庆生于1917—1919年就读于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并兼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学位,1926年至1928年任文华图书科主任。
留学生是图书馆学教育初创时期的重要教师资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留学生赴海外学习的大学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哥伦比亚大学、菲律宾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学校、伊利诺伊大学等,戴志骞、杜定友、洪有丰、袁同礼、李小缘、刘国钧、杨昭悊、李燕亭等留学生归国后为兴起中的图书馆学教育提供了师资保障。
文华图专的教师队伍由海归学者、外籍教师、传统儒士和本土学者组成,以毛坤、汪应文、皮高品、吴鸿志等人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大约占当时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二,海归学者主要代表有沈祖荣、胡庆生、汪长炳、沈宝环、田洪都、徐家麟,外籍教师主要代表有韦棣华、华玛丽、费锡恩、周爱德,传统儒士主要代表有李希如、许学源[3]。文华图专师资在国籍方面,中外兼有,以中国为主;在教育背景方面,中西兼有,以本土教育为多;在教学资历方面,大多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实践经历;在传承延续方面,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注重师资的培养。
随着学校发展和办学层次的提高,文华图专的课程设置渐成体系。文华图书科最初课程包括图书选读、编目、分类、参考工作等。经历1920年至1925年的探索,又增设了中国目录学、西洋目录学、图书馆史、图书馆建筑法、图书习字法、各科实习指导等课程。到1928年前后,课程发展为两个学年共19门,图书馆学专业科目达15门。1930年文华图专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有意识的分类,并形成了五个大类,分别为:专科目录类,主要课程为目录学、参考工作、书籍评选、版本学;学术科目类,重点教授图书馆技术实务,包括分类法、编目学、图书馆经营法、索引、打字、图书馆习字等课程;行政科目类,重点教授图书馆组织与运营,包括图书馆行政、各种图书馆研究、儿童图书馆、图书馆簿记大意等课程;其他科目类,包括中西图书馆史、现代史料、图书馆学讨论、金石学、古器物学、民众教育、通俗读物等课程;语言科目类,包括国文、日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课程。文华图专课程体系表现出“学习西方而不崇洋媚外,继承传统而不厚古薄今”的风格[4]。
民国时期的文华图专图书馆学专业在1949年10月之前入学者共345人,毕业者290人,其中曾经就职的所有或部分单位可考者247人,曾在图书馆任职的毕业生至少占毕业总人数的94%[5]。这一阶段,除了文华图专以外,其他机构也开展了图书馆学教育,包括:①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25年8月设立到1926年秋季学期结束,仅存在一年半左右,专任教师有杜定友,兼职教师有胡朴安、孙心磐、陈伯逵等,邀请了沈祖荣、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等担任临时教师,就读学生约14人,钱亚新、金敏甫等曾就学于此。②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27年在李小缘、刘国钧的推动下创办,设于文理科,学制两年,为辅修系,共培养了本科生34人、专科生11人[3]。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于1941年8月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成立,汪长炳任系主任,学制4年,为民国时期唯一的四年制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共有图书馆学毕业生4届,共81人[6]。④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47年王重民在北京大学创设,民国时期共毕业两届,大约15人。
1.1.3 图书馆学教育兴起阶段特征与成果
多名学者就图书馆学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展开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杜定友先生等人。杜定友提出中国图书馆学校的宗旨和目的,即提倡图书馆专门学术;养成图书馆专门人才;研究欧美图书馆管理方法;发挥中国图书馆学术;培养图书馆服务精神;图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这六条得到了当时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指导参考价值。
这一阶段图书馆学教育的总体特征是:①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数量少,获得政府支持不足,步履维艰。②以职业教育为主,部分学校存续时间较短。③课程体系融合中西,实用性强,毕业生能够较快适应图书馆的工作。④学生数量少,民国时期在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图书馆学毕业生不足400人,但毕业生有强烈的图书馆职业认同感,在图书馆就业的比例很高。⑤文华图专的教育探索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这一时期培养了皮高品、严文郁、徐家麟、毛坤、钱亚新、沈宝环、桂质柏等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向前发展。裘开明、钱存训是这一时期优秀学者的代表。裘开明是文华图专的首届毕业生,1922年3月毕业后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也是中国首位本土培养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担任馆长。1924年秋季,他到美国继续学习,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1927年开始了他在美国长达40年的图书馆生涯,他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创始人和首任馆长,从1927年至1966年,他虽然在多所大学的汉学图书馆中兼职,但从未离开过燕京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7]。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经称赞其为“西方汉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引路人”[8]。钱存训先生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47年前往美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唯一由华人撰写的分册《纸和印刷》,即出自钱存训之手。英国《泰晤士报》当时评价说:“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明尚属首次”[9],《人民日报》也评论他“是学术的骄傲”[10]。
1.2 第二个三十年(1949—1980年):图书馆学教育的稳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学教育稳定发展,多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设立,本科教育、成人教育与短期培训共同发展,专业性、层次性的图书馆学教育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拔尖人才和业务骨干。
代表性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是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1951年8月由文化部接管,1953年随院系调整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原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于文学院中文系下,1949年从中文系独立出来,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1956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均将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四年制本科,并正式建立图书馆学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急需专业人才。因此,除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外,文化部、教育部与各类图书馆也掀起了成人继续教育与短期培训的高潮。文化部于1951年和1954年分别在沈阳和北京开办了图书馆学的短期培训班,1956年北大、武大分别开设了函授的图书馆学专修科教育,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开办了图书馆的干部训练班等。1957年文化部等六单位在南京联合举办全国省市图书馆人员进修班,教育部在北京举办了高等学校图书馆员进修班。1958年,北京市成立图书馆干部进修学校,文化部成立了文化学院图书馆学研究班。这些培训班极大地提升了图书馆员专业素养与能力,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合格的图书馆人才。
1.3 第三个三十年(1980—2010年):图书馆学教育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设立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到设立图书馆学博士后流动站,这三十年是图书馆学教育繁荣发展的三十年。1977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恢复了图书馆学专业全国高考招生。1978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招收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1月,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1月,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首批建立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四次会议增设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评议组,11月,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授权点。2000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的授权点。2003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领域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三十年间,在政府的支持下,图书馆学教育人才培养规模扩大,形成了系统的、规范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
1.4 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化发展
随着国内外图书情报工作不断推进,设立专业学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01年,武汉大学向国务院学位办呈递“关于设置图书馆学专业硕士(MLS)学位的申请报告”到2011年3月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部等七部委联合召开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的会议,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从提出到正式设立历经十年,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开始。最近十年间,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较快,目前共有74所高校招生,且数量不断增多,累计招生超过了1万人。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培养规模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图书馆学教育愈加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化发展面向宽广的信息职业需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中国图书情报部门培养新型专门人才,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成就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一代代图书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学教育规模、体系不断扩大完善,中国百年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2.1 顶层架构: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家出台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相关政策、意见文件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导和支持,确立了图书馆学教育制度。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拟定《图书馆学、目录学科学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规划了二十世纪中期图书馆学的发展。1961年,教育部召开图书馆学专业教材编写会议,在教学计划中增加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和《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指出“有关院校要努力办好图书馆学系”[11]。1980年,刘季平馆长代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讨论通过,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12]。1983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发展和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几点意见》对图书馆学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全面、总体的规划和部署,同年,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工作座谈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讨论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改革问题。1984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1992年,国家教委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200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指导下,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2013年,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图书情报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将图书馆学所属“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名称调整为“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列为排序第一的二级学科。
百年来,国家发布的图书馆学教育政策对图书馆学教育进行宏观调控和指导,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规范化、有序化,图书馆学教育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图书馆学教育活动的高效开展,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2.2 系统框架:教育体系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从模仿西方到自主教育,建立起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的办学制度、学历教育与学位教育的办学层次、面向国内与国际的招生范围、开展职业培训与专业教育的教育体系。图书馆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逐步建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
2.2.1 人才培养规模
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均处于稳定发展阶段。在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方面,1920年至1940年,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本科班共17届毕业130人。1930年至1940年,图书馆学讲习班共4届毕业47人。1941年至1953年,图书馆学专科班共14届毕业175人[13]。1978年以前,中国仅有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持续开设图书馆学专业,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总数约2000人[14]。1978年以后,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规模扩大,到1987年,全国图书情报学本科在校人数在校6300余人[15]。在图书馆学学术型研究生教育方面,1978年到1987年,图书馆学硕士毕业147人,在籍221人[16]。至1998年底,共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1465人、博士43人[17],自2002年至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年均招生200人左右。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方面,我国的专业学位的授予单位已经有74所,截至2022年4月,68所培养单位共有专任教师1983人,研究生导师1258人,据统计,十年来全国累计招收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图书情报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超过11533人[18]。图书馆学本硕博人才培养类别齐全,规模趋于稳定。
2.2.2 学位授权体系
经过百年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学位授权体系日益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权体系。图书馆学本科学位规范化设置的标志是1986年开始的原国家教委分工科、农科、林科、社会科学、理科、医药、师范等门类,分别制定、颁布了本科专业目录,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出现在其中[19]。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规范化设置的标志是197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招收了“目录学研究方向”的三年制硕士研究生[20]。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规范化设置的标志是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图书馆学本科学士学位点22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46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5个,全国各地均有分布,中部和东部分布较多,这样的分布特点与在1978—1987年学科发展形成的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分布特点相关,这十年间共有42所院校建立了相关专业,占总数的75%,东部学位点22个,中部学位点15个,西部学位点5个[21]。
2.2.3 专业师资队伍
图书馆学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自1983至2020年图书馆学教师数量快速增加。1983年,教师总人数为176人,其中教授与副教授数不足二十人。2006年,图书馆学专业共有教师389人,其中教授162人,副教授138人,具有中、初级职称的共85人,跨学科背景为39人[22]。根据“十四五”学科调研统计,截至2020年,图书馆学专业共有教师494人,其中教授188人,副教授219人,具有中、初级职称共87人,全国的中、初级职称的比例比较平衡,其中有51.2%的教师具有跨学科背景(1)数据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十四五”学科调研(图书馆学)。
我国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优秀教师队伍。北京大学的关懿娴、周文骏、吴慰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武汉大学的彭斐章、黄宗忠、谢灼华、台湾大学的胡述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孟广均都是图书馆学教育优秀教师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院校的教师入选了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计划,获得各类国家级人才称号。以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的图书馆学教育家,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图书馆学教学团队也取得了各种荣誉,2007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成功入选了国家级教学团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图书馆学教学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
2.2.4 课程体系建设
根据社会对图书馆学培养人才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不断调整优化。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计划设置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读者工作、图书工作等课程。1985年,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上确定了文献编目、目录学等课程。2003年,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暨图书馆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中提出增加信息组织、信息描述、信息资源建设等课程。2009年,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暨专业主任联席会议中确定学科推荐核心课程为目录学、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数字图书馆及图书馆管理。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规定图书馆学基础、文献目录学等9门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图书馆学课程教育面向图书馆基础业务工作。2018年,《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在9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开设文献计量学等课程,在3—5年内建设网络信息组织、信息素养等前瞻课程,图书馆学课程体系发展为图书情报课程一体化。随后,课程体系向信息管理方向演进。2018年,武汉大学开设含图书馆学专业的社会科学试验班,2023年又新增了大数据与文化、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智慧图书馆原理等多门实验性课程,课程体系更加多元化,以数据、智慧为抓手优化建设,对标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
在图书馆学教材建设方面,各教育机构不断探索,以教材的发展支持教育的规模化和正规化。1920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教材主要是国外资料译著、学术成果汇辑、实践工作经验与方法叙述、传统资料汇编等,多数是翻译或者讲义的形式[23]。而新世纪以来,专业核心课程的编制、课程教材的建设、课程教材的考核等等齐头并进,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材体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历次的工作会议上对图书馆学教材工作做出指导、组织编写,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教育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和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方案。2003年4月在湘潭大学召开的“教指委第二次工作会议暨系主任联席会议”决定举全国图书馆学院系之力编写7门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24]。2015年教指委工作会议商议图书馆学专业教材新编或修订计划。2016年教指委工作会议确立并启动新编教材10种。目前已经建成的品牌教材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的《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教程》《信息组织》等9本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高等学校图书馆核心教材”《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检索》《图书馆学方法论》等23本教材,科学出版社“现代信息资源管理丛书”《信息资源管理学》《数字资源建设与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等18本教材。
2.2.5 国际交流合作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是在国际互动中不断发展起来的。1920年至1949年我国与美国、日本、欧洲交流较多。韦棣华女士1920年创建文华图书科,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沈祖荣等人留美攻读图书馆学,翻译改编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等。20世纪50年代,我国与苏联、东欧交流较多。1953年2月,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基辅图书馆建立书刊交换关系。1955年至1957年,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帮助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学改革,开展了全国巡回讲演和图书馆指导工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同志关于图书馆工作报告集》。1959年5月,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与苏联国立斯达克罗坡里师范学院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关系。彭斐章、赵世良、佟曾功、鲍振西、吕济民、郑莉莉、赵琦被选派作为留苏研究生赴前苏联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留学,这一代人留学归来后成为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与中坚力量[25]。1978年以来,出国攻读图书馆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主要的去向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留美的学生最多,1991年起,每年到美国留学的超过了200人[26]。1978年以后图情领域教师出国交流增多,孟广均、谭祥金、陈光祚、黄宗忠、孙冰炎等多名专家出国进修或访学[27]。1980年,武汉大学聘请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教授林瑟菲(Josephine)博士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从80年代起,美国及欧洲等国和中国的图书馆学交流非常频繁,对推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2年至1988年,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D·斯图亚特教授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进行两次学术访问,作了题为“美国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的自动化”学术报告[28]。西德科隆大学教授、科隆大学哲学系图书馆学专业主持人保尔·卡格拜因教授(Paul Kaegbein)于1985年在武汉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湖北省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29]。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兰开斯特教授1992年来中国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讲学[30]。2000年首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发展国际研讨会暨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发展高级研讨班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院长Leigh Estabrooks教授作了题为“让图书情报学院深深植根于大学与社会中”的学术报告[31]。
iSchool运动以来,中国与国际学者建立良好联系,多名国际专家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给予了支持。在2006年第二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中,美国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院长Raymond F.von Dran教授应邀作题为“信息职业的缘起与发展:融入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32];美国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院长Harry Bruce教授作了《培养数字时代的信息专家》(Educating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in a digital age)的主题报告[33]。美国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院长Liz Liddy教授于2008年代表合作机构为武汉大学成立图书情报国际合作研究院致辞,作了题为“iSchool and What is iSchool”的学术报告[34]。iSchools联盟联络专员、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宾分校图书情报学研究生院院长John Unsworth教授于2009年访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35]。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院长Ronald Larsen教授多次来访武汉大学,交流合作,2013年作了题为“iSchool教育与新一代数据处理家”的学术报告。世界顶尖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s主席、德国洪堡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Michael Seadle教授在2015年第四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做致辞和主旨报告[36]。iSchools发起人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前任院长Mike Eisenberg教授,于2017年武汉大学承办的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iConference2017)上作了题为“iSchools-Our Time is Now!”的主题报告[37]。
我国目前已有13所院系先后加入了iSchools联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是iSchools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成员。中美之间图书馆学教育交流频繁,2000年至今,已经成功召开了四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教育国际研讨会,每届研讨会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探索在不同环境下的发展对策。
同时,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图书资讯学教育与研究领域也合作广泛,在教育发展方面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自1993年至今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地合作举办了十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胡述兆、彭斐章等知名专家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3 图书馆学教育现实挑战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包括学科外部的生态环境挑战、学科自身的建设模式挑战和学生培养中的就业能力挑战。
3.1 学科专业生态
目前,学科之间的竞争激烈,社会资源有限,图书馆学的学科生态环境面临着专业认同、学科归属、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挑战关乎图书馆学的社会认同与未来发展。
通过对近3年30个馆次635个岗位招聘公告的统计调查发现,其中有30.7%的岗位需求图书馆学相关专业,除此之外,需求中文类、历史类、机械类、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涉及专业非常广泛。图书馆需要其他学科的人才是图书馆发展的需求,但是如何提高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是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学科归属反映了学科地位与社会认同。以图书馆学硕士为例,我国图书馆学单独设立院系或设在图书馆的共15所院校,占比46%,合并设院的图书馆学授权点主要在经济管理类学院(24%)、公共管理类学院(18%)。而对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学科前50名的统计发现,独立设院或在图书馆设立的占58%,合并设院的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学科主要在大众传播和媒体类学院(10%)、工程技术类学院(9%)。对74所正在招收图书情报专业硕士(2022年)的院系进行统计发现,我国图书情报专硕所在学院在图书馆或独立设院占比35%,合并设院占到了较大比例,合并设院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类学院、计算机与电子信息类学院。可见,相较于国际,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独立设院或在图书馆的比例相对较低,与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专业合并设院,归属不同,带来不同的风格。
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目前我国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占比例还较高,高校图书馆馆长职位的行政化色彩大于专业化[38]。我国高校图书馆有事业编制的馆员人数不断减少,人才流失(辞职/调离)为新进人力资源的一半左右,职业的稳定性较弱[39]。
在学生就业情况方面,部分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较少选择去图书馆工作,相较于硕博,本科生去图书馆就业更少,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为例,2006—2018级本科毕业生共计644人,其中256人国内升学,113人出国留学,194人就业,其中只有21人去图书馆工作。而毕业生前往信息管理岗位就业相对较多,我国图书情报专硕2013—2021年共计毕业5800余人,其中就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信息管理岗位的约占60%。
在历届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以及我们所做的调查中发现,全国大学的图书情报专业的系主任、院长也较多关注生源的素质与报考的数量、学生对专业的学习热情与兴趣、本专业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配置给本学科的资源与条件、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目标定位等问题。
在社会关注方面,知乎、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用户对“图书馆学”的认知较为单薄,社会讨论热点集中在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学生就业等方面,特别讨论“图书馆学是什么”“图书馆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等问题比较频繁。总体而言,社会对图书馆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图书馆学还有待建立自己的社会形象。
3.2 学科建设模式
新世纪以来,国家颁布了文化强国、文化数字化以及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着时代的新要求。从总体来看,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滞后于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实践的需求还不完全匹配,数量、规模不足,中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培养的学生数量比较少。我国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五千余所,而图书馆学本硕博招生人数较少,2021年本硕博招生人数共计798人[40]。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与学术图书馆数量一万两千余所,2022年图书馆学学位授权人数7000余人[41],再考虑人口基数因素,在每个图书馆可获得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数量中,中美差距更大。
图书馆学作为规模较小的学科,研究者普遍认为图书情报学科在整个学术界还要争取更多话语权[42],增强纳入学校的优先发展的能力,与其他学科竞争的能力,进一步动员支持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社会资本,扩大图书馆学教育规模,提升图书馆学人才培养核心能力。
3.3 学生就业环境
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学生在就业方面难以应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为例,本科课程包括图书馆学基础、信息描述、信息组织、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咨询与决策、数据分析等,图书馆学学术硕士课程包括图书馆发展研究、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信息政策与数据治理等,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包括信息资源建设、竞争情报、各类信息中心管理等,图书馆学博士课程包括图书馆管理专题、科学数据管理专题、信息资源管理专题等。本硕博和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课程体系中不同层级的课程同质化严重,跨学科知识融入不足。图书馆学硕士课程中,科研学习课程占50%,图书馆业务、服务和行业前沿课程约占20%,课程设置较为全面,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图书馆工作、服务相关课程较少,学生对图书馆工作的适应力和服务力较低。在面向广泛的信息职业背景下,图书馆学教育中用户行为特征分析课程较少,学生难以满足用户需求,提供用户满意的行为。总体而言,图书馆学教育还要进一步提升专业人才的职业竞争力,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新需求。
4 新文科背景下的教育展望:培养新一代图书情报领导者
面向未来的100年,图书馆学教育应当如何发展?这一难题需要从未来前瞻与历史回望中得到启发。2019年,教育部启动了“新文科”建设[43],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44],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图书馆学迎来了专业发展的新机遇。展望未来,科学定位图书馆学发展目标,优化培养方案,实现图书馆学的转型改革,打造中国特色图书馆学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回望历史,百年前编纂出版的著作,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仍然是今天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先驱德国学者马丁·施莱廷格(Martin Schrettinger)作为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学者,其著作《图书馆学教程》《图书馆学概览》在今天教学科研中仍然作为重要的参考;印度学者阮冈纳赞所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以及梁启超先生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都在被我们广泛地研究、传播。在当前的数字社会中,Chat-GPT等新兴的人工智能工具快速应用,人机交互、信息组织、计量、融合、共享和智能创造等方面的成果也被图书馆广泛应用。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前的成果和当下成果同时存在,这种场景在未来的100年仍然会延续。文化发展是一种延续的、积累的、面向未来的过程。新文科更加注重传承与创新。因此,我们要在传统基础上、面向未来场景培养新一代图书情报领导者。
4.1 教育重心:由职业资格转向专业能力
过去的图书馆学教育侧重于开设图书馆业务课程,注重培养学生适应图书馆员职业的能力,达到图书馆员从业资格(professional competence),图书馆学的教育领导者更加关心专业的生源、学生对专业的认知以及专业竞争、就业等问题,这些方面在当下学生培养中仍然很重要。但是,在数字社会大环境下,图书馆学学生面临更加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和更加复杂的图书馆业务,应有更加多样的职业选择。图书馆学教育要将教育重心转向人才专业能力(professional capability)建设。开展智慧时代的领导力教育,培养学生适应智能环境下图书馆新业态的能力,信息组织能力、信息检索能力、智慧服务能力等特有的专业能力,使学生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世界,以及正在变化的、未来的智能环境。要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数字能力、适应当前社会需要和未来发展,而目前图书馆学教育在这些方面准备还不充分。对于iSchools提出的教育创新问题,包括跨学科创新等方面的问题,都值得高度重视,探索实践。
4.2 专业视野:外部扩展与专业内化并重
图书馆学教育要注重外部扩展(external extension)与专业内化(professional internali-zation)的并重。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图书馆学专业的外部拓展,使图书馆学与公共文化、数据管理、健康信息等协调发展,使图书馆学与文化、科技、产业有机结合,拓展学科边界;要把图书馆学教育面向更加宽广的信息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科技环境,使图书情报教育应用更广。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图书馆学的专业内化,在知识发现、组织、服务以及图书馆管理与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方面形成核心知识体系,面向特定领域形成数字图书馆学、医学图书馆学、法律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等领域,把这些领域建设得更加扎实,使学生能够适应不同场景下的服务,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适应性。我国图书馆学课程具有注重资源建设、管理与方法等特色,但课程体系中普遍缺乏“服务”类课程,关于用户行为、需求等方面的课程也比较缺乏。图书馆学教育需要进一步完善课程结构,在传统的包括资源建设、分类、编目等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技术”“服务”等相关课程。
4.3 培养范式: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
在新文科发展背景下,学科之间交叉融合态势明显,跨学科合作交流变得更加重要。科学与社会问题都不是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需要多个学科、专家的交流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图书馆学自身具有理论基础的群体性、研究内容的广泛性、研究方法的整体性等特点[45],更具有与其他学科进行知识交叉和融合的条件。在图书馆学教育过程中,由于图书馆工作的专业化,更需要开展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在图书馆学教育融入人类学[46]、管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47]等学科的实践,表明跨学科交叉融合有利于提高学科的竞争力。图书馆学教育要不断发展学科内核,探索新环境下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增强实践适应力。
4.4 社会认同:不断提升学科价值
学科认同体现了学科共同体与社会对本学科价值、作用乃至社会形象的看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深深扎根于社会,不仅要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学专业价值(professional value),而且要不断提升学科价值(disciplinary value)。图书馆学有自己特有的专业伦理,包括平等服务、高质量服务,这些已经得到广泛共识。中国图书馆界确立了“对全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包容性服务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图书馆学的学科价值,正如国际图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所期待的“为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终生学习、独立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为“各类知识的创造和分享提供途径并使其成为可能”,“支撑知识社会的健康发展”[48]。图书馆学还要关注数字社会中,不同人群的信息与文化获取的特殊需要,推进信息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包容。图书馆学对文化、信息、数据与服务的定位是学科价值形成的基础。图书馆学学科价值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与社会的互动,图书馆学的学科价值体系日益丰富。
致谢: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博士研究生秦顺、赵庆香等参与了调研。在此,对他们的参与调研、支持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