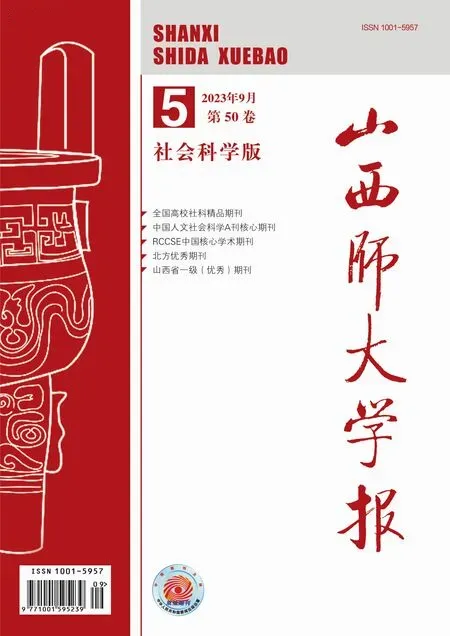康德真理观中的现象性立场
2023-03-02王建军
王 建 军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500)
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把康德哲学比喻成一个“贮水池”:康德之前的哲学概皆流向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皆从康德流出。(1)[日]安倍能成:《康德实践哲学》,于凤梧、王宏文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但就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学说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遭遇来看,难免让人对安倍能成的这一论断产生怀疑。关于自在之物问题,雅可比也讲过一句比较著名的话:“为了进入康德的体系,我们需要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但正因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又不可能停留在这个体系之中。”(2)F. H. Jacobi, Werke. Bd. 2, F. H. Jacobi und F. Köppen, Leipzig: Fleischer, 1812, S.304.(转引自:[美]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柯小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于是,“接受康德哲学”与“拒斥自在之物概念”就在康德之后被难以置信地结合在一起了。很多哲学家一方面攻击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另一方面又强调康德哲学对他们是多么重要。
人们或许会认为,康德哲学对于现代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以其现象与自在之物学说作为评判标准。但问题是,康德的这个学说不同于他的任何其他学说,因为它构成了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石。如果没有这一基石,那么康德的整个体系也就崩塌了。康德本人也非常强调这一点,他甚至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视为一个“启蒙”问题。他指出,“真正的启蒙”(die eigentliche Aufklärung)(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其实是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即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真理只是关于现象的真理,而非关于自在之物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康德为了夯实其在真理问题上的现象性立场,几乎让理性的一切机能都参与进其证明的过程中来。本文试图对这个异常复杂的证明过程进行一一拆解,一方面是为了突显康德证明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后世不必在现象与自在之物的问题上与康德盲目角力,从而避免无谓的失败。
康德认为真理的最小单位是判断而不是概念。对于一个先天综合判断来说,其“可能性根据”就存在于理性自身的“诸认知机能”之中。这些认知机能具体说来也只有五种,即感性、知性、理性、判断力和想象力。其中感性被区分为经验性直观和纯粹直观,理性被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判断力被区分为规定性的判断与反思性的判断,想象力被区分为经验性想象力(再生的想象力)与先验想象力(生产的想象力)。先天综合判断就是由这五种认知机能共同作用产生的真理性知识,而真理之现象性性质正是通过它们的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一、感性
感性作为“被动的接受性”,是与知性的“自发的能动性”相对的。感性的主要功能是为知识提供必要的材料,即感觉(Empfindung)。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对空间和时间进行“阐明”(包括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这种“阐明”(Erörterung)虽然被他解释为“清晰的介绍”(die deutliche Vorstellung)或“解释”(Erklärung)(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页。,但其实际功能却是一种“证明”,即一方面证明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的主观形式而不是认识对象的客观属性,另一方面证明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的形式而不是知性的概念。对于先验感性论的这种安排,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感性在认识中的主要功能是为判断提供关于对象的材料,那么康德为什么不是把感觉,而是把空间和时间作为讨论的主题?
(一)感觉:自在之物的刺激之“效果”
海德格尔在《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一书中曾正确地指出,“康德根本就没有让感觉进入到研究中来”(5)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95),S86.。但这又是为何?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先验哲学探讨的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根据,感觉作为知识的经验性材料,其如何被获得的过程是无须探究的,所以康德干脆将感觉视为“被给予的”而不再探究其起源问题;第二,由于康德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概念来讨论知识的诸要素,并且在这个框架内将作为质料的感觉转换为“经验性的直观”,与之相对的则是作为形式的“纯粹直观”、即空间和时间,这就导致他是在“经验性直观”的意义上来讨论感觉问题。这也就是说,感觉问题虽然并未成为先验感性论的主题,但却也并未缺场,而是以“经验性直观”的身份出现。当然,康德用“经验性直观”而不用“感觉”,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名称问题,而是包含着不同的含义的。康德说:“感觉仅仅是主观的,而直观却是客观的。”(6)[德]康德:《康德美学文集》,曹俊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主观的”在康德那里指的是“个体的”,“客观的”指的是“普遍的”。因此,当感觉转变为经验性直观后,它也就由“个体的”转变为“普遍的”了。但这怎么可能?对于感觉来说这当然不可能,因为感觉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但对于经验性直观来说,这就不仅可能,而且还是必然的了。因为经验性直观与纯粹直观是不可分的,而正是纯粹直观赋予经验性直观以普遍性。“经验性直观+纯粹直观”的含义显然要远远丰富于单纯的感觉。既然如此,空间和时间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以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将讨论的主题锁定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而不是在感觉问题上。对于他而言,经验性直观与感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指发生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的感觉,因而不包括幻觉;而后者是包括幻觉在内的。也就是说,虽然个体的感觉对于感觉者本人来说总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性也仅限于个体,因而这种感觉是不能被用作知识的材料的。就此而言,康德以经验性直观取代感觉,这就从知识材料方面确保了知识的客观性(或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虽然没有对感觉做更进一步的探究,例如对其具体发生过程或其先验结构进行研究,但他毕竟对感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即感觉是感官在受到自在之物刺激后留下的某种“效果”(Wirkung)。他说:“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时,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效果(原译为‘结果’——引者)就是感觉。”(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康德将这种效果也称之为感觉的“变状”(Modifikation)。他说:“它们最终是作为内心的变状而属于内感官的,并且我们的一切知识作为这样一种变状,最终毕竟都是服从内感官的形式条件即时间的。”(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这也就是说,当我直观到某物的颜色,这种颜色其实只不过是该物体刺激我的眼睛而留下的某种效果,而不是该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同样,如果有人用拳头击打我,我感觉到了疼痛,但我不会将“疼痛”视为该拳头所具有的客观属性。效果与属性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主体的感觉,后者是对象所具有的特质。既然如此,一切感觉都只能是物体向我们所显现出来的现象了。康德说:“它们(指‘感觉’)只是作为对特殊器官偶然附加上的效果(原译为‘影响’)而与现象结合起来的。”(9)[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页。由此可见,虽然感觉问题没有成为先验感性论的研究主题,但康德在一开始就从“效果”的角度对知识的材料作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
(二)空间和时间: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
康德又是如何证明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的形式而非自在之物的属性呢?具体来说,他是通过空间和时间的先天性与必然性来证实这一点的。时空的先天性是指,空间和时间不是什么从外部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概念,相反,外部经验本身只有通过空间表象才是可能的;时空的必然性是指我们永远只能设想出没有物体的空间和时间,但不能设想没有空间和时间的物体。
将空间和时间不视为对象的客观属性而只视为感性的主观形式,这可能会激起我们日常经验的反抗:假如时空是主观的,那么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或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世界都不在时空之中吗?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问题涉及时空表象的客观性问题。康德是通过先验想象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先验想象力作为一种图像(Bild)层面上的综合能力,一方面是一种感性能力(图像),但另一方面又具有知性的自发性(综合)。就空间表象而言,想象力借助一切可以“描绘空间的物质”而将对象综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个个经验性的空间表象;就时间表象而言,想象力借助直观者与特定历史事件这两个时间点而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一个经验性时间表象。由于作为想象力综合活动之材料的物质和历史事件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先验想象力由此而构造出的经验性空间和时间的表象也被误认为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附着在空间和时间表象上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从客观事物那里“转移”过去的。时空表象如果离开了直观者,当然就不会存在,所以它们不可能是自在之物的客观属性。因此对于康德而言,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世界上的物体是存在的,但空间和时间表象并不存在。
空间和时间表象的这种特征表明,我们之所以坚信一切客体都在时空之中,实际上不过是因为我们以时空的“眼光”去直观客体罢了,而这种“眼光”(即我们的感性形式)是我们摘不掉的眼镜。既然如此,作为纯粹直观的空间和时间表象就为真理的现象性做了第二重论证。
二、知性
关于知性与理性这两种认知机能,康德是在“先验逻辑”的标题下论述的。这意味着,作为知识之要素,知性和理性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感性提供的关于客体的感觉材料在逻辑的层面上进行理解或思考。其中知性所思考的是局部范围内的客体,而理性的思考则不直接针对客体,而只针对知性本身,即它是在知性判断的基础上再对这些判断做进一步的逻辑推论,并且推论的目标是引领知性关于客体之认识由局部走向整体。“先验逻辑”包括“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两部分,前者处理的是知性机能,后者处理的是理性机能。关于“先验分析论”,康德强调它对应于传统的“本体论”(Ontologie)。这也就是说,先验分析论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来处理传统的“存在(öντα)问题”的。
先验分析论包括概念分析论和原理分析论两个部分。前者处理的是范畴的演绎问题,后者处理的是范畴的运用问题。由于范畴的运用属于判断力的工作,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可归结为判断力在将范畴运用于感性对象上的可能性条件(图型)以及知性为这种运用所颁布的法规(知性原理)两个方面。
(一)范畴的演绎
范畴演绎虽然复杂,但其目标无非是要证明:范畴是知性的主观形式而不是自在之物的客观属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证明是关于纯粹知性概念的证明,而不是关于一般的经验性概念的证明,所以一切基于经验的证明都是无效的。为此康德选用了一种法学意义上“演绎”的证明方式,即一种着眼于“合法性”的证明。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原本属于知性的主观范畴能够合法地运用到感性对象上去,那么这本身也就证明了范畴是知性的主观形式,而非自在之物的客观属性。这也就是说,康德将需要证明的结论先预设下来,如果这个预设在实际中是行之有效的,那么它就是能够成立的。这种合法性的证明与法律上的诉讼相类似。例如,只要张三能够向法庭出示地契,他就能证明他的预设(即这块土地属于张三而不属于李四)是正确的。同理,我们可以预设范畴是知性的主观形式,接着就是要去证明这种形式能够客观地或普遍有效地运用于感性对象,从而使范畴的主观性得到证明。这是康德的总体思路。
这里的关键在于,范畴究竟以何种方式被运用于感性对象。康德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它们对认识的客体的建构,即一切认识的客体都是范畴运用于感性对象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范畴运用于感性对象的合法性问题也就得到了有效的证明。但这种解决方式是以认识对象被区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为条件的,所以范畴的演绎同时也是对现象与自在之物之区分的进一步证明。
康德进而对客体的建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就是他在“A版演绎”中所阐述的三重综合,即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像中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定的综合。其中前两重综合属于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第三重综合属于知性的综合。[顺便提一下,伯纳德·弗雷德伯格(Bernard Freydberg)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想象力》一书中甚至认为这三重综合都是想象力的综合(10)Bernard Freydberg, Imagination i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5.,但这种看法与康德的文本是相冲突的。]通过这三重综合,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客体的经验性概念。但康德并未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概念之所以能够被做出来,还离不开一个先验的条件,即先验统觉。他认为,当我们对对象的感性杂多进行思考、进而形成概念时,我们实际上首先是把这个对象视为一个先验客体,这个先验客体也就是所谓的“等于X的某物”(1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这个“X”可以说是该经验对象概念中的一个“内核”,因为它是使经验对象的一切经验性直观得以关联和统一起来的根据。康德说:“它(指先验客体的概念——引者)不涉及任何别的东西,只涉及那种只要和一个对象发生关系就必然会在知识的一个杂多中找到的统一性。”(1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这种统一性其实也就是知性本身,康德称之为先验统觉或先验自我。由此可见,一个经验性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有一个“自我”(=人类知性)参与其中的,如果没有这个先验自我,关于客体的经验性直观就根本不可能被统一起来,因而它们也就不可能形成关于客体的概念。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知性形成的关于任何一个经验对象的概念,表面上看似乎是纯然“客观的”,即似乎是在指称一个自在之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概念就其形成而言,它不仅是想象力的综合的结果,而且还在其中包含着一个“我”(Ich)。正因为有了这个“我”,所以一切经验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相对的。例如英文单词“paper”与汉字“纸”的含义并非完全相同(前者还有“考卷”之意)。这种不同体现了中、英文语境下的人类知性(自我)的差异性。当然,康德在这里并不考虑差异性问题,他探讨的是“一切人类”的知性,即先验自我,而非经验性自我。也就是说,他探讨的是作为后者之根据的那个自我。
(二)范畴的运用
知性因能够提供纯粹概念(范畴)而被视为“规则的能力”,但这些规则还必须被运用于感性对象之上方能产生出特定的知识(判断)。判断力就是这种将知性的规则运用于感性对象上去的能力。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其实也就是他的真理理论,因为他指出感性和知性都不会“出错”,而唯有判断力才会出错。他认为判断力是一种将“特殊者”归摄(subsumieren)到“普遍者”之下的能力。“原理分析论”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在理性系统中为这种归摄作用找到必要条件,即“图型”和“知性原理体系”。
图型是感性与知性之间得以关联的中介,它作为先验想象力对时间的先验规定之结果,一方面与感性对象相联系(因为“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1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页。),另一方面与范畴相联系(因为先验想象力对时间的先验规定活动是在范畴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也正以此方式使范畴被图型化)。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将这种起中介作用的图型理解为一种与中介双方并列的“第三者”,因为图型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的表象”。例如,量的图型是“时间的序列”,这个图型在方法上表现为“数数”(zählen)。也就是说,由于数数的行为一方面与感性对象发生关系(因为它是以时间的均质性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也与范畴中的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发生关系,所以这种行为就能够成为量的范畴与感性对象之间的中介。图型论对于判断(真理)的现象性意义在于:判断力根本离不开先验想象力的图型,否则它就无法将范畴运用到感性对象上去,虽然它在这种运用中是“可错的”。
图型虽然在正面上为范畴运用于感性对象提供了感性的条件,但这种条件却是一把双刃剑,即它也在负面上对范畴的使用作了“内在的运用”(或“经验性运用”)的限制。这也就是说,一旦范畴离开了感性对象而被运用于自在之物,那么它们就会因其“先验的运用”而成为非法的。康德在界定图型概念时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将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这个知性概念的图型。”(1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知性原理是知性为判断力所立的“法规”(Kanon)。通过这些法规,判断力将纯粹知性概念运用于感性对象,从而真正实现了康德所谓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如果说图型只是判断力运用范畴的可能性根据,那么知性原理则是此运用的现实性根据。因为就知性与判断力的关系而言,后者充当了前者的“执行者”的角色。康德说:“判断力只针对知性的应用。”(1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在这一意义上,判断力是真理的实际制造者。当知性为判断力提供体系化的原理去做判断从而形成真理性认识时,它也就为后者提供了现实性根据。这种立法显然也明确宣告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因为这些法规只不过是对范畴在其经验性的运用中的进一步“解释”,它们“把一切范畴限定在单纯经验性的运用之上,而不允许和不容忍作先验的运用”(1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因此,“知性为自然立法”的含义也是双重的,即它在强调判断力在认识中的能动性时,也强调了范畴使用的界限。康德说:“知性并不仅仅是通过对诸现象的比较来为自己制定规则的能力:它本身就是对自然的立法,就是说,没有知性,就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自然,即不会有诸现象之杂多的按照规则的综合统一:因为现象本身不能够在我们之外发生,而只能实存于我们的感性中。”(1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三、理性
在康德那里,理性作为一种能力可分别从“先验能力”和“逻辑能力”两个方面来看。理性的先验能力是指理性能够产生具有最高统一性的“理念”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的实现还是要借助于理性的逻辑能力,即理性的“推理能力”。推理能力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前者中根据三段论进行推理,在后者中根据“不矛盾律”进行推理。理性通过推理而得出的理念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些概念表象,但这些概念不同于知性概念,它们已从经验领域跃升到超验领域,因而与之相应的“对象”就不再是任何可能经验的对象。
(一)理论理性
理论理性的推理是以三段论的方式从经验性的事实开始的,它得出的结论则是一个在其条件的全部范围内被先天规定了的判断。这个判断从直观综合的立场来看也就是一个关于对象之可能条件的总体性概念、即理念。一个三段论推理可根据其大前提是直言判断、假言判断、选言判断而被区分为直言推理、假言推理、选言推理。由这三种推理(前溯推论)所得出的三个结论、即三种作为绝对总体性的“无条件者”概念分别体现了理性对无条件的实体、无条件的原因和无条件的协同性的追求,并分别构成了传统的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和理性神学的研究主题。这三个理念也就是灵魂、世界和上帝的概念。
既然理念是出于理性为了系统地把握经验对象而推论出来的总体性概念,那么它们的产生就具有必然性。但是,这种最大程度的统一性概念毕竟超出了一切可能经验的范围,所以它们在经验中不可能拥有任何相应的对象,因而仅仅保持为概念。这种概念对于理性的整个推理过程来说具有先验的作用,即它们构成了整个推理过程得以可能的最后根据。在这一意义上,康德称它们为“先验理念”。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由于在整个回溯推论过程中,推论的每一步所涉及的经验概念都对应于一个经验对象,因而我们总倾向于认为,位于这个推论系列之最高项的先验理念也会有一个对象,哪怕它是一个超验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先验理念作为推论的最高项当然还在这个推论系列之中,但在与此系列相对的对象系列中,它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对象了。假如我们一定要为先验理念“安排”一个对象,那么“先验理念”也就由此转变成了“超验理念”。如果我们还要试图对超验理念进行认识,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各种“先验的幻相”之中,如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理性物理学的“二律背反”以及理性神学对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等等。
由此可见,康德对于理性理念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积极肯定先验理念对于知性的范导性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否定对超验理念进行认识的任何可能性。理念的范导性作用虽然并不直接作用于认识对象,而只是引领知性向着最大的统一性不断前进,但这毕竟为人类的认识增添了某种主观的色彩。因为对象世界本身是否具有这种最大的统一性的问题总是悬拟的,但知性在先验理念的引导下毕竟总是将对这种最大统一性的追求当成了一项任务。这就表明,我们的知性认识远非只是感性材料加上知性范畴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起引领作用的理念之手。康德将理念的范导性作用深挖出来,这可视为他对真理之现象性的另一层次的论证。正因为如此,康德在解决理性物理学的第三组和第四组二律背反时,一方面把它们视为混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指出解决这两组二律背反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区分现象与自在之物。
(二)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被运用的理性。实践理性也有自己的最高理念,即“有关一切可能的目的的必然统一性的理念”(18)[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这其实也就是“至善”理念。当然,至善理念涉及德与福两个领域,如果单纯地就德性领域而言,那么其最高理念则是“善的意志”。他说:“在世界之内,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一个善的意志之外,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能够被无限制地视为善的。”(19)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理性的真正使命必定是产生一个并非在其他意图中作为手段,而是就自身而言就是善的意志。”(20)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善的意志也就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也就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虽然只是一种行动的能力,但它在实践知识方面也拥有其“对象”,这种对象可被恰当地称为“善和恶的客体”。康德说:“我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对象概念,是指作为自由所导致的可能结果的一个客体的表象。”(2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实践理性的唯一客体就是那些善和恶的客体。因为我们通过前者来理解欲求能力的必然对象,通过后者来理解厌恶能力的必然对象,但两者都依据着理性的一条原则。”(22)[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9页。例如,金钱就其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作为一般等价物而言是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但它一旦成为我们帮助别人的手段或成为盗贼偷来的赃款,那么它也就成了“善和恶的客体”。
自柏拉图以来,自然之物因为其实在性而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视为“善”的,但康德认为,这种“善”实际上不过是“有用性”罢了。在他看来,一物之善只能在作为实践理性之客体的意义上被看待,而这种客体所揭示的乃是一个意志与导致那个对象之产生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因而是一种基于自由的关系;如果说作为人工产品的物涉及的是该物的“物理的可能性”,即“对象的实存”,那么作为善和恶的客体的物涉及的则是一个行动的“道德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在真理的层面上为客体增加了一层道德的含义或人类自由的色彩。虽然我们在这里惊奇地发现,原本截然对立的自然与自由领域居然在一个普通的善或恶的客体中被轻易地结合起来,但如果我们从“自在之物”的角度来看,这种客体却是对自在之物的一种十足的、渐行渐远的“偏离”,因为它使得一个原本只是自然领域中的客体同时成为一个自由领域中的客体。
四、判断力
康德的判断力理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次区分了“规定性的判断力”与“反思性的判断力”。在此之前,他在认识论中称判断力为“一般先验判断力”。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规定性的判断力,所以在这里只讨论反思性的判断力。关于反思性的判断力,我们首先要弄清它本身的含义,其次要弄清它的“先验原则”、即“自然的合目的性”之含义。
首先,“反思”在康德那里包括知性的反思和判断力的反思两大类别,它们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知性的反思包括逻辑的反思与先验的反思。逻辑的反思属于知性的三重逻辑操作之一,这三重操作分别是:比较(将表象置于意识统一性的关系中进行比较)、反思(把不同的表象放入同一个意识中进行思考)和抽象(剔除掉那些与所有表象不同的表象)。康德认为,知性要形成一个一般性的经验性概念,就需要以这三重操作为条件。至于先验的反思,它是针对逻辑的反思的,即它要对一些概念(如同一性与差异性、一致与相违、内部与外部、质料与形式等概念)在认识论中的起源问题进行考察,即考察它们究竟是从感性中还是从知性中产生的。
判断力的反思不同于知性的这两种反思,因为它根本不是对对象的规定,而是通过对对象的反思来达到主体内部的诸认知机能的协调一致。例如在鉴赏判断中,对象之“美”其实不过是主体的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之结果;对象之“崇高”其实不过是主体的想象力与理性的协调之结果(起初是不协调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协调的)。再如在目的论判断中,对象的“合目的性”其实不过是主体的知性与理性的协调之结果。这也就是说,对象本身无所谓美,无所谓崇高,也无所谓合目的,这些述谓都不过是出于我们内心诸认知机能协调的结果。反思性的判断力与规定性的判断力都是把特殊者归摄到普遍的规则之下的“归摄”的能力,二者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运行机制来说,在规定性的判断力的归摄行动中,那个普遍者是确定的,而在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归摄行动中,那个普遍者是不确定的。第二,正因为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普遍者是不确定的,所以它需要对对象的表象进行反思。但如何反思呢?这就需要一个先验的原则,它就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因此,反思性的判断力与规定性的判断力在先验原则上是不同的,关于后者的先验原则我们在上文中已经阐述过,即那个基于范畴之上的知性原理体系(判断力的法规)。
其次,什么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从对象方面来说,当我们把对象的偶然属性也归于对象的概念时,这些偶然属性就可以被视为“合目的的”(zweckmäßig),因为客体的概念就是客体的目的;从主体方面来说,当我们把客体的一切偶然属性认定为合乎对象的概念或目的时,我们的内心诸认知机能就得到了协调。这意味着,对象的一切属性之所以是合乎其目的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诸机能得以协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朵花之所以如此之美,就是为了让我感到愉快。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对象那里所看到的合目的性(合乎其概念),其实不过是我们内心诸机能协调状态的一种外向的“反射”(反思)。
既然反思性的判断力以合目的性原则作为其反思的原则,那么它所做出来的判断当然就不是对客体的一种规定,而只是对主体的情感的一种表达。康德认为,虽然这种“部分感性、部分理知”的情感对于人类的认识判断与道德判断具有奠基作用(因为“对自然界的崇高的情感没有一种内心的与道德情感类似的情绪与之相结合,是不太能够设想的”(2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并且如果我们没有对大自然的惊叹,我们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大自然的内在结构与统一性问题,但是,一切关于对象的目的论评判毕竟不能被等同于对对象的认识。他说:“虽然目的论的评判至少是有理由悬拟地引入到自然的研究上来的;但这只是为了按照和以目的为根据的原因性的类比而将它纳入观察和研究的诸原则之下,而不自以为能据此来解释它。”(2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这一原则并不涉及就这种产生方式而言这样一些物本身(哪怕作为现象来看)的可能性,而只涉及对它们所作的在我们的知性看来是可能的评判。”(2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既然如此,反思性的判断力在真理问题上的作用就变得十分微妙:一方面它为真理(认识判断与道德判断)奠定了某种情感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将我们关于对象的判断引向了一种与关于自在之物的认识毫无关系的方向上去了。可以说,反思性的判断力及其先验原则的发现是康德在真理问题上对其现象性立场的最有力的论证,因为既然一切判断(哪怕是最客观的科学判断)最终都建立在一种人类情感的基础之上,那么我们的认识怎么可能是关于自在之物的认识呢?在人类的眼光里,一切都在现象之中。
五、想象力
我们最后需要重新提及康德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机能——想象力。康德将想象力区分为经验性的想象力和先验的想象力。前者在我们的经验中十分常见,其本质无非是通过联想的方式将一个图像与另一个图像综合成一个新图像;后者则是我们所知觉不到的,但它在理性系统中实际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上文已经提到,先验想象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直观的能力,但同时又具有知性的自发性。想象力的自发性主要表现为它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只不过这种综合不是知性的综合,而是一种感性的、图像层次上的综合。
纵观康德的先验哲学体系,我们可在许多地方找到先验想象力的踪影。例如,在“先验感性论”中,直观对象的表象以及空间和时间杂多的表象都是由先验想象力产生的。在“先验分析论”中,范畴的演绎所涉及的、出现于一切知识中的三重综合,其中前两种(直观中领会的综合和想象中再生的综合)都是先验想象力做出来的。在“图型论”中,图型本身就是先验想象力对时间的先验规定。在“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美感是出自先验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的结果,崇高感是出自先验想象力与理性的协调的结果。“美的理想” 是先验想象力基于规格理念和理性理念之上而产生的结果。“天才”作为一种能力,指的是由想象力与知性按照一定的比例所构成的东西。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揭示了先验想象力的自由本性,这种本性在艺术领域中以自由游戏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先验想象力在认识中的自发性其实不过是想象力之自由本性的一种受限的表现,即它不过是因为受到理性的限制而显现为一种有节制的自由罢了。因为在认识过程中,想象力的自由必须在受到理性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例如,为什么图型是想象力的产物?这是因为想象力的本性是绝对自由的,因而它可以在不同质的表象之间建立任何联系;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接受知性范畴对其自由本性的约束,这就使得它所做出的图型只能是一种处于受限状态的自由之产物了。在审美领域,想象力同样也要受到理性法则制约。因为想象力与知性、想象力与理性的协调关系也可视为知性与理性对它的一种制约,只不过这种制约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以情感的出现为限度的。例如在美感中,想象力与知性的游戏可以是任意发挥的,但这仍然需要以与知性的某个普遍的规则相契合为前提,否则不会产生出愉快的情感(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把客体想象成某种不知所云的东西)。那么,想象力是否有完全不受理性法则限制的情况呢?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到了颠狂和狂想症等精神疾病,认为它们就是想象力在脱离理性法则下出现的情况。在实践领域,康德也强调不要让想象力“胡闹”,因为对道德法则的遵守是按照知性而不是按照想象力进行的。他说:“德性法则除了知性(而不是想象力)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居间促成其在自然对象上的应用的认识能力了。”(2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既然先验想象力对于理性系统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人类的认识就绝不可能是自在之物的意义上的,而只能是现象的意义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以照相机作为对照:照相机拍摄出的其实是一堆像素,只有人的意识才能从这些像素中分辨出具体的形象来。人与照相机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先验想象力和自我意识,因为前者形成了对象的直观表象,后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象的概念表象。
六、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环节,康德对其真理的现象性立场作了系统性的论证。此论证之主要特点在于其内在性,即它是根据真理形成过程中认识者的诸认知机能作出的。按照通常的观点,真理总是关于一定对象的真理,认识者只能作为真理的“反映者”的角色出现,因而对于真理的实质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对于康德而言,由于认识的“对象”被转化为“感性杂多”,即被转化成某种主观的东西,因此真理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认识对象,而仅仅是被认识主体所建构出来的对象(Gegenstand)、即作为现象的客体(Objekt)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其实是被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从对象中所认识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放入对象中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康德才对认识对象作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这一区分恰恰是他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实质含义。如果我们承认并接受“康德哲学”,那么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他的真理的现象性立场。这一立场既非深不可测,亦非任意虚构,它仅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朴素的同一性命题:人类的认识仅仅是人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