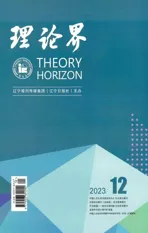“冢”文化释义
2023-02-28谭国武
谭国武
《说文解字·勹部》:“冢,高坟也。从勹豖声。”〔1〕从勹豖声,就是说冢字由勹、豖两部分组成,故又写作“”,依六书言,为会意字。因此,对勹和豖的正确解读,是认知和理解“冢”字的关键。
一、释“勹”
勹是包字的初文,《说文解字·勹部》:“勹,裹也,今字包行而勹废矣。”〔1〕《正字通·勹部》:“按勹为包字之母,包裹皆取义褱(怀)妊。”〔2〕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勽为包”:“《说文》:‘勽,覆也,从勹覆人。’”
甲骨文象人之胞胎形,当为包之初文。《说文》:“包,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甲骨文以“巳”或“人”象人腹中之子。例如“子”小篆作“巳”。故“包”“勽”形同义近,当为一字,许氏强分为二。〔3〕
又,甲骨文“身”“孕”为一字,《甲骨文字典》:“从人而隆其腹,以示其有孕之形,本义当为妊娠,或作腹内有子形,则其义尤显。孕妇之腹特大,故身亦可指腹,腹为人体主要部分,引申之人之全体亦可称身。”《说文》:“身,躳也,象人之身。”《易·艮》:“艮其身。”虞注:“身,腹也。或谓妊娠也。”〔3〕冢字之“冖”,即由孕字之“乃”演化而來。

图片来源:《与古代穴居生活相关的一个汉字——“昷(温)”字本义初窥》
从建筑学的角度讲,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些半地穴式建筑。所谓半地穴式建筑,就是先在地面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浅坑,然后在坑上修建一个窝棚式的房屋。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河南密县莪沟遗址,以及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里均有发现。在同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发现了数十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的半地穴式建筑。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居住之所也从半地穴式建筑过渡到地面建筑,再到后来的巨型宫殿,居住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其名称仍然是“近取诸身”。〔1〕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陶屋基本上作形,如孕形之母腹,先民正是通过陶屋的这一造型,以祈求得到如回归母腹般的安适和保护。直到汉魏时期,居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居住在这种“屋形似冢”的房子里。《魏书·勿吉传》:“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8〕先民还把许多称呼人体部位的语汇用于建筑之上,如房(乳房)、宫(子宫)、殿(臀)、堂(膛)、府(腹)等。
在长期的渔猎农牧生产实践中,初民还观察到其他动植物及其“种子”都有一个外壳(古文字写作“殼”“”),或称包,或称核、皮、莩甲等,对种子核心之“仁”“子”具有“母腹”般的生养化育和保护的功能,表达于文字上,便有了穀、豰、鷇等字,以为形旁的字,实是“包”“昷”字义的另类表达(见后)。就“包”字而言,后来又分化出苞、匏、瓠等义项,“苞”字从苞笋、苞芦、苞橘等物可知,都是外皮包裹子、仁、心等果实的意思。苞瓜又称匏瓜、瓠瓜,东北称之为葫芦。汉王充《论衡·无形》:“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犹人之血也;其肌,犹肉也。”〔9〕其包蕴之义从最初的母腹孕子,到皮壳包裹籽粒果仁,到人及部族聚集、居止的敖包、蒙古包,〔10〕一直到“包举宇内”(贾谊《过秦论》)、“包裹天地”(《文子·道原》)、“包裹六极”
(《庄子·天运》)、“包括四海”(陈寿《进〈诸葛亮集〉表》)等,可谓无所不包。其至大无比实即宇宙。
“宇宙”是中国固有词汇,其原始义为屋檐和栋梁。《说文解字·宀部》:“宇,屋边也。从宀于声。《易》曰:‘上栋下宇’。”〔1〕《淮南子·览冥训》:“凤皇之翔至德也……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高诱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11〕在汉字里,我们看到宇宙二字都是用“宀”即房屋的意象来表达的。宇宙本来就是一座大房子,只不过古人把它想象为其大无比,没有边际,故能“包裹六极”。
晋时“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性嗜酒,放浪形骸,蔑视礼法,所著《酒德颂》著称于世。《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了一则刘伶的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晋记》作宅舍),屋室为裈(kūn,内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12〕
因为房屋对人类的生养庇护之功,人们自然联想到宇宙天地只不过是一所更大的房子而已。
二、释“豖”
许慎《说文解字》释“豖”:“豖,豕绊足行豖豖,从豕系二足”。〔1〕就是说,豕下一画为系足之绳索,故释豖为“系足之豕”。甲骨文出土后,解释“豖”字者,聚讼甚多。一种观点是承继许慎之说。著名畜牧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养猪学奠基人之一张仲葛认为,豕下一画为绳索等系囚之物。他说,据甲骨文记载,“当时驯养野猪,必需用绳束等物系囚一时,或加牿于其头颈等以防其逃逸。如豕字甲骨文作‘豖’。豕字的‘、’(作者注:即豕下一笔)表明是用绳束或加牿的意思。”〔13〕另外,大家如郭沫若、杨树达、闻一多、于省吾、徐中舒、唐兰、孙海波、李孝定等都自有其说。闻一多认为“今案(豕)腹下一画与腹连着者为牡豕,则不连者殆即去势之豕,因之,此字即当释为豖。”〔14〕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二《释豖》:“余疑豖当为豕去势之义,今通语以为阉猪是也。”〔15〕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去势之肥豕,用于祭祀。”〔3〕闻、杨、徐等前辈均释豖为“去势之豕”,从而彻底否定了许慎的释义。此观点一出,立刻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其实,后世学者否定许慎释“豖”之关键有二:一是就字形言,在于豕腹下一画与豕身不连着者,是豕之“去势”,即阉掉之“根器”(雄性生殖器),还是羁绊之索绳;二是豖字的读音与释义。闻一多认为:“豖之本义,当求之于经传之椓及斀劅等字。……案椓劅斀并与豖音同义通,豖本豕去阴之称,通之于人,故男子宫刑亦谓之豖。诗书作椓,用借字。郑作劅,许作斀者,并后起形声字,许君训斀为去阴刑,故无可议,特不知豖乃其最初文耳。”〔14〕也就是说,闻一多以与豖字“音同义通”的椓劅斀等字佐证“豖本豕去阴之称”。
豖字的同族字不多,今天可见的除豖本字外,就是冢及逐、琢、椓、涿、啄等字,因此,我们要真正认识“豖”字,就必须就豖字的字形和读音,借助典籍以及考古学与文化学材料,尤其是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才能详审其真正意蕴。本文认为,许慎对“豖”的解释是准确的。即释豖为“系足之豕”,而非“去势之豕”。如果说,豖为“初文”、本字,则其“音同义通”之字当为刍、畜,而非“去阴”之椓。理由如下。
第一,从野兽到牲畜,从野猪驯化为家猪,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家养谓之畜,野生谓之兽。”〔17〕《淮南子·本经篇》:“拘兽以为畜”。〔11〕《说文解字》:“畜,田畜也。”〔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释“畜”:“田猎所得而拘系之,斯为世代豢养繁衍之家畜。此‘畜’为玄田之正解。”〔3〕考古学发掘证明:继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驯化了狗之后,到了新石器时代,又已经驯养和驯化了猪,因此,被驯养的猪大约在八千到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18〕在从野获到家养的过程中,人类为了驯服禽兽、弱化其兽性,并使之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发明了羁绊、围栅、阉割等一系列措施,才驯养成后来称之为“六畜”或“六牲”的家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因难于驯服而施以羁绊的情况很多,反映在文字中也有类似情况,如马部的()字,读huán,小篆作,《说文解字》:“马一岁也。从马,一绊其足。”〔1〕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从马一绊其足者,与豖同意。赵宧光曰:‘马一岁稍稽绊其足,未就衔勒也。’”〔19〕马一岁可施羁绊,使其不得纵逸。就是说,马在成年戴嚼口和上络头之前,是要施以羁绊的,与猪的形况相同。此字义后引申为“绊”“跘”“靽”,《说文解字》:“绊,马絷也。字亦作跘。”〔1〕《释名·释车》:“靽,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纵也。”〔20〕、豖二字构形理据相同,都是指事字,即从马或从豕,“一绊其足。”〔1〕可证,之“腹下一画与腹不连着者”不是“根器”,而是羁绊之绳索。
《孟子·尽心下》:“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赵岐注:“招,罥也。”〔2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罥之谓绊其足。经文招字与豖古音相近,招之即豖之也。”〔22〕《孟子》之说亦可为证。
第二,豖、畜同音,豖、刍幽侯通读,因此,畜本字作刍,而刍之音义本于豖。
畜的基本义是人所饲养的禽兽,即家畜,今读chù,为名词,由此引申出饲养和养育(禽兽)义,读xù,为动词。据考证,畜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但是不作牲畜用,以畜为牲畜是后起字。牲畜之畜的本字为刍,“牲畜之畜本应作刍”,“刍与畜为幽侯通谐,故借用。”〔23〕而畜、刍读音又都因家猪呼豖而来。
人们把“六畜”分为“刍豢”,所谓“草生曰刍,谷养为豢”〔21〕“草食曰刍,谷食曰豢”〔26〕以及“牛马曰刍,犬豕曰豢”〔21〕的说法恐是定居生活的农业及畜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事了。刍豢之初,似乎并无草食、谷食之别,何况,谷类本就是从草中培养出来的。至今我们还戏说人类是食草动物。另外,按郭沫若的说法,殷人牧牛于田,田中“种植的是以牧畜为对象的刍秣”,〔27〕“最古的田是种刍秣的田”。〔27〕
卜辞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张秉权释为“挈刍”,于省吾、唐兰、饶宗颐释为“氐刍”。饶宗颐说:“《吕览·季夏纪》: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氏刍’,即‘致刍’。”〔23〕这是流行于夏商周之际的一种风俗,意为王室向天下四方征取大量的草料,即“刍”来饲养成千上万的牺牲,以维持连续不断的祭祀活动。张秉权认为,所挈或所致之物,“很明白的是指牛而言的,挈刍之刍,也可能指的是刍豢之刍,而不是刍草之刍了。”〔23〕也就是说,诸侯进贡的“刍”,除了饲养牺牲的草料,还应该有牛等其他牺牲物。这里,我们看到,“豢刍”之刍义已经扩大化了,即由最初的豖延展到包括猪、羊、牛等所有家畜了。《孟子正义》:“犹刍豢之悦我口”,赵岐注:“草生曰刍,谷养为豢。”〔21〕又《孟子正义》引《说文解字》:牛马曰刍,犬豕曰豢,是其解也。”〔21〕朱熹集注:“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26〕《史记·货殖列传序》:“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28〕焦循注刍豢为牛马犬豕,朱熹释为牛羊犬豕。可知,刍豢者起码包括牛马羊犬豕等“五畜”。下面再说鸡,甲骨文有“鶵”字,即古雏字。《尔雅·释鸟》:“生噣(啄),雏”,晋郭璞注:“鸟子生而能自啄食名雏。”〔29〕《说文解字》:“雏,鸡子也,从隹刍声。鶵,籀文,雏从鸟。”〔1〕段玉裁注:“雏,鸡子也。鸡子,鸡之小者也。”〔22〕《淮南子》:“天子以雏尝黍。高曰:雏,新鸡也。”〔11〕从鸟刍声的鶵为鸡子,今家禽及野生鸟类刚生下来的幼鸟统称为鶵(雏),其音从刍。
至今,辽西民间农人呼唤、驱赶或喂食猪、鸡时,仍以“豖豖”之声呼之。〔30〕若发生了家畜闯入田地或园圃,拱翻或祸害了庄稼或菜蔬,人们也说菜蔬被“豖豖”了,从而引申到在群体中有背地说人坏话者为“豖豖人”。在这里,“好白菜都让猪拱了”这句俗语可以说成——好白菜都让猪豖豖了!可知刍豢指的就是以豖(刍)代指的“六畜”,是马牛羊鸡犬豕等的全部。
从后来使用的许多字里,也能看到畜,即豖(豕)可代表六畜的例子。如《易经·彖传》之“彖”,为全体义。方以智《通雅》:“智按何孟春《余冬序录》言彖为豚,《易》皆以言全体,而以爻言分体,因爻为卦爻,故又作肴,加肉焉。郝氏从之,此说甚当。盖为古遯字。”〔31〕另外,家畜畜养称“刍”称“豢”,豢字甲骨文写作(一期合集一一二六七),《说文解字》:“豢,以谷圈养豕也。”〔1〕象双手环护一“豕”(猪)形。其中豕腹内有一“子”形,会意豢养猪(及其他家畜)的目的不仅是吃肉,也为了繁殖猪崽。动物的幼崽称“豰”称“幺”,动物的嘴部称“喙”,等等,也都是以豖代指所有家畜,是豖为家畜总称之明证。
第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2〕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祭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都是头等大事。
闻一多在《释为释豖》一文中已明确了“祭祀所用之牲”〔14〕与“畋猎所获之禽”〔14〕的区别,并悉录卜辞中出豖字者26 例,指出“二十六条中绝对无一卜问畋猎之辞。反之,其为卜问祭祀之辞,则什九确有明征。”〔14〕并以卜辞中与畋猎有关的字皆从豕不从豖,若,,,及,以证祭祀所用之牲——牺牲为刍豢之畜,而非畋猎之禽。但可惜的是,接下来他还是把祭祀用牲——豖之本义引向“既之豕”,即“去势之豕”的假设。原文如下:
在此,我们看到,闻一多所说的“畋猎之禽”与“祭祀之牲”,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野获得来还是家中豢养而成。〔33〕《易经·序卦传》:“物畜然后可养。”〔34〕野获者,禽兽也。祭祀所用者为家中豢养而成,才称牺牲。牺牲者,畜牲(畜生)也。禽兽与畜牲的不同还在于畜牲的人为可控,比如保证用牲时间,而不像野兽那样收获不时。同时,古代祭祀所用之牲,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各项条件必须“中度”,才有资格充当供神的祭品,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礼制,神灵不会歆享。那些身体不健壮、不完整或有损伤的牺牲是绝对不能用的。据《春秋》记载,鲁宣公三年春,准备祭天的牛口部受了伤,改卜其他的牛(重新占卜一头牛来祭天),可是这头牛又死了,所以当年没有举行祭天的仪式。《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国语·周语》都记载了《雄鸡自断其尾》的故事:“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为牺也。’”〔32〕这只雄鸡害怕被选中做祭品,所以自残其身。这虽然只是一个比喻,说一个外人如果像牺牲那样被宠幸只能是招来祸患,但却真实地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牺牲的选择十分严格。《说文解字》:“牲,牛完全。”〔1〕用于祭祀的牛(牲畜)是完全的。《礼记·月令》说:“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35〕也就是说,仲秋八月,周王朝命令太宰、太祝巡视用以祭祀的牺牲,看它是否“全具”——完好无损;再检查一下它吃的草料,看它的肥瘦如何;还要察看它的毛色,一定要符合成例和不同种类祭祀的需要;还要衡量它的大小,角的长短,都要符合要求。牺牲的完整、肥瘦、毛色、大小、长短这五个方面都符合要求,方可供“上帝其飨”。口伤、断尾之残尚且不能用为牺牲,宁可停止祭祀,也绝不将就,而阉割、“既”、“去势(阴)”之豕却能用于祭祀,实在于理不通。
第四,祭祀用牺牲,即家养、刍豢的畜牲,又称畜生,祭祀用“牲”亦取其“生生之意”,以祈人、畜、谷物在交互感染下蕃孳兴旺,生生相续。这样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之德”的要义。
在古代,六畜是财富的象征,司马迁曾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28〕《周礼·夏官·序官》:“掌畜。”注:“畜,谓敛而养之。”〔36〕《左传·桓公六年》:“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杜预注:“则六畜既大而滋也。”〔17〕《说文》引《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可见,畜字本就包含畜生、滋益、聚敛、积蓄之义。由此,也可以证明,祭祀所用之牲不大可能用“去势之豕”,这不符合原始思维中的“相似律”“触染律”和古人祭祀的心理需求。
“六畜”又称“六牲”,猪为六畜之首,因此,畜为六畜之总称,实即“豖”可为六畜总称。在中国文化中,无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相传几遽氏、豨韦氏(又称豕韦、封豨等),乃至伏羲、黄帝、女娲都是猪神。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以天神、地祇、人鬼(祖先)为对象的三大祭祀系统中,猪的“身份”极为特殊。古代祭祀时,牛羊豕“三牲”,豕为最常备,且用之最古最久。《淮南子·氾论训》云:“世俗言曰:饷大高者而彘为上牲。……夫饷大高而彘为上牲者,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饷之,何也?以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11〕说明古人曾普遍认为猪是上等祭品。王公贵族祭祀所用“太牢”“少牢”中,猪为必不可少,至于士、庶人等祭祀时,则更以猪为其主要祭品,民间至今犹然。《礼记·王制》云:“士无故不杀犬豕。”郑玄注:“故,谓之祭饷。”〔35〕就是说不为祭祀,犬豕是不得随意乱杀的。宗庙祭祀中,新做成的宗庙之器须用猪血涂抹以祭祀祖先,《礼记·杂记》云:“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衅之以豭豚。”孔颖达疏:“杀豭豚血涂之也。”〔35〕
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大都发现有随葬的猪骨,以辽西地区为例,这一现象更为突出。从8000年前兴隆洼遗址的双猪葬,到红山文化直至其后的夏家店文化,都发现随葬整猪、猪头、猪颌骨等大量遗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猪形礼器的出现,如小山遗址出土尊形器上的“鸟鹿猪的灵物图象”及多种形态的玉猪龙,猪首形玉饰,双猪首三孔器、璜等,到遍布整个区域的积石冢和积石冢群,愈加显现猪这一动物与红山文化区的紧密联系。
在中原地区,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的家畜第一是猪第二是犬,牺牲中也主要是以这两种动物为主。到二里头文化时代可以看到牛和羊范围有扩大趋势,但是猪优位的状况还是没有变化。直到商代,牛的比重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商王朝取代经济效率高的猪,而把大家畜牛马作为一种权力和威信的象征物来重视,并把这种大家畜作为盛大的牺牲来使用。”〔37〕
从动物学的角度看,猪每年产仔两次,一次产出的猪崽10 头左右。在所有的家畜中,就繁殖能力来说,猪是最好的。种种迹象表明,人类崇拜猪,视猪为图腾,并把猪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很大原因在于猪的这种令人羡慕直至崇拜的强大生殖力,因此,在心理上产生了人与猪的文化认同。
三、冢即种——积石冢产生的文化动因
以上是对“冢”字构成的“冖(勹)”和“豖”两部分的字形分析。因此,我们看到,冢()字与“包”“孕(身)”“昷”等形异义同,实即包、孕、昷的“另类”表达。《说文解字注》:“(冢)从勹。墓取勹义。”〔22〕在先民那里,母腹孕化之“巳”或“子”或“豖”的形况与其他动植物并无二致。另外,“家”与“冢”的构形原理也是一样,“家”由宀和豕组合会意,宀甲骨文写作“”,为地上建筑,“冢”之冖,即勹,甲骨文写作“”,为母腹或地穴半地穴(其尖顶为地面部分)式建筑。区别仅在于居住形态的变化,即房屋由地下逐渐移至地上,秦汉文字中“冢”字也常省写为从“豕”,写作“”“”,是故,豕与豖某种程度可等同观之。依字而言,则家冢几乎无别。《魏书·勿吉传》:“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8〕这是魏晋之际中原人对古代东北勿吉民族居住情况的描述,冢即象家、象屋(地穴半地穴式建筑)而创制(关于冢、种与房屋之关系,限于篇幅,另文阐释)。相同的文化心理,类似的造字理据。还有上面说过的字,最初作字,即后来的殼字,今简化为壳。《玉篇》:“,物皮空也。”〔38〕《列子·黄帝篇》:“卵甲亦曰。”〔38〕《仲长统·述志诗》:“飞鸟遗迹,蝉蜕亡。”〔38〕物皮、蝉蜕、卵甲都是壳,都可以理解为保护和蕴化万物的甲壳、皮、莩甲之类,包蕴之义。郭沫若说:“……今余改读为豰。”〔23〕豰即为小猪,引申而为幼畜、畜子之“通称”“通名”。唐兰、严一萍、饶宗颐等皆从其说。《说文解字》:豰,小豚也。从豕声。〔1〕段玉裁注:“《左传》晋有先縠,字彘子,盖縠即豰字。”〔22〕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豰)乃畜子之通称,不仅小豕也。”〔23〕饶宗颐也说:“豰又为幼畜之通名,不限于豕也。”〔23〕是豰之构意与冢异曲同工,即甲壳包裹的种子或幼子之状。“”之于物可以理解为包、孕、冢之勹,也即保护、孕化胚胎、人子、幼畜之外壳。《庄子·骈拇》:“臧与谷”。崔注:孺子曰穀。〔39〕《方言》八:爵(雀)子及鸡雏皆谓之鷇。〔40〕《广雅·释亲》:子也。〔41〕是声有孺子之义。所以,文字中有猪子之豰,犬子之,鸟卵或蛋壳称,初生鸟子称鷇,谷子称穀,人子称等。由此看出,在先民那里,人、动物、植物各异,但其天然赐予的如母腹般保护与蕴化的外壳是相同的,万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得以孳息繁衍,传宗接代,生生相续。
进入农耕社会后,人类之所以把已逝的先人实施土葬,以冢封之,其实正是这种让祖先回到大自然母腹,回到种子的心理机制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中国文化“生生之德”的核心精神,以及“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文化根基。《庄子》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39〕
冢、种同声相借,冢即种子之“种”字。《水经注》引《春秋说题辞》:“冢者,种也,种墓也。罗倚于山,分尊卑之名者也。”〔42〕根据《周礼注疏》及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人称“说文四大家”中段玉裁、朱骏声的说法:
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疏》山顶曰冢,故云象冢而为之也。(《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36〕
“郑注冢人云。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此从《尔雅》说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22〕
《水经·泚水》注:楚人谓冢为琴。按《海内经》冬夏播琴。是播琴即播冢,犹言播种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第一)〔43〕
“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22〕正是以耕地下种的行为来形象描述封冢的事实。
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谷物,由此可见,兴隆洼人已经开始了谷物的驯化、培育和种植,也就是开启了春种秋收、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的序幕,人类农业的开始正是受到果实、籽粒成熟落地,复归于土,年复一年,生长出同样的下一代植物的启示。在这一过程中,“春种”或者说“下种”所带来的“结果”和重要性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先红山文化的兴隆洼遗址中,出现了独特的“居室葬”现象,这可以看作“冢”最初的形态。居室葬和积石冢中埋葬的都不是普通氏族成员,而是生前具有特殊社会地位、死后成为生者崇拜、祭祀对象的少数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埋在地下的谷物种子,会生长出同样优秀的嘉禾,而把祖先埋于生息居止于其中的房屋内,则是希望在这里长出更多的如冢墓中故人般优秀的后代人才,并生生相续。
古代帝王、皇后或重臣的棺材称为梓宫,实即子宫,隐喻“冢”是生命孕育和重生再生、孳蕃传种之地。死亡在整个生命链条中被视为休养生息、蕴积能量以再生重生的过程。依此则释冢下之豖为阉割、去势之猪,无论如何于理不通。
直到现在,我们俗称的“庄稼人”,除了一般理解的种植庄稼的人外,似乎也是在指称人像庄稼一样,都是地母所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其所表述的是原始思维中,人和植物一样,都是大地生养的,这里体现出的是人母与地母的认同。“原始世界里的‘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及繁衍)是相互关联、相互统一的关系。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远古世界中的‘两种生产’就是一种生产,因为人、动物和植物同样生活在大地上,三者之间的生殖力可以通过与大地的接触而相互传递,这是一种‘接触巫术’,人、动物、植物的繁衍生长不是相互分开和区别的,而是相互认同的关系。”〔1〕
如此,则埋葬逝者以冢,其心理动机就是播种、下种、传种。人埋地下,是希望先人像埋下的种子一样,能够生出更多的可以赓续种族、传宗接代的籽实。一个部族或民族的种子,也应该是那些能够带领部族摆脱困境、走向强大的圣人、先贤或精神导师。换言之,那些德高望隆、“成为生者崇拜、祭祀的对象”〔44〕的人葬于积石冢,成为部族赓续的种子。这也是我们至今称几千年前那些至圣先贤、精神导师为“子”的原因,因为他们在民众心田播种,撒子,如“生生之仁”,〔45〕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相续的原动力。古代开国帝王通称“艺祖”,《说文解字》:“艺,种也。”〔1〕以至后来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都被时人称为“艺祖”,正是委婉道明其为最初种艺之人,或者说,是最初的“种子”或下种之人。
对于中国的这样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而言,种子的作用不言而喻。换句话说,“绝种”“绝户”“断种”的危机是最可怕的。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46〕所以,只要种子在,明年的大地上就会嘉禾满眼,六畜兴盛,丰收在望,部落民族的希望就在。
广布红山文化区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正是这一意识和心理动机的具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