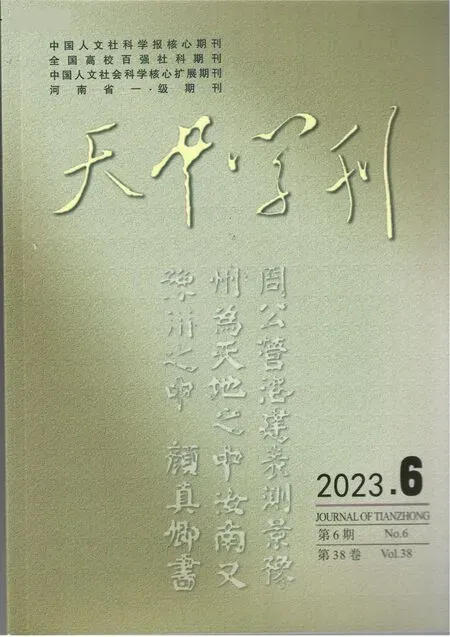医疗主义变迁下的患者自治
2023-02-27翟高远
翟高远
医疗主义变迁下的患者自治
翟高远
(天津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2)
在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主导医疗决策,患者屈从于医生的权威。随着社会发展,个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强调自己对医疗活动的掌控,医疗主义的变迁推动患者自治由理论到实践。医疗个人主义模式下的医疗决策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而中国社会在儒家“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医疗决策更强调家庭整体智慧的参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社会医疗决策范式的分殊。
医疗父权主义;医疗个人主义;医疗家庭主义;患者自治
医疗父权主义作为早期社会的产物,长期在医学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不对称的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权利和权威战胜了患者的无知和脆弱,医生处于医疗活动的中心,剥夺患者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性决断,绑架了患者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医疗父权主义作风逐渐式微,个人权利的觉醒、知识的大众化传播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叠加打破了医疗父权主义占据医疗活动主体地位的格局。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之下,契约式的医疗活动限制了医疗父权主义作风,医疗权利逐渐向患者倾斜,强调患者对医疗活动的自主决定性。在传统儒家“家本位”思想构造的家庭主义医疗模式中,医疗决策融合患者自治与家庭整体意志,强调集体智慧的贡献。本文通过梳理医疗模式从父权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迁过程,探索患者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法治化进程,对中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患者自治范式进行比较,以期为患者权益保障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一、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父权主义模式
(一)父权制作风对患者医疗福祉的增益
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希波克拉底具有崇高的地位,其学派及其学说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称其为“伟大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著名医生盖伦称其为“圣者,一切美好的奇妙创造者”,西方甚至流传着在希波克拉底坟上筑巢的蜜蜂产出的蜜都有治疗婴儿鹅口疮的神奇功效[1]139。《希波克拉底誓言》(下文简称《誓言》)是医生职业的行业圣经,是医学从业者都必须学习并宣誓的誓词,《誓言》规定了医生职业的行为准则以及职业伦理:“我决尽我之所能与判断为病人利益着想而救助之,永不存一切邪恶之念……凡我进入任何人之房舍,皆为病人之利益,决不存在任何谬妄与害人之企图……凡我执业或社交,所见所闻,无论与我之医业有无关系,凡不应宣泄者,我当永守秘密。”[1]144–145这段誓词包含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不伤害原则,医生不得做有损患者利益之事;二是保密原则,医生要保守职业秘密,不得泄露患者的信息。希波克拉底誓言重点强调了从业医生应当具备的专业水准与道德要求,医生须以自身的专业为基础,行利于患者福祉之事,坚决不得有违“不伤害”的医疗传统。
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流行病》中谈到了医患关系,他认为医术活动包含疾病、患者、医生三个方面,医生是医学技艺的仆人,患者要和医生站在同一阵营对抗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时期,医患关系融洽,医生好比成熟而又理智的老父亲,由于患者不谙医事,因此关涉医疗活动的决定均由医生下达,患者遵照即可,此种医疗作风形成了医疗父权主义模式。医疗父权主义模式的生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知识传播不畅通的古代社会,掌握知识便掌握了权力,专业医学知识赋予医生决定医疗活动的正当性,医生在专业知识上具有比患者更优越的条件,医生知道患者更需要什么样的医疗。不惟如此,行善作为早期医生行医的行为准则,要求医生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医生道德身份的认同感使得患者确信医生所为皆为增进患者的福祉。患者作为医学技艺的门外汉,他们往往难以理解高度专业化的医学知识,医生过多的披露反而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从而导致患者拒绝接受对其有益的医疗措施。家长制作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活动的效率,减少了医患之间无意义的磋商,患者凭借医生的治疗得以恢复健康、消除疾痛,这有效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健康。
(二)父权制作风对患者主体价值的侵袭
在早期的医患关系中,医生集医学知识权威、道德权威于一身。古罗马博学家老普林尼在谈及医生的权威时说:“在科学之中确实有一个罕见的现象——任何人只要声称自己是医生,立刻就会有人相信。”[2]287医学技艺作为传统三大学术性专业之一,神秘又复杂,当患者因伤病需要向医生寻求帮助时,他就踏入了异境之地。作为医学技艺的门外汉,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无所适从。医学知识使医生具备专业能力,医生对人性、病理、身体的机制具有深入的认识,知道什么样的医疗决策对患者有利,而患者对复杂的医学知识一无所知,他们参与医疗活动不是明智的选择,会使医患之间的交流产生障碍。因此,在医疗父权制主导的医疗活动中,医生不与患者进行过多的交谈,医生对于患者的病情以及拟对患者采取医疗活动的内容、目的、程序、副作用、疗效等事项通常不多做说明。
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论礼仪》中曾谈及早期医患关系中的医疗父权制作风:“平静且巧妙地履行职责,在照料患者之时对其进行必要的隐瞒。以愉快和真诚的态度给予必要的命令,从他所做的事情上转移其注意力;有时严厉责备,有时安慰以及关怀,绝不透露患者的未来或现状。”[3]在希波克拉底的论述中,医生是发号施令者,为了提高医疗效率要进行必要的隐瞒,患者必须完全听命于医生并遵照其命令行动。医疗隐瞒作为父权制医疗作风的重要手段,有效阻断了患者获知医疗活动信息的途径。医疗保密的后果就是患者对医疗活动一无所知,任由医生做出最符合自己医疗福祉的医疗决定,医生强势地剥夺了患者的知情权。
保密式医疗作风在医学史上早已有之。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在给卡提留斯·西弗勒斯的信中谈道:“提提尤斯·亚里斯托生病已久,忍受着高烧带来的口渴以及疼痛,最近他把我们这些密友叫到他的榻前,拜托我们咨询他的医生,看医生会怎样处理他的犬瘟热。”[4]提提尤斯·亚里斯托是小普林尼的朋友兼同事,他患上了严重疾病,但他的医生却拒绝将病情的严重程度告诉他,不得已之下,提提尤斯·亚里斯托只能求助于他的朋友们,让他的朋友们代其向医生询问疾病的结果。法国医生亨利·德·蒙德维尔是希波克拉底保密式医疗主张的坚定推崇者。蒙德维尔主张医生不必征求患者的意见,患者不可违背医生的建议,患者在任何与医疗有关的事项上都应当遵从医生的指令,医生甚至应该用不服从的后果来威胁他们,通过有选择的告诫和夸大信息迫使他们服从[5]。除了隐瞒医疗信息,医生还通过“善意的谎言”来主导医疗活动。蒙德维尔认为,如果对患者撒谎能够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么医生就不要畏惧撒谎,如若一位教士罹患恶疾,就告诉他将由其来继任去世的主教之位,那么由他来接替主教位置的希望会加速其康复[6]。希波克拉底的保密式医疗作风在第一部现代医学伦理规范《医学伦理规范》中同样得到了延续,该规范规定:“患者应当立即且无条件地遵从医生开具的处方,决不能让自己关于是否对症的外行意见影响了对处方的重视程度。”[7]
在强势的医疗父权主义作风下,患者丧失了主体地位,屈从于医生的权威。患者作为自己生命和身体的主人,有权决定拟对自身采用的医疗措施,并知晓病情、医疗措施的性质、风险等信息。医生具有治疗伤病的道德义务,但并不因此具有治病的法律权利。浑身散发着权威光环的医生实施的父权制做法并非都是正当的,医疗父权制作风常侵犯患者的自主性[8]。
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个人主义模式
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医疗父权主义对医疗活动的把控逐渐松动,人权运动催生患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患者逐渐从医疗父权主义对自主权利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愈发强调自身对医疗活动的掌控,这种理念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潮流。至此,医疗个人主义正式登场。
(一)社会发展和人权运动推动医患关系的转型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突破神学的桎梏,将人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救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价值,复苏人的个性,寻求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在这一时期,医学伴随着文学艺术同步前进,医患关系由彼此信赖的朴素模式向医疗契约模式过渡。19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人权运动推动患者观念的转变,患者谋求关涉自身的健康权益,如终止妊娠和避孕的权利、人体实验中受试者的权利、获知医疗信息的权利等[9]。在患者权利运动的冲击下,医疗父权主义的根基逐渐松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医生打着发展医学科学的旗号对囚犯进行了反人道的人体试验。战争结束之后,国际军事法庭审理了纳粹实施的反人类医疗暴行。《纽伦堡法典》在此背景下出台,明确提出“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受试者得以随时要求停止实验”等要求。纳粹医生的暴行破坏了医患之间的信赖关系,大众质疑医师的行为不全是基于患者利益。《纽伦堡法典》主张进行人体试验必须得到受试者的自愿同意,并应向受试者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让受试者对试验项目及过程具有充分的认知与理解。《纽伦堡法典》动摇了医疗父权主义的权威,促使医学界对患者的医疗权利给予更多的关注,也使得医患关系权利重心向患者一方偏移。1964年,第18届世界医学协会联合大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采纳了《纽伦堡法典》的观点,并在第9条正式确认了受试者的自主决定权。1981年10月,世界医学大会通过了《里斯本病人权利宣言》,明确规定患者享有自主决定医疗的权利,正式肯定了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自主权利和独立主体地位。患者自治政策的落定,医患关系被重新定义,医疗决定不再是医生的专权,医疗活动的主导权由医生向患者过渡,专业优势明显的医生慢慢地从家长型角色逐步转变为解释型、咨询型角色[10]。患者得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决定医疗活动的发展轨迹,其主体性地位得以落实。
(二)患者自治的法治化
在1914年美国舒伦多夫诉纽约医院案中,医生为麻醉后的患者作检查时,切除了她的纤维瘤,鉴于患者于检查之前已经明确要求不要做切除手术,于是患者将医院诉上法庭。纽约州上诉法院法官本杰明·卡多佐于判决中提出:“凡成年且心智健全者,均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未经患者同意而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构成人身攻击,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病人失去意识的紧急情况下进行手术的情形除外。”[11]舒伦多夫诉纽约医院案开创性地使用了自决一词,这是法院裁决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首次司法确认。自主原则作为医学伦理学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旨在规定患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基于该原则,患者得以根据自身的意思做出相关医疗决定,而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自主是人从出生便自然享有的特质,无须法律的赋权[12]。在康德哲学概念里,自主就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不受另一个自由意志的主体所主宰[13]。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有能力判断行为的价值,并为行动的后果负责。黑格尔认为“人的最高使命就是成为一个人”“法的命令就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14]。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在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他自己便是最高主权者,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便是绝对的[15]。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有所为或者有所不为,即便是对他自己有利的行为,除非在紧急状况或者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况下,否则个人不受公权力或者他人的干涉。医疗行为直接作用于患者的身体,患者并不因为生理机能的下降而导致其主体地位的降低,作为人,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决定医疗对自己身体等人格领域的介入及限度。
随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完善,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对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利进行制度建构,从此拉开了患者自治法治化的序幕,患者始脱离其他主体而取得自己决定医疗的控制权利。1990年,美国国会修订了社会安全法第18章的医疗保险和第19章的医疗补助,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①。在这之后,各州根据自己的文化特色以及历史传统,对联邦法律做出本土化的变通规定。如科罗拉多州1992年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马里兰州1993年通过了《健康照护决定法》,以保障病人可以自主做出医疗决定。欧洲的发展稍晚于美国,1997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以“尊重预立医嘱”与“选任医疗委任代理人之选择权”保障病人自主。《人权与生物医学公约》第9条明文规定,施行医疗干预时,应考虑病人先前所表示之意愿。英国、法国、荷兰、挪威及西班牙等国均签订了该公约,虽然各国基于本国内部法制情况存有差异而有不同立法,但各国立法大都遵循此公约精神。就单个国家而言,英国于2005年制定了精神能力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且具备行为能力者,于意识清楚时可以选任医疗代理人或预先做出医疗指示;并设有保护法庭,在遇到争议案件时介入裁判[16]。德国于2009年修正民法,将相关的理念整合到民法典之中,进一步确立了预立医嘱及医疗照管人对病人自主权的保障[17]。与欧美国家相比较而言,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医疗自主权法律规制的关注与研究较晚,是在医疗自主权思潮影响下才逐渐认识到医疗自主权立法的重要性的。韩国2016年通过《关于临终关怀缓和医疗及临终期患者的延命医疗决定的法案》,规定了末期患者拒绝维持生命医疗的程序、措施等。我国台湾地区于2000年通过《安宁缓和条例》,规范末期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并于2016年立法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针对末期患者拒绝医疗维生措施与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等医疗咨商、代理人、程序等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规定,保障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及善终权益。2022年6月23日,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该条例第78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规定,如患者遗嘱要求“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患者平静走完最后时光[18]。深圳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为末期患者实现医疗自主决定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家庭主义模式
(一)医疗家庭主义模式下的医疗活动
患者作为家庭成员,其病情的发展事关整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后续发展,患者的医疗活动并不仅是其自身的事情,而是家庭内部的公共事务,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不享有完全的决定权,其医疗活动的发展由家庭成员集体做出决定,这种作风便是医疗家庭主义的表现。医疗家庭主义在医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在古罗马时期,家父除负有监护权,还负责治疗家庭成员的疾患,担任家庭成员医生的角色[19]。老加图声称自己有一本医学笔记,他用此治愈了自己的儿子、奴隶和家人[2]287。与此类似的医疗家庭主义作风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同样常见。医疗家庭制作风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亦有前例可循,汉代名医淳于意(约前215―前150)为一位名叫成的齐国侍御史诊断,诊后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20]齐国侍御史成身染恶疾,大夫拒绝告知患者病情,却向患者的家人告知。
家,作为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要载体,对于个体而言具有重要的人生价值,家人之间相互扶持、互相依赖,共同推动家庭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基于血缘关系而聚拢在一起的个体集合之间具备更高程度的利他性。亲人之间的互帮互助是出于伦理上的义务,是基于亲缘的情感[21]。汉米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主张利他行为一般出现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血缘关系越近,彼此之间的利他倾向就越强[22]。当患者因病陷入异境之地,其身体以及精神遭受伤病的侵袭,承受能力大幅度下降,若当即告知其糟糕的病情状况(尤其是严重的伤病),恐有加重患者身心负担之虞,易引发患者求生信念的丧失,拒绝配合医生及家庭接受后续的医学治疗。例如,在患者罹患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对严重病况不知情的患者更容易保持一个较为乐观及配合治疗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利于治疗;一旦被告知,出于对恶性疾病的恐惧和担忧,患者反而可能丧失治疗伤病的信心,甚至出现自杀的过激行为。在关涉患者生命健康的重大医疗活动中,往往由患者家属代替患者与医生进行交涉,医生与患者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后对患者隐瞒,阻断实际医疗信息流向患者的渠道,避免患者立即知晓自身糟糕的病状,等待合适的时机再间接、委婉地告知,甚至完全隐瞒。如此做法似有剥夺患者自主之嫌,但在医疗实践中却是相当普遍的。
(二)儒家“家本位”传统对医疗家庭主义模式的塑造
在中国医学史上,家庭在患者医疗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彰显了儒家家庭观的丰满与和谐,在患者医疗、子女养成、婚配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儒家倡导家庭的整体关怀与智慧,家庭在做出这些决定时具有权威性,家庭的这种权威地位体现了家庭在道德和本体论地位上的优先实在性[23]10。在中国式医疗实践中,患者并不总是因疾病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遇,患者的家庭成员往往会为患者提供帮助,他们在医疗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家本位作风之下,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对于家庭内部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项,实质性地影响家庭未来发展的走向。家庭成员若因伤病陷入不幸,其他家庭成员会给予其呵护与照料,与其共渡难关。伤病并非患者独自一人的苦难,而是家庭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家人不仅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往往还需承担患者的医疗费用。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家庭总的经济收入是有限的,患者并不总是具备独自承担高昂医疗费用的能力,如未成年者、年老体弱者、心智不健全者等,诸如此类的弱势群体往往需要家庭财政负担其部分乃至全部的医疗开支。现实社会中,经济拮据的家庭甚至举全家之力也无法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因病致贫的悲剧多有发生。对于恶性疾病而言,即便患者接受治疗,也不能保证完全治愈,治疗之后患者死亡的情况也多有发生。患者的医疗开支分割家庭整体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家庭生活的后续运转,一旦涉及财产支出问题,极易导致家庭不睦、关系失和。不惟如此,疾病导致患者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医疗困局引发患者的内疚心理,当自己变成家庭的累赘,与其承担接受治疗后人财两空的风险,倒不如放弃治疗保全家庭整体。更有甚者,患者为避免拖累家庭而选择轻生[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实施特殊医疗活动的,在患者意识欠缺或者基于人文关怀不适宜告知心理脆弱患者的情况下,应向患者近亲属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并获得近亲属的授权。该条款规定的医疗决定代理的主体限制体现了家庭主义观念,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关系比其他的社会关系更为牢靠,家庭成员相比其他主体会做出更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医疗决策。医疗决定代理人作为患者一方的话事人,倘若没有患者的提前授意也不得擅作主张,而需要同家庭成员(一定情况下还包括患者本人)进行协商,进而共同做出医疗决策。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塑造的家观念里,家庭成员共同构筑一个社会实体,家庭成员内部互相关怀、照料,家庭集体智慧往往能够做出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选择。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体系以及思想观念的分殊,中西方形成了不同范式的医疗决策模式。西方医学伦理学和医事法律规范均把人看作独立的个体,强调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欲求和向往,在完全不受他人操纵或者劝说之下决定自己的医疗活动,甚至不应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23]3。传统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行动逻辑,塑造了具有中国气质的医疗决策模式,在“家本位”思想影响下,患者伤病的发展系家庭集体的公共事务,家庭为患者的医疗决策提供整体智慧。不可否认,家庭整体智慧未必总是产生明智的医疗决策,医疗决定代理人难以感受患者的病痛,加之医疗费用承担等经济利益的驱使,替代医疗决定存在背离患者最佳利益的情形。
中国普遍存在的医疗家庭主义模式虽然有其内生的合理性,但应把握家庭智慧干预的限度,推动“强势家庭主义作风”向“弱势家庭主义作风”过渡,将家庭参与由“干预性角色”转变为“协助型角色”。具体做法可以是:患者具备自主决定能力时由患者自己做出决策,家庭主义作风褪去,以示对患者自主决定的尊重;患者欠缺自主决定能力时,家庭成员以咨询、解释的方式补充患者自主决定能力,协助患者决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共同决定;患者不具备自主决定能力时,患者若已在具备决定能力时预留医疗指示,则遵照其指示进行决策,从而保障患者意愿在丧失决定能力后依旧能够得以实现,而未预留医疗指示的则按照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做出替代决策;同时赋予医疗机构干预权限,防止不当医疗代理损害患者权益。
① 美国《病人自主权利法》条文共计5条,分别是:(1) 告知患者根据国家法律他们有权做出有关其医疗护理的决定;(2) 定期询问患者是否执行了预先指示,并记录了患者对医疗护理的意愿;(3) 不歧视已执行预设医疗指示的人;(4) 确保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预先指示和记录在案的医疗护理意愿;(5) 为员工、患者和社区提供有关患者自决和预先指示的道德问题的教育计划。见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1st-congress/house-bill/4449。
[1] 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程之范,甄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 普林尼.自然史[M].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3] ANNAS G J,DENSBERGER J E.Competence to refuse medical treatment: autonomy vs. paternalism[J].Univ Toledo Law Rev,1984,15(2):561–596.
[4] Pliny the younger.Complete letters[M].Translated by WALSH P 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27.
[5] MONDEVILLE H.On the morals and etiquette of surgeons. Ethics in Medicin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Concerns[M].Edited by STANLEY J.Cambridge: MIT Press, 1977:15.
[6] SIGERIST H E.A history of medicin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45.
[7] DEROUBAIX M.Are there limits to respect for autonomy in bioethics[J].Medicine and Law, 2008,27(2):365–399.
[8] WILKINSON T M.Dworkin on paternalism and well-being[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96,16(3):433–444.
[9] 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26.
[10] 沈德咏,徐艳阳.关于“安乐死”立法化的理论思考[J].政法论坛,2021(1):174–191.
[11] FADEN R R,BEAUCHAMP T L.A history and theory of informed cons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23.
[12] 满洪杰.人体实验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02.
[13] 庄晓平.西方生命伦理学自主原则“自主”之涵义辨析:从比彻姆、德沃金和奥尼尔的观点看[J].哲学研究,2014(2):93–98.
[1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4–85.
[15] 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11.
[16] 蔡甫昌,郭蕙心.病人自主权利法之伦理观点与实务挑战[J].台湾医学,2017(1):62–72.
[17] 德国民法典[M].5版.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635.
[18] 申卫星.以生前预嘱推动实现临终尊严[N].上海法治报,2022-08-05(B7).
[19] 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J].清华法学,2014(1):157–175.
[20] 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6292.
[21] 李拥军.“家”视野下的法治模式的中国面相[J].环球法律评论,2019(6):86–105.
[22] 刘鹤玲.亲缘选择理论:生物有机体的亲缘利他行为及其基因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114–118.
[23] 范瑞平.儒家当代生命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4] 10万手术费压垮一个父亲,悲剧不能重演[EB/OL].(2019-12-13)[2023-05-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787881693777011&wfr=spider&for=pc.
D902
A
1006–5261(2023)06–0023–07
2023-06-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18BFX114);天津大学研究生文理拔尖创新奖励计划重点项目(A1-2022-004)
翟高远(1995―),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