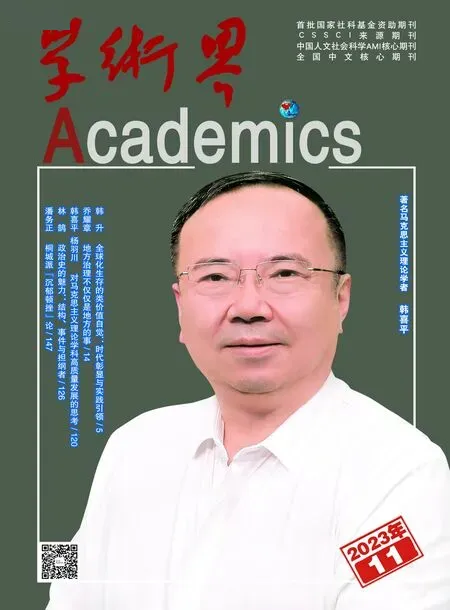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表达及国家形象呈现〔*〕
2023-02-26陈婷婷
陈婷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不断加强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表达能力的建设,是提升国家形象和促进国际交流的一种重要渠道与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话语场中,只有建构和完善能够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才能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同时,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务实的叙事话语表达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同其他国家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进而不断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能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借助叙事话语内容与方式创新,还要不断建构出新的叙事话语资源以维系和提升国家形象,进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议题倡导、议程设置和会议主旨等,也是围绕国际话语场中的叙事话语互动与博弈展开的。谁在国际话语场中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的游戏制定规则,主动发声、善于表达,谁就会赢得更多的主导权和发言权,就能获取更多机会不断提升和展示国家形象。
一、全球治理中国际话语场的变动及叙事话语功能
“全球治理”是人类应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基础性话语,在国际话语场中其也是叙事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向度。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参与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会议,设置各种议题、议程,就是想要借助国际话语场这一平台,进行叙事表达,并对其他主体施加影响。叙事话语功能的调整与转化是为了适应国际话语场的变动与演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国际话语场中各种思潮、观点和理念引发的话语权冲突与交锋。
(一)国际话语场的变动及叙事话语表达
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国际交往中叙事话语的高度重视,国际话语场已成为“不同的传播主体就所占有的话语资源,以期获得受众认同,而行使话语权力、反映话语博弈能力的时空集合”。〔2〕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3〕在国际话语场中,各种叙事话语正是通过在国际层面上世界秩序、全球发展、全球生态、全球变动、国际交往与国家关系等方面的争锋,“积极地构建并重建我们的世界”。〔4〕这里提到的叙事话语主要指对某事件、议题等按照一定的顺序性与持续性进行表达与传播,并且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话语。叙事话语主要借助叙事主体、叙事方式、叙事策略对话语表达进行有效控制,进而产生一种效果和影响。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C. Bremond)认为叙事一般按照以下序列推进:一是基本序列,二是复合序列。〔5〕基本序列是简单叙事,以简单叙事方式达成目标或完成行动;而复合序列则是在基本序列的基础上,调整简单叙事方式,将若干逻辑关系再次组合编排,从而完成简单叙事完成不了的叙事表达。现实中的叙事话语表达,往往要把两个序列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逻辑设定,再根据国际话语场的变动不断调整与优化其功能。在国际话语场中,国家叙事话语一般按照以下方式推进:一是明确叙事议题。在此基础上,控制议程按照“基本序列”方式推进,假定遇到一些阻力,也可以采取“复合序列”方式推进。二是明确叙事主体。明确叙事主体也就是确定“谁来说”,即谁掌控和组织话语议题、决定话语表达方式,确定叙事主体是控制整个叙事的关键。三是明确叙事内容。叙事内容是构成整个叙事的基础,即叙事话语要“说什么”,主要涉及表达哪些观点、内容与要义等,在整个叙事话语表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是明确叙事方式。叙事方式指的是该“怎么说”“如何说”的问题,也就是按照什么程序与步骤的逻辑方式进行叙事,是采取循序渐进式,还是单刀直入式;是选择民主协商式,还是强迫灌输式等。五是明确叙事指向。叙事话语表达要聚焦,要有关注点,需明确价值取向,也就是确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从叙事话语的角度来看,国际话语场是一个被各种权力支配着的特殊场域,有国家叙事话语、国际组织叙事话语以及诸多亚型叙事话语。各种叙事话语处于生产、博弈与变动之中,叙事话语之间相互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国际话语场不断地互动与交融。从国际话语场中的变动,也可以观察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演变及其间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这些权力相互较量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叙事话语之间的冲突与交锋,叙事话语的冲突与交锋突出反映了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提升国家形象这一思考的重要性。
(二)国际话语场中的叙事话语功能
在国际话语场中,如何有效地提升国家形象,确定叙事话语功能是关键和前提。叙事话语功能主要指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张、观点,以及叙事话语按照怎样的逻辑展开并想要取得怎样的效果。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其叙事话语呈现出一定的公共属性,主要选取了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大国责任与义务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议题。在国际话语场中,中国抢占先机、敢为人先,主动承办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并设置议题,全面提升了其国际话语权。其中主要战略举措是连续举办了中国与世界的高层对话,其中主题涉及方方面面。通过议题建构、议程设置将叙事话语向世界各国广泛传播,目的是促使所传递的信息和思想能够被生活在不同制度和文明下的人们理解并接受。叙事话语功能在国际话语场中,按照不同层面定位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话语议题功能定位在全球治理中的一些世界性问题上,话语议题设置、表达及指向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二层次是话语议题功能定位在国家、地区间的合作问题上,话语议题设置、表达及指向部分国家与所在地区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三层次是话语议题功能定位在国内一些问题上,主要是围绕一个国家系列对外方针与政策,进行话语议题设置、表达及指向;第四层次是话语议题功能定位在特定问题的处理上,是针对国内外出现的特定现象、问题进行必要的话语议题设置、表达及阐释。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中国的崛起也促使西方和美国广泛反思自我,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和西方文明并列的重要一极,但是大部分西方人并没有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西方文明统治的威胁。”〔6〕人类文明发展本来就是充满差异性与多样化的,探索文明的方式、路径也绝不可能千篇一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国际话语场中根据自我的发展与现实需求,平等地设定主题与议题,进而与他国展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积极提升、拓展自身的叙事话语能力和空间,使中国式叙事话语充分展示出示范性的“大国新闻”“大国表达”“大国呈现”等特征。中国以当代国际格局大变化为背景,主动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政治叙事”和“战略叙事”〔7〕的根本支撑,而“政治叙事”和“战略叙事”作为叙事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具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话语场中有效提升国家形象的特殊功效,进而达致“增强故事的国际传播力和感染力”这一目标。〔8〕中国深度融入国际话语交往中,正是有效把握了历史规律和顺应了时代潮流,通过制定科学的叙事话语策略、加强叙事话语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议题的国际关注度。中国坚持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开展“政治叙事”,独立自主地对国际问题进行观察、描述和阐释,并积极提出一些新概念、新观点,再经由国际间、国家间、组织间等把这些新概念、新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同时通过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叙述、解释、呈现和宣介中国理念、中国主张。“战略叙事”是指国家在重大事件、决策和议题等方面的叙事话语,在国际话语场中主要围绕各类国际事务,从国际体系叙事、国家叙事和议题叙事三个层面展开,〔9〕其着眼于观念塑造、舆论操控、政策引导,是国家通过叙事话语提升其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进行叙事话语表达时,中国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可能会遭遇西方在战略叙事与话语表达等方面的各种阻挠,因而,需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话语传播、认同与影响力方面不断调整、创新方式方法。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刚开始提出便遭遇一些误读,而我们通过叙事话语的不断阐释、实际运行带来的正面效应以及各方面积极友好的反馈,有效地消除了外界对其的误读甚至恶意解读,进一步提升了外界对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的善意认知。
二、国际话语场中国家形象的认知及呈现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场中,总是想方设法增强国际话语权以提升其国家形象。因为,国家形象塑造在本质上既是国家间话语实践的过程,也是国家间话语权博弈的结果。国家形象在多方话语交流与博弈中得以塑造、呈现与传播。
(一)话语流变中对国家形象的认知转换
自19世纪末起,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语言转向”,引发了学界对人类语言研究的关注。特别是从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话语即是权力”的论断以来,话语理论的影响力日趋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话语理论开始进入国际话语场中,对国际关系起着明显的建构作用。话语不仅能够呈现、建构、改变或提升国家形象,还能够为影响国家形象的情境提供一定的语义阐释,使国家形象的塑造及呈现表现出多样性。通过话语定义、话语叙事、话语影响和框定事实等方式,使国家形象成为国际交往中,认识、理解和判断其身份、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维度与依据。由于话语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权力样态具有建构功能,既可以不断改变传统的国家形象定义,也可以对形象实施新的塑造,还可以不断进行重新解读和赋予其新的形象与意义。因此“话语成为一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形式,在塑造国家身份以及身份表达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10〕总之,话语已成为国家形象生成与变化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可以通过话语为研究国家形象提供更具体、更微观的动态视角。
任何一个国家,其叙事话语均承担着传递、解释以及宣传政策信息和国家意志的功能,在治理者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与社会民众之间发挥着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作用。在国际话语场中,国家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致力于“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11〕这种话语的建构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会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还涉及话语表达、修辞与影响等方面。可以说“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需要用语言加以叙述的,用语言加以表达,用语言加以理解的”,〔12〕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亦需要用话语去表达、建构与呈现。话语构成了人们对国家形象认知与评价的基础条件。
(二)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
国家形象总是与话语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大的国际话语权能为塑造、维系和提升一国形象提供强大支撑。“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国家形象的较量,实质也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13〕通常,一个国家会设计和建构出一整套系统性的叙事话语符号和表达形式,并谨慎地选择恰当的话语,对话语的内容与结构进行精心安排,从而引导公众按照其给定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国家形象。当国家形象受损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话语策略降低负面影响,修复形象。美国学者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的“形象修复理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他指出:“当国家形象受到威胁时,有必要为一定行为做出解释、辩护、调整、道歉和寻找借口。”〔14〕所以,国家形象的建构、呈现与变化过程,也包含着国家身份的话语表达、传播与诠释。依靠话语策略的运用,可以对国家的身份进行修复,进而重塑国家形象。事实上,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地展示出自信与强大的形象也有利于巩固、提升该国的国际话语权;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完善、科学和理论化的话语体系支撑,就会丧失话语主动权和主导权,国家形象也就失去了依托。国际话语场中国家间的互动可以借助叙事话语对议题进行控制,让国家形象与叙事话语勾连在一起,那么国家形象必然会伴随着话语流动、表达与影响而不断变化。谁的叙事话语能力、话语议题、话语议程和媒介实力等处于优势地位,谁就会在议题设置中掌握主动权。在国际话语场中,每一个国家都会竭尽全力地运用其话语资源、设置有效的舆情议题、形成评价规范,并通过各种传播、报道和时评对其国家形象进行评论和定位,这也表明了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深刻的关联性,两者互为影响、相互促进。
(三)国际话语场中的国家形象呈现
在国际话语场中,由于话语具有十分突出的实践性和建构性功能,因此,其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发挥着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形象塑造涉及话语客体(受众)对话语主体的感知、评价及认可。这说明话语主体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来塑造国家形象,话语客体(受众)也可以对他国塑造的国家形象进行解构、再解读和再呈现。话语本身就是国家身份和国家资格的重要载体。虽然,国家形象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叙事话语是塑造与呈现国家形象最重要的一种工具与方法。因为任何国家行为都需要通过叙事沟通和叙事表达,才能被有效感知并关注,而国家身份、资格也是通过叙事话语方式产生与呈现的,从而使自我身份、资格与国别等与其他国家明显区别开来。国家身份总在被不断地阐述、改变和重新塑造,不断通过叙事话语呈现、延续和改变。国家形象的建构、呈现与变动,离不开叙事话语的实践,也离不开不同叙事话语的互动与影响。
国家形象塑造一般是自我形塑与他者形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自塑”与“他塑”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在国际话语场中的叙事话语博弈来完成。国家形象的塑造实质上是由叙事话语承载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大政方针等议题,并进行广泛的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进而促进多方对其充分地了解与认同。特别是在国际交往中,一国的形象大多依靠本国媒体与他国媒体在交往与互动中得以形塑、呈现和传播,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仍以国家和媒体的话语实践为主要依托”,〔15〕也即是通过“自塑”与“他塑”的相互影响而生成。“自塑”呈现主要通过对自身形象的实际表述以达到对他国产生影响的目标;“他塑”呈现主要借助他者对国家形象的评价与感知来影响自身,国家形象最终在双方话语交流与博弈中得以塑造并传播。以叙事话语方式认知他国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一方面他国可能会采取比较客观的叙事报道与传播方式;另一方面他国也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方式的解读,甚至是以污名化方式进行诋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国际话语场中,中国的话语叙事“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过程”。〔16〕主要表现为从感性认知逐渐转向理性分析,再到不断优化与提升。这种构成变化与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和自我身份的定位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目前,中国主导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在以“中国”为主体的叙事话语中展现的最为直接。而在以“世界”为主体的叙事话语中,中国始终积极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生态”以及国际和平与发展等倡议。这些倡议被广泛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话语转化为一种世界话语,为其他国家及其人民提供了关于中国在政治文明发展等重大议题方面的一些认知与判断。这种认知与判断,既是对中国政治体制与政策的认识与回应,也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与评价,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交往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能力。
三、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转向及国家形象困境
国际话语场中国家间话语权的争夺,不仅是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还是发展、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依据与手段。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话语场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革与转向,但是西方一些大国依旧在叙事话语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具有很强的支配力。
(一)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转向
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是以“封闭—开放”“中心—边缘”“等级—平等”“专制—民主”等系列二元对立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但随着新兴国家话语表达能力不断提升,这种传统叙事话语建构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世界观、时代观、责任观、发展观、合作观正巧妙地融入国际话语场中并产生广泛影响,有力推动了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的深刻转向。
一是叙事话语转为“解构”与“建构”并存。在国际话语场中,发展中国家的叙事话语建构能力日益提升,在与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对抗时,能够“充分运用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资源,突破在话语建构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积累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此打破西方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形成的话语陷阱和话语霸权”。〔17〕在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解构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话语的建构能力,一些国家在国际话语场中运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网络话语进行系统性建构,积极融合各种话语,打造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风格与气派的话语体系,形成一整套具有传播力和感召力的叙事体系。二是从“他塑”到“自塑”的动态嬗变。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冲破了西方少数大国话语的宰制和围猎,逐渐由被动接受“他塑”转向主动“自塑”,尤其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敢于积极发声、主动出击,能够自信地树立国家形象,敢于在国际话语场中,抢占舆论主通道,加强舆论引导、传播真相、粉碎谣言、凝聚人心、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消除偏见和误解,营造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舆论氛围,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三是叙事话语逐渐转向数据化和可视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在叙事话语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叙事话语形式、结构与途径的不断创新,其中,可视化就是当前叙事话语发展最明显的表征与特点。可视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图文并茂的形式,带来比一般文字更好的叙事效果,这种视觉化叙事话语更易于调动民众的认知、情感与心智。叙事话语转向数据化和可视化,已经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可视”范畴,促进了其与“可听”和“可感”的交融。
(二)国际话语场中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话语场中,虽然多元差异的叙事话语影响力日益增强,但由于西方少数国家的话语霸权持续存在,以及叙事话语表现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国家对国际话语权主导并垄断,形成了一整套强大且稳固的传播体系,牢牢掌控住了国际话语叙事的主导权。这些国家顽固地坚持以自我为中心,采取“推己及人”的叙事方式,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同时,这些国家把二元对立的话语架构,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中国与美国比较’等话语逻辑,积极塑造‘中国—美国’的联想序列”。〔18〕它们运用多种技术、借助多种组织与多种渠道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话语攻击。二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国家形象在展示方面,依然存在一些“落差”“逆差”“反差”现象,甚至遭遇各种诋毁。这些现象不仅体现了国家间软实力与硬实力之较量,也体现了国际舞台上各国叙事话语能力与影响力之竞争。例如,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抱有怀疑、排斥态度,甚至不惜对其污名化;把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合作,攻击为搞“魅力攻势”;把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以及与非洲各国的合作,攻击为搞“新殖民主义”;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攻击为“分而治之”;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比作新殖民战略下的“马歇尔计划”等。三是中国国家形象遭遇西方话语叙事的妖魔化。西方霸权国家借助在各类媒介上的技术优势,不断炮制阴谋论,搞“信息疫情”战,肆意散播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借机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诋毁。四是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话语概念化能力不足。这种能力不足,主要体现为叙事话语的原创性、引导性与传播能力较弱,特别是在重大标识性概念方面建构能力不足,主动回应各种声音的能力不够,在国际议题设置、议程掌控以及叙事话语导向等能力方面均有待加强。五是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叙事话语防御型表达模式有待改进与完善。中国的这种叙事话语防御型表达主要采取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宣传路径,缺乏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主动型的双向互动;这种叙事话语表达往往采取比较刻板的新闻发布方式,宣教与说教色彩浓厚;其内容比较单调且缺乏吸引力,存在着明显的形式化问题,缺乏深度与宽度。这种叙事话语防御型表达模式,在国际话语场中很难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更难以产生范导力;同时,在各种负面立场、各种偏见和各种杂音包围下,难有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差,无法有效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因此,在新时代的国际话语场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9〕就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如何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认识和阐述世界性的发展问题,才是实现话语权突破的关键。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有效地平衡好国家话语场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关系,进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在认知上存在的一些“落差”“逆差”和“反差”现象。
四、提升叙事话语与改进国家形象塑造的策略与进路
在国际话语场中,只有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叙事话语,才能有效提升国家形塑,首先,要以标识性概念聚焦国家形象;其次,要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双重语境加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再次,要以“自塑”与“他塑”协同的方式呈现国家形象;最后,要以可视化表达改进国家形象。
(一)以标识性概念聚焦国家形象
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需要以标示性概念作为基础性要件。标识性概念主要指“意义明确且内涵外延清晰,有代表性、指示性及核心性的概念”,〔20〕具有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般的意旨。在国际话语场中,中国政府提出了“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1〕这种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具有一定的范式特征。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打造出的标识性概念,以彰显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该概念自提出以来逐渐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理解,更是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目标及愿景,相继被联合国以及安理会决议所采纳。中国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标识性的叙事话语,彰显了当代中国的“天下观”“义利观”与“和谐观”,凝练了华夏文明智慧,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体验和经历的“共在性”联结,不仅超越了国别的认知局限,实现了人道主义观念认知和全球福祉聚焦的视野转向,同时在概念内涵上亦存在巨大的延展性。
(二)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双重语境提升国家形象
要从“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和“世界大局中的中国”双重逻辑出发,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中国视野中的世界”,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化叙事逻辑,是以单一的“西方”文明叙事,形塑人们对于西方国家文明、进步形象的整体性认识;而对于非“西方”国家,则被“西方”文明叙事整体性地描述为愚昧与落后。如果在国际话语场中只遵循“西方中心主义”一元化的叙事逻辑,拒绝多元性与差异性,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西方话语塑造出来的落后的国家形象,那就是剥夺了这些国家基于自己历史和文化禀赋,建构与维系其国家形象的权利。现实中的国际话语场充斥着多元叙事话语,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表达逻辑。中国一直在不断提升叙事话语表达能力,力争在国际话语场中获取越来越多的权力,特别是要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双重语境,统筹好一般性与特殊性双重关系,在世界发展大变局之背景下,讲明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智慧与经验,尤其是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与意义。
(三)以“自塑”与“他塑”协同方式呈现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主要通过“自塑”与“他塑”两种方式完成建构。这两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传播主体的自我形象塑造,另一种是作为传播客体的他者形象塑造。自塑犹如自我独白,他塑则像一面镜子折射他者认知”。〔22〕“自塑”与“他塑”间包含着“破”与“立”的关系。“破”就是要从国际话语场的实际状况出发,努力打破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话语霸权,突破试图把“他者”的话语置于自我控制之下的霸权行径;“立”就是从国际话语场中多样化的叙事话语与叙事体系出发,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合理诉求,努力构建起具有共识性与共同价值的叙事话语逻辑。而“自塑”与“他塑”二者间若能有效互动,则更有利于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话语场中我们要积极倡导沟通与交流,借助有效的沟通与交流营造共同的话语空间、建构共同的话语平台;同时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风采,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语言以及自己建构的话语体系,向世界生动讲述和展现更加真实、立体、文明和开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同时要通过他人之口来真实描述中国,用他者叙事话语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中国,要特别重视叙事话语中“他塑”的主体、方式、内容及特征,要利用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为我们发声,利用世界媒体峰会、金砖国家媒体峰会等机制提升我国话语影响力,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如推特、Facebook等进行话语表达与传播。以“快说”的方式,压缩时空距离,实现无缝对接,尽快发声、争抢时效;以“敢说”的方式,仗义执言、不屈服话语霸权,从全球治理与人类发展的高度,坚定地表达国家主张、国家观点;以“会说”的方式,表达话语背后的思想与理念,把话语背后的“礼”“义”“道”系统且巧妙地阐释出来。
(四)通过可视化表达改进国家形象
可视化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叙事话语方式,它像文字叙事那样拥有反映自身特质的内在逻辑。可视化的实质在于通过数字技术把相关信息与内容转变为直观的图像,把文字信息变为形象符号,不仅可以看图说话,同时还可以利用图像按照自我要求与目的进行系统性整合。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叙事话语可以更多地借助于数字技术,收集、储存、分析与整合各种数据,挖掘出数据与可视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可视化直观展示国家形象。由于数据新闻可视化叙事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可视化技术已经突破了可视性,延展到了可听、可感的层面。叙事话语的可视化表达不仅有助于整合信息,而且在解读文本、揭示事物间的联系、表达观点上更加清晰和有效,有助于塑造国家立体形象,也有助于人们直观地对国家形象加以认知与判断。
当前,全球正处于各种势力交错繁杂、互相冲突的时代,全球性的一些难题更加凸显,而在治理这些难题方面,各主体有效合作与共识度不够。在这一艰难时刻,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中更应当一如既往地坚守务实、平等、发展等核心叙事话语理念,始终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发展观念,用普惠全球、兼容并包的理论方案“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3〕面对国际话语场中纷繁驳杂的观点与看法,中国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凝聚最大的共同价值,彰显兼容并包的大国胸襟,将中国叙事话语表达提升到推进与完善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去。
五、结 语
在国际话语场中,深入研究叙事话语与国家形象的内在逻辑关系十分必要。美国学者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曾指出“叙事”经由不同学科的引用和改造,显然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特质,已超越一般性的“表现形式”成为“人们认识、理解以及解读社会生活的方式”。〔24〕对此,美国学者卡罗尔·弗莱舍·费尔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的看法更是直接和坦率,他认为所有的国家叙事话语都关乎“权力”,呈现出高度的“类型化”〔25〕特征。因此,探讨国家形象,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社会观念层面上,忽略其软实力的运用,特别是忽视对其叙事话语的综合运用。国家形象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国家形象的较量,实质也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在全球治理大变革中,“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如何相互塑造,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26〕国家形象的建构、维系与提升,需要叙事话语提供支撑;尤其是在国际话语场中,我们不仅要积极主动地建构灵活生动、便于互动且议题多样的话语体系;更要抓住具体议题,主动呈现叙事话语,借助国家、国际组织等主体,在互动中进行充分的叙事话语交流与沟通,打破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格局,不断提升叙事话语的表达能力。
注释:
〔1〕〔19〕〔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2〕王景云:《对外传播话语场域的构成、运行与评估——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等:《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4〕〔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52-66页。
〔5〕Claude Bremond,“La logique des possibles narratifs”,Communications1966(8),pp.66-82。
〔6〕参见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专访:《中国崛起正促使西方广泛反思自身制度》,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6091。
〔7〕参见杨明星、潘柳叶:《“讲好中国故事”的外交叙事学原理与话语权生成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8〕Mona Baker,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4.
〔9〕Roselle L.,Miskimmon A.& O’Loughlin B.,“Strategic Narrative:A New Means to Understand Soft Power”,Media,War and Conflict2014 7(1),pp.70-84.
〔10〕Ruth Wodak,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p.29.
〔1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12〕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3〕林伟江:《国家形象与传媒的研究综述》,《今传媒》2013年第11期。
〔14〕William L.Benoit,Accounts.Excuses and Apologies:A 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70.
〔15〕赵永华、王睿路:《制度性话语权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对外传播》2021年第3期。
〔16〕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17.
〔17〕彭修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叙事——从接触、融入到引领》,《当代世界》2021年第12期。
〔18〕赵鸿燕:《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基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20〕张政文:《中心议题、话语领域、标识概念:在电影历史谱系与逻辑中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2〕参见欧阳辉:《国家形象何以自塑与他塑》,《学习时报》2019年4月15日。
〔24〕Somers M.R.,“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Theory and Society1994,23,p.649.
〔25〕Feldman C.F.,“Narrativ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Group Narratives:Patterns of Interpretive Cognition”,in Brockmeier J.& Carbaugh D.(eds.),Narrative and Identity:Studies in Autobiography,Self and Culture2001,pp.129-144.
〔26〕魏玲:《大变局下的中国与国际发展合作》,《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