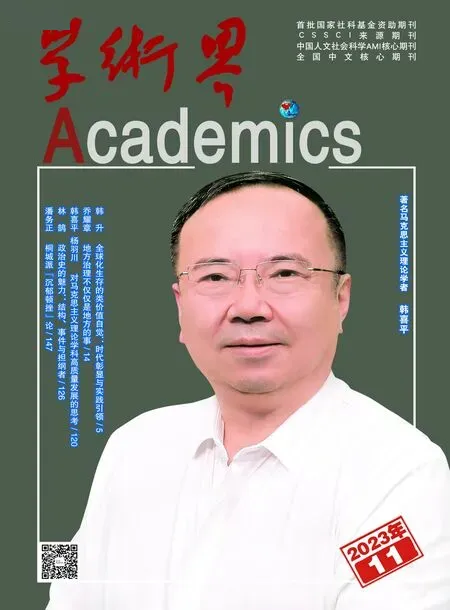生命政治视域下资本主义暴力的分析与批判〔*〕
——以巴特勒、齐泽克和韩炳哲为例
2023-02-26孔明安刘婵婵
孔明安, 刘婵婵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朱迪斯·巴特勒、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韩炳哲均是当代资本主义暴力问题的批判理论家。近些年来,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战争的框架》《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场域中的伦理》、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以及韩炳哲的《暴力拓扑学》《精神政治学》等著作相继出版,但国内学界对暴力理论的关注相对较少,尤其对巴特勒和韩炳哲的暴力理论研究更是尚未展开,故而,探讨和梳理当代资本主义暴力理论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1967年,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在《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结构暴力”,认为“结构暴力”是由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导致的没有具体“施暴者”的暴力,它通常与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相关,虽然其作用形式较为间接、隐蔽和缓慢,但所造成的对生命和人权的伤害程度却是巨大的。〔2〕加尔通的暴力理论不仅引起和平学研究的关注,也引起政治、伦理、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9·11”事件后,面对无数生命在所谓的“合法暴力”中逝去,美国左翼学者巴特勒从政治伦理视角思考国家暴力的运作逻辑和非暴力伦理的规范性条件;西方当红左翼学者齐泽克对之则显露出一种冷峻深邃的精神分析式的批判态度,并指出“暴力类型学的一种冷静的概念的建构必须忽视创伤性冲击”,〔3〕亦即避开显而易见的灾难性暴力,转而探讨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作为“实在界”而存在的基础性系统暴力。韩裔德籍学者韩炳哲则从当今绩效社会出发提出了肯定性暴力,认为暴力不仅涉及社会系统所有成员,而且由于规训技术的日益精妙,暴力与自由业已合二为一,规训对象也由肉体转至精神。在此,厘清三位西方左翼学者在生命政治视域下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暴力问题的理论差异,探求其差异背后的内在逻辑及其联结,对于深化当代资本主义暴力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巴特勒:政治伦理视角下的国家暴力批判
生命是政治权力干预和管理的对象,如何认识生命、政治权力及其二者关系构成生命政治的关键议题。巴特勒认为现代生命政治的特点是生命资格与生命权利的不平等性,具体是指“在权力的区分运作下,有些人群成为了值得承认与表征的主体,而另一些人群则无法享有这种待遇”。〔4〕当政治权力以主权之名罔顾法律限制并导致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利暴露于危险之中时,政治权力由此演变为国家暴力。
首先,巴特勒使用“国家暴力”这一概念旨在揭示生命受到承认的公正社会形态与生命遭受排斥的脆弱处境之间的乖离现象,继而说明生命的脆弱处境源于社会规范的扭曲和政治权力的滥用。“所谓的国家暴力不仅包括战争,还包括各类‘合法暴力’。在其运作之下,特定群体赖以呵护脆弱特质的最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了剥夺。”〔5〕在她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国家权力打着“铲除恐怖”“实施民主”“全球责任”的旗号“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暴力”的执行者,然而国家权力的种种反恐行为非但未能消除暴力,反而频繁地引发暴力与战争,制造不安的生存境况,致使无数生命在被褫夺法律政治地位之后沦为“无效生命”。美国的一系列反恐行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暴力,体现了绝对权力主体自我膨胀的自卫观念。“所谓的绝对权力主体是这样一种主体,他不可能受到他人冲击或影响……不仅否认自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特质,还试图伤害他人,使之成为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对象,由此使脆弱不安成为他人的特质与生存状况。”〔6〕也就是说,绝对权力主体将脆弱特质和遭受侵犯的可能性移至他者,以使自身免受暴力侵扰。这也是巴特勒将对国家暴力的批判与社会不平等的批判联系起来的原因:国家暴力是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现,它加剧了生命价值与哀悼权利之间的差异。在绝对权力主体的幻想之中,由于对他者的潜在暴力的恐惧,以至于明明没有做出攻击的人也会被视为正在攻击,于是,权力主体先发制人地将此类生命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剥夺掉。在不平等的划分标准之下,一类人群的生命值得保护与哀悼,另一类人群的生命则不成其为“生命”。巴特勒对此感慨道:“当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算作主体。”〔7〕基于国家暴力造成的生命脆弱处境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类生存的不平等境遇,巴特勒将以“合法性”为名的国家暴力与“恐怖主义”一同视作“当代暴力光谱中的一部分”。〔8〕
其次,绝对权力主体的幻想和投射方式来自权力“框架”的区分运作,“框架”生产、建构并支撑着国家暴力。“框架”原本是指相片或图像的边框,它规定人们对事物感知和理解的范围。借助图像框架这一绝佳隐喻,巴特勒进而对权力运作逻辑即权力“框架”予以深层说明:“框架乃是国家权力施展自身强制安排能力的所在……各类事件与行动在框架内部得到表征之前,可表征领域早已受到积极有效而又悄无声息的限定,一系列的内容与观点永远无法公之于世,因为框架不允许它们得到表征。”〔9〕“表征领域”位于框架之内,它是可以得到表征与承认的事物;“可表征领域”位于框架之外,它受到国家的限制与框定,是被权力暗中排除和否定的内容。可见,权力主体利用框架塑造着承认和排斥的方式。依循这种区分运作逻辑,框架有效地确立或否定了各种类型的生命主体。毋庸置疑,国家暴力主体对框架的限定势必保证绝对主权者及其“我群关系”范围内的利益,并利用框架塑造生命观念,确立文化规范与社会秩序等,因此,“框架总是会排除、排斥某些内容,它总是会否定其他‘现实’版本的真实与合法地位,摒弃一切有悖于‘官方’版本的异端”。〔10〕更进一步,政治权力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扩大了国家暴力的范围,大众传媒之下的视觉图像亦步亦趋地服从于国家当局强制规定的视角,“暗中塑造、补充着所谓的政治背景”。〔11〕借由各类物质媒介,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圈定公共视听范围,塑造公众情感反应。在此意义上,巴特勒指出框架就是一种暴力,“暴力的定义打从一开始就是特定框架所赋予的,因此当它到了我们面前时,永远都是以被框架诠释、整饬后的样子出现”。〔12〕
再次,即使国家暴力是塑型主体生命的条件,但在巴特勒那里,她并未将暴力确立为主体塑型过程中的全部要素,而是试图阐发主体同权力的共谋关系。在新书《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场域中的伦理》中,巴特勒引入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回应了这一问题。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超我是一种通过蓄意自我克制来对抗破坏的方法,也就是将破坏性导向本身的破坏性冲动。〔13〕由于受社会规范和道德良心的支配,超我往往将对外界的攻击性冲动转化为对自身的压抑和破坏,甚至走向对生命的否定和毁灭。巴特勒认为,正是利用了超我以“反求诸已”的方式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机制,政治权力才得以实现规训主体的目的,国家暴力的发生也才得以成为可能:“主体若屈服于谋杀式的权力形式,就等于是制定出针对自身的暴力,为超我的结构树立起一种政治权力,即一种内化的暴力形式。”〔14〕
最后,巴特勒进行国家暴力批判的目的并不单是揭露主体与权力共谋的悲剧面向,更是力图表明主体和权力之间存在的断裂为主体反抗国家暴力、践行非暴力伦理提供契机。尽管“暴力”塑型主体,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作用并非一劳永逸,“规范塑造主体乃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规范不断重复,因此也不断地同所谓‘塑造条件’发生‘断裂’。”〔15〕规范的操演和重复昭示着规范权力内部存在裂隙和抵牾,也表征着主体本身就具有不连贯、不可控、未完成的特质,这决定了实现彻底塑型主体的不可能性。
在《脆弱不安的生命》《战争的框架》这两部著作的最后部分,巴特勒将关注点转向非暴力伦理,以此作为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挑战的基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把非暴力解读为“消解暴力”,巴特勒所理解的非暴力“并不是什么平和无忧的状态,而是有效表达义愤的社会政治斗争——非暴力乃是审慎表达的怒火”。〔16〕在不公正框架的作用下,主体的愤怒和欲求同样需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表达,从而为他人所察觉和理解。这种“审慎表达的怒火”有助于打破永无止境的暴力模式。巴特勒指出,“非暴力既不是一种德性品质,也不是一种观点立场,更不是什么普适原则。非暴力指出了主体身不由己的矛盾处境:他满腔怒火地忍受着暴力的摧残与蹂躏,却又竭尽全力地同暴力进行着斗争”。〔17〕非暴力理念体现了主体在道德伦理层面的挣扎,即主体并非拥有完美灵魂、毫无攻击倾向的生命体,而是能够同自身的破坏潜能进行抵抗,通过拒绝盲目的愤怒和暴力来打破自恋自私的以暴制暴这一封闭循环的生命体。就此而言,正是因为暴力潜能根植于人类精神机制,“伦理和政治的反思才会聚焦在非暴力的使命上”,〔18〕非暴力才构成一项伦理义务。
总之,国家暴力是在政治框架运作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权利的不平等划分,同时政治权力利用主体在精神层面的共谋欲望实现对主体的规训和塑型。然而,社会规范本身存在的断裂、脱节以及主体的矛盾特性,为主体打破国家暴力、走向非暴力伦理创造了条件。
二、齐泽克: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系统暴力批判
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齐泽克以“斜视”的方式剖析和总结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类型,重点探讨了更具隐匿性和破坏性的“系统暴力”。借助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齐泽克对“系统暴力”的研究旨在让人们摆脱直接可见的非理性暴力,将人们的目光转移至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相关的制度结构层面,并力图从更为隐秘和本质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系统暴力的发生机制予以深层阐释。
其一,系统暴力与后政治的生命政治即恐惧政治紧密关联。“系统暴力”是指为了维持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而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暴力,它表面上常常被感知为事物的“正常”状态,实质上却隐藏着极大的破坏力量。〔19〕齐泽克用物理学概念对其作了形象比喻:“系统暴力就像物理学的‘暗物质’,它是所有突出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对立物”,“支撑着我们用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标准”。〔20〕系统暴力是相对于我们常说的可见暴力而言的,这种暴力无法被直接看见或者觉察到,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构成整个社会层面的基础性暴力。齐泽克援引了16世纪西班牙入侵墨西哥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刚果大屠杀,此间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过程中丧命,但一些西方自由派人士却普遍认为这是历史的“客观”进程,无人刻意制造灾难,甚至比利时国王还被教皇册封为圣人,因为他将刚果殖民地的获益全部奉献给了比利时人民。如此一来,恶贯满盈的比利时国王俨然成为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与埃蒂安·巴里巴尔的过剩暴力相关联,齐泽克认为这种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系统暴力,是“一种自动的排外运动”,〔21〕它认定一些生命是可有可无的。
更进一步,齐泽克将系统暴力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现实坐标之中加以分析。他指出,“当代政治的主流模式是后政治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在根本上是一种恐惧政治;它聚焦于防卫那些潜在的欺骗或骚扰”。〔22〕恐惧在现代社会中始终“在场”,英国学者鲍曼认为“与恐惧的斗争是一项终生的任务”。〔23〕而当今生命政治的出发点就是应对和处理各种风险和恐惧,这些恐惧包括移民入侵、高犯罪率、流行疾病、文化冲突、生态灾难,等等。尤其在以不确定性为显著特征的风险社会,政治权力倾向于放大上述恐惧,以更激进的方式面对各种风险,尽力削弱“他者”的威胁,保证“我们”的安全。齐泽克据此归纳了当代生命政治中出现的两种生命形态:一种是剥夺了所有权利、需要被政治管制的“赤裸生命”,如关塔那摩战俘、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等等;另一种是被视为暴露在危险之中、需要被保护和尊重的“脆弱生命”,如多元文化主义之下的特殊群体。然而,这两种生命形态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种立场,即双方内在地含有对潜在危险和真正他性的排除,所谓需要被保护和尊重的“脆弱生命”无非是拔除了“螫针”的无害的“赤裸生命”。因而齐泽克认为,在恐惧政治的运作之下,所有生命都是行政管理的对象,都是消除了主体深渊维度、化约为抽象对象的“神圣人”。由此观之,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恐惧政治、不宽容的政治,其实质就是系统暴力,无论它将一些群体妖魔化为“赤裸生命”对其进行排斥,还是标签化为“脆弱生命”对其进行保护,其目的都是祛除他者中具有破坏性的成分,从而保障政治主体的绝对安全、维持资本主义系统的顺畅运行。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暴力采取了“新外观”即慈善资本主义。以慈善形式促进社会分配正义本是缩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路径,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慈善却“成为隐藏经济剥削的人道主义面具”。〔24〕齐泽克以“咖啡伦理”为例分析了星巴克广告所暗含的慈善暴力。“通过星巴克‘共爱地球’计划,我们购买的‘公平贸易’咖啡多于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确保种植咖啡豆的农民的辛苦工作得到公平的回报。此外,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并改进咖啡种植业务及其连锁品牌……一杯星巴克咖啡中的一部分将会为这一地区提供舒适的座椅、美妙的音乐以及良好的休憩、工作和闲谈的氛围……当你选择星巴克时,你正在从一家具有关怀之心的公司购买咖啡。”〔25〕星巴克咖啡价格之所以高于其他品牌咖啡,是因为消费者购买的是包括对生态环境和第三世界生产者的社会责任在内的“咖啡伦理”。拉康的“三界说”对此提供了有益思考。具体而言,消费者购买产品时考虑的不是“直接实用的实在界(良好的健康视频、汽车的质量等)”,也不是表征“身份地位的符号界”,而是注重“愉快和意义体验的想象界”。〔26〕这便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奸险之处,它不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性能或彰显消费者社会地位等方式直接而真实地引导消费,而是假以“伦理”“生态”“责任”等各种慈善名目制造出某种虚假紧迫感,诱导人们进行一种“我们必须马上行动”的虚假感受式的消费。当人们心甘情愿地为“咖啡伦理”支付更为高昂的价格时,资本家同时也实现了“从爱欲到荣耀的转移”,〔27〕即从财富积累的爱欲逻辑转向社会认可和声誉。就此来看,所谓的资本主义“慈善”事业十分巧妙地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而大多数人很难察觉到这一剥削过程。
其三,剩余快感是支撑资本主义系统暴力的深层运行机制。“剩余快感”本是拉康理论的核心概念,又称对象小a,即“在它之内而非它”。〔28〕作为拉康派精神分析的继承者,齐泽克进一步将“剩余快感”规定为由对象的积极经验属性所带来的一种额外的、过度的满足。〔29〕按照精神分析理论,主体本身是不完满的、匮乏的和分裂的存在,其中总有一部分东西无法被彻底象征化,这一不可象征化的“剩余”构成了主体欲望的原因。它决定着主体欲望的生成,同时又是主体欲望不可抵达的彼岸,因而主体只能在“再来一次”的重复强迫中追求对对象的过度享用,却无法真正获得快感的完全满足。齐泽克将此逻辑推进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中,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依托剩余快感这一内在驱动力才源源不断地滋生出系统暴力。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淫荡超我面向“表征了权力自身‘不能言明’的剩余快感”,〔30〕亦即隐秘的暴力之维。以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为例,齐泽克认为冠以“正义”“民主”等名义进行的反恐行动掩盖的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野心及其在实施暴行过程中的淫荡快感。另一方面,以疯狂增殖为固有特征的资本逻辑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31〕资本主义社会的“创伤性剩余”表现为生产方式结构的不平衡,而为了掩盖这一结构不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则将这种过剩/余数为之所用”,〔32〕进入了一种全然不顾社会现实影响的、令人战栗的驱力模式,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永不停息地扩张性再生产,保持资本的不断增殖,继而维系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效运转。基于此,齐泽克直接将资本逻辑定义为可怕的“实在界”,它以一种隐匿的、客观的方式支配现实世界却又难以为人们所察觉。
在齐泽克的理论视野中,当代政治已经进入到了后政治时代,后政治的生命政治表现为以恐惧为驱动原则的政治模式;系统暴力则体现在这种将所有生命化约为行政管理对象的统治逻辑之中,它以剩余快感为核心逻辑,隐匿在不断扩张的政治权力和永不停息的资本逻辑背后,成为社会主体不可抗拒的命运。当下,面对资本主义系统难以自我维系的现实窘境,资本主义另辟蹊径地采取了“非牟利的、经济之外的慈善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循环”,〔33〕但慈善资本主义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资本主义”,而非“慈善”。
三、韩炳哲:绩效社会视角下的肯定性暴力批判
与巴特勒、齐泽克不同,韩裔德籍学者韩炳哲认为,在以绩效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暴力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即从排斥性暴力走向肯定性暴力,后者旨在消灭一切可能妨碍资本流动的他者,以便快速实现经济效益。为此,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术不再是对主体的压迫、剥削、规训,而是通过对主体精神世界和自由意志的利用,培养一种自我肯定、自我优化、自我剥削的主体。
在《暴力拓扑学》中,韩炳哲区分了暴力的两种类型即“宏观物理暴力”与“微观物理暴力”。他认为,宏观物理暴力遵循以否定逻辑为特征的免疫模式,免疫防御的对象是他者。他者意味着否定性和异质性,既对主体构成侵扰和危险,同时又辩证地成为主体通过他者之迂回完善自我、建设自我的积极力量。因此,在免疫模式之中,“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34〕不同于外显的宏观物理暴力,微观物理暴力则是含蓄而隐性的,它“通过过剩的扩张将主体解散,从而完成对它的去内在化”。〔35〕“解散”是剔除和解除一切可能导致免疫反应的阻滞,使得暴力在同质化空间里肆意增生。在现代社会,微观物理暴力采取的是“精神化、心理化、内向性的方式”〔36〕侵入主体,基于其不可见性,主体常常对此浑然不觉。透过韩炳哲对系统性暴力、扩张性暴力、全球性暴力等微观物理暴力形式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尽管微观物理暴力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呈现为一种消灭他者、积极扩张且极具隐匿性的“肯定性暴力”。他强调,“世界向肯定性发展,由此产生了新的暴力形式。……肯定性暴力不是剥离式,而是饱和式;不是单一排他,而是兼收并蓄。因此,人们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暴力形式。”〔37〕肯定性暴力的核心特征是剥夺他者身上的排斥性和异质性,消除敌对性关系,继而实现自身的积极扩张。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扩张性成群”,即“过度的绩效、过度的生产和过度的交际,过量的关注和过分的积极主动”。〔38〕由此看来,肯定性暴力是对微观物理暴力的一种直观表述。鉴于肯定性暴力是对他者的驱逐和自身的过度扩张,韩炳哲认为由此产生的必然是一种扁平化、同质化、透明化的世界,而主体在这一回避了否定辩证法的场域中只能走向病态自恋与自我毁灭。
肯定性暴力的隐秘逻辑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产逻辑,剥削形式由此演变为“主仆合一”的新型剥削,即主体在肯定性的“能够”律令下自愿进行自我剥削,最终促成资本的无限扩张。韩炳哲借用德勒兹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对“鼹鼠”和“蛇”的隐喻进一步阐释了他对规训社会与绩效社会的理解。在他看来,代表规训社会的“鼹鼠”是一种屈从主体,其封闭有限的活动空间束缚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然而,后工业社会是追求生产力无限扩张的绩效社会,而“蛇”则可以通过自身运动为生产力开辟空间,由此,“资本主义体系为了创造更大的生产力由鼹鼠模式转化为蛇模式”。〔39〕“蛇模式”与绩效社会的生产模式紧密相关,资本主义经济无节制的过量生产逼迫人们不断地打破边界、自发地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连贯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体系从剥削他者转向自我剥削,从‘应该’转向‘能够’”。〔40〕具体而言,传统规训社会秉持严格残酷的“应当”律令,其特征是震慑力和统摄力有余而生产后劲不足,主体虽然受制于外在压迫而拼命工作,但生产效率和生产空间有其边界和限制,因此生产力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便无法继续增长。绩效社会之下的“能够”律令则解除了一切管制思想,将主体塑造为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鼓励主体自我管理、自我设计和自我统治。“绩效社会是个兴奋剂社会”,〔41〕它对主体发出无尽的“你能够”“你可以”的肯定性要求,使主体自发主动地扩张和剥削自己,并保持一种狂热亢奋的工作状态,进而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地创造生产力。韩炳哲将这种沉溺于内在而隐性的自我暴力之中的新型主体称之为“仆—主”或“主—仆”,主体看似从自我出发,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但充其量不过“重新陷入被奴役的状态,并成为资本的帮工”。〔42〕
肯定性暴力的发生离不开精神政治治理术,即资本主义权力体系通过操纵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精神世界,实现对生命的全面占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紧密相关的是权力治理模式的转变,二者一道促成了肯定性暴力的发生,或者说,作为新型权力治理模式的精神政治就是肯定性暴力的另一种运行形式。由于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对象不再是物质性东西,而是信息、计划等非物质性东西,因此作为生产力的肉体便不再如传统规训社会那样重要,权力治理模式也从规训肉体转为规训精神。〔43〕精神政治的精明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对个体施加影响的镇压型权力,而是通过努力讨好和成全个体、让个体产生自由感和快乐的“讨我欢心”的友好型权力。脸书(Facebook)的“点赞(likes)”功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它拒绝任何伤害和冲击到主体的可能,而主要是肯定、承认和赞赏主体,使主体在自我展示中产生愉悦和精神满足。在这种“点赞”文化中,“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44〕韩炳哲认为正是他者的存在赋予了主体活力,使主体与现实保持着一种流动的、全新的关系,而权力策略则是清除掉蕴含着否定性的他者,使主体沉溺于日益加深的“熟悉感”和无限的自我肯定之中。如果说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经由他者和劳动获得独立意识的奴隶尚有自由可言,那么肯定性暴力之下的主体则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而是丧失了他者性的、毫无生命力的“苟活之人”。消除了同他者的关联之后,主体也随之走向自我瓦解,他将之称为“暴力辩证法”。〔45〕同时,正是在“点赞”的同时,韩炳哲认为主体已然屈从于环境威力法则,并且由于这一屈从姿态是主体积极主动完成的,即暴力行为并非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我指涉性的、内向化的,如此一来,权力体系便以最低成本且最为隐蔽的方式实现了统治成效的最大化。尤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权力能够借助数据监控等方式毫不费力地获取到包括主体潜意识在内的全部信息,继而通过对潜意识的利用实现对主体的全面操纵。在此意义上,数字权力以无声的暴力终结了自由意志,因为它能够“在速度上超越自由意志,赶在自由意志前发挥作用”。〔46〕
综上,如果说在巴特勒和齐泽克那里,暴力处于他者和自我、权力和主体等二元抗衡的关系体之中,那么韩炳哲则将此二元抗衡关系扭结为处于同一曲面上的莫比乌斯带,消除了他者和自我、权力和主体之间的界限,并将暴力类型定义为回避了否定辩证法的肯定性暴力。毋庸置疑,韩炳哲对当代资本主义暴力的新思考不可谓不新颖独到、引人深思,但其言说方式归根结底仍遵循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其批判视角也并未走出生命政治的视域。
四、结语:三种暴力批判理论研究的内在联结
尽管以上三位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暴力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思考和阐释,但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三种暴力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共识内容。
其一,从生命政治缺乏“生命”面向的视角言说暴力。众所周知,生命政治是关于政治权力如何对待个体生命的政治。然而,上述三位学者都认为当今的生命政治缺乏“生命”:当政治权力罔顾法律限制并导致某些群体的生存权利暴露于危险之中时(巴特勒),当国家将所有生命抽象地化约为行政管理的客体时(齐泽克),当权力的触角延伸至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将生命完全“透明化”时(韩炳哲),生命政治便取消了“生命”的面向,政治权力由此异化为暴力。
其二,暴力从显而易见的物理层面转至极具隐蔽性和破坏性的结构层面。巴特勒从政治伦理视角出发提出了假借“合法”之名行不法之实的“国家暴力”;齐泽克从精神分析视角出发提出“系统暴力”,即为了维持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而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客观性暴力,其新形态是“慈善资本主义”;韩炳哲紧扣时代变革,从绩效社会视角出发提出以消灭他者和实现资本快速流动为目的的“肯定性暴力”,政治权力对主体的治理模式不是外在的压迫与剥削,而是隐匿在“你能够”这一肯定性律令下的新型精神政治。
其三,暴力的本质是体现了强力意志或屈从意志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理层面的直接伤害。巴特勒在新书《非暴力的力量》中将暴力与不平等联系起来,认为暴力再现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了生命价值与生命权利之间的差异,因此对暴力的批判就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根本性批判。其实不论是巴特勒所言及的国家暴力还是齐泽克提出的系统暴力,都旨在说明暴力源自社会制度结构的扭曲和权力的滥用,它体现了强者(指制度结构)与弱者所结成的不公平的社会关系。尽管韩炳哲指认的肯定性暴力包含了自我剥削、自我暴力的内容,但究其根本,“自相残杀式”的社会内部剥削问题背后依然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而这一点也正是齐泽克对韩炳哲提出批判的要点所在。
其四,主体与他者的对抗性关系是暴力持存的前提条件。在巴特勒看来,权力的框架预设了各种类型的群体,有些群体是值得承认与表征的“主体”,有些群体则是受到排斥与否定的“他者”。没有区分就没有主体,而排除他者的过程亦即主体形成的过程。齐泽克的系统暴力理论同样遵循了排斥逻辑,他认为权力主体与自身剩余快感的结构性不平衡导致主体总是癔症地将他者视为潜在的威胁,幻想他者试图从自己这里攫取快感,因此权力主体总是先发制人地发起暴力。在韩炳哲那里,肯定性暴力则直接驱逐了他者,因为异质性的他者违背了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所要求的平滑原则。就此而言,暴力的发生表征着他者的“退场”。
总而言之,不同于传统暴力以否定性和强制性的形式对个体施加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的暴力类型更为隐蔽,它将自身伪装起来,以一种所谓“中立的”“合法的”“无害的”形式彰显自身,这导致人们常常置身于暴力之中却毫无察觉。在此意义上,揭露暴力、澄清暴力的运行机制成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以巴特勒、齐泽克和韩炳哲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暴力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暴力批判的理论空间,同时,暴力理论研究对于多维度地展开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也颇富启迪性。
注释:
〔1〕〔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暴力:思无所限》,李元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212页。
〔2〕Johan Galtung,“Violence,Peace,and Peace Research”,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6,No.3,1969,pp.167-191.
〔3〕〔19〕〔20〕〔21〕〔22〕〔24〕〔27〕〔31〕〔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4、2、2、14、36、20、21、12页。
〔4〕〔5〕〔6〕〔8〕〔9〕〔10〕〔11〕〔15〕〔16〕〔17〕〔美〕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何磊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8、83、295、266、143、11、140、279、301、284页。
〔7〕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Dea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2.
〔12〕〔14〕〔18〕Judith Butler,The Force of NonviolenceLondres:Verso Books,2020,pp.136,181-182,148.
〔13〕Freud,The Ego and the IdSE Vol.19,1923,p.53.
〔23〕Bauman,Z,Liquid Fear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8.
〔25〕〔26〕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Verso,2009,pp.53,52.
〔28〕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98,p.268.
〔29〕Slavoj Zizek,Gaze and Voice as Love ObjectsDurham:Duke UP,1996,p.105.
〔30〕孔明安、刘婵婵:《暴力批判与解放逻辑的激进指向——精神分析视域下的齐泽克暴力理论简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4期。
〔32〕〔斯洛文尼亚〕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泽译,台北: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19页。
〔33〕〔35〕〔36〕〔38〕〔40〕〔41〕〔德〕韩炳哲:《暴力拓扑学》,安尼、马琰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21、62、7、5、107、68页。
〔34〕〔37〕〔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7、12页。
〔39〕〔42〕〔43〕〔46〕〔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24、10、33-34、86页。
〔44〕〔45〕〔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