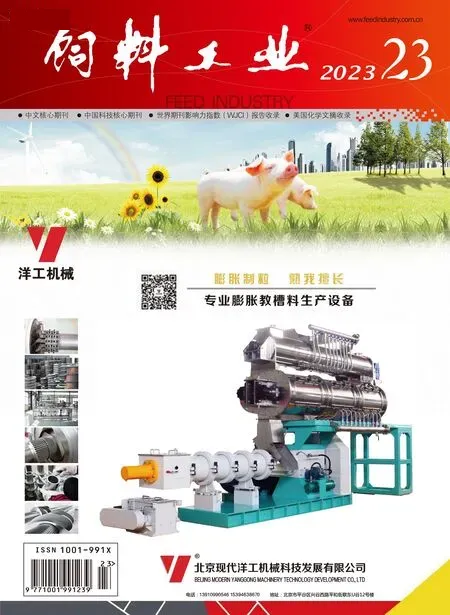牛羊无角表型遗传机制研究进展
2023-02-25阎明毅张强龙
■ 韩 翠 阎明毅 张强龙 吴 森*
(1.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西宁 810016;2.青海省高原家畜遗传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 810016;3.农业农村部青藏高原畜禽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 810016)
角作为反刍动物的重要特征,是一个关键的组织器官[1]。角对野生动物非常重要,是进行自我保护的工具,但对于家养动物来说,角不仅易造成家畜创伤和工作人员受伤,它的形成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物质。有研究表明,安徽白山羊在初始体重、饲喂条件一致时,从1 月龄开始无角白山羊体重大于有角白山羊,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10月龄时,无角白山羊体重比有角白山羊平均大1.97 kg[2-4]。在现代畜牧业养殖中,给幼年牛羊去角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便于管理的同时更具经济价值[5-6]。牛羊角表型具有丰富的多态性:一般公畜具有大角;母畜有小角或无角;山羊有角而绵羊无角或小角;牦牛、藏羊等特殊类群,无论公母均生有1 对大角,部分特殊品种,如泗水裘皮羊生有2 对(4 只)角。牛羊角具有不同表型特征,为研究角遗传特性提供了很多的素材,是多年来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也帮助人类育成众多适应于现代化高效养殖生产模式的无角型动物品种,如无角陶赛特羊、无角阿什旦牦牛等,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角的作用
牛羊品种有不同的角表型,在很多现代生产品种中,为了方便饲喂管理,牛羊是没有角的。从动物育种以及进化的角度来看,角是一个特殊存在的特征。角不仅在对抗捕食者时可进行自我防范,在雄性的选择性竞争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现代规模化饲养条件下,角会导致牛羊间频繁的碰伤现象,甚至会影响皮张的品质以及羊的增重,容易发生疾病感染[7-8]。从饲料转化率方面来讲,一对大角需要消耗很多的营养物质,在冬季可能消耗更多的体能;而无角牛羊则不会因角去耗费大量营养物质,较有角的品种表现出生长发育快、体格硕大、增重较快。有研究发现,相较于有角哈萨克羊,1 岁及2 岁无角哈萨克羊体重分别增加2.3、1.8 kg;1、2、3、5 岁无角哈萨克羊胸围也分别增加2.3、2.3、2.5、3.3 cm;2、3、5 岁无角哈萨克羊胸深比有角哈萨克羊胸深分别增加1.3、2.0、2.8 cm[9]。也不会因角斗而发生伤残,更不易破坏围栏等设施,便于现代化养殖管理[10]。尽管目前育种界认为牛羊的生产性能与角有无并没有直接相关性,但因便于养殖管理,无角品系已成为发展趋势,无角牛羊培育也成为当今世界反刍动物育种的热点课题[11-12]。
在现代化的集群饲养环境条件下,角不仅是加大种群生产成本的原因,而且有可能在人工管理时对人员造成伤害,成为潜在危险源。目前牛羊角型控制基因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证实已从诸多候选基因中筛选出主效控制基因。因此,培育出无角牛羊将会为反刍动物的现代化集约饲养管理做出重大的贡献。
2 角性状遗传机理研究现状
2.1 牛角性状研究现状
牛角是牛科动物特有的组织结构。在男耕女织的原始生产劳动过程中,牛角是对牛牵制的基础,所以牛角是一种特殊且不可缺少的劳动生产力。自进入现代规模化集中养殖后,有角容易发生群内争斗和饲养人员喂食时被误伤等情况,造成了动物之间互相伤害及养殖场无法妥善管理。所以,目前很多养牛场将犊牛去角,人工去角增加了养殖成本,同时容易引起犊牛的一系列应激反应,是一种违背动物福利且浪费人力物力的行为[13-14]。根据生物学分类,牛角属于洞角,在不同的个体和品种中强度和长度都存在差异。角的发育较早,是在出生后才慢慢形成的;牛角是质量性状,遗传方式为多基因遗传。无角牛品种的培育是近年来牛遗传育种的主要方向之一。
牛的无角位点定位在1 号染色体上,将其范围缩小到着丝粒区域[15-16]。在该区间陆续发现4个不同的无角突变。第一个突变发现在欧洲牛品种中,Celtic POLLED(PC)突变,是一个202 bp 的插入-缺失复合体,通过基因克隆得到了无角表型的犊牛[17-18]。第二个突变发现是与荷斯坦牛无角表型相关的候选突变,该突变与PC突变不重组也不影响,称为Friesian POLLED(PF)突变,是一段80 kb 的重复序列,且无角荷斯坦牛并不携带PC突变[19-20]。第三个突变在内洛尔瘤牛中发现,Guarani POLLED(PG)突变,是一段110 kb的重复片段,且无角基因型来自普通牛[21]。第四个突变是Mongolian POLLED(PM)突变[22],在蒙古牦牛和蒙古牛中发现,蒙古牦牛的无角突变定位在POLLED位点800 kb 长的区域,有2 个基因型,在牛科动物中完全保守。对胎儿期90 d PC变异区域的基因表达进行分析,发现有无角表型的角芽组织中RXFP2基因存在显著差异[23]。对150 d的胎儿角组织和无角表型角芽部位进行测序,发现OLIG1、OLIG2、RXFP2、GCFC1和FOXL2表达差异是显著的,对胎儿期70~170 d 角组织进行分析,发现RXFP2、FOXL2有角表型都高于无角表型,但差异并不显著。对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发现控制我国蒙古牛无角性状的突变新基因型——P219ID。
在牛无角性状的研究中,目前将牛无角的主效控制基因定位在1 号常染色体上,并发现了两个微卫星标记与1号常染色体相关。对1号常染色体继续精确定位,发现几个新的标记位点比较有意义。牦牛角性状候选基因的表达研究发现,候选基因在有角和无角牦牛的角基和皮肤间相对转录水平差异不显著。通过有无角牛基因分析,部分无角基因在3、5、18 号染色体上表达差异比较大,由此推断牛角性状的关键候选基因可能是OLIG2和FOXL2[24]。
2.2 羊角性状研究现状
2.2.1 山羊无角性状研究
我国山羊的养殖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代就出现关于羊的文字记录[25]。近年来饲养方式逐步改进,集约管理化养羊业稳步发展。山羊适应性强、繁殖率高、易管理,在我国农牧区广泛养殖。改革开放以来,山羊业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使内蒙古、辽宁、新疆等山羊的饲养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禁牧限牧政策方针,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受伤害,又要使山羊产业持续发展,促使我国山羊养殖业迈入了又一个转折期[26-27]。
早在19 世纪,在无角山羊选育时,发现雌雄比例失调现象,并且伴随着间性个体逐渐增加的趋势,这种现象是无角间性综合征(PIS)[28]。1944 年,将山羊无角和PIS 联系在一起,提出控制间性与角的基因存在关联[29]。2001 年,在山羊1 号染色体上发现一个11.7 kb 片段的缺失,是发生山羊PIS 的原因,且发现调控基因至少有2 个:PISRT1和FOXL2[30]。通过单倍型分析5 只间性山羊发现,有3 只并不是PIS 纯合缺失,原因是不同类型的PIS 缺失。说明山羊性反转的遗传并不是简单的1号染色体上11.7 kb纯合缺失[31]。张宇[28]也发现PISRT1基因的多态性与唐山奶山羊PIS 存在紧密联系,山羊蛋白质转录因子FOXL2具有决定卵巢发育的作用,与无角间性性状存在着紧密联系[32]。由此可知,PISRT1和FOXL2与PIS 紧密相关。张磊[33]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RXFP2、NRDC、NBEA、FOXO1、UNC79、ATG2B和KIAA1429是内蒙古绒山羊角性状的重要候选基因,验证基因NRDC和RXFP2均与角性状显著相关。
2.2.2 绵羊无角性状研究
在早期开始研究绵羊时对毛色及角型等性状进行了选择[34]。人类最早开始研究绵羊的性状就是角型。绵羊角表型的遗传模式远比表面分析的要复杂得多。早在100 多年前,研究表明,在一种两性都严格有角的品种陶赛特角羊和完全无角品种之间的杂交中,只有雄性后代表现出有角[35]。基于这些观察,有研究指出公羊的角是显性的,而母羊的角是隐性的。随后对其他品种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有角和无角等位基因的影响在雄性和雌性绵羊之间是不一样的[36]。有研究发现,绵羊公羊一般都是有角的,无角绵羊很早就被育种学家研究了,公羊无角表型也陆续被研究出来。
在早期研究无角性状时,认为位于常染色体Ho基因座上的3 个等位基因调控有无角表型。将绵羊的“无角位点”定位在10 号染色体上,并且将位点区间缩小到50 kb 的区域内,使预测角表型正确率高达97%。对陶赛特羊和美利奴羊进行全基因组信号选择分析,无角表型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在10号染色体上发现,位置接近RXFP2基因[37]。有研究表明,无角基因位点定位于10号染色体29.3~29.5 Mb区间。在美利奴羊品种中,利用两个SNP 位点,对母羊无角预测准确率达到30%~70%,公羊60%~75%[38],但是不能进行完全预测,因为这两个SNP 不是致因突变。同时,利用251 个微卫星和等位酶标记在野生型绵羊上发现无角位点,将索伊羊无角位点定位到10 号染色体[39]。
通过研究发现,决定羊角尺寸的数量性状基因座(QTL)在10 号染色体上[40]。在研究野生索伊羊群体时,大角公羊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雄性羊有两种表型,正常大角和畸形角,但雌性羊有正常角、无角和畸形角三种表型[41-42]。这种多态性是通过RXFP2在自然和性别选择上相互协调而形成的[43],索伊羊在RXFP2上有两个等位基因:与提高繁殖率相关的大角等位基因Ho+、与成活率相关的小角等位基因HoP,公羊存在三种基因型:Ho+Ho+和Ho+HoP为正常角,HoPHoP有一半为畸形角。
进一步分析欧洲绵羊品种发现,RXFP2基因3’UTR 区域的一段1.8 kb 片段的插入与绵羊无角表型显著关联,且无角对两角表型为显性[44-45]。在中国滩羊同样发现RXFP2上存在一个与无角表型显著相关的同义突变,但在国外的34 个绵羊品种的大样本中并没有特别的发现,位于RXFP2基因3’UTR 区域的插入片段只是在部分绵羊的角表型中出现分离[46]。同时,检测阿勒泰羊RXFP2基因3’UTR区域1.8 kb插入片段,发现与无角表型没有相关性[47]。2020 年,对我国小尾寒羊和湖羊进行重测序分析,检测到10 号染色体RXFP2附近的信号。
尽管无角性状的遗传区间已经确定,但无角绵羊品种繁多,导致结果也是各有不同,有些品种与RXFP2基因有很强的关联,同样有些是不存在关联的,说明角表型基因遗传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将野生索伊羊无角性状定位在10 号染色体,而且调控角长度和角基周长也定位在这一区域。利用芯片进一步确定验证了索伊羊角关键候选基因是RXFP2,也是角长度和角基周长的主要调控基因。但在其他野生群体上并未得到类似的结果,通过对76 个大角羊高密度芯片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并没有发现直接影响角的数量性状基因座(QTL)[48]。总之,绵羊无角与正常角长度和基部周长数量性状都定位于同一遗传区间和同一候选基因——RXFP2基因。
3 展望
角是反刍动物演化最成功的器官之一,也是标志性特征,研究角的进化和遗传机制一直是反刍动物遗传学的热点之一,也是其他特异性遗传性状研究的参考模型之一。牛羊不仅提供肉、奶、毛等生产生活资料,在人类农业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已经确定无角牛羊表型相关基因的定位及遗传调控机制,但无角牛羊的基因组中存在大量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与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有关。未来随着分子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技术的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无角牛羊的培育将会更加成功,为阐明基因在遗传分化和性状调控中的作用提供参考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