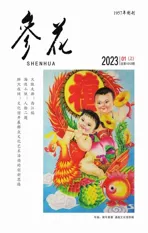西江稻
2023-02-22孙桂芳
◎孙桂芳
一
那个农妇将一只盛满米饭的粗瓷大碗端到我面前,一股浓郁的米香扑面而来,灌满了我的鼻腔。这时,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直射在碗中,碗里的米粒仿佛一颗颗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珍珠,白糯饱满、通体透亮,粗瓷大碗也难掩其光泽。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大口,唇齿间即刻如开满了鲜花一般,荡漾着醉人的芬芳。
“许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米饭了!”我望着农妇由衷地感叹道。
农妇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指着窗外告诉我,这米就是屋外的稻田里产的。我趴在木格子窗朝外望,一排高大的白杨,稻田从白杨树下一直向远方延伸,直达山脚下。虽然遥远,仍隐约可见山脚下散落着的村庄,环绕着村庄的稻田,沿着山脚,又向更远处的村庄延展开去。
栖居在群山环抱之中的西江小镇,盛产稻米。
据《通化县文史资料》记载,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将长白山地区视为圣地,实行封禁。咸丰年间,关内游民增多,西江也闯进了几户人家。这几家人在浑江边的大草甸子上开垦水田,种植水稻。由于大甸子土质肥沃,种出的水稻颗粒饱满,米香浓郁,地方官员便拿此米进贡给朝廷。咸丰皇帝见西江大米白若珍珠、食之芳香,遂封西江大米为御用贡米。每年秋季,进京送贡米的车队浩浩荡荡。
光绪二年,盛京大将军崇实奏请朝廷,要在西江设立通化县,慈禧太后喜食西江大米,唯恐占用了良田,未准。
一九五八年,西江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西江稻米连续多年销往北京。这份荣誉现已被镌刻在石碑上,永久地镶嵌在了西江小镇的稻田上。
我端起农妇递给我的盛满米饭的粗瓷大碗,就仿佛端起了西江稻米的百年历史,又仿佛端起一只盛满热气腾腾的米饭的红色陶碗,米饭散发出的香气,牵引着我,沿着绿油油的稻田,走进了一万年前的上山;上山,洒满了明亮的阳光——那是一万年前的阳光——阳光下,一粒炭化稻米,静静地、静静地,栖息在红色的陶片里。
二
没有人知道那座土丘(后定名为上山),在浙江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北立了多少年。它经历着风吹、经历着日晒、经历着雨淋、经历着月食、经历着年代的变迁,直至有一天,考古队在那里挖了一个二平方米的坑,几片盛着砻糠碎壳的红色陶片,惊现于天光之下。沿着那个坑继续寻找,一粒埋于土壤深处的炭化稻米,后来被考古界称为“万年一粒米”,听从天地的召唤,破开上万年的时空,一跃而出。尘封了万年之久的上山,被这一粒稻米激荡而活,点亮了由它带来的文明之光。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里·克劳福德,在为上山文化的题词中写道:“古代上山人,作为最早耕作稻米的人群,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技术工程师。”
其实,关于稻的起源地,从十九世纪起一直纷争不断,上山“万年一粒米”,或许能为这场旷日已久的纷争,划上终止符。
那么,被尊称为生物技术工程师的上山人,是在怎样的境遇下发现稻可食用?又经过了多少光阴的打磨,才培育出可以大面积种植的稻种?这样深度的、专业的探索,还是交给考古学家去发现和思考吧!百谷自生、冬夏播琴,万物自会沿着其可遵循的轨迹而行。
三
一粒种子,就是一粒稻米;一粒稻米,就是一粒种子,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一粒种子应运而生,随气而长。稻,如同星星之火,以上山为基点,遍布华夏大地,又乘风破浪,远渡重洋。
令我不解的是,上山稻谷遗存显示,一万年前的上山人,从水稻的栽培、种植、收割,再到食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业体系,可这贯穿南北,承载着祖祖辈辈记忆的稻,最初,却为何没有列居五谷之中呢?
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开篇《乃粒》中这样写道:“凡谷无定名,百谷指成数言。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
稻,可是土生土长的华夏原住民啊!
“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随后,宋应星又这样写道。
虽未列居五谷,但稻却始终没有放弃最初的信念,而是带着一身浩然正气,默默地守护着被它点燃的那一缕文明曙光。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在走过了漫漫征途之后,北宋年间,稻不仅跻身五谷行列,且居五谷之首,肩负起养活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使命。有人给稻走过的艰辛之路,命名为“生命之路”。因此,联合国将2004年定为国际稻米年。
四
天地,花了多少亿年的光阴,才成为今天的样貌?人类经过了怎样的锤炼,才从野蛮蜕变成今天的高度文明?
我站在田埂上,眺望着被群山环抱的稻田,眺望着被稻田环绕的西江小镇,心里仿佛被突然涌进来的一道强光照亮。关于这个命题,我不仅需要埋头在堆积如山的先贤们的著作里寻找答案,更需要到大地上追寻,更需要走进田野,和农人一起,将一把稻种播撒进稻田里,将一把秧苗栽种在由水滋养的泥土里。因为,我终于意识到,人类最初创造的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看似消失,实则深隐于泥土里,经过时间的酝酿、发酵,滋养着大地,才使得田野如此肥沃,才使得人类如此兴旺,才使得文明抵达了今天的高度。
我的苦思冥想似乎得到了回应,只见用过午饭的农人,正沿着长长细细的田埂,走进稻田。男人的头上戴着宽檐大帽,女人长衣、长裤,头上裹着红色或粉色的方巾,如灿烂的花朵,和田埂上刚刚绽放的黄色蒲公英,相映成趣。灌了水的稻田像一面镜子,倒映着天光,天好高好蓝,成捆的秧把,被天光轻轻托起。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眼前的景象与诗中描绘的情景多么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东北天冷,敞开六月的门,才开始插秧。
五
探寻地理文化,上山遗址坐落在钱塘江上游河谷盆地中间的低矮山丘;地处长白山南麓、浑江西岸的西江,开垦前是大甸子,被当地人称为江甸子。上山与西江,一南一北,气温相差极大,但我总感觉它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丝丝缕缕的牵连,是这白墙红瓦的村落吗?是这环绕着村落的稻田吗?
中国农耕文化肇始于村落,或者,这样的文化基因;或者血脉相连,才使得中国所有的村落,不分南北,都有着相同的面容吧!
在我浮想联翩时,稻田里的农人已经开始插秧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农人插秧,不分男女,无不卷着裤管,田的水刚淹没至小腿肚,水下是翻了两到三遍的土壤。只见他们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迅速地插着秧,右手插秧的同时,左手的拇指和中指,迅速地从一把秧苗当中分秧,你一行、我一行,南方的稻种就这样植根于北方的沃野上,纤细的秧苗,在浸过水的黑土中扎下根的那一刻,真是令人心动。
我的视线随着片片绿色被拉得越来越远,而一望无尽的稻田,随着农人一步一退,被上万年的绿色光阴覆盖。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望着倒映在水中的农人插秧的身影,我的耳边回响起布袋和尚的《插秧诗》。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我反复咀嚼着,眼前似有一道光划过。何为道?原来,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得清插过的秧,才能看得清走过的路。中国以农立国,由语言、风俗、礼俗,衍生出的哲学思想,便是人类生活的本源——人与自然,民族与世界;这哲学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的元气。
如此再来细究稻,稻字,左边是禾,黄河流域称禾为稻;其古字形上部是米,下部像装稻米的筐。道可稻(道),非常稻(道),古人既用稻谷来比喻富足,也是在警示子子孙孙,稳定的基业,一定是建立在富足的米仓之上。
不只如此,置身于稻田才发现,稻字的右上部,宛如眼前的情景:每一片稻田,插秧的农人都是多人协作,少说七八个,多则十几个。虽然每人一行,但行与行间隔有序,左右照应,使得秧苗如同训练有素的队伍,横平竖直,排列整齐。
我注意到,中间年龄最长的老农似乎是这群农人的核心,左右的人都会随着他插秧的速度行进。显然,他插秧是一把好手,常常直起腰来,左右看看,等一等落在后面的人。等的过程中,他有时会抬头望天,天上飘过的几朵白云,像浪花一样,在他的脚边跳荡,而他,却蹲下身去,抓起田中的一把泥土,放在鼻下用力嗅着。那一刻,我在他的身上,感应到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尽管不知所以,我还是学着那个老农的样子,蹲下身去抓起一把泥土用力嗅着。当浓郁的泥土的味道装满了两个鼻腔,我才愕然想起,闻香识泥土,闻泥土是农人自然的习惯。
作为农史文献的《吕氏春秋》,就强调了要辨土而耕种:“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好的土壤,才能种出好的稻谷;健康的土壤,秧苗才能长成颗粒饱满的稻穗。
西江虽处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但也要靠西江人用心开垦,用汗水浇灌,南方的万年上山稻,才能在阳光和水层叠交错之间,在北方这片黑土地上扎下根来。
光,随风流转,被绿色覆盖的稻田又多了一抹嫣红,那是山风随手抓起一把夕阳,抛洒在稻田之上。我心怦然一动,或许上山万年前用来盛米的彩虹陶灌,正是农人插秧时把倒映在水中的夕阳和在了泥土里,才烧制出那么动人的红色陶器。上山人可曾料到,这抹微醺了江南乡野一万多年的夕阳红,万年之后,也微醺了北方的黑土沃野?由此,用来充饥的稻已不再是一种物质,它是承载着大地的悲苦与希冀,是大地赐予人类心灵的慰藉,是人类文明的星空和坐标。
离开西江时,我悄悄地抓起一把泥土,闭上眼睛,向那素净的地心嗅闻,我仿佛听到了有人在大声地吟诵: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