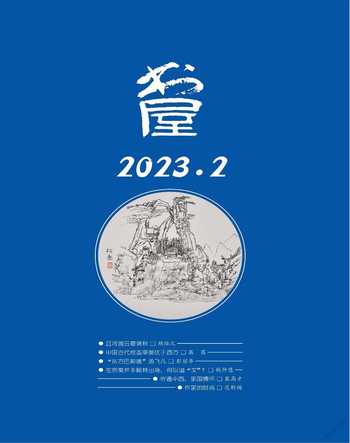左宗棠并非翰林出身,何以谥“文”?
2023-02-21钱仲慧
钱仲慧
謚号,是古人死去后官方对其一生功过的总结,不过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到官方所赐的谥号。在清朝,只有成为官员才有机会,且要得到谥号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品级和品行。通常只有一品大员才能获得谥号,咸丰时期因为战乱放宽要求,为国殉难的二品文官、三品武官以上也有机会获得。
谥号是朝廷对官员一生的盖棺定论,不过这也得看皇帝的心情。比如,张居正死后赐谥“文忠”,可不久万历就翻脸开始清算,顺带撤销了他的谥号。“文”是古代文官谥号的最高等级,其中以“文正”为最,其他如文忠、文襄、文端、文肃、文恭等也是比较尊贵的谥号。整个清朝历经二百七十余年,得到“文正”者不过八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官员谥号先是内阁草拟,然后交由皇帝钦定,但“文正”只能由皇帝特批。
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死后被追赠为太傅,赐谥“文襄”。“襄”是对战功卓著的评定,他平定太平天国、剿灭捻军、收复新疆,“襄”字当之无愧。可据方浚师《蕉轩随录》记载:“故事大臣非翰林不得谥‘文字。”左宗棠是举人出身,连进士都不是,更谈不上翰林了,他怎么会被谥“文”呢?
据《梵天庐丛录》记载,左宗棠最初由举人升道员,后因战功升至巡抚。左宗棠准备西征时,刚好是会试年,于是,一直对自己举人身份耿耿于怀的他在半路上突然上奏,要求卸去军务,进京赶考。朝廷那帮老油条一看就明白左宗棠葫芦里卖什么药,于是商议后赐左宗棠进士出身并授翰林,左大喜。
《梵天庐丛录》的作者是柴小梵,民国文学大家,当时有人称他“两代明清掌故谙,四明巨手重东南”,“柴子小梵有经天纬地之才”。《梵天庐丛录》是柴小梵的得意之作,他历经十年方著成此书,书中主要讲的是明清掌故,出版即成畅销书,十年重版四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但他的说法一定可信吗?
笔者查阅史料,左宗棠在入骆秉章幕之前根本不是什么道员,没有任何官方身份,西征半路要求进京赶考,得以赐进士授翰林,更是无稽之谈。左宗棠性格固然偏激,但绝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
另一种说法是左宗棠因为举人出身,官至东阁大学士却仍被其他同僚歧视,这让他无法接受,于是公然宣布要参加会试。堂堂恪靖侯、大学士要参加会试,这成何体统?慈禧一看立刻下旨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这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了下去。也有说是因为左宗棠战功卓著赐同进士出身,等等,这些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道光七年(1827),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同年因母亲病重,放弃院试,与秀才失之交臂。道光十二年(1832),通过纳捐取得乡试资格,起初并未录取,后在“搜遗”中得以录取。此后六年,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可惜都未能高中。
左宗棠离进士最近的一次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他自己对这次会试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考完后他把文章重新抄写出来给朋友看,以为一定能中。然而,他的成绩是湖南省第十五名,因湖南省超额被撤下,仅取为“誊录”。对于这次失利,他在给周夫人的信中写道:“特自问非战之罪,似尚可归见江东父老耳!”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参加会试。未能成为进士,确实是他的一个心结。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在经历“樊燮案”后不得不离开骆秉章幕府,经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人协助,他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因此成为一名闲散人士。四十九岁的他想再次进京赶考,可一打听,发现不仅路上不安全,就连京城也有好些人想对付他,不得已放弃了进京赶考的想法。这是有据可考的,而且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此想法。
对此,研究左宗棠的大家秦翰才在《左宗棠逸事汇编》一书中指出“奖道员、起监司与会试及清廷赏进士各节,绝非事实”。
那这“文”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
“非翰林不得谥‘文”这个说法本身是片面的。根据清朝的制度规定,汉臣非翰林出身确实不能谥“文”。不过还有补充规定,一旦官至大学士,翰林出身这个门槛就自动消除了。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自然是满足条件的。当时既非翰林又非大学士而赐谥“文”的特例是周天爵,进士出身,生前最高官职是总督衔,他在军中病死,追赠尚书衔,赐谥“文忠”。咸丰念其劳苦,破例赐谥。
年近五旬,仍试图进京赶考,科举在左宗棠心中真的这么重要吗?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八股文的考题通常出自“四书五经”,要求模仿孔、孟等先贤的语气来代圣贤立言,其结构、句法和字数都有严格限制,因缺乏新意和实用价值而被诟病。左宗棠却认为“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他这么说,是因为一篇好的八股文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揣摩,而且其观点还得颇有见地。
选拔制度虽然有问题,可身处其中是难以免俗的。左宗棠不仅自己放不下科举,对孩子的“入学”(考中秀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在家书中与子女们经常聊科举和读书这个话题,特别是跟长子左孝威。
同治元年(1862)五月,身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得知十七岁的左孝威以全县第一考中秀才,他“颇以为乐”。左家几代以来能在十几岁便中秀才的除了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如今又有了左孝威,他怎能不乐?向来不屑于搞人情世故的他主动询问儿子的主考官是何人,要写信表示感谢。同年闰八月,得知孝威以第三十二名中举,他更是异常高兴。不过同时他也开始担心儿子患上年少轻狂的毛病,于是告诫孝威:“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左宗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熟读史书的他也深知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早年都是历经磨难。他担心儿子过早中举会导致“少年意气正盛,视天下无难事”。为此,他特意叮嘱儿子明年无须参加会试,要以学有用之学为主。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得知左孝威进京赶考失利却表示“会试不中甚好”。他不希望儿子们的功名很顺畅,一方面是深信磨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担心这会“占去寒士进身之阶”而于心难安。
在左宗棠眼里,科举不过是块敲门砖,读书本身比科举更为重要。早在咸丰六年(1856),他就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并非为了科举考试,然而没有科举所带来的功名是很难谋生的,所以为了科举功名而读书实属人之常情。那么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左宗棠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成天读书可行为却不如乡野村夫,这种读书好比是鹦鹉学舌,即便能考取功名,对社会、家庭非但没什么好处,反而可能是祸害。读书真正目的是提升品行;有科名的读书人远不如品行高尚的长者,而那些所谓的贵族也比不上一个好的农民。读书识字是为了明理,至于科举考试,无论文章、道德好坏都能得之,不足为奇。左宗棠告诫侄子要立志成为德行一流之人,而不是掉进科举虚名的书呆子。他非常看重立志,而且认为“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子女们能立志向上,那才是真正的体谅父母苦心。
身处封建时代的左宗棠对科举的认知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人。以八股文选拔人才不足取,但问题在人而非八股文本身。读书不是为了科举,而是要能提升品德,要学有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