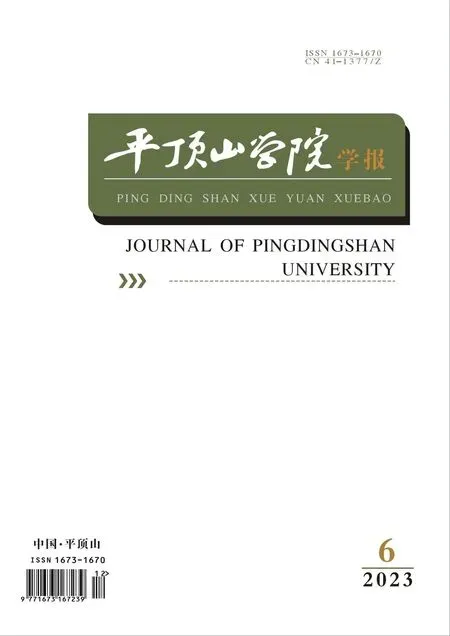理学“敬”论的发展脉络
2023-02-20焦德明
焦德明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海学刊》杂志社,江苏 南京 210004)
一、宋元儒者对“敬”的阐发与践履
一般讲理学史,都会首先介绍周敦颐、张载和邵雍,但这三位思想家尚未深入探讨实践工夫的问题,因此对“敬”没有特别的解说。张载的情况略显特别,他以及整个关学都很重视“礼”,而礼的核心精神是“敬”。只是他的著作中对“敬”的讨论很少,仅见“不敬则礼不行”[1]等区区几条有所涉及,可见敬在张载的思想中并不具有独立地位(1)谢良佐对张载重礼却不重敬曾发表评论,认为张载看到世人“汗漫无守”,所以强调礼,并教人在礼上做工夫,但是其门人后学沉溺在“刑名度数”的枝节之中,能行礼却缺乏对礼的核心价值的理解,“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详参谢良佐:《上蔡语录》,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外编》第3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一)二程及其弟子
理学对敬的重视肇始于二程。程颢“使学者从敬入”[2]。在《识仁篇》中,他要学者“先识仁”,而后便要“以诚敬存之”[3]16。程颢常常“诚敬”并提。诚是真实,敬是恭肃,二者的侧重固有不同,对此程颢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则诚”[3]127,以天、人分诚敬,敬是达到诚的方法(2)《二程遗书》卷六也有“诚然后能敬”的说法,但是紧接着又说“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详参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页。。他自身的践履也主于敬:“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3]60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3]638我们一般认为程颢是洒落派,程颐论其敬可能是将自己的学术渊源归于兄长,以之为援助,更加表明自己的正确性(3)程颐语门人张绎曰:“我昔日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详参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6页。,但我们不能认为程颢与敬无关。程颢对敬的理解与程颐不同,程颢的敬是和乐而不拘谨的。有一种和乐的敬,这是程颢对我们的启发。
程颐与其兄一样重视敬。除诚与敬、“敬以直内”等相同的议题外,他与程颢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庄整严肃。从程颐开始理学真正以“主敬”为工夫,提出“主一者谓之敬”[3]315是他对儒家“敬”论的最大贡献。程颐以“一”说敬,第一次揭示了“敬”的本质,而不是像训诂家那样在警、肃、慎、畏等情绪的形容词间辗转相训,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而从工夫的角度说,“主一”的说法开辟了理解“敬”的一个新面向,使敬从“敬天”“敬长”“敬德”这类有具体对象的敬转进到专一于内心、集中于当下的精神状态的敬,无疑是开辟了理学精神性维度的细致讨论。可以说,程颐奠定了理学对敬的基本理解。
程门弟子继承其师风范,践履主于敬者颇多。朱光庭以“毋不敬”和“思无邪”二句为自己践履之宗旨[3]35,《二程外书》记其践履之效曰“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3]414,可谓得程颐之精髓。朱光庭践履卓然,但于义理上无有发明。程门另有两大弟子对于主敬有所阐发和创新,这就是谢良佐与尹焞。关于谢良佐论敬,《上蔡语录》中颇有记录,此不赘述。除了湖湘学,朱熹也受其影响。乾道九年(1173)朱熹在《答游诚之》中就认为,其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4]2061;绍熙二年(1191)朱熹作《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颇为肯定其学术,又提到他“以常惺论敬”[5]3793。此外,谢良佐论敬反对“矜持”过当,这正是程颢所谓“敬须和乐”的观点;同时,他也反对以“虚静”说敬,恰恰又是程颐反复提倡的。谢良佐同时师事二程,因此对兄弟二人的敬说能兼采其长。尹焞只见过程颐,因此主要是传伊川之学。尹焞自叙曰:“初见伊川时,教焞看敬字。焞请益,伊川曰:‘主一则是敬。’当时虽领此语,然不若近时看得更亲切。”[6]1072可见程颐是以“敬”字来教授尹焞的。乾道九年(1173)朱熹作《尹和靖言行录序》,肯定尹焞有得于“敬”:程门居敬穷理“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废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学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其说之约而居之安也”[5]3637。《伊洛渊源录》也记载尹焞能够力行“敬以直内”[6]1072-1073。可见尹焞自家的践履正是以敬为主,他的贡献主要是提出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4)尹焞门人祁宽问:“如何是主一?”尹焞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不著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详参尹焞:《尹和靖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二)朱熹及其弟子
朱熹重视敬更是一个常识。朱熹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在《名堂室记》中,朱熹自谓其学问得之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5]3731-3732二句。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熹虽始终强调敬义夹持,但对敬的评价却越来越高。他说:“尝谓‘敬’之一字,乃圣学始终之要,未知者非敬无以知,已知者非敬无以守。若曰先知大体而后敬以守之,则夫不敬之人其心颠倒缪乱之不暇,亦将何以察夫大体而知之耶?”[7]2619又曰:“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4]2323再曰:“‘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依据。”[4]2313因此,朱熹晚年提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8]210的说法,可谓其来有自。朱门弟子的评价完全继承了朱熹本人的观念,黄干《行状》与李方子《紫阳年谱后论》均引朱熹《程氏遗书后序》“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5]3625来总结朱熹之学。李方子认为,朱熹之学有三方面内容,即主敬、穷理与反躬,而主敬贯通三者,可见其成始成终之义[9]645。黄干《行状》对此成始成终之义之发挥更甚,认为朱熹以敬穷理、以敬躬行[9]560,唯其如此,穷理与躬行才有归有实。黄干还提到,持敬以主一为先,存心于“齐庄静一之中”,以此方可以穷理;戒惧严敬,知觉不昧,以此方可以躬行[9]560。虽说朱熹曾以程颐主敬致知为车之双轮、鸟之两翼[7]3061,但观黄干、李方子之评价,他实以穷理、躬行为两轮两翼,而主敬其体也。
朱熹不仅以主敬为自身践履工夫,更以主敬教人。朱熹训门人时多告以“主敬”,故其门人后学中亦有不少以“敬”为宗旨的人物。张洽“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斋”[10]2260。蔡元定次子蔡沆作《敬义大旨》,“以敬为入德之门户,义为一身之主宰,发明敬义以示人”[10]2012。朱熹尝谓南湖先生杜煜“论敬字工夫甚善”[10]2123。尽管朱熹本人很重视敬,但他却没有写过一篇专门的“敬说”,而黄干有《敬说》;朱熹最接近敬说的作品是主敬的工夫指南《敬斋箴》,陈淳那里则有专门的疏解《敬斋箴解》。可见弟子们也都如其老师那样实地践履主敬的工夫。在其后代弟子中,王柏之入道因缘与敬特别相关。王柏“少慕诸葛亮为人”,纵情放旷,后孔子的话“居处恭,执事敬”对他触动很大[11]12980。经杨与立介绍,他投入何基门下。何基教以“立志居敬”(5)史蒙卿推崇朱熹之学,也以尚志、居敬、穷理、反身作为“学问进修之大端”。详参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1页。之旨,正是针对其宿习而发。王柏发愤向学,还作《敬斋箴图》以发明持敬之义[11]12981。
朱熹后学弟子模仿程颐《四箴》、张栻《主一箴》和朱熹《敬斋箴》,大量使用箴、铭等文体来督促自己从事敬的修养,颇有将主敬工夫落实到容貌辞气、动静容止的教法上去。程端蒙与董铢所作《学则》[12]的内容就是落实以敬教人的教法。在《读书分年日程》中,程端礼讲道,程颐《四箴》、朱熹《敬斋箴》和真德秀《夜气箴》“当熟玩体察”,还着重介绍了王柏以为“甚切,得受用”的陈茂卿《夙兴夜寐箴》[10]2923-2924。这些都是尽主敬工夫之节目的作品。
(三)其他
胡宏亦重视敬。他曾讲,“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13],朱熹以此为其“议论好处”[8]2845。且他临终时谓彪德美曰,“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8]2587,由此也能看出胡宏对敬的重视。张栻受业于胡宏,也颇重视敬。乾道年间(1165—1173),张栻作《敬简堂记》《敬斋记》《主一箴》等文,阐发主敬之义,其积极性不亚于朱熹。吕祖谦也没有忽视敬:“‘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14]
韩国韩源道中央研究院顾问安仁博士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与瑞丰生态的合作,将韩国在有机农业方面的优质产品及先进理念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优质产品与技术带到韩国,从而实现两国农业的深度合作交流,服务两国绿色农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敬斋记》有“则自有诸己至于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岂独为县而已”[15]228之语,可以说他对“敬”也有基本的认同,然而他所理解的“敬”与程朱或有一定的距离。他在《与曾宅之》中严厉批评“持敬”一语,认为“‘持敬’字乃后来杜撰”[15]3,且言“观此二字,可见其不明道矣”[15]6。在陆九渊看来,“能弃去谬习,复其本心,使此一阳为主于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终食之间而违于是。此乃所谓有事焉,乃所谓勿忘,乃所谓敬”[15]6。陆九渊仍以“发明本心”为说,但敬与本心的关系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总之,宋元儒者相当重视主敬工夫,其践履也是卓有成就的,为后代学者奠定了基本的工夫规模与范式。
二、明代儒者对“敬”的继承与持守
明代理学以阳明学为盛,但阳明学兴起于明代中期以后,在此之前儒者还是传宋人规模,而在此之后仍有大量学者谨守旧说,笃实践履。明人对于主敬的重视正是其中之一。
仅从《明儒学案》所列人物来看,在工夫上特重主敬的人物之多超乎一般印象。薛瑄弟子张杰,“其工夫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的”[16]127;弟子段坚也尝言,“学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参赞者在此”[16]127。周小泉弟子李锦,“以主敬穷理为学”[16]136;弟子王爵,“以操存为学”[16]132。王恕二传马理,“墨守主敬穷理之传”[16]165。吴执御,字朗公,浙江台州人,“深佩宋儒居敬穷理之说”[16]1329。吕楠弟子郭郛,“其学以持敬为主”[16]154。以上学者守宋儒之家法,以居敬穷理为格式,虽践履持敬,但未有许多发明。
还有一些学者特重主敬。赵谦“盖从来学圣之的,以主敬为第一义……庐陵解缙尝铭先生之墓,谓其力学主敬,信不诬也”[16]1049。他生于元末,是明代最早的几位学者之一,其著作《造化经纶图》从内外两方面论敬,确实犹有宋人之笃实,但其论内之敬曰“摄思虑去知故”[16]1053,与程朱“知觉不昧”或有不同。陈真晟,字剩夫,号布衣,亦对主敬颇有心得。与赵谦重视敬之内外相比,陈真晟更着重于敬之动静。动静二字乃主敬工夫之根本范畴,在他看来,动静都要主于一。静的主一之目的是养,可以消除妄念;动的主一是为了有所持,可以抵挡外诱。陈氏著有《心学图说》,而其“心学”的核心便是“敬”[16]1088-1090。以上两位人物在明代儒学史的书写中并不具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确实对于主敬有新的阐发。
作为明初朱子学的重要人物,曹端、薛瑄、吴与弼等对于敬也一样给予高度的重视。曹端,“立基于敬”[16]1061;薛瑄,明代早期著名的朱子学者,号“敬轩”,可见其以主敬为宗旨;吴与弼,一时硕儒,门下出了胡居仁、陈献章等大师,主张“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16]14,可见其工夫也全守朱子家法。
在吴与弼门下,胡居仁“一生得力于敬,故其持守可观”,人称敬斋先生[16]29。“依居仁意,敬之重要如此,当比致知为先”,一如“在其《居业录》篇目中,敬之一项紧接于道体与为学之后,而置于致知之前”[17]。
此外,有些学者将居敬看作“收放心”之方而加以强调。周瑛,“以居敬穷理为鹄”,曾言“始学之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居敬是也”[16]1093。陈献章弟子贺钦论主敬时,同样以收放心为说[16]99。娄谅亦以此为宗旨,即“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指”[16]44。娄谅之著作今已不能见,无从知晓其具体的解说,但其弟子夏尚朴“传主敬之学”[16]66,或许可以由此窥见其门户。
最后来说一说阳明学与敬。王阳明对于程朱主敬之说有所批评,主要在于两点:工夫分居敬、穷理是“二”[18]75-77;《大学》“不须添‘敬’字”[18]88。对此前辈学者已有许多讨论。“明代理学可以说是围绕着阳明所谓‘戒慎’与‘和乐’或‘敬畏’与‘洒落’之辩展开的”[19],阳明学总体上属于程颢、邵雍所开创的和乐或洒落一派,因此对于程朱提倡谨严的“主敬”必然不能契合而有所批评。要注意的是,王阳明门下后学并非都与敬无关。敬的特点是警觉、严肃,对治放肆之流弊是很有效的,反之,当和乐或洒落开始走向极端的时候,便会有人站出来,以严肃警惕之风而加以纠正。嘉靖十三年(1534),王阳明去世不到五年,季本便作《龙惕书》,向以王畿为首的自然派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季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季本的主张是“贵主宰而恶自然”[16]271,这可以说是具有“敬畏”之风的。在王阳明弟子中,能如此正面论述敬者恐不多见。此外,邹守益曾曰“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其学也“得益于敬”[16]336。可见,阳明学中亦可以容纳敬之一路。
以上便是对明代儒者关于敬的讨论的一个并不全面的梳理。明代理学发达,理学家人数众多,学界以往关注的大多是一些重要人物,如罗钦顺、湛若水,以及阳明后学中的典型人物,特别是聂豹与罗洪先,还有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和蕺山学派的刘宗周等。他们对于“敬”确实有很多发明,而我们通过对《明儒学案》的简单梳理,却发现除了上述重要人物,还有那么多理学家对于“敬”有着丰富的讨论。他们一直高度重视“敬”,对于敬之内外、敬之动静、主敬与穷理的关系、存养与省察的关系、主一、敬畏与洒落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广泛涉及。即便是阳明学兴起以后,洒落一派大盛,敬的讨论相比起来不再那么热烈,学者也不再主要实践主敬的工夫,但即使是阳明学内部也还是有“贵主宰而恶自然”的势力,以图纠正阳明后学的流弊。而主敬这一议题的重新兴起,则要等到晚明和清初了。
三、清代理学家对“敬”的拓展与深化
阳明学大盛的时代,学者不喜严肃的主敬工夫,又以居敬穷理为两截,落第二义,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随着反思阳明学潮流的开启,学者们又开始重新评价“主敬”等程朱理学的修养方法。到了明清易代之际,许多专主朱子学的学者也已经成熟起来,形成了或在朝或在野的庞大朱子学阵营。在这样的氛围中,学者们又开始纷纷重视“主敬”。其中,后世评曰以“主敬”为工夫宗旨的朱子学者就有以下诸人:朱用纯,“其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以主敬为本”[20]1648;冉觐祖,于嵩阳书院颁示所著《天理主敬图》等,“问业者云集,一时称盛”[21]243;窦克勤,因书“治法尧舜,学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谨独”受到康熙褒奖[21]243;劳史,自谓“一生用力于敬”[20]1873;方苞以桐城派始祖力护程朱,一本“由敬静以探性命之理”的宗旨[22]。此外,魏裔介、耿介、张夏、陆陇其、张伯行等对主敬的重视更不必赘言。经过乾嘉年间(1736—1820)的低潮期,理学于道咸年间(1821—1861)重新兴起时,唐鉴、吴廷栋、曾国藩、倭仁等更是以践履主敬为日课,深切体察而多有发明。总之,终清一代,“主敬”又重新回到了学者视野的中心地位,再次成为最为普遍和核心的修养工夫之一。更重要的是,清代朱子学对于“主敬”的讨论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其内在理路进行了拓展与深化。
(一)“主一”问题
这一时期的一个新变化是强调“敬天”。作为明末清初朱子学的重要人物之一,陆世仪对朱子学的义理做了全面的阐发,当然也不乏论述主敬之妙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陆世仪很重视“敬天”。虽然敬天思想是理学的应有之义,但明确主张以“敬天”为入德之门却是陆世仪的创见。与陆世仪同时代的谢文洊亦力行主敬工夫,尝辑《程门主敬录》,汇集程门对于主敬的论述。然而,关注谢氏的文章极少,仅见吴震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中有所讨论:“然在吾人看来,其为学宗旨则可以‘畏天’概之。根据其弟子黄采为文洊《日录》所撰序言,文洊之所以主张‘畏天’,乃是为了具体落实程朱理学提倡的‘以主敬为本’的思想口号。”[23]另,其“畏天”也是“畏天命”:“所著《大学中庸切己录》二卷,首以《君子有三畏讲义》,发明为学之要,在于主敬,‘畏天命’一言尽之。”[20]742
提倡敬天、畏天的一个明显效果是使得主敬的工夫有了落实处,所谓“敬天为入德之门”,把天、天命、上帝作为敬的对象,更容易下手(6)“舜光甥问‘敬’字工夫未进,予曰:‘汝看头上是什么?前后左右是什么?“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何处可容吾不敬?’”详参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对于主敬的理解悄悄产生了一种游移。若程颐及谢良佐、尹焞都侧重于在心上论敬的话,以敬天、畏天论敬正是要改变这一思路,把主敬从仅仅关注内心状态转移到天、天命这类对象上去。由于仅仅关注内心的状态会陷入神秘主义色彩,又难与释氏的坐禅划清界限,朱子学者找到一种更为笃实的主敬法也是反思阳明学之大势的自然结果。魏象枢,顺治三年(1646)进士,清初在朝朱子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孙承泽、刁包等人往复讨论,极力反对高攀龙“心无一事之谓敬”[24]的说法,与我们所说朱子学者反对阳明学之空疏有关。在魏象枢看来,孔子言“执事敬”都是落实在具体的事情上,因此绝无近禅之似,绝无空疏之嫌。不过,朱子学者认为明代学术受到禅学污染而走向空疏、朱子学仍旧笃实的观念,并没有令所有人信服。在所谓反理学的思潮中,更有学者把整个理学看作一丘之貉,在他们看来朱子学者想要排除心学的影响而转向笃实是徒劳的。毛奇龄认为,敬不可在心意上说[20]977,李塨也反对“离事言敬”[25]。这些反理学的学者与陆世仪、谢文洊、魏象枢有相似的观点,都主张敬作为一种情感或心理状态,是不能离开具体的对象来说的,否则就是“空言”,是不符合孔子的原始教义的。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哪些人、哪些说法是属于空言的,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诠释问题。由此可见,在此时,有关主敬是否有对象的争论已经全面展开。
彭定求是康熙朝理学的一个特殊案例。对于主敬,其《主敬工夫须变化说辨》[20]1630-1633颇为彭氏家学、后学等所重视,如罗有高在彭定求传记中对此特书一笔[26]。 “主敬工夫须变化”是谁的主张呢?尤侗《艮斋续说》卷十记曰:“予有诗云,‘主敬工夫须变化’,或者非之,作《主敬说》。”[27]可见辩论双方正是此二人。这场辩论也与敬有无对象性有关,双方“全体之敬”和“一端之敬”的说法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
敬有无对象,应该以何为对象,实际上就是“主一”问题。阴承功《主一无适论》是清代中期讨论“主一”问题的重要文献,反驳了王阳明所开“主一”是“主理”之说。在阴承功看来,阳明说主理,就是以理为所主的对象,这样有对象的敬不是程朱所说的主敬之本义。阴承功认为王阳明特别强调以理为对象是窒碍,重申主敬是主一,主一就是专一于事[20]2568-2569。清代后期的潘德舆也很重视“主一”问题,他在《养一斋札记》卷三中讨论了很多与“主一”相关的内容,但他认为,“阳明曰:‘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此语未尝错也”[28]。
(二)静、敬之辩
除了“主一”问题,敬之动静的问题在清代也变得十分突出。反理学思潮以及乾嘉学派的很多人物都反对“主静”,认为这是杂糅佛老之说的表现。例如程瑶田,其《论学小记》中有《述敬》一篇,就反对静中之敬[20]3194-3197。有鉴于此,清代朱子学者开始对主敬与主静的问题即主敬是否以静为本进行反思。朱泽沄与王懋竑交游[20]2079,其作有《朱子未发涵养辨》两篇,阐发朱熹主敬涵养的思想[20]2080-2084,王懋竑则在《答朱宗洛书》中忆及两人曾围绕主静之说“往复论难,卒不能合”[20]2073。其后,夏炘《与胡琡卿论白田草堂杂著书》对王懋竑与朱泽沄之间的辩论做出了总结[20]6036-6038。
(三)敬以存仁
夏炘所著《述朱质疑》是清代道咸年间(1821—1861)朱子学复兴之潮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其中,与“敬”论有关者包括以下诸篇:《朱子己丑以后专发明程子敬字考》《敬贯小学大学说》《敬贯诚仁说》《周子主静即主敬说》《敬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全德说》《朱子以静为本说》等[29]。夏炘比较全面地阐发了朱熹主敬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敬贯诚仁说,一是以静为本说。敬贯诚仁最主要的贡献不是将敬与诚联系起来,而是将敬与仁联系起来。自二程起学者就多说“诚敬”,却较少提及敬以存仁。以仁学来看朱子学的新视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没有这个新视角的情况下,敬与仁的关系是极不容易被发现的。因此,专言敬以包全德,才能真正具有意义。同时,“以静为本”说也要放到这个新视角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这里不再是关于静、敬之辩的老生常谈,也不是敬贯动静的照本宣科。
四、结语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理学“敬”论肇始于二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持续得到阐发,蔚为大观。尽管本文已经对大多数讨论“敬”的理学家进行了重点梳理,仍不免挂一漏万。在这样一个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期待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理学“敬”论的思想价值。另,东亚儒学(7)这里所说的东亚儒学主要是指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在理学影响下所形成的儒学思潮。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因此,为了叙述的完整性,也有必要简要地提及东亚儒学中“敬”的思想。在受到理学的影响以后,也是非常注重主敬的,其容受与创新显示出理学“敬”论对日、韩儒学的重要影响。反之,日、韩儒者的讨论各具特色,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主敬思想具有一定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