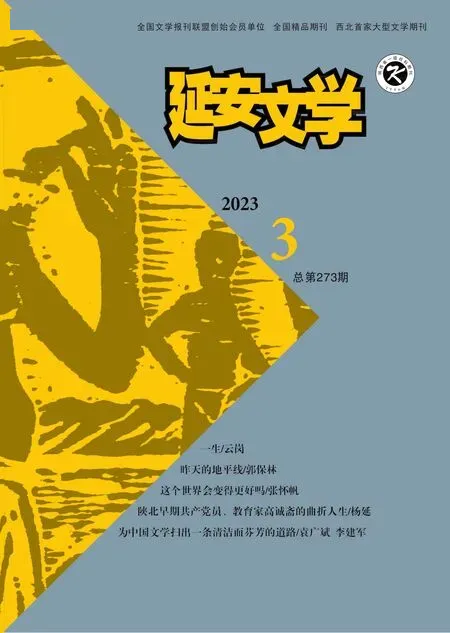走,讨饭去
2023-02-20羊亭
羊 亭
腊月初八清晨,鸡已叫过几遍,天光却迟迟未明。母亲喊了小阿羊两声,没有得到应答。上半夜睡下没多久,小阿羊就发起了高烧,噩梦连连,胡话不断,一次次从梦中惊醒。这会儿虽然睡得很好,但身上依旧滚烫。母亲往他额头和胸口又推了一次烧酒,掖好被角,希望他出一身汗就能退烧。可小阿羊觉得自己不是在被窝里,而是身处寒冬的旷野。周围笼着蒙蒙雾气,脚下是厚厚一层白霜,感受不到丝毫暖意不说,还冷得直打哆嗦。
母亲埋怨道:“都怪那只老鹅!”
前一天下午,小阿羊赶着鹅群来到荒田里。那时节田里的水燕麦长势喜人,不是稀疏的一丛丛,而是油汪汪一大片。老鹅最爱吃水燕麦,吃了这种一年里长得最好的水燕麦,隔天就能下一只蛋。如果是雄蛋,一只可以换一块五的好价钱。除了一年卖两头肥猪,这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就算不是雄蛋,在山乡缺少油水的年月,也可以好好打一回牙祭。每回母亲去镇上赶集,小阿羊和姐姐都盼着她能捎回几只寡蛋。但是他们家的鹅很争气,多数情况下,那些蛋都能孵出小鹅来。母亲高兴,小阿羊和姐姐却高兴不起来。
天色渐渐暗下来,母亲站在屋檐下喊:“小阿羊,快把鹅赶回来。天黑起雾了,衣裳沾了雾气要感冒。”
于是小阿羊赶着鹅群匆匆回家。已经走了一段路,忽听到背后传来鹅的叫声。他数了数,十六只,少了一只母鹅。小阿羊返回去,发现它正在田边的沟渠里嘎嘎乱叫。离群的老鹅满眼惊恐,奋力扑棱着翅膀,想要从沟里上来。小阿羊伸出手,以为能抓住老鹅的脖子把它拽起来,但它错会了小阿羊的意思,慌里慌张地朝一边躲,激起大片浪花,打在手背上刺骨地冷。小阿羊一手攀着沟渠边的小树,一手伸过去希望够得着它。但脚下一不小心,整个人突然往水里滑去,一时慌神,攀着树的那只手也搭不上力了。他感到无边的寒意和幽暗将他吞噬,窒息、混沌、恐惧、孤立无援……
是三叔把他救上来的。当时三叔正在不远的田里给油菜施冬肥,听到水声和叫喊,他赶紧扔掉手上的农活,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小阿羊耳朵里嗡嗡直响,三叔张大嘴巴不知在说什么。老鹅站在荒田里,微微摆动尾羽,一副事不关己的淡漠姿态。
母亲也从家里一路小跑过来,她哭着朝小阿羊骂:“你怎么这么笨,赶鹅能把自己赶到沟里去?”她扬起手要打小阿羊,但最终却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哭得很伤心。
鸡又叫过两遍,窗边才透进微微白光。
小阿羊打了个寒颤:“别拖我,别拖我,别拖我下水,我快冷死了。”
母亲摸了摸小阿羊额头,叹息一声:“莫不是遇到水鬼了?”
她起身去了厨房,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沟里的水漫过小阿羊头顶,那只惨白的手还在使劲拉他,他看到成群的鱼虾从眼前游过,水草在疯狂地摇曳。他突然清醒了,三叔不是在旁边的田里吗?他想喊救命,另一只手却捂住了他的嘴巴。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飘荡:“跟我去水里吧,上了岸,你身上会结冰的。”
“你是谁?你要拉我去哪里?”小阿羊拼命挣扎。
“去水里,做金鱼的伙伴。”
这回是母亲救了小阿羊,她把一块热毛巾搭在小阿羊额头上。总算暖和些了,但是这温暖仍无法盖过身上的寒冷。
小阿羊醒过来,只有十瓦的白炽灯亮着幽幽黄光,照得他睁不开眼。
过了一会儿,母亲端来一只粗碗:“小阿羊,快起来,喝一碗黄糖熬的姜汤,甜得很,喝下去就好了。”
他大口吞着汤,没觉得甜,姜的气味倒很浓,从口腔一直辣到胃里。擦了那么多烧酒都没出汗,姜汤下肚没过五分钟,小阿羊就起了一身热汗,把本就有些潮的被子也打湿了。
出了汗,小阿羊没那么冷了,也不再打颤,只是肚子突然饿得很,仿佛吃得下十个鹅蛋,最好是母亲用葱花炒的寡蛋,外焦里酥,那香气能让每个细胞都轻声尖叫起来。
小阿羊说:“我好饿,就像三天三夜都没吃过东西了,我们家的鹅下蛋了吗?”
“知道饿就对了。”母亲擦了擦眼睛,她的眼珠上布满血丝,一整夜她都没怎么睡。她说,“但是今天我们不吃鹅蛋,别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吃腊八饭。”
她这么一说,小阿羊觉得更饿了。他想起每年这一天吃的腊八饭,大米掺上糯米、腊肉、豆腐干、花生、红豆、红枣,文火慢慢熬煮一小时,再放些萝卜、白菜、海带丝,咕嘟咕嘟冒着香气,最后撒点蒜苗或葱花,又好吃又提热。
小阿羊吞了口口水:“可是爸爸今天不回来。”
前天晚上,在县城面粉厂打工的陈小七带回一封父亲写的信。他说腊八节不回来吃饭,周末也不回来了,他被单位派到市里帮忙,大概要腊月底才回来。他还让陈小七捎回二十块钱,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小阿羊的生日,他常常说,小孩子过生日,再怎么困难也得吃顿好的。他们家厨房里挂着两块腊肉,是母亲冬月初就腌制好的。小阿羊和姐姐每天都要问她几遍: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吃它?母亲说:腊八节,煮腊八饭的时候吃,爸爸到时也要回来吃腊八饭。他们一天天地盼着,那两块腊肉一天天地越来越干,越来越小。他们家可有四口人呢,要是祖母过来就是五个人,这么小两块肉,也不知道够不够吃?
母亲说:“不回来我们也煮。”
天亮后,小阿羊觉得整个人都好起来了,只是仍有一点虚弱无力。母亲想让姐姐帮他向老师请个病假,但他说什么也要去。一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就请假,同学们会笑话他的。然而一上午他的精神都无法集中,他老在想腊八饭煮得怎么样了。母亲可千万别把腊肉切得太小,火也别太猛,不然肉丁都煮没了怎么好吃?其他同学的心思也差不多,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的间隙,总有人伸长脖子朝窗外自家方向张望,要是看到冒起阵阵炊烟,心里就踏实了,要是还没什么动静,难免会有些失落。那天上午,因为心不在焉被罚站的就有七八个,但他们并不显得难过,相反还有点喜形于色。
离放学还有二十来分钟,大概老师也嘴馋了,对他们一帮躁动难安的孩子说:“放学了放学了,都回家吃腊八饭吧。”
小阿羊一口气吃了三大碗,撑得快直不起腰了。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精力从没那么旺盛。下午体育课他们玩丢沙包、跳马、打独脚战,个个背上都热出了汗。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小阿羊就又发烧了,不过比前一天晚上似乎要轻些。姐姐说:“都是下午体育课跳过了头,我就看他一个人跳得最起劲。”
母亲说:“昨天落水的时候,莫不是被吓掉了魂。”
按照乡下的说法,小孩子吓掉了魂,需得在三日之内把魂捞回来。不然魂不附体,时日一久,再好的身板也会出毛病。小阿羊知道,他们村有个叫芙蓉的女孩,下雨天过桥不小心跌到桥下,河床上没一滴水,她也没伤着皮肉,但是过了两天却突然变得疯疯癫癫,跑了不少医院,最终也没治好。还有一个身强体健的少年,放牛时在荆棘丛里让吊脚蜂蜇了一下,照理说并没什么大碍,却在一个星期后死掉了。上年纪的人说,那是被吓掉了魂,魂魄本该住在肉身之内,遇到突发事故被惊吓,灵魂出窍,那原来的身子便成了行尸走肉,不出问题就怪了。祖母是捞魂的老手,曾经为不少孩子捞过魂,而且他们之后都没再出任何事端。母亲当即去了隔壁祖母家。
第二天下午太阳落坡,祖母便提着一个撮箕去了小阿羊落水的沟渠边。小阿羊在家门前搭起板凳写作业,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听到不远祖母的呼喊,他刚要答应,母亲却捂住了他的嘴。
“别出声,那是在喊魂。”母亲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应了,你的魂就以为不是在叫他,到时候冒冒失失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听不到喊他的声音,你会成为一个永远没有魂的人。”
小阿羊吓坏了,屏住气,写字也不敢下手太重。
祖母一路喊了回来。小阿羊仔细辨别她的声音,有那么一刻,他感觉那不像是在喊人的名字,而像是在歌唱,唱一首哀怨动人的魅惑之歌,似乎能蛊惑人的心志,有好几次他都险些答应了。祖母疲惫地来到门前,嘴里还在不停地喊:“小阿羊,小阿羊……我的孙孙哟……”
母亲捅了捅小阿羊的肩膀:“可以答应了。”
于是小阿羊答应了祖母。
祖母紧绷的身子松弛下来,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碗水,气喘吁吁地说:“谢天谢地,小阿羊,你的魂回来了。”
她这么一说,小阿羊感到身体似乎真恢复了往日的健硕,肉身之内,仿佛还有另一个自己。这感觉非常奇妙,但又真切无疑。
但是小阿羊仍然没有彻底退烧,始终在高烧与低烧之间徘徊。母亲说:“看来捞魂也不起作用啊。”
祖母心有不甘:“你是觉得我没有本事?”
“我哪是那个意思,”母亲说,“也许问题没有出在丢魂上。”
“你说他晚上一睡着就讲胡话?”
“他说有一只拉他的手,好像还听到什么女人的声音。我就想,是不是让水鬼给缠上了。”
祖母说:“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还就不相信了,我帮别人捞魂个个都灵验,到了自己孙孙身上却不起作用。”
又一天下午,太阳落坡,祖母再次去了小阿羊落水的沟渠边故技重施。见小阿羊的情况仍然没有一点好转,她对母亲说:“我们确实该想点别的办法了。”然后又对小阿羊说,“走,去找何神仙。”
于是母亲背起小阿羊,跟随祖母翻过两座山,又行了一程弯弯曲曲的小路,终于到了竹林深处那个何神仙家里。他是个清瘦的中年男人,说话的时候轻声细语,眉毛很浓,眼睛大而有神。身着一件洗得泛白的旧中山装,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一点也不像个神仙。
何神仙抓起毛笔,在一张黄纸上龙飞凤舞,口中念念有词。
小阿羊问祖母:“他在念什么?”
祖母说:“念些让你好的话。”
“他写的是什么字?”
“别出声,何神仙是在给你画符。”
“他蘸的是不是血?”
这话被何神仙听见了,他乐呵呵地说:“没错,就是血,而且是阳气极高之人的血,小鬼小妖都害怕。”
他把写好的符烧掉,化在一碗清水里,让小阿羊结结实实地喝三大口。小阿羊不敢喝,心想要是喝了,他就成喝人血的小孩了。
“喝吧,”何神仙说,“喝了任何小鬼都不敢靠近你。”
小阿羊喝了一小口。奇怪,居然是甜的,像母亲冲的白糖开水,于是他大口大口地喝起来。谁知何神仙夺过碗,不让他喝了,把剩下的倒在一个空瓶子里,让母亲每天晚上给他喝一口,分七天喝完。小阿羊看了看瓶子,已经所剩无几,他一口就能干掉。
何神仙小声对祖母说:“确实是让一个水鬼缠上了。是个三十多岁的女鬼,浑身湿淋淋的,眼睛和鼻子都让鱼虾吃了。你们得把她送走才行。”
他们临行的时候,何神仙又画了一道符。这回他没有烧掉,而是装进一个小符袋里,让小阿羊挂脖子上。那个符袋也是红色的,小阿羊怀疑它也是人血染红的,戴在脖子上,突然觉得一阵心惊肉跳。
他们快走出竹林了,何神仙突然在后面喊:“正月十六再带他过来一次,我给他当个保保,日后保他个平安无事,顺顺利利长大成人。”
祖母和母亲谢过他,让小阿羊跪地上先给他拜上一拜。小阿羊照做了,顿时觉得有了莫大的依仗,他也是有保保的人了,仿佛从此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在回去的路上,祖母说:“那个死婆娘,做鬼也不做个好鬼。”
母亲说:“人鬼殊途,只怕她想做个好鬼也难,谁让她生前就喜欢小阿羊呢?”
“哼,到这种时候你还在袒护她。”祖母撇了撇嘴,“我从一开始就没看上她,怪就怪那个陈媒婆,把她说得像观音菩萨一样好,到头来却是个生不了蛋的鸡。她死了,也算让老三得一个解脱。”
她们说的话小阿羊一点也听不明白,自然插不上嘴。
很多年后,小阿羊才从旁人口中知道了些当年的事。原来三婶并不是三叔的第一个女人,在她之前,三叔还娶过一个姓嬏的女子。嬏婶婶的脑子有点问题,不过人生得水灵俊美,十里八村也找不到这样的第二个,三叔着了魔地喜欢她。就算后来知道她没有生育能力,也没有影响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倒是祖父祖母不愿意,眼见这么个七尺男儿没了后,总撺掇他离了再娶,三叔却一直不为所动。人们还说,嬏婶婶虽没有过生儿育女的经历,但是很会照顾孩子,邻居们有事照看不过来小孩,只要和她言语,她总欣然答应,大家对她也很放心。她尤其喜欢小阿羊,据说小阿羊这个小名就是她起的。那天母亲去镇上赶集,把小阿羊托付给她。回来时却不见一人,听到小阿羊的哭声,寻到田边,这才发现小阿羊周身都是湿的。旁边堰塘水面的波澜渐渐平静。三叔扎进水里,不多时便捞出了嬏婶婶的尸体。有人说嬏婶婶突然犯病了,那些年她虽然看上去已完全好转,但人的大脑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谁说得准什么时候又会发作;还有人说是色胆包天的家伙贪图她的美貌,她不从,所以被人推下了水;也有人把目光落到了祖父和祖母身上,都说人心隔肚皮,何况他们对她有意见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小阿羊当时太小,什么都不懂,也记不住。所以关于嬏婶婶的死,最终成了一个谜。
按照何神仙的意思,晚上祖母带上香、蜡、纸钱,去了小阿羊落水不远处的那口堰塘边。看得出来,她其实挺不乐意做这件事。作为一个长辈,眼下要亲自去祭拜一个晚辈,而且还是那个活着时就不讨她喜欢的人,换了谁也不易过心里的那道坎。但是为了她的孙子,她却不得不走那一遭。
祖母回来后显得很生气,母亲以为她还在为自己放低姿态的事心有不平,谁知她突然破口骂道:“那个死婆娘,我要找道士收了她。明天我就去请何神仙,让他亲自来。”
母亲问她是何缘故,她却缄口不语。
第二天,小阿羊晕晕乎乎地从学校回家,发现何神仙坐在堂屋里。他还是上次那身着装,正翘个二郎腿小口饮茶。他说:“小阿羊,你放学了?”
小阿羊点了点头,放下书包。
姐姐问小阿羊:“他就是何神仙?”
小阿羊还没回答,她又说:“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神仙嘛。”
祖母见状,叫姐姐一边去写作业,又对小阿羊说:“不知道喊人吗?”
小阿羊问:“喊何神仙还是喊保保?”
何神仙笑了起来:“谁说他烧坏脑壳了?我看他脑子清醒得很嘛。”
小阿羊喊了他保保,照理说得正月十六正式拜过他才能喊的,但是他既然都答应了,到时候也就是走个过场。
他很高兴,摸了摸小阿羊脑袋:“觉得好点没有。”
小阿羊摇摇头,感觉好像辜负了他,于是又点点头:“看到你我觉得好些了。”
他发出一阵朗声大笑:“你会好起来的,我有办法让你好起来。”
吃午饭的时候,祖母才道出头天晚上堰塘边发生的事。祖母说:“那个死婆娘简直冥顽不灵,我好心好意送走她,她却给我使坏。活着时就不是个东西,死了仍旧一个德性。我点火烧纸钱时,好端端的突然起来一阵阴风,把我手都烧糊了。”说着她伸出被烧伤的拇指,“我往回走的时候,又突然来了几阵风,两团鬼火跟了我好长一段路。”
何神仙问:“你当时回头了没有?”
祖母愤愤地说回了:“她以为她能吓着我,笑话,我什么场面没经见过?”
“坏了,”何神仙长叹一声,“我交代过你千万不要回头的。”
祖母悔恨地说:“我当时一点也没想起,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何神仙放下筷子,抿了一小口酒:“没事,我有办法。”他扭头朝小阿羊笑笑,“不过拜保保的时候,我可得多收一块猪头肉。”
母亲有些为难,却仍然应承道:“那是应该的,应该的。”
何神仙做了法。做法的时候是下午,小阿羊正在学校上课,不过似乎有些感应,在冷飕飕的教室里,他安静地坐着居然出了一身热汗。听说做法费了何神仙不少法力,他离开时,好像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显得十分疲惫,走路也变得一瘸一拐。
他还告诉母亲,要想将小阿羊的毛病根除掉,还要办一件事。需得在农历新年以前,讨够一百户人家的饭,放一起煮了给小阿羊吃,且这一百户人不能和他们家有丝毫沾亲带故。
在他们村里,找一百户人家倒是易事,但他们家是大姓,和村里别的人家或多或少都沾点亲。要把这件事做得圆圆满满,就非得去外村不可了。
第一天母亲讨了十来家。大概吃了不少闭门羹,有些灰头土脸的。那时农村的境况并不乐观,虽然基本都吃上了饱饭,但仍有个别家庭生活艰难。
第二天,小阿羊和姐姐都开始放寒假了。他们嚷着要和母亲一起去讨百家饭。小阿羊的身体还没痊愈,不过走十来里路不成问题。母亲最初不肯,说不能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去经历这些。后来她答应带小阿羊去,姐姐得去田边放鹅,再割些水燕麦回家当猪食。姐姐为此很不高兴,他们临出门时,她恶狠狠地瞪了小阿羊一眼,也许她正是为了摆脱这些,才央求母亲带她一起去。
他们上路了,母亲递给小阿羊一根长木棒。小阿羊以为是要打扮得更像个要饭的,母亲摇摇头,说是为了提防狗。一路上果然有很多狗,不过它们并不怎么理睬母子俩,夹着尾巴灰溜溜跑路。小阿羊的胆子就这样放开了,不感到去讨饭有多么丢脸,突然觉得这像一次奇妙的旅行。
他们讨的第一家是对老夫妻。老婆婆的年纪不太大,但身体不怎么好。她坐在院子中间的藤椅上,椅子扶手那靠着根拐杖。她的眼睛发红,面色黯淡,还有些浮肿。母亲说明了来意,她轻轻地摇着头,啊吧啊吧地不知对老头喊着什么,原来她不会说话。
老头走过来,对他们说老婆婆中风过两次,如今完全成了个哑巴。他还说他们和儿子儿媳分了家,就剩老两口单过。眼看年关将近,他们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他捧了一大捧花生,又给了他们半碗米。
母亲有点于心不忍,但老头说什么也要他们收下。母亲道了谢,叫小阿羊给两位老人家磕了个头。他们已经走出很远,小阿羊回头望见老头还站在门口。
后来他们又去了一户红砖青瓦的人家。院坝里坐着一个女孩子,正捣鼓手里的自来水钢笔,手上沾满了蓝色墨水。她机警地瞟了他们一眼:“你们找谁?”
母亲没有直接说他们是来讨百家饭的,而是问:“小朋友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怪不得,小阿羊望着她手里那支崭新的钢笔,心想等到明年,他也会有一支这样的钢笔了,他可不会像她这样弄得到处脏兮兮的。他已经用过几回姐姐的钢笔,写出的字比铅笔字要好看不少。
“哦,小阿羊,她比你高一个年级。”母亲说,“叫声姐姐。”
小阿羊觉得别扭,他只有一个姐姐嘛,为什么要叫她姐姐?
母亲没有责怪他,又问女孩:“你家大人呢?”
“我妈去山上耙柴禾去了。”女孩指了指背后莽莽苍山,“你找我妈有什么事?”
“没什么,”母亲说,“既然没有大人在家就算了。”
母亲招呼小阿羊便要走。小阿羊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母亲:“我们不讨百家饭啦?”
母亲说:“去下一家吧。”
女孩问:“你们是讨百家饭的?”
母亲停下脚步,脸上突然有了羞愧之色。
“你们怎么不早说,”女孩把钢笔扔桌子上,“我前年也讨过百家饭,也是我妈领我一起去的。起先本来是我爸带我去,但是跑了一天他就不干了,他说他一个大男人家怎么能去干这种事。”
“你们真讨了一百家?”小阿羊问。
“不多不少一百家。”女孩说,“我太姥姥说的,吃了百家饭,再淘气的小人也好养。我生病吃了三个多月赤脚医生开的药都不好转,居然是吃百家饭吃好了,你说怪不怪?”
母亲也颇感好奇,禁不住打听:“你当时得了什么病?”
“好像就是平平常常的感冒,发烧咳嗽,时好时坏,一直都治不断根,医生也说不出个原因。”
“你真是吃百家饭好的?”小阿羊说,“我们讨百家饭,是我保保出的主意。”
“那还有假,我们这里好多小孩子得了病都是用这个办法。”
小阿羊有点失落,原以为这是保保何神仙的发明,未曾想就在他们临村,早先已有这么多人知道并仿效。
女孩给了他们一些食物,然后又指给他们一户人家道:“那是我大伯家,你们去吧,他家里这会儿正好有人在。”
他们在那里轻轻松松就讨到了饭。女孩的大伯是个善良的中年人,要过年了,他家添置了不少吃食,他抓了一大把糖给小阿羊,又给他们装了半袋子江米条。小阿羊看着这些东西就觉得饿起来了,但母亲不让他吃江米条,只给他剥了一颗水果糖。
临近正午时,小阿羊和母亲来到河边的一处人家。
他们老远就看到院门前聚了不少人,院中腾腾冒起白色烟气,走近了才知道他们在杀年猪。肥猪已经宰杀完毕,并且烫过了猪毛,肥白的一整条猪被放在八仙桌上开肠破肚。桌下一只水桶里盛了大半桶猪血,那颜色已经渐渐变成暗红,另一只桶里装了些猪肺、猪心、大肠、小肠之类。一股股臭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让人直想作呕。
小阿羊和母亲走近,拿刀剔骨头的胖子看了他们一眼,嘴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利落地把骨头用刀尖翘起,刀刃再一用力,一块骨头便像耍魔术一样蹦了出来。他朝屋里喊了声:“李支书,你家来亲戚了。”
过了一会儿,从堂屋里出来一个背着手走路的人。他穿的是西服,居然还系了一条红领带,但下身却着一条粗布裤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即便这样,他也算很威风了。那个时候,能穿得上西服的非富即官,都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小阿羊父亲也有一套西装,但他除了去市里,过年过节也很少穿。
那个叫李支书的歪着脑袋喊:“是谁?哪个亲戚?在哪里?”
他喊完话才看到小阿羊和母亲,眉毛顿时拧成了疙瘩。他两步到他们前面,又歪着脑袋把他们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有些恼怒地道:“这他妈是哪儿来的要饭的?”
母亲见了这种人也不免担惊受怕,她小声说:“李支书是吧?我们是邻村来的。这是我的儿子,他叫小阿羊,今冬得了病,他爸又不在家,我们只好按照老办法挨家来讨百家饭。还请你开开恩。”小阿羊站在一旁不敢出声,那个李支书和拿刀的屠夫一样不怒自威。
“讨百家饭?”李支书不慌不忙地裹了支烟,“讨百家饭你上我们村来讨什么?你们村子可是个大村,人比我们村多,也比我们富裕不少。”
“李支书你说笑了,我们村才是小村,大家也不富裕,而且大多是些本家人,讨百家饭最忌讳向本家人讨。我们跑了一条村,也才只讨了七八家。”
李支书看上去很不耐烦,他几次想打断母亲。而母亲这个时候又偏偏没有眼色。小阿羊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这家不好讨他们就去下家好了。但是母亲站那里不动,还想对李支书说好话。
“要饭的乞丐我见得多了。你们这种人倒是挺会耍把戏的,但别以为骗得过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我们真是讨百家饭的呀,”母亲按着小阿羊的肩膀,把他推到前面,“小阿羊,你快给李支书说,请李支书行行好,往后我们一定会记着他的。”
“走走走,赶紧走。”李支书做出了驱赶的姿势,“我不需要你们记着我,因为我根本就没什么要施舍给你们的。”
“随便给点什么也行啊,李支书,求你别让我们空手回去。”
“没有,家里什么也没有。年里年关的,你们也太会挑时间了。旧社会里,只有地主老财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要这要那的。”
他们讨了一上午的百家饭,大家的情形都不太好,但这个李支书家里显然要宽裕不少。那个年月,不是谁家里都杀得起年猪的。很明显,并不是他没什么可施舍,而是他根本不想给他们任何东西。
母亲说:“李支书,你就行行好,给我们一块猪血也行啊,多多少少是你的心意。”
“你们走不走?再不走我放狗了!”
小阿羊有点害怕,不由得捏了捏手中的木棒,心想拿了一路这会儿还真派上了用场。
母亲仍没有要走的意思,小阿羊拉了她一下,她却还呆在那里。
后来李支书真放了狗。那是一只浑身像染了墨汁的黑狗,跳起来快有小阿羊那么高了,黑狗见了生人,仗着有主人家在,翘起尾巴狂吠不止。母亲这才拉着小阿羊灰溜溜地跑,好在黑狗并没有追他们,小阿羊回头看了看,黑狗站在房前,那气势简直和李支书一样,好像在说:“快滚快滚,不然我让你们好看。”
他们一口气跑出好远,小阿羊才发现他的鞋底脱胶了。袜子前面本来就烂了个洞,脚趾头露在外面,没走多大会儿,大脚趾就磨破了皮。
那天中午,他们在一个好心女人那里要了些吃的,临走时她见母子俩都还饿着肚皮,一定要留他们吃了午饭再走。她说:“家里也就我一人。我儿子在省城读大学,男人在省城打零工。”
母亲说:“这时候也该放寒假了吧?”
“早就放了,儿子放了假也去了他爸那里,给他打个下手。钱倒挣不了几个,他爸说,是时候让他体会一下生活的不易。让他去体会好了,生在我们这样的人家,我对他是放一百个心。”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是满满的幸福和自足。
母亲很羡慕她,一个劲地对小阿羊说:“小阿羊,听到了没有。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也能出大学生,你也要中用些,以后读个大学让我和你爸看看。”
小阿羊不停地点头,一直抓着脚趾。他真担心下午还要去一家一家地讨百家饭,半日时间已经让他领略了这是件非常难的事,再走一下午,他的脚趾说不定就断了。
好心的女人给他们做了汤面条。面条很少,菜很多,上面撒了葱花、香菜和油碴儿,特别地香。小阿羊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汤面条,倒不是因为太饿,而是女人的幸福与自足感染了他。吃到最后,他发现碗底居然还有个荷包蛋。他看了看母亲碗里,她也快吃完了,她的碗里没有,好心女人的碗里也没有。小阿羊很想一口把蛋吃了,他和姐姐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寡蛋了,更别提新鲜的荷包蛋。可是他吃不下,他突然很想哭,为他们山乡大多数农村人的贫寒,为别人的这番好心。他对母亲说:“我吃饱了,吃不下了。”
母亲笑了笑:“快谢谢阿姨,你不吃怎么对得起阿姨的这番好意?”
小阿羊对女人小声说:“谢谢阿姨。”
女人对母亲道:“你家儿子这么小,但很懂事。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小阿羊吃得很慢,想好好品尝一下荷包蛋久违的滋味,但只尝到了一种酸酸涩涩的味道。
那天他们讨到了三十来家,算是不错的了。回家途中母亲的心情也好了不少,她还一直记着中午那个好心女人和她说的话。母亲问小阿羊:“小阿羊,你说妈的好日子是不是还在后头呢?”
小阿羊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但不能扫了她的兴。他说:“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晚上洗脚的时候母亲才发现小阿羊的鞋子脱胶了,两个脚趾头都磨破了。本来一整个下午都心情大好的她突然不说话了,一个人坐在那里哭。小阿羊和姐姐看到母亲哭,也跟着一起哭起来。后来母亲一手揽着他们一个,哭得更伤心了。小阿羊又想到了给他们带来好心情的那个女人,对母亲说:“妈,我们的好日子都在后头。”
听小阿羊这么一说,母亲真的就如释重负般,擦干了眼泪,给小阿羊和姐姐也擦干了眼泪,充满信心地对他们不住点头。
第二天母亲说什么也不让小阿羊和她一起去了,她带着姐姐上了路。让小阿羊待在家里做寒假作业,他不用去田里放鹅。
几天下来,临村能讨到的也讨得差不多了,母亲一合计,还差一家就正好满百。为了再讨一家跑外村去是挺不划算的,而本村又根本再无处可讨。姐姐说:“九十九家也可以了,老师教过我们四舍五入,九十九其实也就是一百了。”
祖母说:“小孩子家家的,不懂就不要乱说。”
姐姐争辩:“老师和书上都是这么教的。”
母亲很为难:“也只有先这样,过两天逢场,我去场镇上看看能不能讨到。村子里谁家的情况都好不到哪去,街上的人宽裕点,兴许会好讨些。”
祖母没再说什么,姐姐高兴得好像考了一百分。
过了两天,母亲提了一筐鹅蛋去赶集。小阿羊和姐姐仍像往常一样,希望母亲能带回来几只寡蛋,他已经把讨百家饭的事给忘了。半上午母亲就回来了,她仍然只提了早上出门时的那个竹筐,她的脸色很阴沉。姐姐往竹筐里瞧了瞧,她的脸红扑扑的,她悄声告诉小阿羊:“是寡蛋,好几个呢。”
小阿羊也跟着高兴起来,等着晚上那顿好饭。
母亲一整天都郁郁寡欢。晚上做饭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她把寡蛋完全煎糊了。那顿晚饭他们吃得异常艰难。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母亲起了个大早,她决定无论多么困难也要去外村再碰碰运气。她没有带姐姐,也没有带小阿羊。小阿羊晚上又发烧了,还不停地发抖。天亮时虽好了些,但整个人打不起精神。母亲让姐姐好好照看他,临走时祖母跟了去,她说:“外村我也认识一些人,我一个老太婆跟着去,别人多少会给点面子。”但是她们中午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要到。
他们正在吃午饭,屋里突然暗了下来,门口站着个高大的身影。小阿羊心里一喜,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仔细一看却是三叔。在他的记忆里,三叔离他们家虽然很近,但是平日里基本没怎么走动。
三叔手里端一只碗,他迟疑了片刻,把碗放在桌上,眼睛并不看他们。他说:“大嫂,听说小阿羊病了,我帮不上什么忙,听说你们讨百家饭还差一家?我送一份过来,现在刚好够。”小阿羊凑近看了看,是胡萝卜炖肥肠,还冒着热气呢。
母亲怔怔地站起身:“老三,谢谢你的好意,可是自己家的人送的怎么能叫百家饭?”
三叔半天没说话。他转身走到门口时,突然停下来,背对着他们:“自从小嬏走了,我就再也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从此没有他们那样的父母,当然也就没有兄弟姊妹了。我虽喊你一声大嫂,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还是一家人!”
这时正巧祖母过来了,他俩打了个照面。显然三叔说的话她都听到了,虽然很生气,却故作镇定地道:“好啊,既然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也不稀罕你的施舍。你把东西端走。”
三叔没有理她,径直走了。
祖母坐下来,大口喘着粗气。小阿羊真担心她会把碗摔了,谢天谢地,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失声哭了起来。哭过一阵,她狠狠地说:“当我没生这个儿子!”
现在好了,刚好讨够一百家,这就是名正言顺的百家饭了。不过小阿羊和姐姐都在担心一件事,就是三叔送他们的胡萝卜炖肥肠到底能不能算数?如果算,他们就没有三叔了;如果不算,这大年关头让他们再上哪儿去讨?
母亲又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了,她觉得这些天没有白努力。
一九九二年的腊月三十,他们家不吃丰盛的年夜饭,不吃饺子,他们吃百家饭。午饭过后,母亲把讨来的东西倒进大铁锅里,居然有大半锅,另外还有些未经烹煮的生食,她得先煮熟了再倒进大铁锅里一起热。天气很冷,母亲却忙得满头大汗。
半下午些,父亲总算回来了。小阿羊老远就看到他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托满了东西,那可都是他们一年的念想。父亲把两包东西放下,又提了一大包吃的去厨房。见母亲在那里忙,他朝锅里看看:“你这做的是什么?”
母亲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父亲讲了一遍。本来挺高兴的父亲突然沉下脸,说:“这都什么年月了,你们还信这个。妈就不说了,你好歹是个年轻人,也净弄这些封建迷信。”
不等母亲反应过来,父亲推着车就出了门。母亲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般不知所措……
天擦黑了父亲才回来,原来他去场镇上给小阿羊配了药,让他赶紧把药服下。西药很苦,小阿羊直反胃,不过感冒冲剂就好多了,甜甜的像糖水。
小阿羊以为父亲会把他们好不容易讨来的百家饭倒掉,没承想当母亲把热好的饭端上桌,他居然说自己小时候也吃过这样的百家饭,他还说:“今年我们就过一个不同以往的年三十。这东西能治病是假的,不过里面包含了世上所有人家的酸甜苦辣。吃了它,你们也就体会了一回生活的忧喜和苦乐。”
他的话让小阿羊很泄气,再看看碗里的东西,真叫人提不起胃口来。看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小阿羊尝了尝,味道居然不错,像腊八饭。结果他吃了三大碗。
农历一九九二的最后一夜,他没有再发烧。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母亲不让小阿羊吃药,说新年的头一天就吃药像什么话。父亲却说,你那些老毛病还是改不了,新年怎么了?病好了身体好了就行。于是他还得吃药。
母亲摸了摸小阿羊的额头,无比欣慰地笑了。她说得去场镇上买两块猪头肉,到时候拜保保要用。父亲摇了摇头,无奈地道:“真是无可救药。”奇怪的是他没有阻止母亲,而是像个大孩子一样拉着小阿羊和姐姐跟在母亲后面,快乐地去了镇上。
他们在镇上碰到了三叔和三婶,父亲正要和他说新年好之类的吉祥话,他却转过脸去,假装没有看到他们。父亲自言自语道:“这个老三,简直不像话,还拿不拿我当大哥?过去多少年的事情了,我们这还像一家人吗?”
姐姐朝小阿羊吐吐舌头。小阿羊知道,姐姐心里想的和他一样,这回他们真没有三叔了。